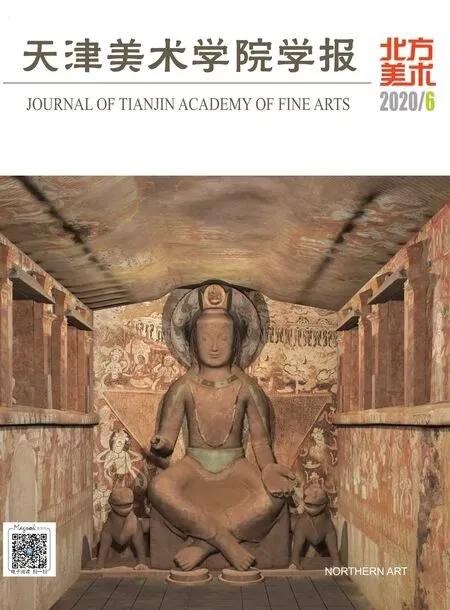莊子的宇宙意識與中國山水畫的構圖空間
劉建榮/Liu Jianrong
宇宙意識在中國古代的春秋戰國時期已有討論,最早提出宇宙觀的著述是戰國期間的《尸子》,作者尸佼為商鞅門客,在商鞅變法失敗獲罪后逃到蜀地,著書立說。他在書中提出“天地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在此,尸子指出,“宇”是空間觀念,“宙”是時間觀念。莊子則進一步提出了宇宙在時間與空間上的無限性。
一、莊子的宇宙意識
在莊子看來,宇宙時空的生成,實質上就是天地之中元氣的流動變化,在這一過程中,陰氣與陽氣相交互通,化生萬物,也產生了時間與空間。莊子在思考宇宙的時空觀上更注重無限性的討論:“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乎本剽者,宙也。”①宇,指空間,即尸子所說的“上下四方”,莊子認為“宇”是“有實而無乎處”,即認為空間確乎存在,但是沒有實際位置,沒有邊際;宙,指時間,即尸子所說的“往來古今”,莊子認為“宙”是“有長而無乎本剽”,即認為時間有長度,卻無所謂開始,也無所謂終結。宇宙在空間上沒有邊際,在時間上無始無終,而人占有的空間有限,人的生命也有終,與無限的宇宙相比,人的存在太渺小了。
莊子不時描述人在宇宙中所占空間的渺小:“吾在于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于馬體乎?”②人活于世,與天地相比,就所占空間來說,像小石小木與大山的關系,就數量來看,人也不過是宇宙存在的萬物之一而已,與萬物相比,更是不值一提。對于宇宙在空間上的無限性,莊子以湯與棘的對話形式進行了形象說明:“湯之問棘也是已:湯問棘曰:‘上下四方有極乎?’棘曰:‘無極之外,復無極也。’”③由于無極之外還是無極,宇宙在空間上無限地延展,人們根本無法憑借自身的理性去把握上下四方的空間。
莊子也不斷描繪人在宇宙中存在時間上的渺小:“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④人之一生,如白駒過隙,十分短暫,瞬間而過,倏忽而死,終有一天,魂魄必將消逝,身形也將隨之而去。“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于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⑤天地時間無窮,人就算再長壽,與無窮的天地相比,人的生命也是有涯的。莊子通過人生命的短暫和宇宙時間的無始無終對比,突顯出人生的無可奈何,人只能順應前行,無可選擇,所謂“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⑥,盡皆如此。宇宙無限的時間,人們是不能夠把握的,也不可能知其始終,“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⑦,“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⑧。
對于宇宙在時間上的無限性,西方哲學家也有自己的思考。與莊子一樣,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也對宇宙的時間流逝相當敏感,他說:“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必死的不朽,不朽的必死;生活在他們的死里,死在他們的生命里。”⑨強調生命不是靜止的,萬物皆流。強調死亡的必然,宇宙的變化。19世紀法國哲學家柏格森受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的影響,認為時間比空間真實,變化比存在更接近現實。在柏格森看來,要想把握生命,就得從生命最根本的現象——時間著手。真正的時間是“綿延”,因為生命本身永遠不可能被分割或中斷,所以叫作綿延。但是,如果我們把生命用符號來表達,我們實際上就是把生命狀態由流動變為靜止,把生命空間化,計量時間就是將時間空間化。⑩生命不斷在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每一刻都不同,不能預測,所以,宇宙的每一剎都是新的創造。
柏格森的時間理論對19世紀末的藝術影響很大,在藝術作品中強調時間的綿延,也促進了印象派的產生,印象派畫家力求表現光色的瞬間變化,從而將所有的圖像融入瞬息變化的時間氛圍中。在這個方面,印象派巨匠莫奈即為典型,他癡迷于在不同的時間面對同一景物作畫,來捕獲光影變動對自然景物的影響,魯昂大教堂曾畫過多次,一個干草垛畫過30多次,也曾畫過181幅《睡蓮》。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強調把時間空間化,印象派的繪畫理念就是柏格森生命哲學的藝術展現,一天中的不同時間,一年中的不同季節,對著相同的景物,通過多幅圖,來展現生命的流逝,時間無盡的綿延。
相比于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面對宇宙的時間流逝,莊子更加關注人如何面對無限的宇宙空間,為了突破宇宙空間的界限,他提出了“逍遙游”的思想。
二、逍遙游的俯瞰視角
在《詩經》中,就已出現了“逍遙”一詞,并與莊子后來所提出的逍遙含義相類。《詩經·鄭風·清人》中有:“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之句,其中“逍遙”與“翱翔”為互文,“逍遙”,可做翱翔之解,意指鳥在高空上自由飛翔。
莊子的逍遙基本含義也為翱翔,延續了《詩經》的說法,不過,莊子賦予“逍遙游”以宏大的宇宙意識,莊子借助高飛九萬里的“鵬”“乘云氣、御飛龍”的神人的視角,以俯瞰的方式,來彰顯宇宙之大。先來看看高飛于天的鵬,鵬是由北冥中的鯤化身而來,“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鵬騰空而飛,“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鵬擁有幾千里長的翅膀,能飛到九萬里之上的高空。莊子描述了鵬從九萬里的高空向下俯瞰的景象:“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游動的霧氣像野馬奔騰,塵埃飄揚,天色蒼茫,遼闊高遠,沒有盡頭。
莊子也欣賞神人、至人、圣人之游。高居于藐姑射之山的神人“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不吃五谷雜糧,乘云駕龍的神人,能自由自在在四海之外游玩,“乘云氣,御飛龍”,視角必定是在從高空之上的俯瞰。而至人呢,“至人神矣!……乘云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至人之游是“乘云氣,騎日月”之游,視角也是高空之上的俯瞰。而圣人的無名之游則是“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游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乘坐虛渺之鳥,飛到六極之外,游于虛無所有之處,視角同樣是高空之上的俯瞰。為什么這樣俯瞰呢?因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圣不作,觀于天地之謂也”。至人、圣人這樣做是為了探究天地間的大美,這種大美,只有俯瞰的角度才能觀其萬中有一。
莊子的宇宙觀,體現在繪畫上,便是一種大山水意識,以畫幅的方寸之間,來展現宇宙空間的無限。
三、莊子的宇宙意識與中國山水畫的構圖空間
魏晉南北朝時期,莊學大興,莊子的宇宙觀在東晉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中體現出來便是“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以展現“宇宙之大”為藝術人生的追求。
彼時的文人受莊子思想影響很深,逃離黑暗的政治環境,到山林中尋找心靈寄托,由此中國山水畫開始發展。宇宙空間是無限的,畫幅所展現的藝術空間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畫幅中展示宇宙空間的無限,成為中國山水畫論經常探討的重點。
南朝宋的宗炳所作《畫山水序》是我國山水畫論之始,作為繪畫史上第一篇闡述山水畫的文章,意義非凡,在此篇幅不長的文章中,他探討了為何畫山水,以及如何畫山水,提出了如何以方寸的畫幅展現千仞之高山:“且夫昆侖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睹,迥以數里,則可圍于寸眸。誠由去之稍闊,則其見彌小。今張絹素以遠暎,則昆、閬之形,可圍于方寸之內。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于一圖矣。”宗炳指出,要想畫昆侖山那么巨大的山體,只有在遠離昆侖山數里的地方觀看,才能在方寸之內表現出山的形勢。幾千尺高的山峰可以用豎畫三寸表現出來,幾百里的風景可以用橫畫數尺體現出來。方寸之內,如果表現得好,可以小見大,嵩山和華山的秀美,都可以在一幅圖畫里展現出來。
到南朝陳時,姚最在《續畫品》中,提出作畫的目的就是為了“立萬象于胸懷,傳千祀于毫瀚”,“萬象”指宇宙間所有景象與事物,“千祀”就是千年,“毫瀚”即毛筆。這就是說,畫家要能立宇宙萬物于胸懷,能描繪千年往來古今于筆端。南朝梁時的蕭賁擅長在團扇上畫山川,姚最贊揚他“咫尺之內,而瞻萬里之遙,方寸之中,乃辨千尋之峻”。《南史》也記載,蕭賁“能書善畫,于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之遙”。蕭賁不癡迷于眼前的草木花石,而要在咫尺之間,造出萬里之勢,在方寸之中,畫出千尋之峻,這種大山水意識,受莊子宇宙觀影響頗大。
唐代朱景玄在《唐朝名畫錄》序中說:“畫者,圣也。蓋以窮天地之不至,顯日月之不照。揮纖毫之筆,則萬類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繪畫就是揮毫能隨心所欲地描繪萬物,在一寸見方的紙絹上作畫,可以使千里江山置于掌上。唐代王維《山水論》指出:“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石,隱隱如眉;遠水無波,高與云齊。”“丈山尺樹,寸馬分人”,講到山水畫中山、樹與人的比例關系,“分人”與“丈山”相比,更顯山之大、人之小。
受莊子宇宙意識的影響,在繪畫中如何以尺寸之幅,展現千里之勢的探討,逐漸走向成熟,北宋郭熙的“三遠”理論,正是這種繪畫理論成熟的標志,也體現了中國山水畫的意境所在。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人之看者,須遠而觀之,方見得一障山川之形勢氣象”,即要描畫山川大物,必須要遠觀,才能顯現山川的氣勢。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著名的“三遠”說:“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巔,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后,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高遠之色清明,深遠之色重晦,平遠之色有明有晦。高遠之勢突兀,深遠之意重疊,平遠之意沖融而縹縹緲緲。其人物之在三遠也,高遠者明了,深遠者細碎,平遠者沖澹。明了者不短,細碎者不長,沖澹者不大。此三遠也。”其中的“高”“深”“平”都是對山體本身外在體態的描述,無有其他,但加上一個“遠”字,足以使人的目光從眼前之景拓展到畫面以外,以想象力來補充畫面無法展現的無限空間。

(傳)〔唐〕王維 雪溪圖 絹本水墨 縱36.6厘米,橫30厘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北宋〕郭熙 早春圖軸 絹本水墨 縱158.3厘米,橫108.1厘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與“三遠”理論相對應,郭熙又提出了關于山、樹、人比例的“三大”:“山有三大,山大于木,木大于人。山不數十百如木之大,則山不大;木不數十百如人之大,則木不大。木之所以比夫人者,先自其葉,而人之所以比夫木者,先自其頭。木葉若干可以敵人之頭,人之頭自若干葉而成之,則人之大小,木之大小,山之大小,自此而皆中程度,此三大也。”在山水畫中涉及山、樹、人之間的比例,郭熙的“三大”理論是王維的“丈山”“尺樹”“分人”理論的具體化,郭熙和王維相同,都是以人的“小”來襯托山的雄偉高“大”,以人之“小”來襯托自然之大,宇宙之大。受郭熙“三遠”理論的影響,后世繪畫理論家也提出自己的“三遠”。宋代韓拙在《山水純全集·論山》中提出“闊遠”“迷遠”“幽遠”的“三遠”論:“有近岸廣水,曠闊遙山者,謂之闊遠;有煙霧溟漠、野水隔而仿佛不見者,謂之迷遠;景物至絕而微茫縹渺者,謂之幽遠。”韓拙的“三遠”更加注重山與水的關系,突出了山水間的蒼茫感。元代黃公望在《寫山水訣》中進一步提出“平遠”“闊遠”“高遠”的“三遠”論,是對郭熙和韓拙“三遠”理論的綜合和繼承:“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之闊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不難看出,“遠”體現出觀者不為畫中物象所束縛,將目光轉向無限的宇宙空間,去感受宇宙之大,之高,之闊,之蒼茫。
傳統山水畫,受莊子宇宙觀的影響,不耽于具體畫面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而是想展現廣闊的構圖空間。而“三遠”之說則更進一步,不滿足于畫面本身的方寸與咫尺,讓人的目光突破畫面本身,延伸到畫面外宇宙的無涯無際。
四、中國山水畫的構圖空間與審美心理
德國古典美學家康德曾經分析過人為什么喜歡崇高之美,他認為就審美對象而言,崇高的特點在于“無限制”或“無限大”,“自然引起崇高的觀念,主要由于它的混茫,它的最粗野最無規則的雜亂和荒涼,只要它標志出體積和力量”。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人類對宇宙的欣賞,正體現在欣賞時空的無限性。這種崇高之美,如康德所說,可以是數量上的體積巨大,也可以是擁有引發崇敬之情的那種宏大力量或氣魄。中國山水畫中追求的“丈山尺樹,寸馬分人”“咫尺之內,而瞻萬里之遙”“高遠”“闊遠”等展現的正是這種崇高之美。山水畫所展現的視覺空間只是有限大,而暗示的宇宙空間則是無邊無際。“遠”作為山水意境追求的目標,力圖突破有限的山水空間,達到無限的宇宙空間。
康德也曾分析過人類欣賞崇高之美的心理原因,就審美心理來說,如果大自然只展現了一種威力的話,我們是不會欣賞它的,我們之所以欣賞宇宙的大美,是因為我們并沒有為它屈服,它激起了人內心的勇氣和自我尊嚴感,所以說,崇高不在于自然,而在人的心境。
由此可見,自然審美的最高境界并非是崇尚自然貶斥生命個體。只不過,西方哲學強調主客二分,主體在欣賞崇高之美時,有明顯的主客沖突,是將痛感轉化成快感,而中國哲學向來提倡天人合一,由之,在欣賞大自然崇高之美時,是看到宇宙之大,所以“游目騁懷”的樂事,是把繪畫當作“立萬象于胸懷”“揮纖毫之筆,則萬類由心”的,在作畫時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交融境界。
注釋:
①《莊子·庚桑楚》,《莊子今譯今注》,陳鼓應譯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611頁。
②《莊子·秋水》,同上,第411頁。
③《莊子·逍遙游》,同上,第11頁。
④《莊子·知北游》,同上,第570頁。
⑤《莊子·盜跖》,同上,第779頁。
⑥《莊子·知北游》,同上,第563頁。
⑦《莊子·齊物論》同上,第41頁。
⑧《莊子·德充符》,同上,第157頁。
⑨張志偉《西方哲學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頁。
⑩張汝倫《現代西方哲學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頁。
?《詩經·鄭風·清人》,祝鴻杰、段憲文注《詩經》,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頁。
?《莊子·逍遙游》,《莊子今譯今注》,陳鼓應譯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頁。
?《莊子·逍遙游》,同上,第3頁。
?《莊子·逍遙游》,同上,第21頁。
?《莊子·齊物論》,同上,第81頁。
?《莊子·應帝王》,同上,第215頁。
?《莊子·知北游》,同上,第563頁。
?〔南朝宋〕宗炳《畫山水序》,收入倪志云著《中國畫論名篇通釋》,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版,第53頁。
?〔南朝陳〕姚最《續畫品序》,同上,第120頁。
?轉引自倪志云對姚最《續畫品序》原文所作注釋,同上,第148頁。
?同上。
?〔唐〕朱景玄《唐朝名畫錄序》,同上,第182頁。
?〔北宋〕郭熙《林泉高致》,收入盧輔圣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修訂本)(第一冊),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
?同上。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二版,第3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