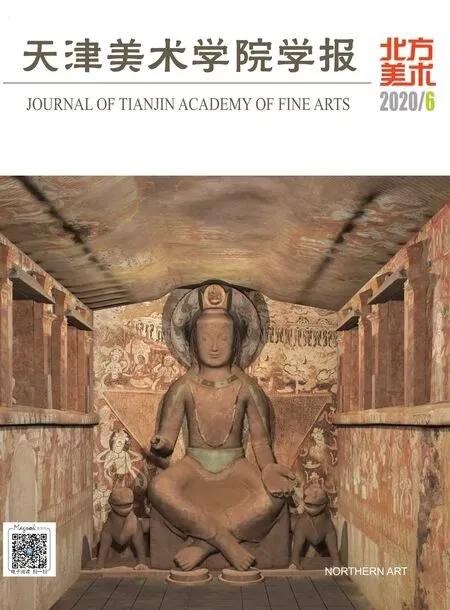清末勛章“雙龍寶星”的造型特征與文化內涵探論
劉寅凱 林德祺
一、溯流求源——“雙龍寶星”造型考據
19世紀下半葉,中國與外國交往逐漸密切起來。由于中國特有的傳統文化和政體與西方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清政府仍以傳統方式來獎賞有功人員,具體有“加官進爵、封妻蔭子、建坊旌表、優老尊老、入祀祠宇、身后哀榮等制度”[1]。對于八旗營總職銜以下獲軍功者,一般授予紙質功牌。紙質功牌的樣式類似于當時的執照。清末紙質功牌也會因捐糧款、實心辦事等原因頒給漢人。在鎮壓太平天國時,清政府雇傭外國人組成的常勝軍(前身為華爾洋槍隊)由于在戰斗中表現優異,其領導者華爾和其他頭目皆被清政府授予職銜,同時還有大量的金銀賞賜。但是由于授予外國人職銜不合乎清禮制,大量賞賜金銀也恐被其他外國人攀比和效仿,長此以往清政府財政也無法承受,因而迫切需要一個合理的獎勵形式來適應當時的需要。同治元年(1862),為了獎勵配合淮軍在上海外圍戰斗中取得多次勝利的外國人,江蘇巡撫李鴻章上奏稱:“其余兩國出力員弁,即由臣飭令會防局,仿制該國功牌式樣,另鑄金銀等牌若干面,分別酌給佩戴。”[2]以此為契機,清政府各級官員在與“洋人”交往過程中,紛紛設立仿造國外勛章、獎章樣式的金屬功牌,作為獎賞專門授予“洋人”以示“交好”。
同治二年(1863),直隸總督崇厚在給一名外國人請賞時,被恭親王奕駁回。他建議崇厚照會所在國使館,由該國自行獎賞。這名外國人得知后竟然表示情愿只領金屬功牌。究其原因,“只賞洋人”金屬功牌佩戴與設計皆與當時西方授予勛章相似,本國獎勵實則遙遙無期,而獲得清政府所頒“只賞洋人”金屬功牌就可以佩戴和炫耀了。當時一些與外國人頻繁接觸的清政府官員也意識到了“只賞洋人”金屬功牌受外國人歡迎的原因。同年,崇厚以西方勛章制度為藍本,結合中國金屬功牌(賞賜國人)的傳統樣式,制訂了用于獎勵外國人的“勛章”。此方案得到了總理衙門大臣奕的認可,于是“仿外國頒勛章之例,試造金寶星及銀牌”[3]。旋即崇厚在天津試制了“金寶星”。“金寶星”分為金質、銀質兩種。其中金質“金寶星”又分三個等第,一等、二等和三等金質“金寶星”(圖1)分別重一兩四錢、一兩二錢、一兩。銀質“金寶星”重一兩。“金寶星”基本形狀為圓形,正反面中心處皆用爪鑲工藝鑲嵌寶石,正面均有“大清御賜”字樣,下方還有表示等級的字樣,兩側配有云紋。金質“金寶星”背面為雙龍紋飾,銀質“金寶星”為螭虎紋飾,正反面外圈處均有回紋裝飾,上下兩端有云形環首,上端用于懸掛,下端配有流蘇,其仿造的原型主要是玉璧等。有研究者指出:“‘只賞洋人’金屬功牌有‘禮器’的屬性,將‘器’的‘形’和‘意’都指向中國古代的‘禮器’玉璧,‘昔者君子比德于玉’,將玉璧的‘美德’通過‘形’賦予‘器’本身,也暗喻希望獲得者具有這種美德。”[4]這一時期的“只賞洋人”金屬功牌均為各地仿造外國勛章形制自行鑄造,但大部分也都以崇厚造辦的“金寶星”為基礎,這為“雙龍寶星”造型風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圖1 金質二等“金寶星”正反面
在清政府與各國交往的過程中,作為國際外交禮儀,應對外交官贈予本國勛章示好。但“金寶星”不適合國際外交場合,而且授予外交官代表戰功類的“功牌”也不妥當,同時,“只賞洋人”金屬功牌從根本上來講還是下賜臣屬的姿態,不符合兩國平等往來的實際。且功牌制造形制不統一,也影響了清政府對外交往的現實需要。“1881年末(清光緒七年),奕向清政府上奏《總署奏厘定獎給洋員寶星章程折》,擬以‘只賞洋人’金屬功牌(金寶星)造型為基礎,制定并頒布了雙龍寶星章程”[4],用來獎勵“出力”的“洋人”,并且規定了其等第設置、設計樣式、所配執照內容和褫奪條款,規定了不同等第由不同部門制造和授予,可以看出“雙龍寶星”的授予面非常廣,幾乎囊括所有階層,而且被授者不拘泥于是否來過中國,只要做出有利中國之事即可被授予“雙龍寶星”。在制定清朝“寶星制度”的過程中,清末著名外交官曾紀澤發揮了重要作用。曾紀澤是清末重臣曾國藩次子。作為清政府的外交官員,曾紀澤在一系列外交活動中深感國外對勛章的重視,因此他在光緒八年(1882)的一份奏折中奏請清政府設立勛章,并“恭稽會典,考證西圖,并參以愚見,擬就寶星章程。首列優等,以備致予邦君;繼列各項名目,以酬出眾勛庸;末附五等功牌,以獎尋常勞績。除繪圖帖說連同翻譯西國寶星章程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備查核”[5]。曾紀澤奏請并制定的寶星章程中提到的勛章最后被命名為“雙龍寶星”。“雙龍寶星”分為五等,其中一、二、三等中每等又分三個級。光緒二十二年(1896)又對頭等第二和頭等第三的授予對象進行修改,使之更為具體。光緒八年的第一版“雙龍寶星”外形尺寸比外國勛章稍大。光緒二十三年(1897),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上奏《總署奏改定寶星式樣請旨遵行折》,奏請將“雙龍寶星”改版,以便適應外交場合,迎合外國人的審美習慣。這次改版主要集中在“雙龍寶星”的外形和材質上,將原來方形、菱花形、葵花形和圓形的“雙龍寶星”外部加以星芒,將二等以下的“雙龍寶星”改為銀質。此外,還明確了“雙龍寶星”的產地,增加了副寶星。一般將光緒八年至光緒二十二年期間制造的“雙龍寶星”稱第一版(圖2、圖3),將光緒二十三年之后制造的“雙龍寶星”稱第二版(圖4)。

圖2 第一版頭等第二“雙龍寶星”

圖3 第一版二等第一“雙龍寶星”

圖4 第二版二等第二“雙龍寶星”
二、器道相宜——“雙龍寶星”造型意蘊探察
清代的造物藝術追求裝飾的繁冗華麗,器物造型華貴奢靡、雕琢繁瑣,“這與清代上流階層享樂生活有著直接的關系”[6]。而數千年來形成的文化傳統定勢使傳統造物思想有著強大的包容性,外域文化的精華最終都會被吸收到中國傳統文化當中,融合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并體現在中國傳統造物思想當中,最終影響到器物的造型。“雙龍寶星”在清代造物潮流的影響下,既有滿族和漢族自身審美的文化特點,又融合了其他多元文化,造型雍容華貴,具有濃郁的宮廷氣息。尤其是在滿族以金、銀、珠等材質為貴,又喜好全面性裝飾、多元素堆疊的審美文化影響下,“雙龍寶星”制造工藝精益求精,配以寶石鑲嵌,且用色明亮艷麗,具有豐富的視覺效果。根據等第的不同,其裝飾華麗程度也不同,體現出了民族性和時代性特征。這就使“雙龍寶星”造型文化意蘊更加濃厚。
第一版“雙龍寶星”的基本造型有長方形、菱花形、葵花形和圓形;第二版“雙龍寶星”中心處也是菱花形、葵花形和圓形,僅在此基礎上外加星芒,以求符合外國人的審美(表1)。“雙龍寶星”從造型上來說,可以斷定取自銅鏡。采用銅鏡造型,即是中國傳統造物思想指引下造物品類更迭和文化積累的結果。銅鏡最早出現于舊石器時代,直至清代中晚期才逐步被取代。方形銅鏡最早出現于春秋戰國時期,屬異形銅鏡,比較罕見。第一版“雙龍寶星”頭等由于獲得者身份較高,所以仿造的是稀少的長方形銅鏡造型,上部有云紋環首作佩戴用。菱花形銅鏡出現于唐代早期。將銅鏡的外形做成菱花形,也使銅鏡的寓意與形式更好地結合起來。第一版“雙龍寶星”二等用菱花形銅鏡造型,第一版“雙龍寶星”三等用葵花形銅鏡造型,上部有云紋環首作佩戴用。絕大部分的銅鏡都為圓形,“圓板具鈕一直是中國銅鏡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國銅鏡的主要特點之一”[7]。第一版“雙龍寶星”四等、五等和第二版“雙龍寶星”中心處造型均為圓形,上部有云紋環首作佩戴用。“雙龍寶星”雖然取“鏡”作為自身的造型來源,但取用的卻不是“鏡”的功能,而是著重表現背面。銅鏡的命名有時就是根據背面的圖案,“雙龍寶星”即是如此。銅鏡的背面一般分為圖案區、邊緣、鈕座和鈕等部分。鈕可以系帶,用于拿取。“雙龍寶星”中鑲嵌的寶石模仿銅鏡鈕。這一部分運用了寶石作為裝飾材料,如珍珠、紅寶石、紅珊瑚、藍寶石、青金石和硨磲等。運用這些在自然界中形成的特殊物質并人為賦予其品格,體現出前人在造物過程中對自然的深刻認識。其構思既參考了清代“以頂戴別尊卑”,也契合了“佛教七寶”之意。

表1 第一版和第二版“雙龍寶星”造型
有研究者指出:“早期銅鏡特殊的宗教作用,尤讓人產生敬畏與崇拜心理。古代人們對鏡子能映像、反光等物理特性不能理解,認為發光的都是寶貝,光明就是暗鬼的敵人。”[8]東晉葛洪《抱樸子》描述道士進入深山都要帶一面銅鏡,如果碰到鬼魅,用銅鏡就可以分辨。在道教中,銅鏡有通神和作為煉丹法器等多種用途。在佛教中,銅鏡同樣是一種法器。在唐代,高僧為了啟發修行,曾經把十面銅鏡放置在佛像四周,并用燭光映照,以此詮釋佛教奧旨。銅鏡也是滿族重要的宗教用品,與薩滿文化有關。在滿族的薩滿服飾上,懸掛的銅鏡越多,薩滿的法力就越高強。銅鏡保護著薩滿的頭部、前胸和后背。薩滿認為銅鏡可以抵抗邪惡的侵襲。滿族入關之后,隨著滿漢文化的融合,滿族的銅鏡逐漸與漢文化趨同,既有滿族特色,又包含漢文化特征。在古代盔甲胸口的位置上,有一部分凸起的盔甲。這部分較其他甲片厚且表面光滑,而且在受到沖擊的時候可以起到保護心臟的作用,所以被稱作“護心鏡”。有研究者稱:“清朝入關前防護裝備不甚完善,由于戰爭需要和經濟發展,清朝繼承了明朝制造盔甲的模式并加以改良,也淘汰了重型鎧甲,而多改用輕型甲及裝飾性鎧甲。”[9]“護心鏡”是明清中高級武將盔甲的共有部件。在清代中后期,清軍的盔甲逐漸輕型化、裝飾化,大多只具有禮儀性質,作為大型閱兵和儀式中的穿著。后期,盔甲已經完全成為皇親貴胄與一些中高級武將華麗的“禮服”。“雙龍寶星”在佩戴時貼在衣服的胸口上,宛如盔甲的“護心鏡”一般(圖5),暗含保護獲得者免受詛咒與攻擊之意。

圖5 佩戴第一版三等“雙龍寶星”的法國軍人
中國傳統造物思想比較突出的特點是重視“器”與使用者的關系,即“器以載道”,即通過器物的色彩、工藝和裝飾特點體現審美意識和價值。其所表達出的人文關懷和理性營造正是中國傳統造物思想的核心。將“器”的“形”和“意”都作為寄托造物者思想內涵的載體來感化使用者是中國傳統造物思想的精髓。由此,便將造物行為上升到了“道”的高度。銅鏡在中國古代除了用于日常,還被懸掛在房梁或者門上,取宗教中的辟邪之意。“雙龍寶星”運用銅鏡造型一方面取意“辟邪”,另一方面也有借古喻今的意味。我國古代經常將“鏡”與“鑒”混用。成語中的“破鏡重圓”“以史為鑒”等都反映了古人所提倡的美德。“雙龍寶星”運用銅鏡造型,也是希望這些美德可以體現在獲得者身上。這也展現出了鏡的文化外溢。在清末對外交往的過程中,“雙龍寶星”實際上是以一種中介的形式將清政府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施加在獲得者身上。其造型、圖案、色彩、材料等都具有一定的審美性,同時又體現出一定的精神性,“而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體現出一定社會的價值觀、倫理觀,同時又塑造著一定的審美主體”[10]。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外務部上奏請求清政府賞給出使大臣寶星,并對本國的外交官出使外交任務時只佩戴外國勛章、獎章,而無本國勛章的情況進行了說明,希望清政府可以將“雙龍寶星”的授予范圍擴大至外務部的外交官們。此后的三年間,“雙龍寶星”勛章開始授予高級外交官。但也有例外。如在清宣統二年(1910)東北鼠疫中主持防疫的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都督伍連德,就因防疫有功被授予第二版二等“雙龍寶星”(圖6)。可以看出,“雙龍寶星”在這時不僅具有外交作用,還解決了內部榮譽授予的問題。

圖6 佩戴第二版二等“雙龍寶星”的伍連德
三、不約而同——銅鏡的文化溢出、共鳴與反哺
銅鏡文化在東亞地區流傳很廣。早在彌生時代,日本便接觸到流傳過來的中國銅鏡。在“雙龍寶星”設立的第二年,即1883年,清總理衙門發給駐日本國大臣黎庶昌一份電文,內容是將新設立的“雙龍寶星”圖鑒兩本送給他們以“閱備查”。收件人除黎庶昌外,還有日本外務卿井上馨。無獨有偶,清光緒十四年、日本明治二十一年(1888)初,日本設立了一款名叫“瑞寶章”(圖7)的勛章,從勛一等至勛八等共八個等級,授予“對國家盡力者”。“瑞寶章”的設計以古代寶鏡為中心,搭配十六連珠,外部有放射的光線。其中的古代寶鏡模仿收藏于伊勢神宮的神器——“八咫鏡”。“八咫鏡”是一面銅鏡,為日本三大神器之一,歷來作為日本皇室的信物。日本有一個神話:“素盞鳴尊”大鬧高天原,“天照大神”非常生氣,便躲進天巖戶的洞穴中,天地瞬間墮入黑暗。諸神共同制造了“八咫鏡”懸掛于天巖戶前,并一起跳起了祭祀舞蹈。“天照大神”好奇地從洞中出來,天地又再次充滿日光。日本歷史文化研究文獻稱:“‘天照大神’是日本皇室的祖先神,也是日本神道所尊奉的主神。”[11]“八咫鏡”可以看作是“天照大神”的代表。因此,“瑞寶章”的銅鏡造型寓意雖然與“雙龍寶星”有所不同,但在“神性”方面是大體一致的。在日本三大神器的研究和流傳圖像中,“八咫鏡”的造型大部分都是圓鏡,但在“瑞寶章”中出現的“八咫鏡”卻為菱花形銅鏡造型,這是否是受到“雙龍寶星”的影響,還是單純為美觀才使用菱花形銅鏡造型,目前還沒有定論。在日本平安時代的法律《延喜式》中對放“八咫鏡”的橢圓形盒子有具體尺寸的描述,有學者推算出“八咫鏡”大概是直徑不足49厘米的銅鏡。自古以來,“八咫鏡”不被輕易示人。據說明治天皇曾經打開放置“八咫鏡”的盒子,隨后下令子孫永遠不得打開。這也給“八咫鏡”的造型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雙龍寶星”和“瑞寶章”設立僅隔六年,卻同時使用了“鏡”作為勛章的造型元素,看似“不約而同”,卻也合情合理。這是銅鏡文化在東亞地區挪移的產物,說明“鏡”在東亞地區有相當大的文化共鳴。

圖7 日本勛一等瑞寶章,主章與掛章中心處均為“八咫鏡”
在近代,甚至出現了銅鏡文化反哺現象。日本侵華期間炮制了所謂的“滿洲國”。1940年(偽滿康德七年,民國二十九年,日本昭和十五年),溥儀從日本迎回了“八咫鏡”的復制品,并創立“建國神廟”供奉。這面“八咫鏡”是由日本京都制鏡師制作的復制品,而且還制作了具有防空功能的唐柜作為盒子。在后來“滿洲國”制定的一種“為對社會的功勞者或個人的篤行者賜與表征其名譽”[12]43的褒獎制度中,有“褒章”、“牌”(圖8)和“褒狀”三種類型的獎勵。這其中的“牌”又分金、銀、青銅三類,每類又有大小之分,共計六種,用來“賜與其善行雖系與應賜與褒章之善行為同一性質,但由其功績程度或堪為民眾模范之點觀之未達用褒章賜與時”[12]58。這類“牌”所使用的即為銅鏡造型。

圖8 偽滿勛章及徽章圖海報,右下角銅鏡造型即為褒獎制度中的“牌”
四、結論
清末勛章“雙龍寶星”的銅鏡造型是多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是清末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下的產物,也是那個時代金屬工藝美術的集成,不但對本國功勛榮譽制度和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也引起深受中國文化熏陶、影響的域外國家的共鳴。在“實用性—神性—禮儀性”的變化過程中,銅鏡的實用性逐漸喪失,其文化內涵和美好寓意卻保留了下來。“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雙龍寶星”的銅鏡造型被寄予了厚望。它以審美的方式吸引獲得者——華麗外形和繁復裝飾所帶來的榮耀和快感,并加入了意識形態,使獲得者被權力所馴化,從而成為社會樣本,以挽救風雨飄搖的清政府。盡管“雙龍寶星”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清政府的統治,但在清末半殖民地半封建背景下,其更多只是籠絡人心而已。考證清末勛章“雙龍寶星”的造型特點與文化內涵,有助于爬梳清末金屬工藝美術的造物理念與思路,從而為中國傳統造物文化提供歷史和話語支撐,同時對新時代中國功勛榮譽表彰制度的建設也有一定的參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