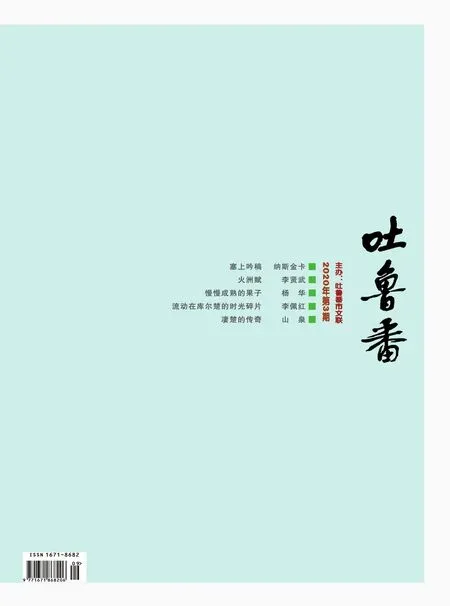西域印象
趙長春

阿孜汗村的無花果
吐魯番葡萄哈密瓜,阿圖什無花果人人夸。
游走新疆,瓜果必嘗。吃正宗的,甜嘴蜜舌。到阿圖什,就吃無花果。阿圖什的無花果個大、汁濃、色澤艷麗,含糖度高,被當地人稱為樹上結的“糖包子”。
那個下午,天氣晴好。我們在松他克鄉阿孜汗村無花果民俗風情園,品嘗到了正宗的無花果。雖然夏果盛季剛過,秋果旺季還沒到來,園子主人一再表示遺憾。
當年,在阿圖什支教,我們居住的市二中,與松他克鄉臨界。沿著阿圖什市松他克路東南方向出發,兩三公里,就到了松他克鄉松他克村。周末,我在這里趕過巴扎,去少數民族學友家玩。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我們二十幾位支教同學,受邀在松他克村的吐爾遜家,體味了維吾爾族待客的豪放、真誠與熱情。
十多年了,故地重游,再返松他克鄉,開心之余,我還多了份激動:期待能再遇見當年的新疆大學學友。
濃郁墨綠的樹葉子下,黃紅有間的無花果點綴其中,我沒有那么急迫地去摘它。印象中,少數民族朋友家,都有一個后院,是花園,也是果園。風搖,花媚,果香,徜徉其中,賞心悅目,歲月靜好。總感覺又回到了吐爾遜家的后園子里。記得我們進她家院子后,洗手,脫鞋,入座在廊下的花氈子上,吃了各色水果后,大家又不約而同地起身,進了她家的后園子,聽她講如何摘果,講關于無花果的傳說。她有一雙會說話的大眼睛。從她那里我知道了,無花果,維吾爾語的發音為“安吉爾”,唐朝時期從波斯傳入阿圖什。這里,位于新疆西南,氣候、土壤等比較適宜無花果生長,一年三熟,有夏果和秋果之分,種植面積大。阿圖什,被稱為“無花果之鄉”。
那就吃吧,同行的朋友提醒。我說,“好吃,當年這里的無花果是一元三個,現在是三元五元一個。”我摘了一個尾部開口較小的,葉子合好,對拍,果子裂開,糖汁晶瑩,果肉軟糯,汁水豐富、甜而不膩,好吃!
見我如此,援疆干部、松他克鄉的陳副鄉長看看我,“你來過這里?”大學畢業的他,跨越近萬里,志愿來疆工作,業績突出,不到三年,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基層干部了。
見他如此,我就說了我的故事,說了頭天晚上在阿圖什二中校園內的徘徊。我找到公眾號上的那篇文章,讓他看,看吐爾遜的照片,“就是松他克村的,現在,應該三十四五歲了……”
他笑了。我們加了微信,傳了照片。他說,“我試試,松他克村沒有多遠。只是時間關系,咱們不能前往了。”
是的,明天,我們就要啟程,前往阿合奇縣。
悵然中,我盼望陳鄉長能夠通過他聯系的村干部,找到吐爾遜,找到她家,雖然我的線索如此渺然。
一邊交談,一邊游園。阿孜汗無花果民俗風情園,四星級的農家樂。大門進來,葡萄長廊貫穿園區,無花果樹分布左右。園中十字口,是一個歌舞廣場,圓形。四周是維吾爾族建筑風格的涼亭、廊床,環以水流。游客賞景、品果、聽歌、看舞,或者加入“麥西來甫”,一起歌舞。
暮色漸降,游人多起來了。園主阿不都外力·玉蘇甫很開心,阿孜汗村家家戶戶都有無花果果園,他的最大,“政策好,新疆穩定和諧,黨的領導亞克西!”
我們圍坐在無花果樹下,阿不都外力·玉蘇甫眼一搭,就摘下正好吃的果子。他說,無花果又叫映日果、奶漿果、蜜果、隱花果,史書上叫“阿驛”,說明是從外地引進來的。無花果重,一個果子約一兩半甚至二兩。他說,“你的朋友,這樣吃,一會兒沒法吃飯了嘛!”
哈哈!哈哈!
這個我知道。維吾爾民族待客,是一道美味連著一道美味,不是饕餮者,有口欲沒有肚腹,再回味,可難受。
羊肉、無花果、秘制腌料,恰到好處的烤制火候,無花果餡烤包子上來了,金黃誘人;阿圖什架子肉上來了,果香混合著肉香;還有奶皮子蒸卷,無花果醬……
吐爾遜,今天,我在你的家鄉,我不關心美味。我祝福你,吉祥,幸福,安康,亞克西!
在喀拉鐵克山口遇見駱駝
最近一次遇見駱駝是在從阿合奇縣返回喀什的沙漠公路途中。一路可見牛羊、戈壁、沙礫、荒漠、綠洲、雪山、紅柳、草原、白楊、駱駝刺,當然還有駱駝。
翻越喀拉鐵克山口下來,平坦開闊的剎那間,幾只駱駝隱約在戈壁灘上。我驚叫了一聲:駱駝!順著我的手指方向,同車人看過去時,又一個轉彎,就看不見了。
對于我的新奇,健談的司機師傅笑了,“不是野駱駝,是當地人放養的。”司機師傅是當地人,一路穿行中,我們一直交流著這荒天野地的生物。他說著這里有什么,那里有什么。他指點著遠處的一個村子,“我在那里釣過野魚,河水嘩嘩,野魚翻滾,一釣一個準。”
對于駱駝,他說這里是塔克拉瑪干大沙漠邊緣,也有野生的,只是很不容易見到了。剛說完這些,我就發現了遠處的那幾峰駱駝。再轉過幾道彎,托什干河遼闊的背景下,我們又看到了,慢慢悠悠地,駱駝隱入夏末的柳樹林中。
駱駝最早以童話的形式進入我的印象:記得當年有篇課文,說是一只駱駝和一只羊爭論個頭高低的優劣,最后請牛大哥給評理……老師估計也沒有見過駱駝,僅憑書本上的插圖給我們講說一番;只是我記住了駱駝的雅稱“沙漠之舟”。后來,學過《駱駝祥子》的節選,感覺老舍先生賦予了“祥子”這一文學形象的駱駝寓意:面對困境的無奈與彷徨,逆來順受,消極地忍耐在世間。還有《城南舊事》中,那進入北京城送貨的駱駝,一身的臟亂和疲憊,不堪風塵、黃沙。
后來,還是在新疆,我偶遇了實實在在的駱駝。那時,我正在新疆大學讀書,在烏拉泊古城的風雪中,與一峰駱駝對望。它臥在雪中,高仰著頭,安靜,平靜,高大的身材也能顯出優雅的氣質。粗脖子下須長且厚,隨著反芻,掃撫著雪粒。它挺著胸,我感覺它對我有些傲視,疑惑我到這古城參拜岑參的原因。我想走近時,它鼻翼吸閉反復,突然站了起來,忽地吐了一口唾沫,呼呼地跑開了,一順腿跑,左邊前后蹄,右邊前后蹄,如劃船,很協調,自然。后來知道,這個季節,公駱駝發情,溫順的它,易怒,噴唾沫之外,還敢咬人、踢人。
說著駱駝,我們在一段長長的直行路線旁停車。往南看,公路從喀拉鐵克山北坡掛下來,隱約明滅;往北望,公路直入遠處的蒼茫地平線中,很美的拍攝背景。八月底的南疆,風涼如內地的秋末冬初,空氣中彌漫著野蒿的藥香。如果說內地的蒿草香是被秋日暖陽曬出來的,在這里,藥香是被風凍出來的。那蒿草,比內地散發的香味更濃郁,但草株很瘦弱,枝條如粗針,簇簇擁在風中,咬緊地面。我隨手拽了一把,放在車上,香味溢滿了整個車廂。
路的兩邊,還長著不少的駱駝刺,匍匐地面,灌木簇生,如柴,灰白色的細枝末端,粒粒小刺。我試了試,很扎手,但卻是駱駝的一道好菜。維吾爾醫書中,駱駝刺的花有很好的保健、抗癌作用,可以制成駱駝刺花醬,藥用價值高。可惜,不是花期,沒有看到花的模樣。只是不少枝條上,掛著一朵朵的褐色駝毛,隨風飄動。司機說,這是駝絨啊!積攢多的話,做件駝絨服,防寒得很!
在說笑聲中,我們繼續上路,聽著刀郎的歌,特別是老電影《戴手銬的旅客》的插曲《駝鈴》,蒼涼、悲壯、憂傷,叫人回味不已。歌聲中,我凝視著窗外,想再見駱駝……
駱駝,對于沙漠戈壁來說,就是神奇的精靈。耳朵里有毛,阻擋風沙;眼瞼雙重,長睫毛濃密,可防止風沙進入眼睛;鼻子能自由關閉。食物選擇上,以梭梭、胡楊、沙拐棗等各種荒漠植物、鹽堿植物為食。它們四肢細長,蹄大如盤,走著,駝鈴聲聲,不緊不慢,為這遼闊的蒼涼,補寫了溫暖,升華了動感。它們真的可以驕傲,昂首俯瞰一切,沉得住氣,從不著急,慢慢地走,一步一個腳印,不怕終點的遙遠,沒有退縮,砥礪前行。
細究,砥礪前行就是為駱駝量身的詞語。砥,細膩的磨刀石;礪,粗糙的磨刀石。沙漠,戈壁,荒灘,對于駱駝來說,就是真正的砥礪。如此,駱駝就是真正的砥礪前行者!
茶顏罐色在喀什
在新疆,有件雅事兒,茶館喝茶。
特別是在喀什的那段日子里,印象深刻。
喀什的茶館很多,有不少上百年的老茶館,各具特色。你只要走進去,就能品味出新疆茶館獨有的感覺。
喀什人,喝茶就是喝茶,很純粹。一壺老茶,老壺,銅質,銀質,配幾只鑲了金邊銀邊的細瓷碗。喝茶者席地而坐,說東說西,不急不躁,悠然而漫長,如同檐下那悠然響起的鴿鳴,咕咕,咕咕,咕咕,時光也就慢了下來。
我喜歡坐在陽臺的桌子旁,隔窗看他們喝茶。窗口的茶座,多是為內地來的人設置,有靠背,我還不太習慣盤腿而坐。
喝久了,就想學著他們喝茶。茶進口,慢慢咽下,剩一點,再冰糖入唇,咬嚼,咯崩咯崩響。茶香,糖甜,在舌尖上彈跳。
還有他們愜意的那種感覺。半躺半坐,撫著胡須,目光悠然地漫過別人的頭頂,穿過了屋頂,好像沒有著落,就那么不經心,或者心情沉沒到一處深遠,一處少年時光,無人知曉。
還有茶館外面的地上,幾塊地毯,圍坐著一些茶客,也是盤著腿,就著馕、烤包子、干果,一口,一口,慢悠悠地品茶。這些當地的中老年人,所表達的順其自然,無關其他,學不到。
在祖國西部邊陲,聽著鴿哨,看著藍天白云,品賞著飄過秦時明月漢時關的縷縷茶香,捧一本早已經喜歡卻不能靜下來閱讀的書,心靈真的會靜下來,遠離了所謂的紛亂與恩怨。
喀什老城最熱鬧繁華的地段,是吾斯塘博依路和庫木代爾瓦扎路的交匯處,有座百年老茶館。這些年更為出名,是因為電影《追風箏的人》的影片開頭,就是這座百年老茶館的厚重樣子。
在喀什,我總覺得老茶館有了靈性,較勁地活在人間,為茶和水的相擊與碰撞提供了一處優雅的場所。在這里,茶成為水最美的風景,水就是茶久等的歸人。
有些茶館里,還擺放著民族樂器。喝著,彈撥一曲,跳上一段,也是愜意。
茶館還是和解、道歉的好地方,很容易通過喝茶把一些矛盾解決掉:角落中,幾個人,茶一端,碗一碰,掌一擊,拍了胸脯,過節就消解了,文雅于內地喝酒稱兄道弟的方式。
相較于純粹的喝茶感覺,喀什的茶,卻有著多種的花色。玫瑰茶、冰茶、花茶,茶色多多,茗香裊裊,演繹著不同人的茶道。在喀什的日子里,我試著走進不同的茶館,品味了當地的清茶、奶茶、油茶,還有花茶、果茶、果仁茶、藥茶、核桃茶,香茶等,茶為水釋放了生命中最美的馨香,包括諸多茶類的混合滋味兒,都香。都是好感覺。
最喜歡的是果茶。干果,如葡萄干、沙棗干、杏干、核桃干等,熱水撲上去,立即釋放壓縮的熱情!加鹽,入奶,放糖,根據口味、心情、天氣,帶上一本書,慢慢地捉摸幸福、平靜、平淡,真好。
更好的是,目光悠然中,撞折了一道會心微笑,來自某雙長長的睫毛下,很會意……可美!
就如我眼前的茶和水,在喀什,不早不晚,我們共同相約這里,仿佛千年前的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