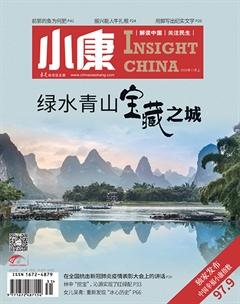王宏甲:到最貧困的地方去
簡宏妮

攝影/卡樂圖片
接受采訪時,王宏甲正在貴州畢節的鄉村中參與當地的脫貧攻堅,電話里都能感受到他的忙碌和風風火火。
2018年,著名報告文學作家王宏甲榮獲“全面小康十大杰出貢獻人物”,頒獎詞中這樣寫道:“腳踏實地,深入生活,他曾在兩年內走遍全國100多個鄉村。在他的作品中,人們感受到了時代神經脈動的豐富多彩”。
最近這兩年中,王宏甲做得最多的事,仍然是去全國的農村采風。山東煙臺市、河南南街村、河北周家莊、山西賈家莊、浙江滕頭村……許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跡。讓他逗留時間最長的,就是畢節——這個擁有45個少數民族、貴州貧困人口最多的地級市,大概是他目前最深的牽掛。
見證畢節脫貧模式
貴州畢節,地處烏蒙山腹地,毛澤東曾有詩詞描述它:“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畢節氣候高寒冷涼,少數民族眾多,是貴州貧困人口最多的地級市。
在畢節調研和參與脫貧,王宏甲最深的感受是,這里貧困程度很深,脫貧攻堅的任務非常艱巨。畢節從2016年底開始推行“大黨建統領大扶貧”。王宏甲解釋:“這里的含義,‘大黨建講整個扶貧過程當中都要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大扶貧講的是除了建檔立卡的貧困戶,還需要關注邊緣戶,因為貧困戶和很多非貧困戶之間只是一墻之隔、一步之遙。要防止非貧困戶在脫貧攻堅中成為貧困戶,還要防止已經脫貧的農戶返貧。 ”
在貧困的畢節,王宏甲前后跟蹤采訪4年,其中駐扎的時間將近兩年。他深刻了解到畢節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出貧困的。王宏甲感受到最有價值的一個部分,就是集體經濟——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如果沒有集體經濟,它脫不了貧。”在他看來,像畢節這樣的貧困地區,把單打獨斗的農民組織起來走集體化的道路,是必由之路。
2018年,貴州省委書記孫志剛提出了農業產業革命“八要素”,在全省推廣,即產業選擇、培訓農民、技術服務、資金籌措、組織方式、產銷對接、利益聯接、基層黨建。王宏甲的感受是,每一個要素,都跟發展集體經濟相關。
“個人種稻谷、種土豆或者養豬、養雞,這都是傳統的。今天講發展產業,都是針對集體來說的。所以它是一個適合于發展集體經濟的產業革命八要素。”
比如“八要素”的第一條是講產業選擇。幾千年來,種桑養蠶是浙江等江南地區的產業,隨著浙江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不能夠把大量的土地拿去種植桑樹了,于是發生了“東桑西移”。那么畢節是否適合選擇種桑養蠶呢?
“畢節的高山冷涼氣候不容易產生蟲害,桑葉是最不適合打蟲藥的;畢節的喀斯特地貌留不住水,但種桑樹不需要澆水,而且它的根系還會把土壤抓住,幫助蓄水和保土。那么畢節選擇種桑養蠶就是適合的產業。畢節有些村這么做了,效果很好。”
上世紀80年代,畢節是國務院批準的全國唯一一個扶貧開發試驗區。王宏甲說,總書記曾要求畢節“綠色發展”,畢節有些村莊接過“東桑西移”這個產業,選擇種桑養蠶,就是在喀斯特地貌的荒山上造綠水青山。
用腳走出文學路
王宏甲,福建建陽人,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致力于紀實性文學的創作。從《智慧風暴》到《新教育風暴》再到《塘約道路》《中國天眼:南仁東傳》,王宏甲的每一部作品都聚焦現實,充滿了對現實的觀察和思考。
王宏甲喜歡宋代詩人陸游的一句詩:“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他很認同這個觀點:深入社會,深入實際,否則得不到美妙的文章。
“我的同行有一句話說,報告文學是用腳寫出來的。要走到那些很偏僻的地方去。今天脫貧攻堅的大戰場,多數都在那些集中連片的特困地區,多是窮鄉僻壤。”此,王宏甲深以為然,而他確實也是這樣做的。采寫報告文學30多年,王宏甲從未停止走和問。他的知識來源有兩大體系——書本里的知識,加上幾十年不間斷的調查和詢問。近幾年,他跑了全國20多個省、市、自治區70多個縣市的240多個鄉村。
在“用腳走出來”的這條創作路上,王宏甲最享受的是他跟農民之間純粹的感情,這包括從基層干部群眾那里汲取的智慧。在他看來,所謂“用腳走出來”,并不是單純指艱苦,更是創作中必不可少的歷練:“我們平常講‘履歷,‘履歷就是穿著鞋子天南地北去走的經歷。讀書不一定破萬卷,行萬里路是要有的,鞋里存儲的記憶往往比從書本里看到的更牢靠。”
王宏甲非常熱愛中國傳統文化。他認為中國人講“學問”,西方人講“知識”,二者是有不同的。知識主要從書本中來,而學問的來源有兩個渠道:一個是通過讀書學來,還有一個就是通過問獲得。“有很多知識,書里是看不到的,特別是新的知識。中國講‘做學問,沒有人講‘做知識。做學問就是不僅要從書本上學,還要到社會現實中去問。”
“世界需要良知”
王宏甲的《非典啟示錄》,從寫作到出版整整十年,是目前為止世界上唯一一本從第一例追蹤到最后一例的記錄人類防治烈性傳染病的書。2003年非典暴發后,王宏甲寫信給中國作協,希望到一線采訪。很快,作協組織了一個八人作家團深入疫區采訪。那段時間,王宏甲深入多家醫院、社區、大學、鄉村、指揮中心等,采訪方方面面的專家、醫護人員和患者。這本書在2013年出版,王宏甲覺得,最重要又最艱難的部分,就是第一年的采訪。他需要實地去考察,要冒著生命危險采訪。
作為報告文學作家,選擇創作主題時,會最先考慮的什么?王宏甲的答案是:“有沒有意義,在當下對多少人有用。”
2016年,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貴州安順市塘約村走進了他的視野,回北京后,在那個村的見聞一直在他腦海中翻滾,于是他創作了《塘約道路》,講述貴州省安順市塘約村在黨支部領導下,把承包地重新集中起來統一經營,走同步小康之路后產生的奇跡。《塘約道路》出版后,被農村黨支部書記們廣泛閱讀。
在王宏甲所有的作品中,他覺得“對每個成長中的青少年都會有用的”是《讓自己誕生》和《世界需要良知》。“《讓自己誕生》致力于講人的精神成長。我們這些年講成才,成才屬于知識層面的事。人的成長不是從50公斤長到70公斤,人的成長包含了精神的、情感的、信仰的、志向的成長。 ”
《世界需要良知》是王宏甲在首屆中法文學論壇的演講稿。在他看來,文學藝術最大的社會作用,是在錢財橫行、權勢霸道、人的精神流離失所的地方,發揮拯救人心的作用。
英國哲學家培根在16世紀說“知識就是力量”,曾影響了歐洲近代社會。王宏甲在21世紀初的巴黎講臺說“世界需要良知”,良知與知識具有不同的內涵。“世界需要良知”是王宏甲的文學觀,也可以擴大到他的教育觀、歷史觀、文明觀。
“光講知識就是力量是不夠的。如果沒有人類的良知抑制知識跋扈,知識也可以毀滅世界。我認為良知是唯一能夠阻止這個世界倒塌的東西。”王宏甲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