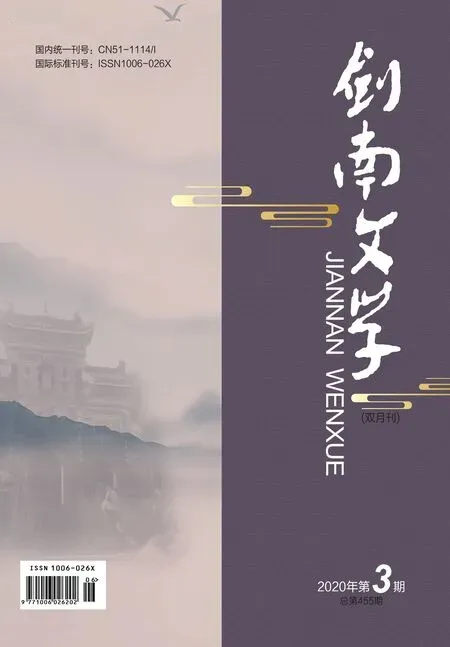這一天
□譚雪花
映雪是被吵醒的。
她試圖用枕頭把腦袋蒙住,無奈聲音太大,掩不住,心里暗自懊悔不聽自家老王的話,每晚非要堅持開窗睡覺。
摸出枕頭下面的手機一看,八點都沒到呢。樓下的動靜是越發地大了,聽上去還不止是兩個人的聲音。這對于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日益冷清的小區來說,倒也添了一點人氣。
映雪披上棉服,走到窗前往外看,果然又是樓下那個犟老頭在鬧。說起這個犟老頭老張,還真跟茅廁頭的石頭一樣,又臭又硬。年前,在政府的牽頭下,小區要對樓梯和樓頂安全隱患進行整改,單元十戶人家,其他九戶都同意了,唯有這個老張頭,堅決不簽字。樓棟代表和鄰居分別上門做工作,均是油鹽不進,還跟人吵了幾架。大家后來猜他不配合,大概是因為出去租房要花錢,加之他家在二樓,對加裝電梯之類的改造,自覺受益不大,所以不情愿。為了完成簽字,眾人合計,大家共同出資,給他一家在外面租房。沒想到老張頭仍然不同意,把上門的工作人員罵了個狗血噴頭:“你們有幾個臭錢了不起啊,老子不差錢,我就是不搬。”工作人員氣得哭,給大家一說情況,大家都覺得老張頭一家不可理喻。
今兒這大清早的,這老張頭又鬧的是哪一出?
“我在屋頭都蹲出煤炭灰了,咋就不能出去走走?街上人花花兒都沒有一個,哪個來傳染我噻,哪個來傳染我噻?”這是老張頭的大嗓門。
“大家都在屋里頭待得住,就你一個人要悶死?你沒聽說昨天小區旁邊那家醫院才來了個疑似病人啊,你非要出去惹!感染了可不是你一個人的事,全家都要一起隔離!你今天出了這個門,就別回來了,你不怕老娘怕,一家大小怕。”這是他老伴兒的河東獅吼。
“傳染傳染,天天你們都在念,這么大個城,幾十萬人,也才7 個人得肺炎,搞得雞飛狗跳,門都不讓出了,跟坐牢一樣。憑啥不要我回來?我偏要回來,你個膽小怕死的老婆子。”
對于預防傳染,映雪對這種說法深以為然:100 個人里面,80 個人嚴防死守,18 個人無所謂,2 個人到處作死,這2 個人就會通過18 個人讓80 個人的努力白費。老張頭算18還是2 呢?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為老不尊的人吧?映雪心里很是鄙夷,卻沒有作聲。
熱鬧看完了,映雪也就不打算接著睡,洗漱完畢之后,來到客廳,看見十八歲的兒子穿戴整齊地坐在沙發上,滿面愁容。
“樓下吵到你啦?”
兒子今年高三,高考已進入倒計時,此時正是最關鍵的時刻。說起來這一屆的高三學生,大略也是他們的命數。有人說,這屆高三堪稱傳奇:出生遇非典,高考遇肺炎,不宜復讀 (全國多地明年實行新高考模式,取消考試大綱)。學校原計劃二月一號復課,因疫情形勢嚴峻,又擱置了。省教育廳的文件,隔兩天又在更新,總結起來就兩字:“待定。”開學遙遙無期,只能自己在家復習。
兒子如今是全家人的重點保護對象,故而映雪在年前就對娘家和婆家的兄弟姐妹“三令五申”:不要串門,不要聚會,疫情面前,人命第一,任何僥幸都有可能奪人性命。她甚至對年前執意要回江安老家的弟媳婦放了狠話:“你若是執意要回去,回來后就不要和我們接觸了。假如因為這個影響了我娃兒高考,我是要埋怨你們的。”這話可以說是相當的不留情面了,但映雪覺得自己實在是不敢拿兒子的事情來打水漂,小心小心又小心,以至于家中掌事的大哥都私下批評她有點緊張過度了。
“媽媽,我想去醫院一趟。”兒子聲音有點低沉。
“咋的了?!”映雪一下子緊張起來,現在“醫院”跟“病毒”一樣,是個敏感詞匯。
“我昨晚拉肚子,還嘔吐,睡前癥狀不是很嚴重,就沒跟你們講,結果半夜起來好幾次,又吐又拉。”兒子頓了一下,小聲說:“我覺得自己還有點發燒。”
映雪這下汗毛都豎起來了,眼下,“發燒”就是個禁忌。真是怕啥來啥!在廚房里忙活的老王提著菜刀出來,也是一臉焦急。“咋就發燒了嘛!”他說。
一家人面面相覷,屋里出現了短暫的沉默,而后,父子倆都把詢問的眼神投向了映雪。這個時候,映雪倒是感覺到自己是“一家之主”了。
映雪這個時候的腦子也是慌亂的。微信上到處都在傳,一旦哪里發現了病患,馬上從開始的單元樓棟隔離,然后封閉整個小區,鄰里之間很快就會出現鋪天蓋地的質問和責怪。去醫院?映雪第一反應是排斥的,現在發燒去醫院意味著什么?后果是什么?她想都不敢往下想。可是不去嗎?這段時間以來,不斷擴散的疫情和不斷攀升的數據,又在提醒每個人都有被感染的可能,不能心存僥幸。
“我還是去醫院吧!”還是兒子做出了選擇,“早去晚去都得去,早去早治療。”說到后面,聲音怯怯的,畢竟還是一個孩子。
老王默不作聲地脫下圍裙和家居服,穿上了外套。映雪從內心的糾結中緩過神。“我們先冷靜一下,”她用手勢示意父子倆,“你說你發燒,量過體溫沒有,多少度?”
“還沒量,” 兒子說,“你摸摸我是不是有點燙嘛?”
“糊涂!”
映雪一下子就生氣了,然后從醫藥箱里找出一個電子溫度計。這個溫度計是幾年前在網上買的,也不知還能不能用。她使勁甩了幾下,看見上面顯示了數字,還有電,這才遞給兒子,示意他夾在腋下。
映雪認為,根據他們最近活動的范圍和情況,兒子是斷不會染病的。
“時間到了。”兒子取出體溫計。
夫妻倆異口同聲:“多少度?”
“37.3。”
“那是有點發燒哦。”老王這下也愁眉苦臉了。
映雪依舊不甘心,把溫度計猛甩幾下:“量量我!這個溫度計很久沒有用了,量量我就知道準不準了。”
又是一個五分鐘過去。
“多少度?”這下,換父子倆異口同聲了。
“35.8。”
“咋個可能?!”這下是三個人異口同聲。
“所以我就說不準嘛。”映雪一下子舒了口氣,“我們先咨詢一下醫院,再決定去不去,好不?”
電話接通了醫院的朋友,醫生朋友仔細詢問了癥狀,詳細了解了兒子的生活規律和飲食習慣,得出如下判斷: 估計是空腹食用了過多的柿餅,加之春節期間的飲食過于油膩,造成胃腸道感染,引起腹瀉和發熱。建議先居家觀察一天,吃點止瀉養胃的藥 (比如藿香正氣液),再吃點感冒藥,多喝水。特別強調不要外出,隨時觀察體溫。
這個時候,醫生的話就是定心丸,一家人一致決定居家觀察。兒子立刻服用了氣味沖天的藿香正氣液,映雪三五兩下就把茶幾上剩余的柿餅給扔了,吩咐老王重新改菜譜,回廚房熬粥。
老王是個“惰性氣體”,因為身體不好,加之家住頂樓,又沒有電梯,平常回了家,十匹馬都別想把他拉下樓。可今天他就是覺得家里的藥不管用,不顧映雪的阻止,口罩、帽子、手套……全副武裝地出了門。一會兒的工夫,就氣喘吁吁地拎回來一大包藥。映雪邊給他噴灑酒精消毒,邊無奈地搖頭。老王很沖地對她說:“你不要管,不出去一趟,我就始終心不安。”
一個上午在焦急和苦熬中過去。午后,兒子起床,倒是沒有腹瀉了,可電子溫度計上面的數字,依然是37.3 度,沒轍的老王苦著臉不說話。這下,換映雪全副武裝出門了。老王追到門口問:“你又干啥去?”
“我買水銀溫度計去,這個電子溫度計肯定不準。”
小區大門口,從左到右不過兩百米的距離,經營著四家藥房。映雪一一走進去,每家的店員都是一如既往地熱情:“溫度計早就沒有了,是和口罩一起脫銷的。”
映雪失望地走出藥房,又撥通了醫生朋友的電話。講真的,這些天已經夠給醫生朋友添亂了,先是找口罩,后是買緊俏藥品,打電話咨詢……她都有些不好意思打擾人家了,但又想不出其他的辦法,她只能硬著頭皮打電話。朋友在電話里悄聲告訴她,她正在開會,會后聯系,然后匆匆掛了電話。
平常宅在家里不覺得冷,在外面走動一下,才發覺天氣還是很寒冷的。寬闊的大道上空無一人,往日繁華的酒店也是門庭冷落車馬稀,街上一派 “千門萬戶閉,唯有藥房開”的景象,說不出來的冷清。街角處有幾個戴紅袖章的,應是社區的防疫工作人員,他們不時探頭警惕地往映雪這邊瞧。映雪想,要是自己繼續在這里站著,估計他們就會過來“關心”自己了。為了節約一個口罩,映雪決定不回家,就在這附近邊溜達邊等醫生朋友開完會打電話。
圍著小區走了幾圈,映雪終于等到了醫生朋友的電話。醫生朋友說,就在剛剛開完的會上,醫院再次強調了疫期的管理工作,重點就是醫療器械、醫療物資的集中管理和統一分配問題。朋友不無遺憾地告訴她:“真的是愛莫能助!”
映雪望著陰沉沉的天,心里說不出來的難受。平生第一次,她感受到了深深的無助和不知所措。拖著沉重的雙腿往回走,握在手里的手機不時傳來震動,心煩的她點開一看,是鄰居群里大家轉發的各種關于疫情的信息,和互相鼓氣的話。映雪看完不無感慨地發了一句:“現今找個溫度計,都比登天還難!”并配了三個痛哭的表情。
快走到樓下的時候,映雪接到一個陌生的電話:“鄰居,剛剛在群里看見你在四處找溫度計。我家年前多買了一支,如果你急需,我們可以支援你。”
映雪大喜:“是是是,我急著要,太感謝了,請問您是哪家?”
“二樓老張頭家。”
老張頭?就是那個她鄙夷的自私自利的犟老頭?映雪的嘴張成了“O”型。
“特殊時期,我就不給你送上門了。我已經把溫度計用口袋裝好,掛在我們家門把手上面,你自己來拿一下。”
映雪從一瞬間的錯愕中驚醒,連聲道謝。經過二樓的時候,她果真看見老張頭家的門把手上面掛著一個白色的小塑料袋。
望著這支溫度計,映雪不禁生出許多感慨。突發的疫情,像一塊巨石砸進了我們原本平靜有序的生活。它帶給我們恐懼和困惑,也喚醒了我們內心的善良。或許我們曾經有分歧,甚至曾道不同不相為謀,但在巨大的災難面前,我們仍然能團結一心、彼此溫暖的。有這樣的力量在,誰還能說我們翻不過去這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