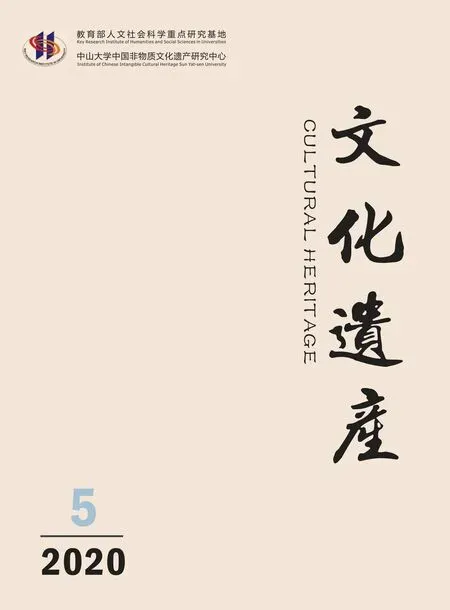《山經》“無草木”“沙”及其相關詞匯的統計分析
吳曉東
《山經》(亦稱《五藏山經》)描述了很多事物,林林總總,十分繁雜。在這樣一個景象中,給人印象較深的,總是山與從山上發源的江河,以及這些山水滋生出的鳥獸魚蟲、花草樹木、還有埋藏于山石間的金銀銅鐵,后期的插圖繪本,都傾向于呈現出生機勃勃的奇靈異獸,似乎整個《山經》都是一派孕育生命的郁郁蔥蔥的景象。其實,除了這些,《山經》還有與草木相對的“無草木”與“沙”的描述,比如《南次二經》說:“又東五百里,曰夷山。無草木,多沙石。”(1)袁珂:《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6年,第14頁。《山經》里共講述了447座山,其中“無草木”的竟然達95座之多,占了21%,五分之一強。試想一下,如果我們身邊的群山中,五座有一座不長草木,光禿禿的,那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景象。如此之高比例的“無草木”,在《山經》中的分布是怎樣的呢?《山經》分南、西、北、東、中五部分,我們不妨對“無草木”的具體分布進行詳細的統計分析,以更為全面地看到《山經》所展現的真實景象。
《南山經》共3列山系,39座山,無草木的山14座,占35%。其中《南山首經》這一山系共9座山,無草木的有2座,《南次二經》共17座山,無草木的占了9座,達到了一半以上,《南次三經》共13座山,無草木的占了3座。
《西山經》共4列山系,77座山,無草木的10座,占12%。其中《西山首經》共19座山,無草木的有3座。《西次二經》共17座山,無草木的有1座。《西次三經》共22座山,無草木的有4座。《西次四經》共19座山,無草木的有2座。
《北山經》共3列山系,88座山,無草木的山30座,占34%。其中《北山首經》共25座山,無草木的就占了11座。《北次二經》共16座山,無草木的有8座。《北次三經》共47座山,無草木的有11座。
《東山經》共4列山系,46座山,無草木的山20座,占43%。其中《東山首經》共12座山,無草木的有4座。《東次二經》共17座山,無草木的山比例比較大,有9座。《東次三經》共有山9座,無草木的就占了5座。《東次四經》共有山8座,無草木的有2座。
《中山經》共有12列山系,197座山,其中無草木的21座,占10%。無草木的山系有中次二經、中次三經、中次五經、中次六經、中次十經、中次十一經和中次十二經,共7列。另外的5列山系沒有提到無草木,這5列山系加起來共82座山。這7列有“無草木”描寫的山系情況具體是這樣的:《中次二經》共9座山,無草木的山有3座。《中次三經》一共只有5座山,其中無草木的有1座。《中次五經》共15座山,無草木的有3座。《中次六經》共14座山,無草木的有7座。《中次十經》共9座山,有2座無草木的山。《中次十一經》是所有的山系中山最多的,共有48座,但無草木的山只有2座。《中次十二經》有15座山,無草木的山有3座。

各列山系無草木的山數目統計如下表:
從這些數據來看,生態最差的是東部,43%的山沒有草木。其次是南部,無草木的山達到35%。再次之是北部,無草木的山為34%。最好的是中部,只有10%的山無草木,其次是西部,無草木的山占12%。《山經》是一部先秦著作,從語言文字特點看,至少也應在商代以后,如果我們設定《山經》成文是在周代,那當時人們涉及的區域也就與目前中國的區域大致相當。就目前中國生態來看,西部遠離海洋,雨量較少,生態最差,但在《山經》里西部“無草木”的山只占12%,遠比東部、南部好。南方是一個多雨區域,炎熱而植被豐茂,在《山經》里“無草木”的山百分比卻居第二位。至今尚未出現沙化的東部地區,在《山經》里“無草木”的山百分比確是最高的。這不僅與中國目前生態狀況不符,就是與古代的生態也是不符的。
除了關于無草木的描述之外,《山經》還有一些關于沙的描寫,同樣反映了生態的惡劣。在《山經》里有21處提到“沙”字,其中19處提到的“沙”可確定是描寫沙土沙石的,14處將無草木與沙并提:
又東五百里,曰夷山。無草木,多沙石。(《南次二經》)
又東五百里,曰區吳之山,無草木,多沙石。(《南次二經》)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白沙山,廣員三百里,盡沙也,無草木鳥獸。(《北次二經》)
又南三百里,曰番條之山,無草木,多沙。(《東山首經》)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葛山之尾,無草木,多砥礪。(《東次二經》)
又南三百里,曰盧其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沙水出焉。(《東次二經》)
又南水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石。(《東次二經》)
又南五百里,曰緱氏之山,無草木,多金玉。原水出焉,東流注于沙澤。(《東次二經》)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諸鉤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東次三經》)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中父之山,無草木,多沙。(《東次三經》)
又東水行千里,曰胡射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東次三經》)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流沙,行五百里,有山焉,曰跂踵之山,廣員二百里,無草木。(《東次三經》)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無皋之山,南望幼海,東望榑木,無草木,多風。是山也,廣員百里。(《東次三經》)
中次六經縞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東望谷城之山,無草木,無水,多沙石。(《中次六經》)
另外還有5處只提沙而未提無草木: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其尾踆于東海,多沙石。(《南山首經》)
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西次三經》)
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于嬴母之山。(《西次三經》)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灌題之山,其上多樗柘,其下多流沙,多砥。(《北山首經》)
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洹山,其上多金玉。(《北次二經》)
除此之外,還有兩處名稱里含有“沙”字,一處是《東次二經》的空桑之山:“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北臨食水,東望沮吳,南望沙陵。”(2)袁珂:《山海經校注》,第126頁。另一處是《西次三經》的長沙之山:“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于泑水,無草木,多青雄黃。”(3)袁珂:《山海經校注》,第47頁。“沙陵”是專有名稱還是指沙丘,不得而知,“長沙之山”也是同樣,但后面因出現“無草木”的描述,似乎這個名稱也可能真的與沙有關,正如《北次二經》里的白沙山一樣“盡沙也”。
在這些提到沙的地方,有8處是關于沙漠的。即《北次二經》的“廣員三百里,盡沙也”,“流沙三百里,至于洹山。”《東次二經》里的“流沙三百里”“流沙百里”,《東次三經》里的“曰流沙,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西次三經》里的“觀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曰流沙,二百里至于嬴母之山”。這些沙漠少則百里,多則五百里,已經不是很小的范圍。這些沙漠與“無草木”的山共同構成了一幅生態惡劣的景象。這些沙的分布在南、西、北、東、中五個方位都有分布。而且,我們發現,這些沙漠不僅分布在北經、西經這些現實中確實干旱少雨的區域,而且也分布在《東山經》,在14處與“無草木”并提的“沙”中,《東山經》占了10處,而且大沙漠達到4處之多。這與中國地理的狀況不符合,中國東部不僅目前雨水豐沛沒有沙漠,古代也未曾有過沙漠。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山經》里如此之多“無草木”的山與“沙”呢?
干旱少雨會導致土地石漠化、沙漠化,從而導致草木無法生長,但從以上“無草木”與“沙”的分布情況看,《山經》的描述有悖于現實。另外,一座山無草木也有可能是因為海拔太高導致終年積雪而無法生長草木,就像珠穆朗瑪峰那樣。《西次四經》的上申之山是“上無草木,而多硌石,下多榛楛,獸多白鹿。”(4)袁珂:《山海經校注》,第70頁。意思是山的上面沒有草木,下面有,榛楛一類的植物很多,而且白鹿也很多。這一上下對比的描寫很符合高海拔的推測,但《山經》里類似這樣的描述不多。海拔高一般會導致山上有雪,那么《山經》里關于雪的描述怎樣呢?《山經》里關于有雪的山的描述不多,一共也就5處,如下:
西北三百里,曰申首之山,無草木,冬夏雪。(《西次四經》第11座山)
又北二百三十里,曰小咸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北山首經》第15座山)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狂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北次二經》第7座山)
又北四百里,曰姑灌之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北次二經》第13座山)
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北次三經》第33座山)
這五座冬夏都有雪的山都與“無草木”聯系在一起,可見這些山無草木的原因確實是因為冬夏有雪造成的寒冷導致草木難以生長。造成冬夏有雪的原因可以單靠海拔高,比如處于非洲的乞力馬扎羅山,雖然此山處于赤道一帶,但由于海拔很高,達5895米,其山頂終年積雪,山頂上無草木生長。也可以單靠緯度高,無論是南極圈還是北極圈,由于緯度高,遠離赤道熱帶地區,即使海拔很低的平原地區,也是終年積雪。還有一種情況就是靠海拔與緯度的結合,比如歐洲的阿爾卑斯山脈海拔不算特別高,其最高峰勃朗峰的海拔也才4806米,但由于所處的緯度偏高,海拔與緯度兩者的結合導致了山脈多處山峰終年積雪,無草木生長。以上五處冬夏有雪的山只有一處是在《西山經》,其余四處都是在《北山經》,可見在《山經》作者的觀念里,北方是容易導致夏冬有雪的區域。雖然當時的人意識不到這是因為緯度偏高造成的,但已觀察到了這一規律。與這些山相鄰的其他一些山并無同樣描寫,這說明同處于北方也不一定就會冬夏都有雪,除了緯度高之外,還需要達到一定的海拔才會導致“冬夏有雪”的結果。可見《北山經》這幾座山的“冬夏有雪”是由高海拔與高緯度兩者結合導致的,從而也才導致了“無草木”。《西山經》那座山的“冬夏有雪”或許只是單因海拔,也可能是兩者的結合。不過,“冬夏有雪”導致的“無草木”只占95座山里的5座,比例不大,這不會是導致無草木的主要原因。
除了這些“無草木”與“沙”的分布與現實不符之外,還有一些“無草木”的描寫不符合邏輯,比如《南山經》里的柢山是“多水,無草木。”(5)袁珂:《山海經校注》,第4頁。而亶爰之山是“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6)袁珂:《山海經校注》,第5頁。又有水又不長草木,只能解釋是海拔太高,植物無法生長。就目前中國版圖內的南方地區,要找到14座因高海拔而無法生長植物的山,基本不可能。《南次二經》有一些描述極為矛盾,比如“羽山,其下多水,其上多雨,無草木,多蝮蟲。”(7)袁珂:《山海經校注》,第12頁。這顯然是整座山都雨水充沛,但就是“無草木”,如果說環境惡劣不適合動植物生長因而“無草木”,這里又“多蝮蟲”。關于云山的描寫也值得注意:“又東南五十里,曰云山,無草木。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雩琈之玉。”這里說“無草木”,又說“有桂竹”或“有桂、竹”。如果是“有桂竹”,那么這是一種竹子,不屬于草木,如果是“有桂、竹”,那么這一描寫就自相矛盾了。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山經》里“無草木”與“沙”的描寫有諸多可疑之處,我們有理由懷疑這些描寫是真實可信的,其中有可能摻雜了一些想象的成分。
筆者在《四面環海:〈山海經·山經〉呈現的世界構想》一文里提出過《山經》是一個想象的地理世界,(8)吳曉東:《四面環海:〈山海經·山經〉呈現的世界構想》,《民族藝術》2011年第2期。這里對此觀點進行一些補充,以便闡釋《山經》里為什么如此之多“無草木”的山。
《山經》里提到海的地方有30處。這30處“海”有兩種性質,一種是地理位置確定不了的,這有6處。《西次三經》第6座山泰器之山提到2次:“是多文鰩魚,狀如鯉魚,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東海,以夜飛。”(9)袁珂:《山海經校注》,第52頁。《西次三經》第7座山槐江之山提到1次:“實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10)袁珂:《山海經校注》,第53頁。《北次三經》第22座山發鳩之山也提到2次:“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11)袁珂:《山海經校注》,第111頁。這兩次都是說的東海,講的是精衛銜木石填東海的故事。另外,《東次三經》說:“無皋之山,南望幼海,東望榑木。”此幼海是個專有名稱,可能是指湖泊。剩下的24處屬于另一種,這24處的海與山聯系在一起,其地理位置可以借助山的位置來加以判斷。如下:
“其首曰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麗麂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南山首經》第一座山)
“箕尾之山,其尾踆于東海。”(《南山首經》最后一座山)
“虖勺之山……滂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海。”(《南此二經》第14座山)
“漆吳之山……處于東海,望丘山,其光載出開車入,是惟日次。”(《南此二經》最后一座山)
“禱過之山……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南次三經》第2座山)
“丹穴之山……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南次三經》第3座山)
“發爽之山……汎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南次三經》第4座山)
“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南次三經》第9座山)
“南禺之山……佐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海。”(《南次三經》最后一座山)
“騩山,是錞于西海……淒水出焉,西流注于海。”(《西山首經》最后一座山)
“崦嵫之山……苕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西次四經》最后一座山)
“渾夕之山……囂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北山首經》第21座山)
“湖灌之山……湖灌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海”(《北次二經》第14座山)
“敦題之山……是錞于北海。”(《北次二經》最后一座山)
“景山……景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海澤。”(《北次三經》第25座山)
“樕螙之山,北臨乾味。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東山首經》第1座山)
“番條之山,無草木,多沙。減水出焉,北流注于海。”(《東山首經》第5座山)
“姑兒之山……姑兒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海。”(《東山首經》第6座山)
“北號之山,臨于北海……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東次四經》第1座山)
“東始之山……泚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東次四經》第3座山)
“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海。”(《中次九經》第2座山)
這24處“海”分布在關于22座山的描述中,其中招搖之山、騩山、北號之山分別提到兩次,但兩次都無疑是指同一海,比如關于招搖之山的描述時首先說招搖之山臨于西海,接著又說從招搖之山發源的麗麂之水西流注于海,顯然這個海就是招搖之山所臨的西海。也就是說,這24處“海”也可以視為21處。
關于這些海,有學者認為有的是湖泊,河流注入這些海,可能注入的是湖泊,這樣才好解釋“西海”“北海”這些概念,因為中國只有東邊與南邊面臨海洋。比如清人畢沅注釋《西山首經》里“騩山錞于西海”之“西海”時就認為其為中國西部的青海湖,清代呂調陽著有《五藏山經傳》,他解釋《南山首經》招搖山所臨的西海為“馬品木達賴池”,并說明此池“周二百余里”;解釋《西次四經》崦嵫之山邊上的海為“哈拉淖爾”湖。這種認為海即湖的觀點一直被沿用,比如今人徐顯之在注釋《西山首經》里“騩山錞于西海”之“西海”時就沿襲了畢沅的觀點,而且在注釋《北次二經》敦題之山所臨之北海時又認為其即貝加爾湖。(12)徐顯之:《〈山海經〉淺注》,合肥:黃山書社1993年,第21、57頁。也有學者認為這些海就是海洋,并提出《山經》四面環海的猜想,(13)邱宜文:《山海經的神話思維》,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第29頁。但由于沒能證明這塊被海環繞的大地在何處,所以未能被人們認同與重視。只要對這些海所處的位置,或者說這些海與山聯系的特點加以統計,其顯示出來的特點就能很好地反駁認為這些海即湖泊的觀點。
以上這些“海”的描述分兩種,一種是說山“臨于海”“踆于海”“錞于海”“處于海”,意思都是說山就在海邊。另一種是說水“注入海”。前者有6處,后者18處。很巧的是,這6處臨海的山,全部都是山系中處于兩端的山,其中第一座的有3座,最后一座的也有3座。另外,還有4座處于兩端的山所發源的河流直接注入海。也就是說,這些海與山系首尾的山巒聯系在一起的占45%,比例是非常之高的,這其中必有奧秘。我們知道,山系兩端的山巒,朝外的一端便是《山經》所描述的地域的邊緣,所以,這似乎說明了,《山經》所描述的地域,是一個環海的板塊。
在這24處提到“海”的,只有1處出現在《中山經》里。《中山經》一共12列山系,為什么只提到有一條河流注入海里?我們知道,所有的河流,除非是內流河,否則都是要注入海里的。《山經》里說某一條河“流注于海”,那是指它直接進入海里,它不作為其他河流的支流。《中山經》所述河流無數,唯獨說發源于岷山的江水“流注于海”,那是因為長江不是任何河流的支流,所以只能說它注入海。如果一條河流是其他河的支流,在《山經》里就會說它注入某一條河流,比如《西次三經》的“洵水出焉,南流注于黑水。”(14)袁珂:《山海經校注》,第60頁。《西次四經》的“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15)袁珂:《山海經校注》,第69頁。如此說來,以上這些與“海”聯系在一起的山,除了《中山經》的岷山,其他的都離海洋很近,其所發源的河流直接流入海洋。
我們來看《南山經》的“海”與山的關系。《南山經》一共有9座山與海聯系在一起,其中4座是處于山系首尾的山,占44%。《南山首經》只有2座山與海有聯系,即招搖之山與箕尾之山,這2座山分別處于山系的首與尾,也就是說,是此山系最邊緣的山。《南山經》一共有3列山系,都是從西到東。處于西部邊緣的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發源于招搖之山的麗麂之水又“西流注于海”,而處于東部邊緣的箕尾之山“踆于東海”,這恐怕很難將這“西海”與“東海”解釋為湖泊。這其實不是孤例,《南次二經》最后一座山即漆吳之山也是“處于東海”。漆吳之山是最后一座山意味著它是南部第二列山系靠東最邊緣的山,這山“處于東海”,和第一列山系靠東最邊緣的箕尾之山“踆于東海”完全一樣。更有甚者,《南次三經》最后一座山即南禺之山,其流出的佐水則是“東南流注于海”。關于這座山與海的關系很值得玩味,這山叫南禺之山,應當理解為南隅之山,即南部靠邊角的山,這與它所處的位置是吻合的。《南山經》只有三列山系,《南次三經》是最外邊的一列,南禺之山是最后一座山,自然也就處于東南角的位置,也就是所謂的“南禺(隅)”,難怪發源于此的佐水是“東南”流注于海。至此,我們已經能覺察到,《南山經》邊緣的山靠近大海不少,如果再考察《南次三經》的山,這一特點就更展露無遺了。《南次三經》除了上文說的最東端的南禺之山是靠海的,第2、3、4、9座也是靠海的,它們分別是禱過之山、丹穴之山、發爽之山、雞山,它們發源的浪水、丹水、汎水、黑水不匯入任何河流,直接“南流”注于大海。《山經》按南、西、北、東、中這種順時針方向來排列順序,如果《南山經》也是按這種順時針排列,《南山首經》當在最里面也就是最靠近中部地區,《南次二經》在其南面,《南次三經》最靠外。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南山經》與海的關系,即大海圍繞著《南山經》所描述的區域。
那么《西山經》又是怎樣一種狀況呢?《西山經》有四列山系,都是從東到西排列。那么這四列山系是怎樣排位呢?換言之,哪一列最靠南,哪一列最靠北呢?按照上文說的,《山經》是順時針方向排列,那么就應該是《西山首經》位于最南邊,《西次二經》在其北面,然后是《西次三經》《西次四經》。從一些河流的流向也可以證實這一點,《西山首經》云:“松果之山,濩水出焉,北流注于渭。”(16)袁珂:《山海經校注》,第25頁。《西次二經》云:“數歷之山……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17)袁珂:《山海經校注》,第40頁。從楚水向南流注于渭以及濩水向北流注于渭來分析,《西山首經》應當排在《西次二經》的南面。所以,《西山經》的敘事是從南到北一列山一列山地敘述。另外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就是因為《南山首經》的最西端的山已經靠海了,所以《西山經》整體上都在《南山經》的北面,也就是說,西南區域是被《南山經》的山占據的,《西山首經》的山不可能靠近南海。《西山經》四列山系都是從東往西排列的,所以四座最西端的山才是這一區域的邊緣。那么這4座西端最邊緣的山與海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呢?騩山被直接說是“錞于西海”,另一座崦嵫之山雖然沒有明說靠海,但由它發源而出的苕水直接“西流注于海”,也就是說,4座有2座是可以確定為靠海洋的,占50%。
再來分析《北山經》的山。《西次四經》只有最西端的崦嵫之山靠海,其它山都不靠海,因為《山經》的西北部這一區域為《北山經》所占據,《西山經》的山除了兩座與西海靠近之外,不會與北海靠近。《北山經》有三列山系,都是從南到北的。按《山經》的規律順時針排列,就是《北山首經》最靠西,《北次二經》居中,《北次三經》是三列山系最靠東的。因此,《北山經》處于邊緣的山就是《北山首經》一整列,以及《北次二經》《北次三經》末尾的山,也就是最北端的山。那么這些山與海的關系怎樣呢?《北次二經》最后一座山敦題之山被說成是“錞于北海”,《北山首經》第21座山渾夕之山發源的囂水“西流注于海”,這一列山按理都是最靠西的山,西流注于海是合理的。《北次二經》一共16座山,其第14座湖灌之山發源出的湖灌之水“東流注于海”。湖灌之山不是最北端的山,不過說它發源出的河流直接流到海里,也不是沒有可能,只是如果說“北流”比較合理,說“東流”有點讓人費解,因為這里離東海應該有很遠的距離。《北次三經》共47座山,其第25座山景山發源的景水“東南流注于海澤”,這一描述也不清楚出于什么原因,無論是位置還是流向,都不是很合理。不過,像《北山經》這樣描寫不靠邊的山發源出來的水直接流入海里的,除了上文提到的江水之外,沒有別的了,數量不多。
再來看看《東山經》。《東山經》一共有四列山系,都是由北到南走向。按順時針的排列方式,當是按《東山首經》《東次二經》《東次三經》《東次四經》由里向外排列。用食水作為參照物來判斷四列山的排列也是會得到同樣的結果:《東山首經》云:“東山經之首曰樕螙之山,北臨乾昧。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18)袁珂:《山海經校注》,第121頁。《東次二經》云:“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北臨食水。”(19)袁珂:《山海經校注》,第126頁。因為食水是東北流入海的,而空桑之山北臨食水,所以可以判斷空桑之山在樕螙之山的東南面,由此也就可以推論《東次二經》的山系在《東山首經》山系的東面,符合順時針排列的規律。如此,便是四列山系起始的山巒(也是最北端的山)以及《東次四經》整列山處于最邊緣。這些處于邊緣的山共有3座與海關聯,即《東山首經》第1座山樕螙之山、《東次四經》第一座山北號之山,以及《東次四經》第3座山東始之山。樕螙之山發源的食水直接“東北流注于海”,東始之山發源的泚水直接“東北流注于海”,北號之山不僅其發源的食水直接“東北流注于海”,而且它也被描述為“臨于北海”。
基于以上分析,這些海基本都與處于山系邊緣的山相關聯,這就使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即《山經》所描述的區域是一個四面環海的板塊。那么,這個四面環海的板塊有多大?從《山經》里關于風的描述我們可以得出這個板塊就是整個世界。
《山經》出現“風”字共18次。這些“風”分兩種,一種是說某種動植物的功能或特征,比如某種動物出現了,或吃了它的肉,就會有風雨。比如《北山首經》云:“有鳥焉,群居而朋飛,其毛如雌雉,名曰,其鳴自呼,食之已風。”(20)袁珂:《山海經校注》,第146頁。《中次八經》云:“神計蒙處之,其狀人身而龍首,恆游于漳淵,出入必有飄風暴雨。”(21)袁珂:《山海經校注》,第184、185頁。《中次十一經》云:“有獸焉,其狀如彘,黃身、白頭、白尾,名曰聞獜,見則天下大風。”(22)袁珂:《山海經校注》,第146頁。這一類型共出現13處,對《山經》板塊區域大小的判斷沒有什么作用。另一種是說某山出風或多風,這一類型只有6處,其中有4處位置比較特殊,如下:
又東四百里,至于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多怪鳥,凱風自是出。(《南次三經》第5座山)
又西二百里,曰符惕之山,其上多棕枬,下多金玉。神江疑居之。是山也,多怪雨,風云之所出也。(《西次三經》第17座山)
又北五百里,曰錞于毋逢之山,北望雞號之山,其風如飚。(《北次三經》最北一座山)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無皋之山,南望幼海,東望榑木,無草木,多風。(《東次三經》最后一座山)
《南次三經》是南邊最外部的一列山,按以上的分析,這里是靠海的。《南次三經》一共有13座山,旄山之尾是第5座山,算是位于中部,雖然不是正中。旄山吹出來的風叫凱風,《詩經》里也有一首叫《凱風》的,歷來學者都將凱風解釋為南風。《山經》說從這里出南風,應該是出于把這里想象為南極。
符惕之山是《西次三經》的第17座山,因南邊有《南山經》以及《西山首經》《西山二經》的山擋著,北邊有《西次四經》以及《北山經》的山擋著,所以《西次三經》這列山系應當處于相對正西的位置。說從這里出風,當是把這里想象為西極。
錞于毋逢之山處于《北次三經》最北端。《北山經》與《東山經》都是南北走向,《北山經》三列,《東山經》四列,所以《北次三經》算是處于中部。《北次三經》一共47座山,錞于毋逢之山是最后一座,也就是說,這座山大致是北部邊緣中間的一座山。說這里“其風如飚”,當是把這里想象為北極。
無皋之山是《東次三經》的最后一座,在《東次三經》的東邊還有《東次二經》,無皋之山雖不是處于最東端,但這里應該是正東方向,因為這里“東望榑木”,榑木即扶桑,是古人想象的日出之地,因此,說這里“多風”,當時把這里想象為東極。
從以上的分析看,旄山之尾、符惕之山、錞于毋逢、無皋之山這四座山應該是處于《山經》所想象中的四極所對應的方向,所以這里有出風當與四方風有關。《大荒經》有關于四方風的描寫,如下:
名曰析丹,東方曰析,來風曰俊,處東極以出入風。(《大荒東經》)
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風曰乎民,處南極以出入風。(《大荒南經》)
有人名曰石夷,來風曰韋。(《大荒西經》)
有人名曰鵷,北方曰鵷,來風曰。(《大荒東經》)(23)此句應出現在《大荒北經》,參見吳曉東《〈山海經〉語境重建與神話解讀》,北京:中國社科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213頁。
“育遺”應當就是“因因乎”的不同寫法,詩經《國風·邶風·凱風》云:“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無令人。”(24)向熹譯注:《詩經》,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0頁。與《山經》里的凱風也是吻合的,由此可以推斷旄山之尾、符惕之山、錞于毋逢、無皋之山這四座山所出的風便是四方風,而四方風都是出自想象的四極。
由此可以看出,《山經》所構建的不僅是一塊四面環海的大陸,而且這塊大陸就是想象中的整個世界。至此,可以判斷《山經》不會是調查所得,而是由于祭祀的需要,羅列出一些山水來,祭祀這些山水,便是祭祀天下。不過,雖如此,依然難以否認《山經》所描述的山川有些是真實的,特別是《中山經》里的山。《山經》本是以一些真實的山川為基礎來敘事的,但說到中原以外的荒遠無稽的地域,祭祀者已是無能為力,只能憑借想象向壁虛構了。
明白了《山經》有很濃厚的想象成分,就很容易理解它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無草木”的山與“沙”了,這些“無草木”的山與“沙”主要分布在南、西、北、東四方,而《中山經》相對較少,正是因為祭祀者把四方想象為比較惡劣的區域。也正因為其目的是為了把四方描繪成一個比中原更為惡劣的區域,便不顧一切地把一些不好的東西都堆積在一起,這就造成了一些邏輯上的混亂,比如《西次四經》說:“又北百八十里,曰諸次之山,諸次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是山也,多木無草,鳥獸莫居,是多眾蛇。”(25)袁珂:《山海經校注》,第71頁。多木無草的現象尚可理解,因為樹木茂密,遮住了陽光,陽光不能射到地面,所以地面可能不長草,但后面的“鳥獸莫居,是多眾蛇”卻無法解釋了,有樹的地方應該是有鳥獸居住的,這里卻說只有蛇,沒有鳥獸。這很可能是出于一種對西方的想象,鳥獸是善的象征,而蛇是惡的象征,把西方想象成一種毒蛇盤繞纏居之地,連鳥獸都不敢去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