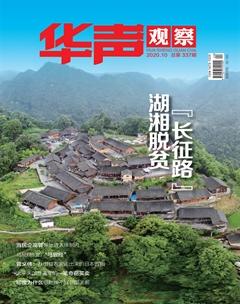“槍手”編劇那些“隱秘的角落”
肖莎 楊代媛

每年出產的電視劇數量眾多,光靠幾個出名的編劇單獨完成工作是不可能的,這樣的情況下,“槍手”就像明星的替身一樣,十分常見。
近日,編劇王先生和楊女士以侵害作品署名權為由,將《隱秘的角落》攝制方及出品公司訴至法院。原告認為,被告在與他們終止合作后,擅自在拍攝過程中使用原告創作的內容,但播出時并未將原告署名為編劇,嚴重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權。
目前,案件在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進一步審理當中。由此,編劇的署名權問題成為了議論焦點,并引發對編劇行業中“槍手”生態的關注。
“槍手”編劇:已成業內常態
李川(化名)是一名小編劇,他就是人們口中的“槍手”。
李川告訴記者,對于一些小編劇、剛畢業的學生或是兼職編劇而言,“代筆”就是他們工作的主要內容。
一部電影或電視劇,需要編劇簽字的版權授權書才可以備案,表明獨立創作。一般大咖編劇們都有自己的工作室,在接到項目后,可能會尋找“槍手”來進行創作,并提前簽署一份編劇協議——雙方約定價格、具體工作內容以及最后不署名。
曾做過“槍手”的編劇林夏(化名)告訴記者,編劇這個行業和其他行業一樣,有各種各樣的合作方式。這次《隱秘的角落》引發那么多人討論,終歸還是因為該劇火了。
《中國電視劇產業發展報告2019》的數據指出,2018年,我國生產完成并獲得發行許可證的電視劇共323部,共計13726集,平均單部集數為42.5集。
每年出產的電視劇數量眾多,光靠幾個出名的編劇單獨完成工作是不可能的,這樣的情況下,“槍手”就像明星的替身一樣,十分常見。
然而,每年都有幾部“火”了的電視劇,如果編劇發現自己參與的劇本火了,最后卻因為之前的協議而沒有署名權,該怎么辦?
林夏說,這種情況對編劇的發展是有一定影響的,畢竟將來要做項目,片方也需要看到你的作品,而代寫因為不署名,很難被認定是自己創作的內容。
“干這一行,收入和名氣是掛鉤的。小編劇們還是更多把做‘槍手的經歷當作學習和磨練,在圈內小有名氣之后也可以拿錢自己成立工作室,而有了名氣之后,就可以和制片方爭取項目地位、編劇話語權等。”林夏說。
價格低廉:每集5000元起步
一般編劇的費用是制片總費用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而“槍手”的費用卻遠遠低于該價格。李川告訴記者,他主要接網劇,一集的稿費在5000元左右。“我這樣的小編劇,一般就是寫稿、拿錢、走人,署名權是基本沒有的。”
而林夏的情況要比李川好很多,她接電視劇劇本代寫時,每集能夠有1萬元左右的稿費。她認為,目前“槍手”普遍存在,主要是因為行業中懷揣著夢想來打拼的年輕人很多,他們會將“槍手”的經歷作為鍛煉和學習的機會,而片方也正是看中這一群體價格低廉的優勢,從而選用。
“現今的藝術高校中,隨著擴招以及藝考的學生與日俱增,曾經可能只有十多人左右的班制迅速擴充,變成了三四十人的班級。在這么多的學生中,真正能成為大咖編劇的,屈指可數。”林夏說。
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網絡的普及,越來越多的平臺需要作品來做內容的填充和盈利。頂部的資源在被分食的過程中,依然有大部分的機會和資源留給底層的個人和團隊。于是,大大小小的影視文化公司孕育而生。可這其中,不論是礙于發展還是搶占份額,許多小作坊開始無所不用其極,利用信息差和畫大餅,網羅了一波寫手,開始進行項目制的創作。
在這些寫手中,大部分人不斷把好玩有趣的點子和想法落筆成文,而后完稿、定項、拍攝、成片、發行……最終卻不在編劇名單里。
“一部分人選擇維權,但是慢慢維權路上阻礙重重,有的放棄,有的等待許久成功了,時間、精力差不多也透支了。而另一部分人,往往因為夢想等原因,心甘情愿繼續做下去。”李川說。
專家:人身權不可放棄,“槍手”身份認定難
北京京師(鄭州)律師事物所律師劉兆慶認為,署名權是著作權的一種,根據著作權法第十五條之規定: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的著作權由制片者享有,但編劇、導演、攝影、作詞、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權,并有權按照與制片者簽訂的合同獲得報酬。
著作權法并未明確規定署名權不得放棄或轉讓,但署名權屬于著作人身權,而著作人身權所要保護的是作品和作者之間的人身聯系。署名權不可以通過合同或者協商的方式放棄,作者放棄署名權的條款因為不合法,因此無效。
而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李揚則認為,“槍手”代筆的現象應當分情況討論:如匿名代筆者系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的雇員,且作品系基于職務創作完成,則按照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第三款規定,單位取得所有著作權,包括著作人格權和著作財產權。但是,如匿名代筆者和他人系平等主體關系,且代筆系契約約定,而非完成職務創作,則非作品創作者在作品上署名為創作者的契約約定,涉及作者身份權保護的核心范圍,應屬無效。
總之,確認作品創作者地位是作者身份權保護的核心范圍,在不損及確認作品創作者地位的情況下,通過契約改變創作者具體的署名方式,應當承認此約定的有效性。
“約定不署名不能解釋為創作者放棄作者身份權,代筆也不能解釋為轉讓作者的身份權。否則應當視為違反民法典中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不得違反法律、不得違背公序良俗的規定。”李揚說。
重慶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法學博士張小強認為,署名權屬于精神權利,以作者自己的意思為基礎,可以不署名、署假名或署真名。但是這項權利本身從法律意義上是不能放棄的。
“實際操作中,‘槍手們簽訂編劇協議,只是默認了別人侵權但不追究署名權的侵權責任,這并不是法律意義上的放棄,合同或者口頭協商都不能約束創作者放棄署名權。”張小強說,如果“槍手”在后續過程中作為作者反悔,要求署名,只要能證明其作者身份,仍然可以通過法律維護自己的署名權,因為限制署名權的合同條款是無效的。
“如果限制署名權的條款有效,就會帶來嚴重的道德問題——花錢請‘槍手這一行為就會受到法律保護,這顯然有違公序良俗。”
劉兆慶告訴記者,在文化產業中,對于組成團隊進行作品創作,最后通過合同對署名權進行約定“槍手”或者外包團隊的身份,目前在法律界有很大的爭議。但從目前的主流觀點來分析,其身份不受著作權法的保護,暫且處于一個灰色地帶。
摘編自《法治周末》2020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