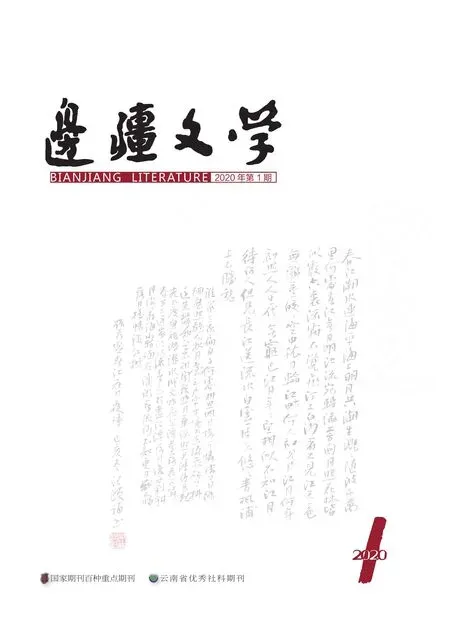白 壁 (長詩)
苗族
【題記】烏江畔,徒有斗室一壁,刷新白,懸舊物五件如下:
1.水虎
水虎半臥。水通常被省略,為空白。
我得先從想象一片水域開始,領悟白壁的茫然:
無限的白,趨近于無;白,獨虎的外圍空間。
膩子粉養著錦雞,碘鎢燈照著永夜,
在立起來的平面上尋找白壁的水性,依稀可見透光。
女工的陰影曾經讓她的面漆多了幾重,
總是沒能將自己刷白。而這是水虎的幸運
它從人類那里收復一片湖泊,為了寧靜
它將虎尾卷起來,和漣漪保持一樣的弧度
絨毛散開,水線作為刻度不復存在,
無垠,就是不干預,水虎的內心柔軟,
殺氣全無,臟器有一半被白代替。
它的下半身成為水質,水旋即為單色調,
女匠人將顏料傾空,她有未曾設想的空茫。
她的臉頰無意貼近的地方,其時為虎臉秘境,
光澤從黑線條之間的空白處傳來,凜冽。
而又安然。黑對白是一種侵襲,但是白從未撤退。
黑將虎氣收斂起來,筆觸成為規勸。
有一些善意是胡須輕輕地點擊,重拙在腕,
不在天靈蓋。為了將死亡牽引,朝向誕生,
須得有一枚刻畫骷髏的本心,而白壁上分明是頭顱,
森林簡化為毛發在它凌空的位置,漸至枯槁。
前傾之身,扭頭即能回眸,與我的凝視重瞳,
短兵相接,化干戈為墨汁。為避其鋒芒
我將獨眼與其對視,其勢雙倍;繼而蒙雙眼,
其氣在側,如隔空起波瀾,竟至將江湖逼起,
朝我水氣淋漓而來。棄面具,定睛,
繞過重筆,透過閑筆,看見背景如白,
如河川消隱,如嘯叫隱匿,如我提著白晝,
鑒定未來之敵:此物骨骼清奇,面有深淵,
背脊有天垂鞍韉,無神靈愿以此為坐騎,
居于湖,岸線綿延未有盡頭,空有綁縛之心。
太過死寂,白壁容不下動彈。湖水隱蔽的顫抖,
已經進入我幻境。明處的虎面,燈盞般掃描,
它已經孤獨得只剩下我,墻壁上大水蕩漾,
因其把控絲毫未見溢出。我閉光,穿戴黑幕,
夤夜而來,卻忘了脫下錦衣。
也忘記備足氧氣。它的呼吸,輕微,靜候老邁,
和死亡。白壁凈是異類,無一可歡愛,
傳襲已是惘然,復制已是贗品,有人用匕首,
畫出真跡,鎮虎之寶,僅為一枚閑章。
我以中年之軀隱居,在金石之框內,
復得入壁懸掛。體內血氣循環,隱忍,終日誦虎。
2.馬燈
誦虎如誦經。得舊馬燈兇光殘照。掠過白壁,
便是照過空白之湖。更亮了,燈盞謙遜地揚威。
我從印泥里掙脫,虎痕已經由中心成為邊緣,
我將繞行殺虎。正面迎擊毫無相遇可能。水黯淡下去,
虎骨漸去,如水漬。我終于暴露在光芒之下,
被施以古老的黥面之刑。不規則的力量,
判定了遞進式死亡的不平衡性。但有火苗,
從核心擴展,撫慰夜色,如同撫摸上天的絨毛,
只有玻璃理解這種光滑面子上的裂紋。
有一種鐵器是這塊玻璃的近親。它對焰火進行豢養,
內部狹小,越燃燒,越耗氧,只有從內向外打開,
才能挽救內焰于自閉癥。看上去搖曳是存活的方式,
外焰更綠了。火的花朵進行了無氧呼吸,
然后凝結成炭。我欲伸手成灰。水虎一定也有此意。
它的毛發燒焦前縮了回去,鋼筋一樣淬骨。
我聞到了有機質的自絕味道,摸黑進入舊馬燈,
又燃燒的翅翼,也有這樣的味道。有毒氣體,
從玻璃的縫隙緩緩釋放。白壁終有虛妄的灰蒙,
無附著之物。氤氳而起的樣子,像在逃難。
光和塵埃,都沿著直線行走。即便飛翔,
也不會轉角。白壁因此滿是暗象,有待我的命名。
舊馬燈懸掛于歸途,才稱其為恩光,而今夜,
它心有千仞而只取一壁,在前去殺虎的路上,
像一個指路的智者,成為我的同謀。
火的本性,使它追趕可能的每一個影子。火起,
則白壁黑虎,火滅,則黑壁無虎。水虎還在,
火星一經模仿嘯叫,就會復燃。我潛伏,
狀如抱守寂滅。舊馬燈打起燃油的點滴,
火的狀態堪憂,需要輸液。需要我將旋轉按鈕,
向右轉動。我從不將這個動作做到極致。
火焰被人為放大是危險的,但是玻璃仍能罩住它。
這是一塊被模具化的玻璃,圈占火的多余部分。
水虎在左,微弱的一滴穿過火與水的邊界,
玻璃應聲碎了一孔,我也聽見微光噗嗤一聲,
如念頭一瞬間蒸發,如我與未來的聯線斷了一條。
水來借光了;水來入火了;水找到了與火交媾的疤痕。
水有幽微的使命,火便為其留足隧道。
我習慣于物質的排斥,我震驚于死敵的吸附,
和穿越。舊馬燈就在恩仇序列的中間,
分開,照亮。恩我,仇我。白壁經卷一般深睡眠,
有一些夢境實現了卷曲。我借此翻閱大水,
一面一面地,深入波浪的禁地,和字符的肇始,
任何一個光源外部,都有悔恨的絲綢,
讓經,從緯里抽出;泄漏的,是罩不住的。
任何一部燃燒史,都有通透的避世,
讓榫,從卯里抽出。我像自我手術者,
用以青壯之心鑿白壁。我春光乍泄,誦木。
3.木劍
誦木如誦劍。得用滑膩的山茶木,以尖銳的指向,
向自己的執念之路,進箴言。
每一片木花如雪,會自動蜷縮,似從有形空域脫身,
用以對抗平鋪直敘的壁面。拙者把玩其節疤,
便是把玩凹凸有致的骨節,以對應澀滯的境遇;
少年把玩其筆直的部分,光潔而又溫潤的手感,
與幻湖邊的水虎膚質類似。我已漸漸體悟殺伐,
便是在少女的木質上祛除多余的旋轉痕跡,螺旋一般的,
纏繞而上的嵌入式的痕跡,藤蔓已枯,
沒有什么再能將殺虎之劍挽留在原木之中了。
去邊料如削盆骨,取劍花如在木中鑿出古老的火星,
制劍過程忘卻未來的攻擊,虎漸漸隱匿,
血腥前醉心于藝術,死亡真是緩慢精細的打磨,
少年畏懼虎,便是畏懼遼闊的消逝。存在,
作為一股強大的迎候的力量,在生死臨界,
等著一件藝術品插進喉嚨。存在便等同于虛無。
存在便與虎同體,與水構成無界,與火同歸于燼。
其時我已經開始用漢字制作巫蠱,用倒裝句,
制作回收光芒的劍鞘,用剪切的牛尾,懸掛于劍柄,
讓木頭獲得尊嚴般的修飾,一抖手腕,
便是玉米須一樣飄逸,水虎的周圍已是漫漶的光圈,
我用云朵蒙面,欲行刺客之事。
其時我已經展開身體的封面,如同展開墓碑,
恍惚之間水虎被霧氣包圍,我的少年之劍也懸上白壁,
神秘的成長,貫通不惑之年,繼而超越,
向白壁的未知空間而去。我已經學會了呼嘯,
但是沒有聲音,無人能聽見這靈魂里的打擊樂。
沉悶意味著我在血管里奔襲,木劍沉默,意味著:
一種姿勢可以令我致命。一成不變地有限生命,
多么像是可笑的永恒。我還那么相信水虎會先死。
木劍對白壁的占據長不盈尺,角度呈銳角傾斜,
破壞了白壁的方正,而又產生奇妙的平衡。
白壁因此法度森嚴,正式宣告從火里煉出了鋒芒。
水虎的深蹲似乎更深了些,有一些水,
將光拾起,反照朦朧虎眼。它微閉,另一些光斑,
在它的黑毛上靜靜地找到聚火焦點。
少年執舊馬燈,穿過鬼靈之水,手中木劍,
已然從蒼山抽出,從大茫然里抽出,
我在白壁上沿著無序的水紋行走,越過中年之謎,
再沿著漆紋行走,穿過青年之亂,接著,
沿木紋行走,滑過少年之懵懂,不停,
沿掌紋行走,撫過兒童之局促。我一生修煉,
只為御劍飛行。白壁在深夜發出劍鳴,
如歡愛的沉吟。我知道它在誦唱劍訣。
我附件一般心有旁騖,再次枯坐,誦土。
4.泥弓
誦土如誦弓。如誦彎曲。拼命的弧度是經火炙烤,
無名木是宿命木,它修長,
有山間美男的前半生。可它是大地的奴隸,
只配為泥成弓。它的后半生被細鐵絲套牢。
不得再以身段示人。配件的身份,幫兇的角色,
這便是徹底屈服。它不再向天穹抬頭,
而是經年累月,被父親之手掌握,
不斷地消磨意志,將壘土之泥,從模具箱上削去。
其時我尚年幼,不足以自己造出土磚,
不足以建出白壁的前世,我只會用鋼鐵的細線勾勒,
將柔軟的深田黑泥,劃出光潔的面子。
我匍匐,用盡身體的極致推拿,為磚塊植皮,
一直將泥工置于父親的上限。迅捷的動作,
從十歲開始就熟練掌握。我要殺水虎,
那時候我不自知,冥冥之中的絕招,練成
左手木劍,右手鐵線,這必殺技只需要兩下。
一塊土墻的后世,來到城市中央,
便成為白壁。泥弓也如影隨形,
作為木劍之側的附件,懸掛在我伸手可彈奏的高度。
夜未央,弦樂起,我撥動泥弓便是整個大地在抖動,
發出的聲音竟然如同父親的嘆息。
此時如再起殺虎之心,鐵絲就會嗚咽。
三十年來,佳木已像老銅,堅硬而又光滑,
沉實而又無害。可我知道它的真理,
就是替別人抹脖子。發出醒世之音,它又是和音歌手,
總在尋找萬物的空隙,和大地的致命軟處。
我得帶著它逆行,回到我詩句的賓語部分,
跟著木劍,折返至火光的燃點,
倒逼至大湖,如同溯流到我詩歌的言外之意,
劍光明晃,泥弓的應和是心理場,是潛意識,
在攻擊性的文字中,它身份特殊,
只能是虛詞,抑或是隱形的氣。
它不是詩歌的眼睛,不負責看見水虎的絕望,
是我秘而不宣的莫測感。或者,
它就是節奏。但是我殺虎,離開這個節奏,
無法完成。我連綴起來的字跡,依靠這個節奏,
改變我以及水虎的內心。我明顯聽到獸中之王
呼吸更緩慢了,它因為信仰藝術而放松了警惕。
我萬事俱備,只欠祝福。是的,我要誦銀。
5.銀褂
誦銀如誦誕辰。它在子宮之外,在襁褓之外,
于我嬰兒的恩賜,裹住我,
銀鈴鐺在褂子上幸福地碰撞,那聲音只能是庇佑。
之前,祖母用它庇佑嬰兒時的父親,
現在,母親用它庇佑我。
我明白銀子深刻的謙遜、堅韌和忠誠。
銀匠能為我一生打造的合身感,數十年前,
父輩就已經體驗到了。銀匠甚至還能為神靈定做
合適的外衣,銀子配合月光的唱詞,
在每一個凌晨都像是為我的故鄉送來新生,
大地殘忍,總有缺憾如棄嬰;大地悲憫,
總有善念如銀器,為悲傷的人間修補缺憾。
它永恒的光流失,絕不為了浪費,
它短暫的整容和變形,絕不為了幻城的手工藝。
我因此得到了祖傳的匠心,鈴鐺形,
薄皮,不厚重,不向笨拙的農人炫技,
它從我零歲起,就深入我的肌膚,我與銀子互相溫暖
互相磨礪,它是我金屬中的兄弟,
是我的母親,另一個兒子。我的面相和它是異姓,
我的內向和它是孿生。我終于,拋棄了它,
為此銀子不發聲數十年。至于今,我在烏江之濱,
覓得一白壁,適合懸掛懷舊之物。適合感傷。
也適合驅動文字的兵卒圍剿未來的攔路虎。
它移居白壁,便是深入我的羈縻之城,
我畫地為牢,白壁其中,銀子因為危局而報警。
我開窗,有江風徐來,水虎波瀾不驚,
我再面壁二十年,大寧靜,如誦亡靈。
繼而老朽,穿銀褂,赤裸手臂,
穿透詩歌的通靈處,轉入幽微秘徑,
步行于長長的暗廊,每一處嘀嗒的提示,
都是我的詞語在指向下一步。陽面上,
我在向水虎宣戰,劍指,弓藏,燈火遍布無人間,
水虎臥波如沉船,有看不見的下墜。
我繼續在白壁的陰面疾行,詩神身居地下,
先布下迷宮,我找到的每一枚透明的字符,
都是精準有效的,才能從題材和修辭的亂象中,
干凈利索出來。我終于在銀子那里學會了自證光明,
在泥弓那里學會了深藏悲涼,在木劍那里,
學會了尋找刺點,一招斃命。
當然,我還向燈火,學會了埋葬這門讀心術。
我從分別從陰陽兩面出來,挑起漩渦,大湖旋轉
水虎已經消失,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