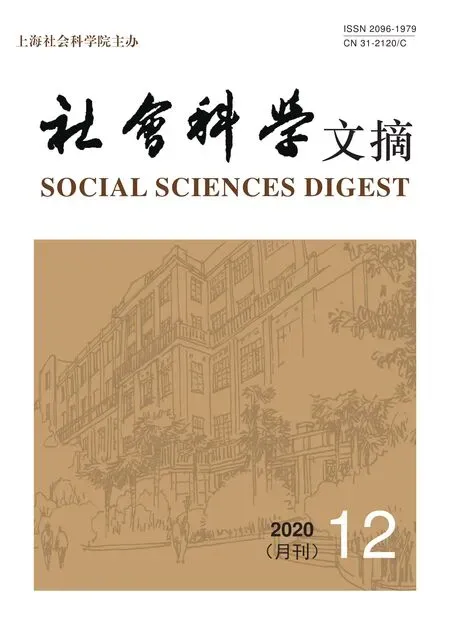對抗還是讓步?
——大國崛起進程中的鷹鴿策略取舍邏輯
文/楊原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崛起國在面對來自霸權國的遏制和打壓時,什么條件下會傾向于選擇對抗性(鷹)策略,什么條件下傾向于選擇讓步性(鴿)策略?
(一)理論層面的“對抗—讓步”兩難
國家如何在對抗性策略和讓步性策略之間作出選擇,涉及國際關系理論中威懾(deterrence)和螺旋(spiral)兩種模型的經典爭論。威懾模型認為,強硬立場和有力的威脅有助于展示捍衛自己利益的決心,從而防止沖突的發生;讓步和妥協性策略則會釋放軟弱信號,招致對方更多的挑戰。螺旋模型則針鋒相對地認為,讓步能釋放善意從而避免或緩解安全困境,強硬策略則會塑造和強化對方對自己的敵對認知,從而引發沖突螺旋,導致沖突升級。對抗和讓步策略的優缺點恰好互補,造成了這兩類策略在實踐中的取舍兩難。
在復雜的大國政治中,保持有效的威懾非常重要,為此需要讓潛在對手相信其破壞現狀的行為一定會對其自身帶來巨大損失。但同時,通過自我克制、主動示善等方式增進互信、避免不必要的沖突和沖突升級同樣非常重要。在霸權國的戰略壓力下,崛起國的策略選擇不僅直接關系自身利益,而且會極大地影響兩個大國的互動進程和體系安全狀態,這意味著從“對抗—讓步”視角研究崛起國行為規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政策層面的“對抗—讓步”兩難
冷戰結束后中國長期堅持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表現出明顯的現狀偏好。但是,隨著美國戰略壓力的不斷加大,中國戰略界開始出現對既有外交戰略的反思。一些學者指出,過分低調和示善,有可能限制中國應有的國家利益拓展空間,使中國在與美國的“討價還價”過程中陷入被動,誘發美國更大膽的挑戰。2018年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以來,中國仍然堅持了以斗爭求合作的總體方針,對美國提出的平衡貿易逆差、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訴求總體持合作立場。這些政策在戰略界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爭論。在學者們討論合作性政策是否對中國有利時,另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也隨之浮現:如果中國的對美政策增加“強硬”和“對抗”的比重,是否會強化兩國的對立情緒,導致沖突螺旋,甚至由此引發一場新冷戰?現在的中國顯然正處在一個戰略取舍的十字路口,面對美國不斷升級的戰略打壓,究竟是選擇強硬反擊還是緩和退讓,正日益成為中國對美戰略的焦點問題。
崛起國鷹鴿策略的取舍邏輯
(一)大國競爭的動因問題
受以新現實主義為代表的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和美國對外政策話語的影響,許多研究都認為安全是大國對外行為的最主要動機,引發大國間沖突的最主要機制是安全困境。如果大國的目標函數真的只是確保自身安全,沖突真的只是源于無政府狀態下的恐懼和錯誤知覺,那么螺旋模型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強硬反擊和對抗會損害自身利益(安全),適當的讓步和安撫有助于緩和和規避沖突。
但問題是,安全困境并不是導致國家間軍事和戰略競爭的唯一機制,真實的利益沖突同樣會引發類似的進程和結果。在與霸權國的互動中,崛起國的策略選擇是否符合(遵循)螺旋模型的預期(建議),取決于雙方的戰略互動是否真的受安全困境機制的驅動。根據現有理論,安全困境的存在至少要具備以下兩個條件中的一個:互動雙方的動機(motive)都只是確保自身安全而不是尋求增量利益;互動雙方的意圖(intention)都不包括損害或削減對方的利益。遺憾的是,在崛起國和霸權國的戰略互動中,這兩個條件都很難滿足。
首先,大國間戰略競爭的主要動機是榮譽和地位(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狹義意義上的權力),而不是安全。近年來,國際關系學界逐漸意識到將國家動機純粹簡化為追求安全的錯誤,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地位動機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指出以追求地位為主要動機的位置競爭(positional rivalry)是大國戰略競爭的主要類型。在位置競爭下,崛起國和霸權國的沖突源于真實的利益沖突而不是無政府狀態下的恐懼。霸權國會擔心崛起國的崛起導致自己的地位下降,由此產生的地位焦慮會促使霸權國阻撓崛起國地位的提升,甚至即使崛起國主動進行戰略收縮也難以弱化霸權國的威脅認知。
其次,大國在戰略競爭中對彼此很難完全保持善意。崛起國與霸權國的競爭通常由實力對比變化而引發,隨著實力的轉移,霸權國會越來越難以相信崛起國的克制承諾,日益明顯的相對衰落前景會逐漸強化前者對后者發動預防性進攻的意圖。近期的研究甚至顯示,即使放松“國家知道并能預見權力轉移”這個假定,權力轉移背景下承諾問題依然存在并且依然可能引發戰爭。而對崛起國而言,發動沖突和戰爭能夠起到迫使其他國家承認其地位的效果,甚至無關其結果是勝是敗。
可見,大國戰略互動通常都不構成安全困境。正因如此,美蘇冷戰從整體上看并不屬于安全困境,而更適合被視為是一種大國間的持久性競爭(enduring rivalry)。同時這也能解釋為什么多數實證研究都不支持螺旋模型的假設:該模型的理論前提在真實世界中很難完全滿足。厘清大國競爭的動因問題,為我們準確揭示大國互動中崛起國一方“對抗—讓步”策略的取舍邏輯掃清了障礙。
(二)消耗戰博弈下崛起國的決策邏輯
相比較于由安全動機驅動的安全困境模型,有地位動機驅動的大國競爭更適宜用“消耗戰”博弈加以刻畫。在消耗戰博弈下,博弈雙方為爭奪某個利益而展開競爭,當其中一方選擇退出時,另一方贏得該利益;在雙方都未選擇退出時,雙方每堅持一輪都須支付相應的成本。在這個限定下,對每個參與者來說,對方退出的時間越早,己方收益越大;對方下一輪退出時己方的收益,大于己方在這一輪退出時己方的收益。當兩個大國投入資源爭奪地位、榮譽和權力,且雙方均難以在某單次戰爭中取得對對方的決定性勝利時,雙方的競爭與消耗戰博弈的上述兩個特征相吻合:雙方都希望對方先退出競爭,并且為了迫使對方先退出,雙方都愿意比對方堅持更長的時間。現在的問題是,什么因素左右著這場“消耗戰”的勝負,進而影響著博弈參與者的決策?
1.物質資源(實力)對比
競爭雙方可支配物質資源的總量對比從根本上決定了消耗戰博弈的最終結局:誰的資源總量更大,誰就能堅持更長的時間。這意味著,在完全信息情況下,物質資源總量較多的一方在第一輪選擇爭奪,較少一方在第一輪選擇退出,是該博弈的純策略納什均衡。不過,大國物質資源的對比不是靜止不變的,大國一方面會因競爭而消耗資源,另一方面又會因經濟發展而創造資源。如果經濟發展創造資源的速度超過了自身因競爭而消耗資源的速度,那么國家的可支配資源總量仍然會隨時間增加。顯然,那些物質資源“凈增速”(經濟發展創造資源速度減資源消耗速度)較低的大國,將最終因相對物質資源較少而敗下陣來。因此,一方面,處于權力轉移過程中的大國會關注各自實力隨時間的相對變化趨勢,另一方面,相比較于軍事實力,大國特別是守成大國會更加關注經濟發展潛力。
從崛起國的定義可以看出其物質實力增速快于霸權國,這種相對有利的實力變化趨勢決定了崛起國在“對抗(強硬)—讓步(溫和)”的政策光譜中存在偏好后者的固有傾向。這是因為,首先,時間在崛起國一邊,相比較于現在,崛起國在未來與霸權國交戰或談判的處境將更為有利,因此,崛起國有動機推遲沖突;其次,避免沖突有助于保持和促進崛起國的實力增長趨勢,如果過早選擇強硬和對抗策略,則不僅會喪失原有的積累實力的機會,而且會招致其他國家的制衡,從而額外消耗自己的發展潛力;最后,根據前景理論,實力崛起的過程處于收益區間,在該區間內行為體會更傾向于規避風險。因此,相比較于地位下降所引發的地位焦慮(status anxiety),地位上升速度低于實力增長速度所引發的地位不一致(status inconsistency)導致國家采取冒險舉動的可能性更低。
也正因如此,越來越多的批評者質疑經典權力轉移理論關于崛起國有修正主義傾向的理論預設,畢竟崛起國冒險用一種未經檢驗的新秩序取代一種正在促使其崛起的現有秩序,還不惜為推翻現有秩序、建立和維持新秩序支付巨大的成本,這樣的設定是令人費解的。正如戴爾·科普蘭(Dale C.Copeland)所說,“只要冷靜對峙下去有利于本國的發展,就沒有理由打破現有的格局”。從這個意義上講,崛起國的“修正主義”主要體現在改變現有物質實力對比而不是現有秩序的規則和制度上。具體到中國這個崛起國,隨著實力的增長,中國在處理領土爭端時使用武力的意愿在下降而不是上升。
總之,相對物質資源是消耗戰博弈的根本約束,崛起國的實力增長預期使其有意愿在較長時間內選擇較為克制的合作性政策。2018年美國為打壓中國經濟和科技發動貿易戰,但中國政府認為“中國經濟長期向好大勢沒有變”。基于這一判斷,中國在貿易戰中的應對總體保持了克制和合作的姿態。20世紀30年代,面對德國的不斷挑釁和擴張,英國政府認為通過大規模重整軍備,自己與德國的實力均衡能夠在30年代末得到恢復,因此決定在此之前對德綏靖以爭取更多的發展時間。
反過來,如果霸權國的打壓和遏制政策使崛起國的實力增長預期逆轉,則崛起國出于奪回自身物質實力發展主動權的理性考慮以及身處損失區間愿意承受風險的心理傾向,會轉而選擇強硬和抗爭性策略。一戰后日本工業結構所需的原材料和石油幾乎完全依賴進口,而美國和英國自1930年之后開始增加貿易限制,到1941年8月,美英等國切斷了對日所有石油貿易。對此日本決策者一致認為,除非恢復石油進口,否則經濟衰退將危及長期安全。為恢復貿易,日本天皇最終批準了全面戰爭計劃。
2.決心對比
相對物質實力并不是決定消耗戰博弈結果的唯一因素,因為現實世界中博弈雙方的資源總量以及各自愿意投入的資源總量等信息往往是不對稱的。在不完全信息情況下,誰能讓對方相信自己有能力和意愿消耗比對方更多的資源(堅持更多的輪次),亦即展示更大的決心(resolve),誰就能夠迫使對方首先退出競爭。這一點在核對抗中體現得最為明顯,而即使是常規軍事沖突中,決心與沖突結果也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從博弈模型來看,在不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消耗戰中,表現得更加強硬、更有決心的一方預期收益更高。
消耗戰博弈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參與者有動機證明和捍衛自己的決心。國家不僅僅關注自己行為的短期結果,還關心其長期影響。其他國家會觀察一國的行為并根據其既有行為所建立的聲譽作出相應的決策。當一國的決心遭到對手的質疑和挑戰時,前者必須要考慮如果自己在當下作出讓步會對自己決心的聲譽(reputation of resolve)造成何種影響,進而對自己在未來博弈中的處境產生何種影響。實證研究顯示,發出威脅的一方如果在過去的強制性外交中作出過讓步,則當前其威脅的目標方作出讓步的可能性更低;過去退縮過的國家更有可能在未來遭到挑戰。
由于一國過往行為所建立起的決心的聲譽能夠增加自己在未來博弈中討價還價的籌碼,聲譽越高越有可能迫使對手在未來輪次首先退出博弈,因此捍衛決心的聲譽必然成為大國競爭中影響大國決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個體預期未來博弈的輪次越多,聲譽對個體的重要性越大。對自身決心的聲譽的關切會直接影響大國在“對抗(強硬)—讓步(溫和)”政策光譜中的選擇。實證研究顯示,決策者越重視他國對本國決心的看法,就越愿意將爭端升級而不是讓步。向對手證明自己的決心,是國家發動軍事沖突的重要動機。
1995年5月,美國宣布允許中國臺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訪美。中國決策層對美國此舉意圖的判斷是“測試一下中方在臺灣問題上的底線”,看中國是否會“吞下李登輝訪美苦果”。為打消美方幻想、展示捍衛本國主權的決心,長期堅持韜光養晦戰略的中國政府迅速作出決定,采取了包括開展連續9個月大規模臺海軍事演習、召回駐美大使、暫停兩國副部長級以上高層訪問等一系列強硬反擊措施。根據最近的一項研究,建立和捍衛自己決心的聲譽同樣是近期中國在南海地區采取強制政策的重要考量。
3.理論假設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將崛起國應對霸權國挑戰時的決策邏輯總結為三個假設。假設1:如果霸權國挑戰的主要目標是抑制崛起國物質實力(主要是經濟實力)的發展潛力,但這種挑戰和遏制并未從方向上逆轉崛起國對自己未來實力發展前景的原有預期,則崛起國的政策偏好是規避風險,傾向于選擇讓步和合作性政策。假設2:如果霸權國抑制崛起國物質實力增長的行為逆轉了崛起國對自身發展前景的預期,由預期收益轉變為預期損失,則崛起國的偏好是接受風險,傾向于采取強硬和對抗性政策。假設3:如果霸權國試圖試探和挑戰崛起國捍衛自身利益的決心,使崛起國感到如果在當前作出讓步,則不僅當前自己須付出重大代價,而且未來對方很可能會提出更過分的要求,那么崛起國會傾向于接受風險,選擇強硬和對抗性政策。
研究發現與政策啟示
解決“對抗—讓步”兩難問題的關鍵是明確互動雙方的動機和首要目標。如果雙方動機均為確保自身安全,首要目標都是避免沖突和維持合作本身,那么讓步(合作)性策略顯然更有助于實現這類目標,也更易被國家所采用。但在崛起國和霸權國的戰略互動中,兩個大國都絕難將自己的目標僅僅限定在維持本國(生存)安全上,而往往均將相對地位和影響力作為自己的主要戰略目標。在這一目標函數下,面對霸權國的打壓和遏制,崛起國在“對抗—讓步”策略光譜中的偏好將受到可支配物質實力對比、決心對比以及實力變化趨勢三個因素的影響。如果霸權國的遏制沒有逆轉崛起國對自己未來物質實力發展前景的原有樂觀預期,則崛起國傾向于選擇讓步和合作性政策;如果霸權國的遏制逆轉了上述預期,或者霸權國挑戰了崛起國捍衛自身關鍵利益的決心,則崛起國傾向于選擇強硬和對抗性政策。
自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尚未改變中國政府關于“中國經濟長期向好大勢沒有變”的判斷,因此截至目前中國對美外交總體仍保持克制和合作。根據本文理論,如果未來美國聯合其他國家加速與中國經濟脫鉤,強化對中國的科技封鎖,并由此影響到中國在21世紀中葉實現民族復興的自我預期,或者美國在臺灣、南海等事關中國崛起的重大問題上嚴重挑戰中國的決心,中國外交的戰略取向將被迫向對抗(強硬)端傾斜,如此則中美兩國在短期內的對抗乃至敵對局面將很難避免,世界被重新割裂為兩大對立陣營的冷戰風險亦將顯著上升。在當前對華強硬已成美國兩黨最大共識的情況下,上述暗淡前景出現的可能性正在迅速上升。中國在選擇對抗性戰略之后如何盡可能減少對抗對自身國力增長的負面影響,將是中國能否贏得這場“消耗戰”的下一個關鍵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