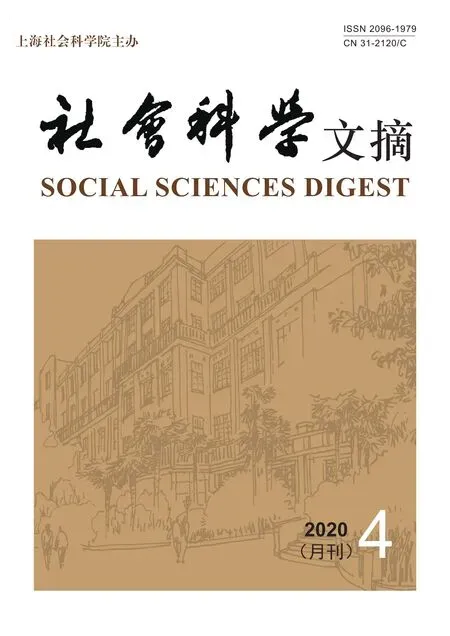社會學(xué)的理論危機與齊美爾的方法論基礎(chǔ)
文/王赟
自然科學(xué)式的圖景劃分往往依賴生物學(xué)在近代廣為采用的屬加種差邏輯。
社會學(xué)也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但大多數(shù)時候表現(xiàn)為代價而非成就。在社會學(xué)內(nèi)部出現(xiàn)了兩種具有明顯問題的研究傾向。第一種將社會看作社會科學(xué)之總和的地位,其他社會科學(xué)分支學(xué)科只是社會學(xué)的子學(xué)科。
第二種傾向首先將其他較易確定的對象交給諸如經(jīng)濟學(xué)、法學(xué)等學(xué)科,然后將“剩下的”稱為社會學(xué)。社會成了現(xiàn)代人之規(guī)范化生存諸范疇的剩余;而社會學(xué)則成了現(xiàn)代人對其規(guī)范化生存諸范疇之剩余的規(guī)范化認(rèn)識。
研究對象問題導(dǎo)致了“社會學(xué)的理論危機”。事實上,從社會學(xué)的古典時期開始,齊美爾對這個話題的思考就非常重要:限定了社會學(xué)的是對象和方法的聯(lián)系。本文試圖通過對對象、方式和心理設(shè)置三個方面及其相互聯(lián)系來分析齊美爾方法論的基本設(shè)置。正是通過這三個因素及其相互間的聯(lián)系,齊美爾將“社會化過程之形式”確定為社會學(xué)的獨特對象;形式則同時意味著經(jīng)驗的重要性和人際層面的相互-行動的必要性。反過來,社會學(xué)也因此同時得以確立它的科學(xué)性和學(xué)科邊界,來走出自身的理論危機。
對象、方法和心理因素設(shè)置
首先,齊美爾揭示了學(xué)科和對象間的不對稱。從史學(xué)或美學(xué)目的出發(fā),人們可以研究一幅畫的價值。在此情況下,作品的史學(xué)或美學(xué)意義是我們的研究對象。但同時,一位自然科學(xué)家同樣可以以別樣的科學(xué)目的研究這幅畫。如畫的顏色會具有什么獨特化學(xué)構(gòu)成等等。對于社會學(xué)來說,從對象角度出發(fā)并不能得出關(guān)于學(xué)科門類的專屬分類。
由于根本不存在不涉及經(jīng)濟、法律、宗教、歷史等因素的社會,社會學(xué)所考察的現(xiàn)象或現(xiàn)實,同時就是經(jīng)濟學(xué)、法學(xué)、宗教科學(xué)或史學(xué)所考察的那些現(xiàn)象和現(xiàn)實。
在方法論角度上,他宣稱,整體論觀念下的社會無法在功能主義意涵之外提供社會存在的意義;而在方法論缺陷之外,社會無法成為真正外在于人及其行動的整體,任何被整體論評價為“社會”的因素同時也必然是關(guān)于個體人的因素。
因此,對象和方法的有機聯(lián)系才能確定一個自成的社會學(xué)。它使社會觀念與個體或自然得以互相區(qū)分,并在科學(xué)分類中給出社會學(xué)真正的角色。
社會學(xué)所觀察之物因此處在兩個層次上。首先,相較于其他科學(xué),社會學(xué)所擁有的就是日常的那些內(nèi)容;它建立在對社會生活的日常和內(nèi)生因素的把握之上。其次,社會學(xué)的建立,在于用獨特的方法論,使學(xué)科在認(rèn)識層面與日常生活中的知識或其他社會科學(xué)的知識做出區(qū)別。
對象問題的核心因此實際上就是方法論問題,必須建立一種合適的視角來思考具有如下特征的社會:首先,社會并不真正與組成它的個體相割裂;其次,社會也從來不是零散分布的若干單位或個體的簡單數(shù)量之和。構(gòu)建了完整社會單位的,是處于相互和有機過程中的個體、他們的沖動和目標(biāo)。齊美爾眼中的社會從經(jīng)驗意義出發(fā),其中“完整單位”的提法已經(jīng)潛在指向了“交互”意涵。社會的完整單位的提法潛在意味著組成部分間的交互性。
人的心理來源、沖動、旨趣和其他心理活動在齊美爾筆下是最根本的行動來源。一方面,它們是社會生活中人之存在的最根本單位;另一方面,它們通過對這些存在的表現(xiàn)進行觀察而進入社會學(xué)。這些實踐中可被觀察的心理因素構(gòu)成了社會和社會學(xué)最基本的內(nèi)容。
必須同時強調(diào),構(gòu)成社會的這些心理因素也還并不是社會學(xué)直接和立刻的對象。這些心理因素僅在同步整合/對立的相互聯(lián)系上才進入社會學(xué)研究。心理因素如果要構(gòu)成通過經(jīng)驗可感知和觀察的社會,就必須籍由一個必不可少的過程:社會化過程。
作為純粹社會學(xué)對象的社會化過程之形式
既出于個人本能也出于社會需求,人具有與他人交往的意愿和能力。那么,人就以理性和意愿的雙重手段符合了先天提供的交往可能性,并因此向個體提供了無盡的共同生活的能力和可能。齊美爾將社會化過程之形式(以下簡稱形式)看成個體和社會整體之間的媒介。形式還是某項具體實踐和關(guān)于它的抽象認(rèn)識之間的媒介。
齊美爾的形式描述了一種人的獨特范疇或者關(guān)于這個獨特范疇的觀念:通過形式,不同的個體在社會現(xiàn)象中相互-行動。一方面,個體并非某個整體社會的功能組成部分,因此相互-行動區(qū)別于共同行動,前者更為強調(diào)個體以各自意愿為出發(fā)點,并在“對于自我”和“對于他人”兩個維度提供行動效果。另一方面,相互-行動強調(diào)了動態(tài)的社會化過程。人通過互動不停地對其所處的社會聯(lián)系進行調(diào)節(jié),形成了永恒的動態(tài)過程。其結(jié)果是,形式因此要么是社會聯(lián)系本身,要么是個體處于其中的社會聯(lián)系所發(fā)生的情境。歸功于這些聯(lián)系和情境,個體性不是個體的孤立狀態(tài),而是個體在社會場景中的聯(lián)系狀態(tài)。由于形式既是本體性的社會機制,又是認(rèn)識對其的正確把握,因此,它提供了克服純粹主體性而通向“相對客觀的”和“相對群體的”的可能性。
齊美爾的形式觀念因此指出了其方法論首要原則:人之經(jīng)驗是社會和社會學(xué)的來源。經(jīng)驗并不意味著純粹個體維度的應(yīng)激以及應(yīng)激在認(rèn)知中的儲備,而是指向人的社會本能:人以共情或說共同經(jīng)歷的方式來理解他人。在實踐中,個體那種并列擺放的潛在狀態(tài)就通過形式被轉(zhuǎn)化成相互關(guān)系上的向量。行動者之間因此總存在狀態(tài)上的共生性和機制上的交互性。
基于實踐,形式過程使復(fù)數(shù)意義的個體得以結(jié)成互動聯(lián)系,社會從中生成。社會學(xué)因此通過對形式的研究來建立對社會現(xiàn)象和人的理解。由于形式通過旨趣等心理因素對行動中的個體和他們的共同活動進行了重組和聯(lián)系,社會學(xué)并不陷入“局限于對心理因素進行主觀描述”的心理主義和由純粹主觀性帶來的唯名論陷阱。通過形式,社會學(xué)完成的是從主體認(rèn)識達到存在之客觀呈現(xiàn)的過程。
此外,對于社會學(xué),必須通過對這個過程的研究來把握社會本身。對社會化過程的功能研究有助于理解其在社會中的運行機制,但這并不能否認(rèn)如下事實:社會化過程在個體及他們之間是自生的。功能主義只是將社會化這個自生和自為的角色變成了一個純粹的認(rèn)識工具,用來滿足某個外在并被假設(shè)為高于人的原因,這樣的原因根本就不存在。
齊美爾社會學(xué)的獨特對象就是形式本身。形式意味著實踐和研究的聯(lián)系,以及由實踐中的形式所凝聚了的那些內(nèi)容與社會表現(xiàn)出的整體模態(tài)和趨勢之間的聯(lián)系。
形式與普遍法則不具可比性。普遍法則意味著公式或模式與由它所揭示的事實間的普遍、先驗、排他的關(guān)系。形式并不是某種力或某種實存,而更多的是一種有效聯(lián)系了人的關(guān)系和方式。不對行動者之間的關(guān)系、環(huán)境和他們之間的聯(lián)系網(wǎng)絡(luò)進行把握,就不能把握形式。此外,將形式當(dāng)作一個認(rèn)識方式,又暗指了一種獨特的社會學(xué)方法。
齊美爾對實證主義的反對,還在于后者與功能主義思想的聯(lián)系。人類社會中的個體以某種方式組織起來,這確實作為效果產(chǎn)生了某些功能。但首先,個體行動的目的是每個個體自身的生活,而并非功能性的生存或社會維持。個體只間接地向社會提供其行動和與他人互動的影響;功能則只是他的行動和互動在后天意義上的效果。
社會學(xué)作為專門學(xué)科的獨特性寓于對象到方法的聯(lián)結(jié)上。雖然與其他門類共享來自于日常的直接內(nèi)容,社會學(xué)的對象只能是社會化過程之形式,因為對象意味著直接內(nèi)容和社會學(xué)獨特的形式方法之間的內(nèi)部聯(lián)系。其最大特征因此在于與其他社會科學(xué)門類相比明顯具有差異的對待直接內(nèi)容的方法。
如此,才能把握齊美爾關(guān)于社會學(xué)的“社會科學(xué)之幾何學(xué)”比喻。形式并不致力于普遍意義上的法則,形式本身就是一個正在演進社會中的過程。社會學(xué)致力于理解這個過程及其中因素的運作。至于個體,由于他直接關(guān)涉于生活中的多種形式,他本人也通過對這些形式的研究來部分得到揭示。對社會個體的理解只能通過形式研究來完成,形式聯(lián)系了外部世界和個體所具有的社會聯(lián)系。如此研究的重點在于最細(xì)致的和最根本的心理因素,因為正是這些因素在互動過程中反射回自身,在社會存在意義上的個體性之下塑造了心理存在意義上的個性。
作為形式驅(qū)動者的心理機制
齊美爾認(rèn)為,每一個形式背后都有一個支撐它的心理機制,一個處在更深層次的旨趣、動機、理由等。把握一個形式因此意味著同時在作為行動內(nèi)部沖動的心理機制上,和作為行動效果的人際互動上,把握個體的心理機制。所以,不考慮個體或個體間的心理機制就無法研究形式。形式又同時是個體間溝通和相遇的表現(xiàn)。個體同時具有獨立和交往的二重狀態(tài),這構(gòu)成了個體和他者間的關(guān)系,社會也得以可能。
必須避免將社會的構(gòu)建建立在對個體心理機制的排斥之上。如果主體性意味著個體在其行動中的特殊性,那么社會化及其形式則是主客體聯(lián)系的保證:社會的運行并非主體的直接產(chǎn)物,而是“伴隨主體”的過程。
齊美爾也非常強調(diào)他者的角色。社會聯(lián)系首先是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互助聯(lián)系本身。通過這些聯(lián)系才形成了生活世界。同樣,自我與他者之間的聯(lián)系處于人際這個維度,它使得客觀性可以基于主體性而得出。
社會和歷史因此就是社會化過程本身,通過這些過程,且歸功于相互聯(lián)系,個體成為個體“們”。
重提齊美爾在《社會如何可能》中指出的三大“先天形式”因此顯得非常必要。這些形式是社會這個本體存在的基礎(chǔ)。首先,人通過類型化的方式來了解其他個體。其次,人的生命/生活同時具有私密和公共意義。第三,社會一經(jīng)人的意識把握,就現(xiàn)象學(xué)地展開。第一形式意味著,人只能通過預(yù)先習(xí)得的認(rèn)識以類型化的方式形成預(yù)置模型,并在遇到新的對象時,由對象被主體把握了的相似性而將其納入相應(yīng)的已有認(rèn)識類型。“類型化”因此是認(rèn)識過程的普遍實踐(而非實證)邏輯。這種認(rèn)識的構(gòu)建方式意味著與經(jīng)驗相關(guān)的雙重運動。一方面,經(jīng)驗是人得以建立知識的唯一可能。另一方面,類型化內(nèi)在地要求類型、概念,和通過共同點而將一定數(shù)量的個體聯(lián)系在一起的形式。
第二形式意味著,通過無盡的創(chuàng)造過程,個體和社會同時成為可能:個體意味著社會性,就像社會同時意味著個體性一樣。社會作為個體和生活世界之間的橋梁因此對個體和外部世界同時具有歷史或社會意義。人通過在社會中接受知識和形成認(rèn)識而是其所是。傳統(tǒng)、習(xí)俗和信仰標(biāo)志了一個人的特征。但同時,人在“此刻”的社會生活又通過對行為及其中的心理因素的接收反過來生產(chǎn)著新的知識和認(rèn)識。這一過程又是對自我和社會進行重構(gòu)的過程。
第三形式意味著,個體在其相互行動中生成社會,社會也同時向組成它的個體提供社會角色來占據(jù)。“每個個體看起來都完美地整合到某個社會位置上”這種感受在日常生活隨處可被體會到,但這種所謂“完美”是現(xiàn)象而非某個法則給出的。
齊美爾因此特別反對通過某種自然科學(xué)式的規(guī)律來解釋社會。整體論觀念的主要問題就在于無法徹底如愿地在社會學(xué)分析中祛除個體心理因素:這是由個體和他們所組成的社會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所決定的。心理因素和情感沖動是社會構(gòu)建不可分離的因素。事實上,正是這些因素解釋了個體的社會性來源。這些因素也并不僅僅是可被闡釋的;它們的運行首先是社會的必要條件。應(yīng)該致力于展現(xiàn)作為存在的社會如何在一個動態(tài)過程中,通過形式同時聯(lián)系了個體和生活世界。
作為方法論基礎(chǔ)的形式與心理機制的重要性
社會學(xué)家的問題不僅僅是知曉社會如何構(gòu)建,還必須指出社會為何以及在何種狀況下是必不可少的。瓦蒂爾提出,用知識(savoir)視角取代舊有的功能主義的認(rèn)識(knowledge)視角是緊迫而必要的。認(rèn)識視角預(yù)設(shè)了行動者以包括他人在內(nèi)的行動對象為工具來實現(xiàn)其行動這一功能,而這并非人的社會狀態(tài):人的社會行動當(dāng)然包括某些策略和功能行為,但人在此之外首先是社會性地存在著的。兩個觀念的差距指向?qū)嵺`意圖。實踐中,人不僅接受外部社會和他人傳遞的信息并對他人做工具性的開發(fā),而是首先期許著和他人溝通交流,用以傳播信息、形成社群、維系交流,并在非目的性的意義上構(gòu)建了社會。
因此,社會學(xué)首先將注意力放在心理知識在社會化過程之形式的構(gòu)建過程中的狀態(tài),并將社會的構(gòu)成本身當(dāng)作目標(biāo)。齊美爾并不將社會學(xué)設(shè)置在心理學(xué)之上。他強調(diào)的是,一方面,社會的構(gòu)成處在個體、機構(gòu)化和整體社會的相互行動過程之上;另一方面,這個過程如果沒有作為催化劑的心理機制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
心理因素對兩個學(xué)科起到不同功能。心理學(xué)將眼光局限于個體層面,在個體心理運行機制中研究心理因素,致力于建立對心理狀態(tài)的內(nèi)生解釋。社會學(xué)則通過對心理因素的研究,在人際因而是形式層面,研究作為“對象的部分內(nèi)容”的心理因素。如果個體的理由和意志使其可以面向一個心理目的,社會學(xué)上,研究指向的則或多或少是另一個明確區(qū)別于自我心理構(gòu)建的目的:一種人際的心理目的。社會目的只能存在于社會化過程中,由于心理因素在社會內(nèi)容中體現(xiàn),且這些因素首先被當(dāng)作“心理上的”,我們才可以在其中提取出“社會學(xué)上”的目的。
由此筆者認(rèn)為,兩個學(xué)科的區(qū)別既在功能上又在方法論上。一方面,雖然都包括心理因素,社會學(xué)卻是在人際層面考慮這些因素。如果心理學(xué)研究心理機制,社會學(xué)則利用這些心理機制建立社會學(xué)觀點。另一方面,社會學(xué)的形式方法面向的是社會性的意義或價值,而非返回到個體上的病理心理學(xué)取向。
此外,心理學(xué)和社會學(xué)僅在個體范疇也不具有完全對等的對象。一個社會現(xiàn)象并不能被單純理解為個體的心理機制及其結(jié)果,還同時包括了一些無意識因素及其影響。研究者必須意識到,1)復(fù)數(shù)意義上的個體心理機制塑造了社會聯(lián)系;2)社會聯(lián)系聯(lián)系了個體;以及3)這兩個層面間的永恒往復(fù)。
結(jié)論
將心理因素等同于主觀,進而等同于前科學(xué)或非科學(xué)的范式在今天越來越受到質(zhì)疑。客觀主義無法回答社會學(xué)在祛除方法后造成的對象混雜的局面和相應(yīng)的理論危機。與此同時,齊美爾的方法論基礎(chǔ)既強調(diào)了方式到對象的聯(lián)系,又強調(diào)對包括心理因素和心理機制在內(nèi)的所有因素的廣泛聯(lián)系。
作為一門學(xué)科,社會學(xué)對象的獨特性必須建立在與方法的聯(lián)結(jié)之上。社會學(xué)與其他社會科學(xué)分享來自于實踐的同樣內(nèi)容,卻要求考慮人際層面的互動及其影響。作為一門科學(xué),社會學(xué)強調(diào)人在個體和人際層面的行動、動機、效果,因而與經(jīng)驗質(zhì)料、心理因素保持親密聯(lián)系,卻由于“形式”這一內(nèi)在要求同時區(qū)別于心理學(xué)和自然科學(xué)式的實證主義或整體論社會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