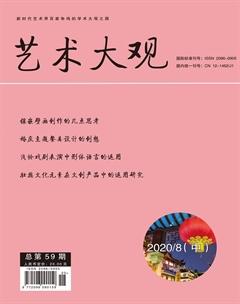文山州壯族傳統舞蹈道具的應用與語義表達
摘 要:文山州的壯族傳統舞蹈多采用道具配合表演,除了身體的語義表達外,其使用的道具也被賦予新的含義,二者聯系緊密有著深厚的表意內容。探索其道具在傳統舞蹈中的語義表達,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當地傳統舞蹈投射出的文化內涵,有助于多維度的思考當地傳統舞蹈的傳承與發展。
關鍵詞:壯族舞蹈;道具;應用;語義表達
中圖分類號:J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0905(2020)23-00-02
語義所表達的是語言的含義,它是語言學中的概念。舞蹈的語言主要是以身體為傳播媒介來表達的,除身體的舞蹈動作外,其相關使用到的道具、場景等都充當了舞蹈表達的重要語義。文山州作為云南壯族的聚居區域,有著壯族傳統舞蹈文化的典型性,對于文山州整個地區而言,當地傳統舞蹈中所使用到的道具都是這些傳統舞蹈活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這個民族的歷史文化、風俗習慣、生產生活等各個方面都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充分體現了文山州壯族傳統舞蹈地域性道具應用的語義表達特點。
一、“擬獸”類道具的運用及其語義
文山州壯族傳統舞蹈中有著許多的動物形態,這些動物形態既體現在舞蹈動作姿態上,也體現在服飾與道具上,它蘊含著當地壯族民眾對某些特定動物的情感寄托和崇拜。這類型的舞蹈通常會利用動物形態的道具,去模仿動物的神態和生活特性,然后以“擬人化”的動作為載體,再現了特定時期族群的動物信仰符號,強調了族群與動物的和諧共存關系。
(一)紙馬舞道具
紙馬舞道具的制作較為復雜,有著民間手工藝造型制作的藝術特征,具有民俗研究價值以及制作傳承的實用價值。在文山當地,壯族紙馬舞之所以可以獨樹一幟、趣味橫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紙馬道具在紙馬舞蹈當中的巧妙運用。常見的紙馬道具外觀以一匹活馬為原型由馬頭、馬頸、馬身、馬尾構成,然后用竹條編制,馬身中間鏤空,表演者把馬形道具由頭往下套在腰部位置,雙手提住兩邊馬身起固定作用,中間鏤空的位置剛好夠容納一個表演者。現如今的紙馬道具經過數百年的演變也融入了一些現代審美的元素,無論從外觀還是工藝制作的技術上都有了很大的變化,紙馬道具由最初稻草編織的草馬、白紙裱糊的紙馬,演變到現今色彩豐富、顏色鮮亮的布馬。根據《文山縣志》的記載,壯族的祖先曾隨白馬將軍出征,后因迷路滯留本地,后世族人為紀念白馬將軍,故扎紙馬道具跳紙馬舞來緬懷將軍。也有當地老人口述:是為紀念一位名為王三姐的壯族民族英雄在戰爭危難中急中生智,巧扎紙馬道具智退敵軍,故這一習俗流傳至今。在當地紙馬舞屬于較高規格的喪葬祭祀舞蹈,帶有祭祀性質的語境,但現今喪葬祭祀的約束性功能已經消失,無論什么場合都可以表演,從道具的美化和表演功能的改變,可以看出紙馬舞動作和道具的語義表達是和時代多元文化的影響是分不開的。[1]
(二)牛頭舞道具
在文山壯族地區動物圖騰眾多,崇拜結構多元,但對于牛的喜愛卻是比較突出的。壯族善種植水稻,牛與他們的生活勞作關系最為密切,是他們最得力的農耕助手,在長期牛與人的農耕生產生活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愛牛、護牛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在當地至今還流傳著諸多關于牛的故事,有著專屬于牛的節日和舞蹈。表演牛頭舞時牛頭儺面具是其必須使用的道具,該道具通常由風干的牛皮、竹條、布或者厚綿紙做成,表演時多為兩人協同完成,一個半直立著身體耍牛頭,另一個弓腰拱背飾牛背甩牛尾,有時也會由一個人獨立完成。道具的使用讓觀眾直觀性地看到牛的形象,再配合動作的傳神表演從而實現了道具由“物”至“意”的轉換與升華,有效增強動作的表現力,體現了壯族民眾對牛的熱愛、對收獲的期盼,對人畜興旺的訴求。[2]
二、戰爭類道具的運用及其語義
文山壯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從各氏族之間的相互戰爭、吞并、分裂,經歷了無數的氏族更替和民族變革,這樣漫長的民族戰爭史也形成了當地壯族尚武的民族氣節,至今其傳統舞蹈中也還保留著很多手持兵器類道具的戰爭性舞蹈,這類舞蹈通過戰爭類道具的使用,讓舞蹈更勇猛粗狂、氣勢磅礴。例如:棒棒燈舞蹈的道具使用。
在當地,棒棒燈的傳說故事多以降服妖魔(戰爭)為主,它所使用的一對花椒樹短棍,也是區別于壯族其他舞種最顯著的特征。表演時,兩短棍相互敲擊,聲音鏗鏘有力,在敲擊聲響的伴奏下踝關節、膝關節、臀、臂、腰,全身都有大幅度的彈性跳動,具有武術“短棍舞”“兵舞”的典型特征。棒棒燈短棍道具的使用,不僅突出了戰爭類道具的文化符號功能,更是凸顯了棒棒燈舞蹈動作的語匯表達,在表演中極大的突出了其舞蹈蘊含的團結、正義、無畏的英雄氣概,讓觀者振奮人心,舞者氣勢豪邁。
三、生產生活類道具的運用及其語義
生產與勞動、生活與用具是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標志,而生產生活中的用具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呈示出來的具物符號。大家常說,藝術是來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的,而用具是生產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分,這也說明了生產生活中的用具它與藝術的發展是有緊密聯系的。文山壯族依水而居,善耕勤勞,喜歡干凈,生產生活用具具有多樣性,實用性、適應性等特征,而聰明的當地壯族民眾利用這些用具特征巧妙的創造出了舞蹈動態語匯,于是就產生了手巾舞、草人舞等一些廣泛在當地流傳的生產生活道具型舞蹈。
手巾舞和草人舞通過使用手巾、犁、鋤頭、稻草衣等生產生活的用具,集中反映了這個民族的生產生活場景,謳歌了壯族人民勤勞、智慧的精神風貌。手巾舞和草人舞表演時雖有固定的流程,但動作多為簡單隨性、自然樸實,非常貼近他們日常生活中的動作特點,例如:播種撒谷、栽秧犁田、收割晾曬等,這些簡單的動作由于有了生產生活類的用具作為道具,從而升華成了藝術化生活的符號,讓表演者更多地創造出了身體的動作語匯序列,擴大了手巾舞和草人舞藝術維度的呈現,多視角地展現了當地壯族崇尚生活、崇尚自然的農耕情懷。
四、祭祀類道具的運用及其語義
文山壯族是滇越的后裔,多為信仰自己的原生宗教,相信萬物有靈,崇拜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銅鼓是他們溝通神靈的主要“法器”和“樂器”。壯族祭師與神靈溝通祭祀時必會敲鼓而舞,從而也產生了銅鼓舞,當舞蹈與祭祀有了親密關系,祭祀活動中所使用的道具“銅鼓”就具有某種隱性的指示性,是其“法器”也是銅鼓舞所使用的“道具”。
銅鼓舞在表演中使用具有祭祀特征的道具,不僅表現了當地壯族的民俗風情,也體現銅鼓文化的傳承,通過動作與銅鼓道具結合的舞蹈語言,指引人們看到銅鼓舞現象下的壯族宗教本質,那是對神的膜拜、對生命的贊頌,是壯族民族精神與力量的象征。
五、藝術作品中的道具運用及其語義
當地有著較多的壯族舞蹈藝術作品,這些藝術作品中也多為使用道具來刻畫人物內心世界、營造舞臺氣氛、增加舞臺色彩、深化作品主題,其每一個藝術作品后面都蘊藏著編舞者,對作品的精心編排和道具的巧妙運用。
(一)巧用“巾”類軟道具
這類型的道具在作品中的應用中較為普遍,它可以最大化的延展身體的表現空間及運動軌跡,在道具輔助性拉長的視覺沖擊下,充分地突出了肢體的動態之美。例如:文山州民族歌舞團創作的壯族舞蹈《手巾舞》編導把傳統舞蹈中的手巾加長加寬,手巾在舞者的手中通過拋、甩、抖如白云劃過天空一般形成了一道道弧線,擴大了肢體在舞臺中的占有空間,時而靜止時而動,形成了極富美感的畫面,暗喻了壯族平和、善良的民族性格。
(二)活用“木質” “皮質”“ 鐵質”類硬道具
文山州壯族傳統舞蹈的道具除了較為柔軟的“巾”類道具外,多為“木質”“皮質”和“ 鐵質”的道具,例如:紙馬舞的馬形道具,棒棒燈的花椒棍道具,牛頭舞的儺面道具、銅鼓舞的鼓道具等,這類道具多帶有地域性的典型色彩,在應用中多會改變它的形態與大小,只抽離它所蘊含的典型性符號內核進行再次物化的“表意”呈現,所以會對作品的表演風格產生較大的影響,使得表演的體態、律動、舞姿更加的豐富化。例如:文山市民族文化傳承展演中心編創的《紙馬瑤》,通過縮小紙馬道具,把套在腰上的道具調整為執在手中,極大地解放了肢體的可動性和可舞性,增強舞蹈作品表現的感染力,展現了壯族人民勇敢、樂觀的民族氣質。
六、結束語
舞蹈道具只是一個具象的物體,本次論述只是窺探了其在舞蹈中的一個點,它與這個民族背后的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但又不失個性。對于文山壯族而言,其傳統舞蹈道具在舞蹈表演中充當了相當一部分的語義,它不僅能直觀地體現了舞蹈本身的表達,同時也蘊含著這個民族內在的歷史沿革、文化內涵、風土人情等各方面的信息,是壯族文化的重要載體,凝聚著他們美好的情感寄托和高度的審美追求。
參考文獻:
[1]謝遲.湖北傳統舞蹈道具的語義研創[D].長江大學,2018.
[2]白云武.云南文山壯族傳統祭祀舞蹈調查研究[J].文山學院學報,2017,30(04):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