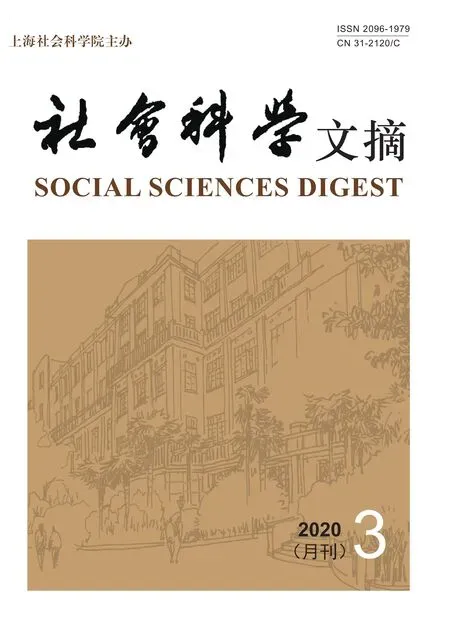鄉土社會與單位社會:基于成員權利的辨析
社會治理問題,與社會的性質及其變遷的判定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后者是社會學的重要主題之一。從“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分析,“鄉土社會”與“單位社會”基于“熟悉社會的本質”而建立起了聯系,兩者無疑有相同之處;不過,它們的不同之處也同樣明顯。本文提出從“個人與社會關系”這一社會學的元問題或基本問題出發,發掘“鄉土社會”與“單位社會”的這類不同。
辨析清楚這兩種社會的不同,有助于人們獲得一種明確的社會變遷感,也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今中國社會及其變遷的方向性問題。“鄉土社會”和“單位社會”是當今中國社會所以由來的兩個傳統,無論當今社會與之距離多遠(事實上并不太遠),在性質上差別有多大,作為社會變遷的前提,這兩個傳統的影響力仍是存在的。可以說,這兩種社會的辨析,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們理解40多年來中國社會的變化。
鄉土社會的“熟悉”和“陌生”
“熟悉社會”一詞可以追溯到費孝通先生。費孝通在“描述”鄉土社會的時候,用了“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這樣的說法,在這里,“‘熟悉’的社會”是一個描述性用詞,主要用來總括性地描述“傳統”“鄉土社會”的特征。在強調鄉土社會作為“‘熟悉’的社會”這一特征時,費孝通強調了鄉土社會中的鄉民對人和物兩個方面的“熟悉”:因為“生而與俱”,所以有了人際信任,信任進而成了規矩,對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就有了信用,人和人相處的基本方法(比如“孝”)也被提出;因為“熟悉”物,所以不需要抽象的普遍原則,而能把握住足資利用的各種“個別關聯”。除此之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費孝通強調了鄉民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賴以存在的重要基礎,或者說是鄉土社會之所以為“鄉土社會”的根本——“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生了根在一個小地方”。
將傳統鄉土社會描述為“‘熟悉’的社會”,當然是對的。說“鄉土社會里從熟悉得到信任”,并說這信任是規矩,亦屬真知灼見。但我們切不可由此就認為在“鄉土社會”只有“熟悉”因素、沒有“陌生”因素,總是能達成“信任”,而不存在“欺詐”。
事實上,在討論整個社會結構的格局時,針對中國傳統社會(不只是鄉下還包括城里)普遍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費孝通先生提出了“私的毛病”。在個人的“私的毛病”的背后,乃是一套對應的群己、人我界線的劃分方法,他稱為“自我主義”。由此形成的人和人的關系,最核心的是以“己”為中心的親屬關系和地緣關系。如此聯系而成的社會關系網絡或圈子,帶有“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的特性,費孝通稱為“差序格局”。“差序格局”(以及“自我主義”)具有相對性和伸縮能力,可外伸,亦可內縮。如此一來,公私也具有了相對性,“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內看也可以說是公的”。并且“富于伸縮的社會圈子會因中心勢力的變化而大小”。
需要強調的是,“社會圈子”不僅會因“內向”的“中心勢力的變化而大小”,也會因“外向”的人與物的“社會可熟悉程度”“而大小”。在“差序格局”相關的理論框架中,行動可能涉及的社會范圍內的人與物的“可熟悉程度”(其進一步界定,將在后文探討)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自變量。費孝通觀察到的“差序格局”,特別是其中“私的毛病”,正是因為中國傳統社會對其社會成員而言,乃是由近及遠逐步“陌生”或者說“可熟悉程度逐步降低”,“熟悉社會”與“陌生社會”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在邊界上就變得模糊了。
費孝通說傳統社會中的人“自我主義”,梁漱溟卻說他們“互以對方為重”,兩者一定程度上都是對的,只是需要加以澄清。對于鄉民來說,在自己所熟悉的鄉村社會之外還存在大規模的“陌生社會”,而傳統社會中的“‘熟悉’的社會”也往往都是鑲嵌在“陌生社會”之中的。
有鑒于此,社會生活中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極可能是兩種因素混合作用的結果;不能簡單地將其歸于要么是“熟悉社會”,要么是“陌生社會”的本質特征。也許我們更應該問:哪些重要的結構性因素會帶來該社會中人們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改變,進而在社會變遷的考察中更具基礎性意義?
“傳統社會”的沿襲與變革
正是因為傳統社會既包含著“熟悉”因素,又包含著“陌生”因素,所以在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過程中,一些“熟悉”因素,比如說某類“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也就會有所沿襲。比如,謝俊貴教授就認為不僅“中國早期的城鎮”,而且“單位社會”也應當是一種熟人社會。只是由于我國20世紀末正式開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原來束縛于計劃經濟體制之中的單位人(包括城市的單位人和農村的社員)開始走向了市場,“熟人社會”才發生了動搖。
無獨有偶,劉少杰教授在《中國市場交易秩序的社會基礎——兼評中國社會是陌生社會還是熟悉社會》一文中,描述中國社會的本質、判斷社會變遷時,對這樣的沿襲性有堅定的強調:
當第一閾值在波峰1,2之間時,若不進行特征點一致性補償,則特征點t2將會提前一個周期,在波峰5下降沿的過零點處,此時若要保證特征點一致則到達特征點時間應調整為t1;當第一閾值在波峰3,4之間時,若不進行特征點一致性補償,則特征點t2將會滯后一個周期,在波峰7下降沿的過零點處,此時若要保證特征點一致則到達特征點時間應調整為t3。綜上所述,到達特征點時間T應根據第一閾值所在位置選取為:
中國的熟悉社會并沒有發生質變,不僅農村社會仍然延續著傳統的社會結構和制度關系,而且城市社會也沒有真正實現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質變。利己中心、倫理本位、親情紐帶、圈子關系、輕視原則、崇尚權勢,誰能證明這些傳統社會或熟悉社會的本質特征在哪個社會層面上消失了?在我看來,中國社會的這些本質特征,不僅現在沒有消失,而且,再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也未必能夠消失。正是這些本質特征表現了中國社會的制度結構,具有超常穩定的中國社會的制度結構不會在十幾年的歷史中徹底改變。
對這段話的核心觀點,即“利己中心、倫理本位、親情紐帶、圈子關系、輕視原則、崇尚權勢”等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將在中國社會較長時間內存在的觀點,筆者深表贊同。
但傳統社會在當今時代的變革也頗為復雜。最粗略地看,傳統社會中熟悉的部分(鄉村社會)正在“陌生化”——無論是政治權力影響下賀雪峰所謂行政村的“半熟人社會”性質,還是市場經濟影響下吳重慶所謂自然村的“無主體熟人社會”性質;傳統社會中陌生的部分(鄉村社會之外的社會)在當今改革開放和網絡化時代則正在“熟悉化”,或者至少是有了更多“熟悉化”的可能。學術界對正在“熟悉化”的一面強調得還不夠,劉少杰等學者對這一點的分析有其價值。
不過,沿著前文初步提出的“社會可熟悉程度”的思路,在可熟悉程度不同的組織或社會體系中,考察“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及其變化,特別是諸如“信任”或“不信任”之類具體行為的出現乃至全面鋪開,也許更有助于我們反過來思考“社會可熟悉程度”的意涵,對于正確定位和理解“熟人社會”“單位社會”同樣不無裨益。
單位社會的“熟悉”及“陌生”
有關“信任”的研究,特別是其對立面——“殺熟”的研究,能夠帶給我們有關“社會可熟悉程度”意涵的啟示,幫助理解“單位社會”。鄭也夫《走向殺熟之路》一文借助洛倫茲在《攻擊與人性》中的研究,指出“殺熟”是有生物學根源的,“同種資源的爭奪決定了‘殺熟’比‘殺生’更為殘酷”,并認為這一邏輯也適用于人類行為的分析,介于親屬與陌生人中間的“熟人”間關系也可能因“同種資源的爭奪”而埋藏下“殘酷廝殺的種子”。鄭也夫指出單位社會中具有挑起“政治殺熟”的條件,并為“經濟殺熟”,即類似“老鼠會”的傳銷騙局,掃除了心理障礙、組織基礎和輿論壓力。
如果將單位社會看作是“熟悉社會”,按說該社會應該能夠“從熟悉得到信任”,但在鄭也夫眼里,單位社會卻“前所未有地在社會基層造就了一種制造怨恨與不信任的組織機制”,原因何在?
在分析單位制時,鄭也夫指出,由于一切物質利益只能從單位獲得,且制度“把本屬于社會的生機勃勃的黨派生活和政治參與固定在單位中,并將政治追求與社會地位的晉升牢固地系結在一起”,因此單位成員全面依附于單位;在心理層面,由于單位分配事項過多、過細,成員對生活的不如意也不免“統統凝聚和發泄在單位上”,使得“單位制度普遍擁有的功能是,造就人們對本單位的不滿和仇恨”。
由此,有必要特別指出“退出”的重要性。對單位的全面依附,意味著單位成員特別是普通成員不那么容易“退出”本單位。相反,被外部權威所認可的“領導”或“精英”卻通常是流動的。因此,單位內的人際關系容易受到外在權力系統的挑撥與左右。于是,對身處單位的個體而言,外來力量的運作和切入方式是否是“可熟悉的”具有決定性意義。
單位社會還通過政治或社會運動“制造”對更廣泛的社會系統的“忠誠”或迷信,只是這種“忠誠”或迷信落實到單位內部,便很容易導致單位成員之間陌生感和整個單位中陌生因素的增加。具體而言,單位外剛性的標準會被單位內的部分成員親近和利用,導致另外一些成員被視作“異類”,甚至“被退出”到單位之外;即便不是如此,也勢必會形成“忠誠”或“積極”與不“忠誠”或不“積極”的對立。單位內分化的結果,經外來力量稍加確認,就能導致單位內權力和資源分布結構的改變,陌生因素及成員間的不信任感也就產生了。
總之,單位社會的“熟悉”與“陌生”是分化的,有賴于行為者進行組織和斗爭的能力,及其在單位內外權力體系中的位置,而這樣的位置又容易被外在力量操控而不斷變化。因此,“殺熟”這種極端的“私的毛病”的泛濫,可以解讀為是“社會可熟悉程度”因結構上的某種劇變、政治運動和傳銷行為的“顛覆”而迅猛降低所導致的結果。
“社會可熟悉程度”再探討
從澄清問題的要求出發,有必要站在“整個系統”的角度,對“社會可熟悉程度”這個概念加以明確。該概念可明確如下:“社會可熟悉程度”指的是,在一個社會中對于現實空間中交通及信息等技術意義上行為可及范圍內的“人、財、物”及抽象社會系統中的“責、權、利”等,任何社會成員只要想了解和熟悉,或者在有必要了解和熟悉時,就能夠以比較低的成本知悉真實情況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越大,“社會可熟悉程度”越高;這種可能性越小,“社會可熟悉程度”越低。
參照這一定義,中國傳統社會是“社會可熟悉程度”不高的社會。不僅在于人們不怎么了解外部世界,還在于交通不發達、地域相對“封閉”(技術上人們常規行動的可及范圍相對較小)導致人們不容易從這個“地方”或這塊“土地”輕松“退出”。此外,“山高皇帝遠”導致它不容易受外來力量的挑撥與左右,加上“落葉歸根”這類涉及“身后想象力”的傳統文化觀念的規制,“殺熟”也就不會是普遍的系統性現象。
在傳統社會的變革過程中,無論是單位社會中的“政治殺熟”,還是經濟領域中以傳銷騙局為極端的“經濟殺熟”,則都可以說是“外來力量”強有力運作的結果。在此,人們“進入”或“被誘惑進入”了相對陌生的“外部世界”,龐大的“組織和社會系統”是對行為者而言更具安身立命之本的平臺,是決定行為者生命、自由、資源、權力、地位的基石,有的行為者甚至對之更感認同。于是,“殺熟”(這里的“熟”是原來的“熟人”)在這樣的背景下可能成為“投名狀”,成為表決心、表忠心的重要方式。
因此社會成員面對社會組織時的“退出-進入”維度有助于人們考察“社會可熟悉程度”、社會性質及其變遷。“退出-進入”的權利及空間的相對變化帶來人們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改變,從而對社會性質及其變遷具有基礎意義。“退出-進入”某個具體組織或社會系統相關的一系列因素,如“退出權”“退出成本”“可進入”“進入成本”等,也可作為“社會可熟悉程度”的一種指標化的衡量方式,在一個“可熟悉程度”較高的社會,每個人都較為自由地“退出-進入”某個具體單位、組織或社會系統,甚至人們還有較強的自我組織能力和空間。
“社會可熟悉程度”和“退出-進入”的關系也觸及了社會學的基本問題,即關于“行動者個體之間的相互作用與社會共同體的存在與作用的關系”的問題。對于考察社會性質及其變遷而言,從成員權利的角度出發,“社會可熟悉程度”/“退出-進入”作為一個分析框架,可能構成對“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視角的補充或推進,且更有分辨力和預測性。
結論與討論
關于社會性質及其變遷,經典社會學從多個角度展開過探討和分析,本文則嘗試主要從成員權利的角度,得出名為“社會可熟悉程度”/“退出-進入”的分析框架,用以開展社會性質及其變遷的考察。
具體而言,我們可從“社會可熟悉程度”著眼,認為“進入”或“退出”一個現實空間、具體單位或組織系統的成本、方式及可能性,會影響人際關系、組織關系、個人與社會以及環境的關系,進而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
于是,對社會性質及其變遷的判定,需要聚焦到這些更基礎的結構性因素上。作為理想類型,鄉土社會和單位社會有不同的“社會可熟悉程度”;單位社會中“社會可熟悉程度”不確定性更大,不同社會成員間的分化也更為明顯,在較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力量的左右。而就“退出-進入”這個指標來說,鄉土社會和單位社會中的“被退出”“退出權”“進入空間”“進入渠道”等都有很大的差異。
當今世界,“社會可熟悉程度”以及“行動者個體”特別是其中權力弱勢方的“退出-進入”自由度的提升,需要一系列前提。這些前提應該包括:(1)“社會”成員之間未處于大規模的暴力沖突或其他層面的系統性敵對狀態;(2)越軌的事實和懲罰不因為權力的優勢地位而受到掩蓋和規避;(3)“行動者個體”之間基本權利平等;(4)各類社會“組織”乃至各類“行動者個體”有便捷的信號發送和接收系統,能以較低成本達成對相關信號的一致理解。與以上相反的狀態、行為或時空及制度安排,比如恐怖活動、信息屏蔽、霸權主義、逆全球化等則意味著“社會可熟悉程度”的降低或“退出-進入”權利及空間的壓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