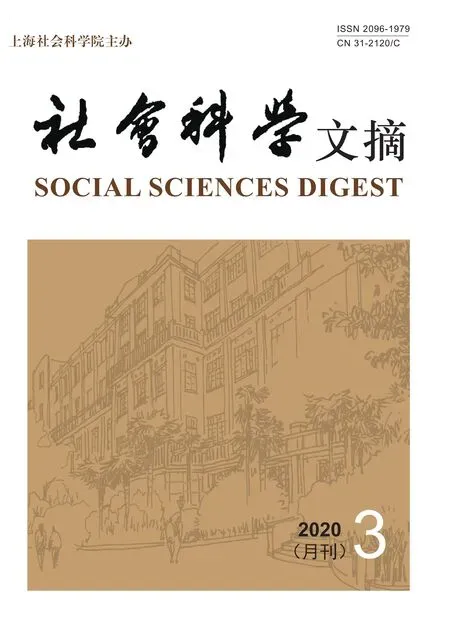漢魏之際文人關系中文學類型的確立
在我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上,文人關系與文學存在著密切的內在關聯。因為文人既是文人關系的主體,也是文學創作的主體。依據我國古代文人關系的性質,我們可把文人關系分為政治、文化、學術、文學等不同類型。文人關系的類型不同,對文人文學創作產生的影響也不相同。所以從文人關系的角度探討古代文人的文學創作與文學的發展,應是一條可行的途徑。從東漢中期至魏明帝太和年間的漢魏之際,是我國古代社會發生重要轉型的時期。該期文學之所以也發生了巨大變革,其中固然有多種原因,但該期文人關系性質的變化是重要原因之一。因為與之前相比,該期文人關系有了新的發展,出現了文人以文學來構建彼此關系的新情況。這主要表現在文學不僅成為該期文人之間建立關系的一大目的和內容,而且成為他們借以建立相互關系的一種主導形式,文學作為文人關系的一種嶄新類型獲得了確立。在我國古代,“文人”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群體,其內涵有一個長期的演變過程。所以本文在論述過程中考慮到“文人”演變的歷史實際,涉及先秦至東漢初這一時期時用“士人”這一稱謂,涉及漢魏之際時則用“文人”。
文人關系中文學目的從自然到自覺的轉變
從文人關系的目的來看,在我國古代文人關系發展史上,到漢魏之際文學才擺脫了自然依附于政治、文化學術等目的的附庸地位,作為文人建立人際關系追求的目的之一,則發生了從自然到自覺的轉變,為文人關系中文學類型的確立提供了目的上的條件。
先秦時期士人建立人際關系的目的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建立在利益基礎之上。這不僅表現在士人與統治者的關系上,還表現在士人與士人之間的關系上。戰國后期的荀子就發出了這樣的感嘆:“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其二是建立在道統基礎之上。一方面,這可以通過先秦時期士人與統治者之間的關系予以說明。此時期的士人在與統治者建立關系時,就彰顯出對自己學派道統這一目的的積極捍衛。另一方面,這在先秦時期諸子學派內部成員之間的關系中也有鮮明的體現。這也就是孔子為何說“士志于道”“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原因所在。
西漢至東漢初期,由于政治上的一統與思想上的儒學獨尊所引起的社會風氣和士人價值取向的變化,士人關系的目的也發生了變化,政治和經學成為士人建立相互關系的重要目的。這在該期士人與統治者之間、士人彼此之間的交往中皆有體現。漢初的吳王劉濞、梁孝王劉武、淮南王劉安等之所以廣招士人,士人之所以紛紛前來投靠他們,其目的主要是政治的。西漢武帝以后儒學成為統治者治國的指導思想,儒家經學也就自然成為士人之間建立關系的一大目的。
先秦、西漢至東漢初期道統、政治與經學作為士人建立彼此關系的目的,不僅被他們所認同和接受,而且成為了士人一種自覺的追求。就此期士人關系建立目的的總體情況而言,雖然也涉及了文學,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們在追求道統、政治與經學等目的時的一種自然顯現,文學還未獨立成為他們追求的目的,更談不上自覺。
漢魏之際,除政治、經學等被文人繼續作為建立相互關系的目的之外,又出現了文學被文人作為建立彼此關系目的的新情況。這時的文學在文人交往目的中的價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顯,不僅擺脫了之前依附于道統、政治、經學的附庸地位走向了獨立,而且作為文人之間建立關系追求的目的之一而發生了從自然到自覺的轉變。這種轉變在東漢和帝、安帝時期就有了一定程度的顯現。東漢后期的桓帝、靈帝時期,文學作為文人建立相互關系目的的意識愈益明確和自覺。如文人、統治者之所以積極主動地和蔡邕建立關系,其目的就是基于蔡邕非凡的文學實績和超拔的文才。
建安時期文人匯集鄴下,依附于曹氏父子,文學所起的作用更為重要,文人之間把文學作為建立關系的目的來追求的自覺意識更加突出。《三國志》卷一九載:“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曹操組織的這次活動,完全是以文學創作為目的的。盡管此次活動是由曹氏家族成員參加的一次家族活動,但就曹操的地位和影響來說,他的這一舉措,無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向曹丕、曹植兄弟宣告了文學創作作為文人建立關系目的的獨立性、自覺性和合法性。因為從東漢后期開始,家族文學作為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就遠遠超出了家族本身,而具有了影響文學發展方向的引領意義。曹氏家族的這次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更是如此。此后,曹丕、曹植兄弟在鄴下西園、南皮等地,自覺組織由建安其他文人參加的以文學為目的的活動,就是典型的表征。曹丕、曹植兄弟與王粲等六子之間之所以相互友善、成為好友,原因就在于他們有一個皆好文學的共同目的,而且這一文學目的是獨立于其他目的之外的,是文人特別看重和自覺追求的。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人,雖然也有文采,但由于與王粲等六子相比,他們的文學才能有所遜色,所以在曹丕、曹植兄弟心中,其地位自然也就無法與王粲等六子等同了。由此可知,建安文人不僅把文學作為了彼此交往的重要目的,而且依據文人文學才能的高低來決定文人之間關系的遠近親疏。也正是這樣,文學在文人建立關系目的中的地位也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并且與政治相比也毫不遜色,成為了文人自覺追求的“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從而具有了與“經國”同等重要的不朽的意義。
總之,在我國古代文人關系發展史上,至漢魏之際,文人建立相互關系的目的上,不僅擺脫了之前從屬于道統、政治、經學等目的的自然狀態,而且成為了他們主動的自覺追求,發生了從自然到自覺的重大轉變。
文人關系中文學內容從依附到獨立的發展
從文人關系的內容來看,我國古代的文人關系發展到漢魏之際,文學作為文人交往的一項內容,經歷了從依附到獨立的發展,為文人關系中文學類型的確立提供了內容上的條件。
先秦時期,士人關系的建立在內容上居于獨立地位,這主要體現在與他們建立關系時所追求的道統等目的相一致的權力富貴、治國理政、道德倫理教化等方面。此時作為我國古代士人這一社會階層的形成期,其身份非常復雜。范文瀾先生曾把當時的士人分為學士、策士、方士或術士、食客四類。就這四類士人彼此之間建立關系的內容而言,盡管豐富多樣,但居于獨立地位的則是權利富貴、治國理政、道德倫理教化,“文學”只是為這些內容服務的,并不是被士人作為獨立于它們之外的內容來看待的。文學作為士人構建相互關系的內容在這些活動中還未獨立,只是依附于其他內容而存在的。
西漢到東漢初期,由于受執政者以儒家作為治國思想理念的影響,再加上士人身體力行的現實實踐,士人之間建立關系的內容也與儒家所倡導的孝道、忠君等思想密切相關,處于獨立地位的士人關系主要體現在治國理政、經明行修等方面。這照樣能夠從該期士人關系建立的內容中得到說明。像西漢初期藩王與士人之間關系的建立,西漢武帝與宮廷士人之間關系的建立,所彰顯的獨立內容就是以治國理政為主的;像西漢和東漢初期太學、郡學以及蘭臺、東觀等士人之間關系的建立,所彰顯的獨立內容主要是以經明行修等為主的。當然這個時期士人關系建立的內容中也有與文學相關的,但主要是依附于治國理政、經明行修等內容而存在,文學的獨立地位和價值也被治國理政、經明行修等內容所遮蔽。
漢魏之際,尤其是建安時期,隨著文人立言價值觀從余事到主導的轉變,文人交往中的文學內容日益增加,其地位也愈益重要,實現了從依附到獨立的發展,成為文人彼此建立關系的獨立內容之一。這可從兩個方面予以說明。一方面,此時文人的文學創作本身作為文人活動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文人在活動中彼此交往的一項獨立內容。此種情況在東漢安帝至靈帝時期文人的游藝活動和游藝文學創作中,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彰顯。建安之后,曹氏兄弟與建安諸子之間、建安諸子彼此之間所開展的游藝活動與創作的游藝文學作品更是如此。像應玚的《馳射賦》《校獵賦》、邯鄲淳的《投壺賦》等,就是他們在從事游藝活動中創作的,也是以描寫文人所開展的游藝活動為內容的。所以,這些作品就具有了雙重的價值,它們既是文人從事游藝活動過程中的內容,也是文人在活動中彼此建立關系的內容,并且其文學地位是獨立的,是不依附于其他內容而存在的,彰顯的是文學本身所具有的審美和娛樂功能。這個時期文人在交游活動中創作的同題共作與贈答的作品,同樣既是文人從事交游活動過程中的內容,又是文人在活動中彼此建立關系的內容,其地位也是獨立的。在這些活動中,文學作為文人活動的有機內容,不僅是文人之間建立關系時文學內容的具體展示,而且與活動中的其他內容相比也具有了獨立的文學價值。
另一方面,作家、作品作為客體也獨立成為該期文人之間建立關系的對象。像建安諸子、曹氏兄弟在交游、談論等活動中相互交流的內容之一,就是對作家、作品的談論和品評。文學在他們開展的這些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彼此建立關系內容的獨立組成部分。如曹植的《與楊德祖書》、楊修的《答臨淄侯箋》,就這兩篇文學作品而言,不僅是兩人建立關系的具體表現,也是兩人建立關系的具體內容。就兩人建立關系的具體內容來說,其中心議題就是圍繞文學來展開的,所以文學也就自然成為了曹植、楊修兩人關系得以建立和維系的獨立對象。再如曹丕的《典論·論文》《與吳質書》、吳質的《答魏太子箋》、陳琳的《答東阿王箋》等,也是如此。這些作品中所討論的建安作家作品,從文學的意義上來說,不僅是獨立的,也是建安諸子、曹氏兄弟之間關系得以建立的主要內容之一。這在該期文人的辭賦、詩歌創作和其他活動中也有體現。
可見,漢魏之際,尤其是建安時期,文人通過文學來展示才能成為文人之間建立關系內容中的一大景觀。文學作為文人交往的內容,擺脫了之前依附于權力富貴、治國理政、道德倫理教化、經明行修的從屬地位,成為與它們并肩的主要內容之一,其地位、價值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完成了從依附到獨立的飛躍發展。
文人關系中文學形式從輔助到主導的跨越
漢魏之際,文人出現了借助文學這一形式來建立彼此關系的新現象,文學作為此時文人關系建立的形式之一,實現了從輔助到主導的跨越,為文人關系中文學類型的確立提供了形式上的支撐。
先秦時期,士人把利益、道統等作為建立相互關系的主要目的,把權力富貴、治國理政、道德倫理教化等作為交往的獨立內容。受此影響,他們也相應把政治、文化、學術等作為建立彼此關系的主導形式。如《中庸》“五達道”中的君臣是借助于政治這一形式而建立的,朋友是以共同的文化、學術愛好等志趣這一形式為基礎的。從中就可以看出該期士人借以建立關系的主導形式。
西漢到東漢初期,士人關系的建立多是對先秦時期的繼承。西漢武帝以后,由于采取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受儒學思想影響的政治、文化、學術等成為士人之間建立關系的主導形式。如此時太學、郡學中經師、太學生等彼此之間的關系,就多是借助于受儒學思想影響的政治、文化、學術等而建立的。這從東漢班固的《白虎通》中也可以得到證明。《白虎通義》中所說的“三綱六紀”,就有君臣、師長、朋友是建立在政治、文化、學術等形式上的。這說明政治、文化、學術也是該期士人關系得以建立的主導形式。
先秦到東漢初期士人關系建立的形式中,也有與文學這一形式相聯系的情況,但總體而言,與政治、文化、學術等主導形式相比,文學只是處于輔助的地位,還沒有成為一種與其相比肩的主導形式。
漢魏之際,文人之間在建立關系時除繼續借助政治、文化、學術等形式外,又進行了開拓性的創新和發展,把文學從之前被士人作為建立相互關系的輔助形式中解放出來,賦予了它真正的文學價值,使其成為文人彼此建立關系的主要形式之一,實現了從輔助到主導的跨越。這在東漢后期的順帝到靈帝時期就有明顯的表現。此時文人借助于文學這種形式進行交流愈來愈被他們認可、接受和實踐,文學在文人借助于建立相互關系的諸種形式中的主導性也日益突出。
特別是到了建安時期,文人借助于文學獨立進行彼此交往,文學真正成為文人之間建立關系的主導形式之一。這在建安文人的交游、創作、談論和游藝等日常生活中,皆有典型的表現。他們在這些活動中或活動之后,彼此之間借助于文學這一形式交流、溝通,已成為普遍現象:其中有借助詩歌的,如贈答詩、宴會詩、游覽詩、斗雞詩等;有借助辭賦的,如抒情賦、游藝賦、詠物賦、征行賦等;有借助散文的,如文人之間的來往書信和大量的表、疏、記、贊、序等。可以說是文體多樣,形式豐富。有關這些借助于文學形式進行交流的例證,在建安文人關系中不勝枚舉。
漢魏之際,文學開始從作為之前士人之間建立關系所借助的政治、文化、學術等形式中解放出來,逐步成為文人彼此建立關系的主導形式之一。尤其是經過建安諸子、曹氏父子等文人的大量實踐,文學成為他們借以交往和促進彼此關系鞏固與發展的一種主導形式,實現了從輔助到主導的跨越。
結語
從東漢中期至魏明帝太和年間的漢魏之際,我國古代文人關系確實有了新的發展,尤其是建安時期,出現了文人以文學構建彼此關系的新情況。這主要表現為文學在文人關系的建立中,作為文人追求的目的發生了從自然到自覺的轉變,作為文人交往的內容經歷了從依附到獨立的發展,作為文人借助的形式實現了從輔助到主導的跨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完成了文人關系中文學類型的建構,使文學作為文人關系中的一種類型得到了確立,成為與文人關系中政治、文化、學術等類型相比肩的類型之一。
當然,漢魏之際文人關系中文學類型的確立,并不意味著它與文人關系中的政治、文化、學術等類型毫無聯系。相反,它以獨立的姿態與文人關系中的政治、文化、學術等類型相互滲透、相互吸納、相互影響、相互促進,更加有效地參與了文人關系的建構,實現了文學與政治、文化、學術等相互之間的深度融合和貫通,賦予了文學更加豐富的內涵,增強了文學的厚度和張力。
漢魏之際文人關系中文學類型的確立,不僅拓展了古代文人關系構建的渠道,提高了文學在文人交往中的價值和地位,彰顯了文學在文人關系構建中所具有的獨特藝術魅力,推動了文學的繁榮發展,而且為以后文人關系的開拓創新提供了借鑒。可以說,漢魏以后的文人關系無不受到它的影響。繼建安文人群體之后,竹林七賢、二十四友等文人群體代代層出不窮,就是最好的表征,其文學價值是不容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