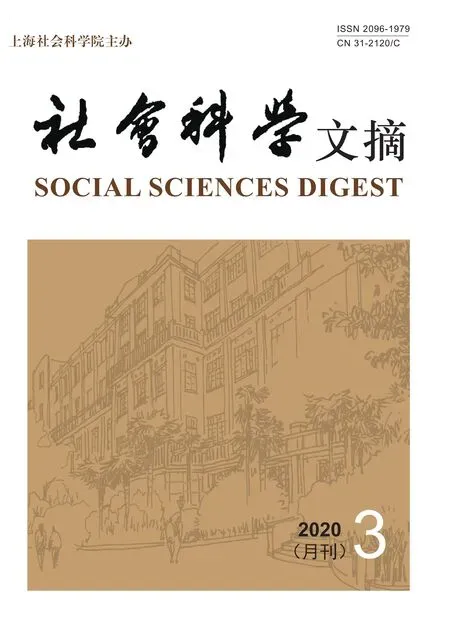“歷史化”的構想與矛盾
一
作為一種文學研究的策略和實踐方式,中國文學史的“學術史”十分短暫。迄今為止,無論是歐洲文學史研究還是中國文學史編纂,這種學術語言逐漸積存了一些問題。這并不奇怪。一種學術語言通常顯現為一種視角,一種范式,或者一個相對聚焦的領域,洞見與盲視并存。特殊的視角敞開一些層面的時候,另一些層面可能轉到了背陰的一面,甚至遭到遮蔽。人們無法擁有一個全知的視角,無法巨細無遺地再現全景,取消聚焦同時意味著取消獨特的發現。因此,意識到各種學術語言內含的限制不僅可以保持思想的彈性,避免陷入某一類型結論的獨斷,同時有助于學術語言的拓展、補充,增添必要的補丁。文學史編纂遭遇的一部分問題源于既定視角的封閉性,考察對象的某些性質徘徊于視角之外,遲遲未能贏得足夠的關注;另一部分問題來自既定視角的延伸——持續的考察逐漸進入縱深,一些模糊的、忽略不計的內容顯出了特殊意義,強烈要求合理的解釋。這一切構成了學術語言的內在層次,帶動概念、術語系統的新陳代謝,保證學術語言與考察對象之間始終保持對話、互動的活力。
如何編纂當代文學史?“當代”仿佛缺乏線性的時間長度,當代文學此起彼伏地分布于人們周圍,活躍的程度遠遠超過穩定性,眾多作品之間的權衡、比較以及聯系和呼應的描述遠未完成,紛至沓來的作家無法在文學史構建的大師座次之中找到毋庸置疑的位置。這時,“當代文學史”可能是一個冒失的,甚至得不償失的稱謂。很大程度上,“當代”這個概念擁有的積極意義是尖銳、犀利、令人激動的現場氛圍以及閃爍不定的多種可能,而不是老氣橫秋的“歷史”面目。文學史賦予的秩序即是指定標準,規范表情,這時,“歷史化”猶如制作學術套餐配備的烤箱。
二
對于當代文學史的編纂說來,“歷史化”時常設立了一個相對的觀念:“批評化”。這種表述似乎暗示了一種強大的學術努力:盡快使作品擺脫文學批評的掌控,安全地降落在文學史監管的領域。
盡管“歷史化”與“批評化”存在許多重疊的區域,二者仍然顯示出不同的指向。“批評化”更多地指向作品本身,指向文學的現場,指向當代文化氣氛,甚至某種程度地介入商業宣傳。批評家的判斷帶有明顯的個人風格,見仁見智;各種激情未經時間的沉淀,往往包含即興的成分。他們可能卷入與作家、讀者的互動,擊節稱賞或者無情討伐隱含了各種不同觀點的激蕩。“歷史化”對于文學批評的“印象主義”與“專斷主義”——朗松的概括——嘖有煩言,文學史開始轉向作品生產的種種外圍的、相對穩定的因素,譬如作家的身世、某種主題的歷史淵源、另一些作品的相互衡量、經典秩序的復雜參照,如此等等。“歷史化”業已退出文學現場,平息置身其中的特殊情緒,甩下各種意氣用事的褒貶,“歷史化”包含的時間距離仿佛增添了鑒定的“客觀成分”。盡管二者之間存在各種過渡的梯次,但是,兩種原型涇渭分明。因此,愈是清晰地區分二者,這個問題愈加尖銳:“批評化”與“歷史化”之間的關系。換言之,二者是不分軒輊的兩種文學研究方式,還是構成了初級至高級的發展,猶如童年階段成長為成年階段?文學史作者顯然傾向于后者,有意無意地賦予“歷史化”某種優越感。“批評化”的初步加工僅僅為“歷史化”提供基本原料;作為后續的另一種方式,“歷史化”更為成熟,更為嚴謹。“歷史化”之于“批評化”毋寧形容為指導者與被指導者,雙方的關系不可逆。歷史的評判仿佛意味著最高同時也是最終的評判。
相對于“批評化”,“歷史化”顯然更為關注隱含于作品之間的來龍去脈。斷言一部作品的獨創、開拓之功或者貶抑一部作品因循守舊、平庸無奇,文學史是一個必不可少的背景。一部作品贏得的各種評語業已包含文學史的注解——例如,所謂的“獨創”亦即聲稱,文學史的檢索證明這一部作品的許多內容前無古人。如同從個人品行的鑒定轉向家族身世與血緣,文學史力圖在時間維度顯現諸多作品之間的關系網絡;當然,文學史考察的復雜程度遠遠超出家族追溯。文學史不僅分析帶有血緣聯系的作品,同時分析作品的不同類別,解釋沖突的美學如何分別造就各自的杰作。開啟經典遴選機制的時候,文學史必須周密地考慮經典之間的平衡與協調,尤其是各種類別的經典——譬如,詩歌、小說、戲劇,或者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如何保持均衡。顯而易見,“歷史化”必須某種程度地犧牲作品的獨立自足換取文學史的寬闊視域。
“歷史化”傾向于冷卻沖動,撤離現場,對于起伏的激情潮汐打一個問號。即時的喜怒哀樂缺乏深思熟慮的斟酌,各種情緒無不帶有膚淺的氣息;置身于事實的發生現場恰恰遠離真實。現場互動往往沉溺于紛雜的細節,目迷五色,只有退到歷史的位置上才能仰望宏大的目標。總之,“歷史化”時常覺得,現場體驗是一些沒有價值的花絮,重要的是經受“歷史考驗”。所謂的“歷史考驗”往往托付給時間,時間距離提供可信的結論。時間之流仿佛具有某種神秘的功能,認識之筏漂流的距離愈長,回首瞻望的對象愈清晰。
許多時候,文學現場的“批評化”與文學史提出的結論存在差異,甚至相距甚遠。然而,為什么不是將這種差異解釋為不同語境結構的必然產物,并且對于差異的雙方相提并論,而是輕率地認為后者比前者更為可信?李白或者杜甫同時代詩人的相互評判必定比我們對于唐詩的觀點遜色嗎?這時,“歷史”概念隱藏的無意識是,此刻、現場、即時的存在僅僅是泡沫一般的表象,真實的本質只能在塵埃落定之后現身。這種無意識隱含了存在主義與本質主義的分歧。存在主義正視此刻的存在,盡管此刻存在的諸多表象無法吻合未來認定的“本質”。本質主義的思辨認為,某種絕對的“本質”高懸于宇宙深處,潛伏于無數表象背后,不可能立即浮現,只有耐心地等待“歷史化”篩去那些混亂的瑣屑,“本質”才能穿過歷史包含的時間長度隆重登場。這種理論預設充分肯定了“歷史”,輕蔑地摒棄了當下;同時,這種理論預設清晰地劃分了“表象”與“本質”,“表象”無足輕重,眾望所歸的“本質”只能授予歷史。現場與表象的結合無望提供正確的認識,正確的認識依賴歷史與本質的相遇。
這種理論圖景的未竟之處在于,無法精確地斷定“歷史”的時間長度。哪一個時刻是歷史發現“本質”的“標準時間”?這個缺失的邏輯前景是,“歷史”之后還有“歷史”,“再解讀”之后還有“再再解讀”。后來居上,新的結論必定更為正確,以至于嚴肅的“本質”遲遲無法一錘定音。歷史無限拉長,某一個時刻出現的“歷史化”遲早又會被擠兌為另一種“批評化”。
如果不是在無盡的時間之流引入語境結構,“歷史化”無法擺脫這種理論困局。一種觀點通常誕生于既定語境,并且在既定語境接受衡量與評判。少量的觀點可能穿透既定語境的限制而將余熱帶入另一個語境結構,這并不能證明一個結論:大量囿于一時一地的言論缺乏意義。孔子或者柏拉圖的大部分思想已經過時,但是,他們之所以無愧于偉大思想家的稱號,毋寧因為他們的觀點之于當時語境結構的巨大作用。文化時間——而不是物理時間——從來不是均勻地流動,而是由一個又一個大小不一的語境銜接與疊加起來的。既定語境之中某些觀點享有的崇高聲望可能在另一個語境結構急劇衰減。“批評化”與“歷史化”分別置身既定語境陳述各自的結論。如果人們覺得某些“批評化”的觀點平庸乏味,參照的是另一些具有真知灼見的“批評化”觀點,而不是因為姍姍來遲的“歷史化”。換言之,只有共同的語境才能提出統一的衡量標準。
文學批評業已承擔分析、品鑒和評判當代文學的職責,為什么“歷史化”仍然尾隨而至?這時,與其將文學史視為文學研究收尾的清場工作,不如關注文學史的開拓性——這種學術語言之所以再度介入,恰恰由于文學史作者意識到另一種語境結構的到來。他們迫切地覺得,只有文學史才能充分地顯現另一種語境結構提出的深刻主題。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新文學大系、50年代的現代文學史編纂、80年代的重寫文學史乃至90年代的《再解讀》無不顯示出這種特征。
三
編纂當代文學史的時候,許多作者表述了一種觀點:當代文學的“歷史化”是“學科”規范的完成。“歷史化”時常被視為種種知識的穩定劑,載入史冊的結論不容任意篡改。因此,“學科”對于“歷史化”的垂青意味著,這一套知識已經定型。學院體制內部,“學科”是知識傳授的一個樞紐,包含一套完整的基本規定,譬如教材、課程、課時、作業、考試,等等。這些規定組成了知識傳授的標準流程,平均的意義上顯現出教與學的最大效應。然而,許多“學科”的設計并非無可爭議,只不過這些爭議交付知識與權力的協作關系給予平息。“文化研究”對于學科歷史的考察表明,某些學科的知識傳授與權力要求存在復雜的糾纏——“學科”(discipline)的另一種翻譯即是“規訓”。從知識的生產、分類、包裝、檢索到運輸與消費,學院體制設置的“學科”基于現代性平臺。至少可以發現,古典知識與后現代知識的生產、消費模式遠不相同。京師大學堂課程設立之前,文學史并非文學研究的“標配”。
對于文學史編纂說來,文學觀念不是游離的空中樓閣,而是內化為處置各種史料的前提。各種文學觀念濟濟一堂,對于所謂的“歷史化”構成巨大的理論壓強。毫無疑問,史料包含基本的穩定性,沒有人可以任意將《創業史》的作者認定為丁玲,也沒有人可以斷定劉心武的《班主任》完成于20世紀90年代。盡管如此,人們必須正視事實的另一面:相同的史料可能造就相異的文學史。歷史著作決非巨細不捐的流水賬。諸多素材遵從哪些組織原則?多數歷史學家力圖超出編年史的簡單體例,闡述時序之外更為深刻的內涵。這些事實無不揭示歷史的雙重性質:過往發生的一切具有客觀性質,然而,歷史著作來自各種敘述的建構。“歷史的建構”是一個涵義豐富的事實。不論眾多思想家從哪一個維面接受與闡釋這個事實,這種觀點逐漸退出了思想的舞臺:歷史猶如地表之下一個固定的礦藏,歷史研究僅僅是發現和展示。文學史亦然。
四
回到文學史的獨特立場,人們同時意識到另一些歷史類別的存在,譬如哲學史、經濟史、法學史、化學史、數學史,或者工業史、農業史、戰爭史、災難史,等等。這種狀況可以分解為兩個后續問題:首先,文學史與總體歷史的關系;其次,文學史與另一些歷史類別的關系。
何謂總體歷史?一種簡單的觀點是,總體歷史即是諸多歷史類別的相加。歷史不設門檻,沒有哪一種人類活動隔絕于歷史之外。然而,諸多歷史類別是無機堆放,還是按照某種原則組織起來——后者顯然接近于有機整體。無機堆放提供的是各種類別的總和,甚至不存在中心與清晰的邊界;按照某種原則組織通常顯現為一個同質的總體,盡管每一個歷史類別承擔的功能遠不相同。文學史組織于總體歷史的肌理之中。正如許多思想家指出的那樣,現代性降臨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民族國家的崛起,這個主題同時成為文學史的指南。一部厚重的文學史是民族國家歷史之中令人矚目的一頁,一批偉大作家的名字可以使民族國家熠熠生輝——盡管他們的貢獻僅僅是若干卷文學名著。
然而,人們可能產生的疑問是,民族國家包含的內容是否被某些文學史作者想象得太簡單了?他們仿佛認為,諸多歷史類別始終保持相同的姿態與步調向同一的目標沖去。這種前提之下,文學史、哲學史、經濟史乃至工業史、農業史不存在實質的內在區別。如果每一種歷史類別的敘述無不按照相似的邏輯演示,那么,文學史往往不知不覺地成為政治的附件——政治逐漸充當了諸多歷史類別的內在模板。不論如何表述文學史考察的動機,一些當代文學史作者的意圖是,借助文學史的跳板躍入政治領域。他們覺得,“審美”是一個狹窄的概念,無法容納當代文學史的內涵。相對地說,他們寧可援引政治邏輯作為統籌當代文學史的主軸,當代文學史的重大任務是解讀時代的政治無意識。
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政治提供的宏大敘事不容置疑地左右了各個歷史類別的論述,政治領銜諸多歷史類別的狀況獲得了大量歷史敘述的支持。然而,考慮到民族國家的諸多方面構成,考慮到“人的全面發展”,各個歷史類別包含的獨立意義從未完全消失,譬如文學史的審美意義。如果文學的頑強存在并未被哲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覆蓋,那么,作為“藝術地掌握世界”的生存范疇,審美必然具有獨特而尖銳的精神內容。集中展開這些精神內容的時候,文學史不僅可能與各個歷史類別相互呼應,也可能與各個歷史類別相互修正,相互制約。
談論文學史編纂的時候,我更愿意證明審美是總體歷史內部一種不可或缺的能量——這也是我回顧《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種文學史觀念的前提。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在論文之中表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首先意味著文學史從社會政治史的簡單比附中獨立出來,意味著把文學自身發生發展的階段完整性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曾經從四個向度概括20世紀的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文學”“改造民族的靈魂”的主題、“悲涼”的現代美感、新型的文學語言結構。如果認為這些特征的發現來自60年代美國社會科學的輔助——如果“改造民族的靈魂”或者白話文之后文學形式的革命是80年代現代化敘事生產出來的,那么,20世紀中國文學的獨立存在顯然是一個令人懷疑的事實。顯而易見,這種觀點沒有聽到審美自己的語言。事實上,即使在世界范圍內,晚近幾個世紀的文學也不是現代性敘事的標準合作者,無論是憤懣而悲傷的現實主義還是陰郁而反諷的現代主義。對于所謂的“現代性”,文學的審美立場帶來復雜的態度——與眾不同的接納與反抗。
《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四個概括是否完整,這并非我試圖回答的問題。我愿意指出的僅僅是,這些問題的回答涉及眾多衡量構成的網絡:涉及史料與文學觀念的緊張、“批評化”與“歷史化”的銜接與平衡、進化的線索與個別的自足,涉及文學史與另一些歷史類別的參證與對立,文學史置身于總體歷史的位置以及不同時段產生的不同意義。當然,當代文學的語境結構可能使文學史的敘述成規遭受更大的壓力。這個網絡制造的話語空間充滿種種歧義、矛盾和曖昧不明的區域。只有意識到這種學術語言的復雜程度,思想的縱深才能敞開。一些作者幸運地免除了這些理論糾葛的困擾,那么,他們的苦惱或許會轉向來自學術市場的報告:書店柜臺上大同小異的簡版文學史著作已經過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