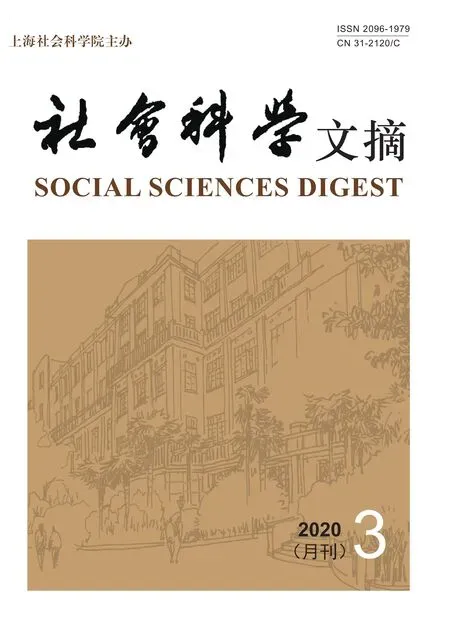魔幻現實主義與幻覺現實主義文學生產肌理的比較
兩種美學內涵的歷史嬗變
幻覺現實主義生成的元語境是德國19世紀著名女詩人安內特·馮·德羅斯特-徽爾斯霍夫(Annette von Droste-Hülshoff)的詩歌。經德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克萊門斯·黑澤爾豪斯(Clemens Heselhaus)在其專著《安內特·馮·德羅斯特-徽爾斯霍夫的作品與生平》(1971)提出,幻覺與現實兩詞的矛盾組合被視為矛盾修飾法。他指出她的詩歌多涉及一種瀕臨死亡的或宗教的幻覺和夢境主題,“將細節的觀察、現實的刻畫與豐富的想象力相結合,處于由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的過渡,但又不屬于二者中的任何一種”,由此稱為幻覺現實主義。1981年《牛津20世紀藝術詞匯大全》將其作為一種超現實主義風格收錄,定義為“精細正確的細節描繪,但這種現實主義并不描述外部現實,而是用現實手法描述夢境和幻想”。30年后,諾獎征用這個術語為莫言的創作風格命名,在時間和空間語境上存在了雙重跨越,在譯介轉換中經歷了延宕誤讀,因此值得析出它與莫言創作的匯合點,進而定位莫言帶給它的新坐標。它在瑞典語版本中為“幻覺般的敏銳”(hallucinatorisk sk?rpa),在英、法、德、西班牙文報道中以“幻覺現實主義”(hallucinatory realism)這一概念形式出現。我們承認以概念形式為莫言文學定性比描述性的語言更為直接決斷,更有助于與魔幻現實主義形成涇渭分明的格局,盡管這個概念本身與莫言的創作存在差異。所以中國學界在接受這個名稱之余,需著手以莫言的藝術風格去豐富和發展甚至重塑這個概念的內涵。以此為目標,本文以莫言與馬爾克斯的創作為例,比較分析以莫言為標識的幻覺現實主義與以馬爾克斯為標識的魔幻現實主義的文學生產肌理。
1983年德國學者林德勒(Burkhardt Lindner)教授在《新批評》刊物上發表的《幻覺現實主義:彼得·魏斯的作品〈抵抗美學〉,注釋和藝術的死亡區》一文。他認為彼得·魏斯發表《抵抗美學》的同時附上的作家與眾多政治流亡幸存者的訪談對話以及作品創作過程的細節記錄,與作品文本構成互文,讓讀者發掘到一種不同于歷史書寫的另一種真實。這種真實所具有的美學價值如作家所言:“已經分辨不清哪些是真實的(authentic),哪些是創造的(invented),它們都是一種真實”。這樣的“真實”用彼得·魏斯為其劇作《托洛斯基》的評論來解讀:“(該劇)有些方面的紀實,更適合采用一種幻象的,近乎幻覺的形式。”這種創作方法讓林德勒認為“幻象(vision)、幻覺(Hallucination)和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具有將令人懷疑的判斷復制成真實的生活感受”的效果,屬于幻覺現實主義。“就是試圖將眾多人物特點融入進一個富有廣度的、開放的、神秘聯系的、同步發生的記憶網絡中的‘我們’”。最終“追求到的是一種類似夢境的真實”審美旨歸。這段表述具象地解析了幻覺現實主義的建構肌理,即凸顯其個體的、主觀的現實特性,兼顧了心理衍生的諸如夢境這類藝術形式的運用。2001年,美國伊麗莎白·克瑞莫(Elisabeth Krimmer)教授研究安內特·馮·德羅斯特-威爾斯霍夫詩歌中的死亡意象及其女性作者身份的特點時,認為“向夢幻世界的過渡因為有對自然環境的詳盡描述作為鋪墊而更加引人入勝”,肯定這個矛盾修飾法的美學價值。此外,較之文學批評,這個術語更多出現在影視評論,強調以夢幻式的蒙太奇影視記錄現實的方法讓觀眾對真實現實產生新鮮的體驗而受到推崇。
相比幻覺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這一名稱出現之初有同樣的“矛盾情結”(ambivalence),其肇始于繪畫而聲名遠播于文學,同樣歷經40余年。1925年德國畫家弗朗茲·羅(Franz Roh)首次使用它,旨在倡導表現主義漸行漸遠的抽象態勢向現實主義的回歸(這個回歸成為后表現主義),即對“奇幻的、異域的、遙遠的對象”的青睞,這奠定了魔幻現實主義審美內涵的基本框架。選用magic而不是mystic,是因為羅要明確籠罩被表征的世界的不是神秘,而是“隱藏在這個世界背后的悸動”,且以此區別于超現實主義。1927年這篇文章被譯介到西班牙語世界時,“魔幻現實主義”被置于后表現主義的前面而得到凸顯,引發拉美文學界的關注。1948年委內瑞拉作家阿多諾·烏斯拉·皮耶特里(Arturo Uslar-Pietri)將這一表述應用于拉美文學,定義為“現實世界的第三維度,是人原初心智中真實和幻覺、現實和超自然的融合”。但1943年底親身旅行拉美的僑居法國的超現實主義拉美作家家阿萊霍·卡彭鐵爾(Alejo Carpentier)提出“美洲的神奇現實”一說,指出“神奇不是用抽象的形式和人為的綜合想象顛覆或超越現實發現的,而是根植于自然與人的時間和空間現實之中。在這里無需昭告,拉美多變的歷史、地理、人種和政治讓不可能的并置和神奇的混合發生”。雖然擇詞不同,但他更好解讀出了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美學的核心內涵。1955年,美國魔幻現實主義研究學者安吉爾·弗羅(Angel Flores)提出魔幻現實主義的起點為1935年,以博爾赫斯發表的文集《恥辱通史》為標志。因為博爾赫斯受卡夫卡的影響,尤其對“現實與奇幻融合”的敘事手法的借鑒,以及對《變形記》的西班牙語譯介,都對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家群體,包括對馬爾克斯產生過直接而巨大的影響。這一影響促成了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拉美文學爆炸。今天來看這種影響和后來馬爾克斯對中國當代作家包括莫言的影響模式非常相似。1967年墨西哥裔美國作家及批評家路易斯·累爾(Luis Leal)以“它不是什么”和“它是什么”的句式,清晰闡述了魔幻現實主義的獨特性。他認為,“魔幻現實主義文學沒有像超現實主義那樣應用夢幻母題;也不像奇幻或科幻文學那樣扭曲現實或創造出一個想象的世界;也不像心理文學那樣強調人物的精神分析,他們從不去發現行為背后的理性或沒有能力去表現他們自己。魔幻現實主義也不像現代主義那樣是一場由創造精美形式為旨趣,也不以創造復雜結構為旨趣來主宰的美學運動。[……]魔幻現實主義也不是魔幻文學。它的目的是表現情感,而不是喚起情感”。而關于魔幻現實主義是什么,他說:“魔幻現實主義尤其是通過通俗的或優雅的形式,以精致的或淳樸的風格,以封閉的或開放的結構表達出對現實的態度。這個態度是什么?[……]魔幻現實主義作家面對現實并努力去整理現實,去發現事物、生活和人類行為中的神秘。”這個闡發與羅存在本質上的共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魔幻現實主義與莫言的幻覺現實主義本質上的差異。此后在魔幻現實主義風行的半個世紀里,關于魔幻現實主義的定義從沒達成一致過而持續被闡述。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980年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的德巴·加倫特(Jeanne Delbaere·Garant)對英語語境中的魔幻現實主義類型的三類劃分:通靈現實主義、神話現實主義、志怪現實主義。從這里不僅可以窺見魔幻現實主義的多樣性趨勢,還會發現其難以界定的緣由恰恰是,這種超現實主義文藝理論與民族美學相結合的方法論大大激發出了新的文學生產力,強勁地驅動了文學的不斷創新發展。
由此可見,從超現實主義到魔幻現實主義,從魔幻現實主義到幻覺現實主義,再一次驗證了文學形式陌生化進程的軌跡。超現實主義實現了對呈現現實的藝術路徑和技術的理論建構,其背景是心理科學,其創意之奇屬于發明;魔幻現實主義追隨超現實主義的理論指導,但其背景是人類學,其創意之奇屬于發現,再現了原始思維之妙。所以歐洲超現實主義在創作個體的追求新奇發明中走向小眾,而魔幻現實主義則專注拉美民族的獨特心理,憑借人類原始思維審美下的集體無意識,獲得世界讀者的認同和贊賞。這一與民族美學結合的方法論,取得了毫無爭議的成功,并啟發各民族美學的噴發,包括喚醒中國作家對本土現實和藝術寶藏的開掘,促成了幻覺現實主義的生成。面對幻覺現實主義的降臨,國人沒有準備,瑞典學院院士、曾17次出任評委會主席的謝爾·埃斯普馬克(Kjell Espmark)教授解釋說:“我們采用hallucinatory realism(HR)一詞,而避免使用magic realism(MR),因為這個詞已經過時了。魔幻現實主義這個詞,會讓人們錯誤地將莫言和拉美文學聯系在一起。當然,我不否認莫言的寫作確實受到了馬爾克斯的影響,但莫言的‘幻覺的現實主義’主要是從中國古老的敘事藝術當中來的,比如中國的神話、民間傳說,例如蒲松齡的作品。”這里談到的“過時”,意在標識HR與MR的不同;“影響”則肯定了幻覺現實主義與魔幻現實主義之間的聯系,如諾貝爾獎官網發布的莫言簡介中所明確提及的“他敘事中的魔幻現實主義印記”,但真正使其擔起不再是魔幻現實主義的則是其凸顯的本土化因素。當時不懂外語的莫言在媒體最初誤譯為魔幻現實主義的語境下曾毫不猶豫地表達這個HR應是“與中國的民間故事密切相關”。這樣“中國的魔幻”(相對于拉美魔幻而言)注定要讓原西方語境下的基于精神分析的幻覺現實主義概念內涵得到豐富和發展,從僅以現實描繪夢境的藝術手法發展成為一種融入了“中國民間傳說、歷史和當代社會”所建構出的凸顯中國民族美學要素的幻覺現實主義美學風格。
魔幻現實主義和幻覺現實主義美學需依托公認代表其美學的作家馬爾克斯和莫言的作品來具象呈現其生產肌理,所以依據文學創作原理從“習慣選擇的故事類型”“處理這個故事的方式”“敘述這個故事時運用的形式等”因素所營造出的“獨特的腔調”,比較作家文學生產的價值觀、文學生產的美學路徑、文學生產的本土化策略。本文基于這三個維度論述經典魔幻現實主義和幻覺現實主義文學生產肌理的不同美學旨歸。
文學生產的價值觀:“舉重若輕”與“舉輕若重”
文學生產的價值觀決定了作家文學生產的價值取向,它在馬爾克斯和莫言對文學生產資料上所選擇和處理的敘事立場中反映出來。他們分別截取了社會現實的兩端,莫言選擇發生在社會底端民間的故事,而馬爾克斯選擇社會頂端的權力階層。在敘事立場上,莫言運用普世情感支撐起自己的民間敘事立場,盯著正史所輕視的人寫,寫他們的現實處境,寫他們人性中的崇高、偉大,把他們被壓抑、被忽視,甚至被遺忘的聲音從傳統高雅文化的層層遮蔽下透射出來,這種舉輕若重的責任感成為莫言作品的現實力量之源。而馬爾克斯則以剖析拉美民族政治獨裁統治的精英立場,錨定舉足輕重的重要人物,穿越權力的重重迷霧,揭示出這些人的殘暴虛偽、孤獨膽怯、荒誕猥瑣,對擁有至高獨裁權力帶給民族深重災難的他們進行戲謔與嘲諷,在沉痛的歷史現實深處傳遞給讀者舉重若輕的氣度。
文學生產的美學路徑:自出機杼與破繭化蝶
馬爾克斯和莫言通過創作個性實現各自美學的經典化,這兩種美學特色主要由作家的本土文化背景及其自身文學素養兩大因素的化學反應來成就的,而這兩大元素的特點可以概括為“混雜”和“系統”。如果說系統和混雜的本土文化生態塑造了莫言和馬爾克斯的文學生產審美意識,那么混雜的和系統的文學修養則催化了莫言和馬爾克斯的個性審美路徑的走向。馬爾克斯的本土文化背景是混雜多元的,文學修養則是系統的。多元文化賦予他感性的自由,系統修養賦予他嚴謹的歐洲式理性。他以西方美學價值觀與方法論理性審視這個土著文化、歐洲文化、非洲文化乃至東方文化交融混雜中的美學樣態,找到以魔幻統籌審美、催化藝術、詩化現實的力量,從而自出機杼,析出代表拉美文學巔峰的魔幻現實主義經典美學。而莫言的本土文化背景是系統的,文學修養是混雜零散的。系統的中國悠久文化不知不覺中潤染了莫言的美學底色。混雜的文學素養留給他不畏經典束縛的自由天性,讓他后來沒有受到本土文學經典系統性的限制與禁錮,也沒有在西方文學強大的影響下失去自我。所以面對厚重的傳統,莫言既順應也破壞,既解構也重構,但從未動搖其傳統儒釋道美學思想的基礎;面對蜂擁而入的西方文藝思想,他先拿來,再改造,再制造。這種對傳統的和外來的大膽借鑒、大膽實踐、大膽表達的氣度,決定了他在破中探索出擁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莫氏美學路徑,通過破繭化蝶蛻變出當今世界文壇代表中國美學意蘊的幻覺現實主義。
文學生產的本土化策略:“移植”與“嫁接”
在世界文學共和國中,魔幻現實主義和幻覺現實主義美學都以民族特色見長,其生產策略都明顯呈現對外來文學的本土化趨勢。橫向地看,這種趨勢的背后與世界政治、經濟發展所推動的跨文化交流版圖延伸密切相關。縱向地追溯,馬爾克斯代表的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本土化的質料主要來自歐洲文學,尤以超現實影響顯著;而莫言的幻覺現實主義本土化的質料則來源更廣,可以說是社會學意義上的整個西方文學,不過以接受魔幻現實主義影響最受關注。外來元素的汲取既有利于促進本土文學的發展,也有利于本土文學的世界接受,馬爾克斯和莫言的成功都不同程度地受益于此。比較它們的本土化策略,我們采用“移植”與“嫁接”這對植物學上的概念來描述。移植指將植物移動到其他地點種植;嫁接是把一種植物的枝或芽嫁接到另一種植物的莖或根上,使接在一起的兩個部分長成一個完整的植株。馬爾克斯筆下的隱喻、創作手法無不可以找到歐洲的根脈。他正是將這些歐洲理性移植到拉美的感性文化與美學土壤中,培育出魔幻現實主義美學之花。莫言的美學則一直植根于中國本土文化土壤中,即使接受的外來影響都是翻譯的,而翻譯后的西方文學在莫言看來已然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所以這注定了他在本土文學審美的枝干上嫁接外來美學的枝芽,催生出今天幻覺現實主義的碩果。可見莫言文學生產肌理構成以本土為主,外來為輔,馬爾克斯則恰恰相反。這樣本土和外來兩方面因素的融合模式決定了他們文學生產美學的不同樣貌。
這兩種策略直接影響了他們作品的世界接受。莫言多依托本土歷史事件,以此開掘人類集體無意識的引發共鳴,但基于歷史的建構往往提高了跨文化理解的難度,讓作品的傳播遭遇困境,這也是其譯者葛浩文的感受。而馬爾克斯則跳出歷史,在建構微觀生活時空里投射拉美歷史,將讀者的期待視野建立在行動的演繹中,這極大減少了閱讀背景知識的阻礙,便利了其作品的世界性傳播。
綜上所述,從魔幻現實主義與幻覺現實主義概念沿革,可見出這組概念自產生到進入文學生產的曲折歷程,發現歷史和時代因素已無法界定其統一的內涵,但民族性成為他們的歸屬港灣。馬爾克斯和莫言的文學生產實踐推進了魔幻現實主義與幻覺現實主義的經典化,讓兩種現實主義文學生產及其肌理的分析與比較有了代表性的文本支撐。從中可見,這兩種美學都扎根于民族本土心理現實傳統,馬爾克斯給混雜與狂歡的拉美文化以理性,重在拉美美學體系的建構;莫言對固若金湯的傳統價值體系以挑戰與突破,重在張揚其個性的美學重構,在這里它們“舉重若輕”與“舉輕若重”的文學生產價值觀、自出機杼與破繭化蝶的文學生產美學路徑、移植與嫁接的文學生產本土化策略得以辨識和歸納,進而使讀者得以更深入地理解兩種文學生產的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