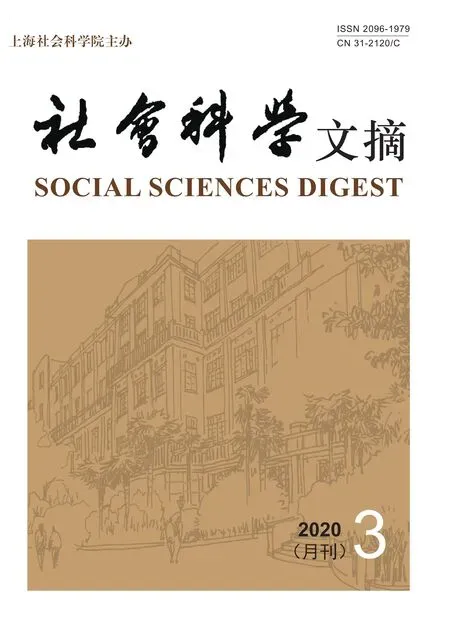監察法與刑法的關系梳理及其癥結應對
隨著最新憲法修正案與監察法的頒布實施,監察運行的合憲性與合法性得到了保證。在此前提下,監察法與其他部門法如何有效銜接,是監察法出臺后應當關注的重心。這一問題如何解決會對監察法運行及其監察體制改革的成效帶來直接的檢驗。基于此,需要以監察法與刑法之間的關系為視角,對這兩部法律之間的關系進行學理檢視,并在厘清彼此關系的基礎上對國家監察全覆蓋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適用癥結予以考察并給出相應見解。
監察法與刑法的內在關系及其厘定
(一)作為憲法性法律的監察法與刑法之間的協同關系
厘定監察法與刑法的關系,首先需要澄清的問題是,二者在適用中的位階關系如何。如果我們只是看到二者在合憲性層面的一致性,而不回答上述問題,那么一旦在實踐中產生疑問,則無法根據彼此間的共性特征得出答案。
“國家監察法是國家監督領域的基本法,屬于憲法性法律。”之所以認為監察法屬于憲法性法律,原因在于監察法涉及權力運行的結構性調整。在監察委員會確定下來之后,原有的“一府兩院”變為當下的“一府一委兩院”,新設的“監察委員會”這一權力機構得到了修正后的憲法確認,其政治機關與政治權力的屬性已經體現。而刑法是以犯罪與刑罰為核心內容的法律規范,以刑事責任追究為重心。監察法的政治權力與國家機關運行的特性決定了其要劃歸為憲法性法律,而以司法權力為依托和罪刑規范為內容的刑法則屬于基礎性法律。
雖然監察法和刑法都以憲法作為自己立足于法律體系的法律根據,但是這一共性特征仍然無法識別監察法與刑法的差異。監察法之所以歸入憲法性法律是由于監察法是對憲法原則條款的細化。而刑法之所以被認為是基礎性法律是因為它牽涉到社會關系的方方面面。我們不能把“憲法性法律”等同“憲法”。無論是憲法性法律還是基礎性法律,都是由最高權力機關頒行實施的規范性法律制度,在適用中不存在“誰優于誰、誰服從誰”的問題。憲法性法律只是說明其與憲法權力運行上的關系直接,并不由此說明效力上的層級。作為基礎性法律的刑法需要認同憲法性法律的權力架構與運行機制,憲法性法律也要在基礎性法律的框架內相互協調和規范實施,而不能產生直接或者間接的抵牾。因而在監察法與刑法的關系層面上二者并不存在法律位階問題。
(二)監察法之下的職務犯罪調查需要在刑法的框架內運行
監察委員會作為分散式反腐向集中式反腐的機構創設,其統轄了職務違法與職務犯罪調查的一體化處置,因而相比于檢察機關之前的反貪瀆職機構,監察委員會成立之后的法律活動領域更寬。因此監察委員會適用的規范依據并不以刑法為全部,而囊括了與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等有關的所有規范。盡管監察法與刑法的關系只是所涉法律關系的一部分,但由于對公權力人員職務犯罪的調查需要刑法的規制,因而監察法與刑法必然發生關聯。這一內在關聯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其一,監察法的實踐運行應當遵守刑法基本原則。監察法賦予了監察委員會查處職務犯罪的權力,這一權力的運用與正當行使脫離不了刑法的制約。而且,罪刑法定原則作為當代法治社會的限權原則,監察委員會對職務犯罪的調查必須在刑法基本原則下行事。
其二,依據監察法查處的職務犯罪需要根據刑法認定。監察委員會查處的職務犯罪追究刑事責任要根據刑法予以判斷。刑法是界定犯罪與刑罰的法律,罪與非罪的認定都不能脫離刑法。刑法在監察法的實施過程中起到案件性質的界分功能,并引導監察委員會根據刑法對職務犯罪作出判斷,根據刑法涉及的刑罰輕重對應后期的司法級別管轄。
其三,監察委員會行使監察職權時受制于刑法的規制。監察法賦予了監察委員會相應的權力,但是監察委員會自身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這不僅是權力與義務的對等性原則決定的,更是法治環境下權力行使的正當性與有限性決定的。刑法此時發揮的現實功效,不能理解為刑法對監察法的反向制約性的體現。因為刑法對監察主體的刑責追究是為了保證監察權的正當行使,并不是為了制約監察機關的監察權。
監察法實施與刑法適用中的癥結問題梳理
“監察法的制定,標志著反腐敗法律制度體系的骨架已經搭建完成。”監察法的生命在于實施,監察運行是實體與程序的一體化銜接及其運行。既然監察法與刑法之間存在內在關聯,那么監察法的運行與現有刑法的罪刑規范及其適用能否契合則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一)監察法實施對不同身份混合性共犯案件的查處
監察法第十五條列舉了監察對象,這些對象均具有公權力的特殊身份。監察主體對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進行監督、調查、處置。然而在監察法的實施過程中,如果系不同身份組合而成的共同犯罪,此時是否統一受制于監察法、是否由監察委員會統一調查就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監察法對調查對象的規定仍然主要是就單一主體身份的違法犯罪而言的。但是,就實踐中職務犯罪的類型來看,共同犯罪不在少數,尤其是非身份的共犯。如果非國家工作人員在共同犯罪過程中起到了主犯的作用,而且最終定性將以非公權力主體構成的犯罪論處,此時監察機關有調查權嗎?在監察留置權與監察對象的規定不對應的前提下,如何理解監察法的立法規定、如何通過刑法的共同犯罪予以梳理、監察委員會啟動自身的監督調查權有無正當性根據等方面的困惑仍然存在。
(二)監察法實施對職務與非職務犯罪并罰案件的查處
在監察對象涉及職務犯罪的情形下,這一超越職權的嚴重危害行為屬于監察法的適用范疇。問題是監察對象觸犯混合性質數罪的案件類型客觀存在,此時在同一行為人既有職務犯罪又有普通犯罪時,究竟是由監察委員會行使監察權一并查處職務犯罪與普通犯罪,還是由監察委員會與普通偵查機關分別行使自己的職責?
監察法第四條規定:“監察機關辦理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案件,應當與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執法部門互相配合,互相制約。”該條款指出了監察機關與其他司法機關和執法部門存在的聯系,但需要明確的是,這一規定并沒有陳述監察委員會可以查辦非職務犯罪案件。如果被調查人因職務犯罪案件查處的同時又發現有普通刑事案件的,此時作為數罪并罰的案件該非職務類刑事案件究竟應由誰來進行案件的查處呢?
(三)監察調查時職務違法與職務犯罪案件的時效適用疑惑
監察法的實施為監察委員會多種法律措施的適用提供了依據。監察法規定,監察委員會可以行使12種調查措施:談話、訊問、詢問、查詢、凍結、調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驗檢查、鑒定、留置。除了留置之外,前面的11種都是之前的反腐機構有權采用的措施。監察法賦予監察委員會的調查權有其特殊性,這一調查范疇包括了職務違法與職務犯罪不同性質的案件,因而從適用類型上就可看出“監察調查”并不等同于“司法偵查”。監察委員會的調查權是否受制于刑法規范的限制,還需要考量刑法規定的時效制度能否得以適用的問題。在當下的職務違法并不需要適用時效制度的前提下,職務犯罪的調查是否適用時效制度的爭議就必然存在。
(四)監察法實施中監察違法類型與刑責追究的困惑
監察法并沒有明確劃定監察委員會及其工作人員的屬性。由于監察委員會已經納入憲法明確規定的國家機構之中,因而其作為特殊類別的國家機關并不存在障礙,監察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自然應歸屬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但按照現有對監察委員會特殊政治機關的性質定位,不能把監察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劃歸到司法工作人員或行政執法人員的范疇。這就導致在刑法既有的職務犯罪中,由于并不是籠統地以國家公權力人員進行主體限定,因而如果涉及監察委員會及其工作人員的刑事責任追究,在刑法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所作的罪名劃分中,原有的刑法罪名能否對其適用就必然是一個現實問題。
(五)監察法中的職務犯罪與監察調查管轄的范疇問題
在監察法第三條規定了監察委員會作為監察專責機關,要對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進行調查。第三條同樣提到監察委員會“依照本法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進行監察”。因而,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進行監察是監察法總則中的明確表述。需要明確的是,“監察”與“調查”本身意義并不等同。“調查”的核心是就已經發生的違法犯罪行為進行回溯性的證據搜集,為下一步的責任落實提供基礎。“監察”的范圍要寬泛得多,結合第十一條的規定來看,包括了對公職人員廉政教育、履職用權、廉潔從政、職業道德操守等方面的監督檢查;對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的調查;對違法公職人員進行政務處分,對履職不力或失職失責的領導人員進行問責,涉嫌職務犯罪的向檢察院移送,向監察對象所在單位提出監察建議等。
在現有監察法未直接界定職務犯罪的前提下,在實施過程中,必然要參照刑法的規定進行考察,并在內涵劃定的前提下,進一步厘定職責范疇與調查范圍。但“法法銜接”牽涉到多元法律之間的關系,而且刑法作為基礎性法律具有自身的運行機制與目的歸宿,監察法中的語詞內涵與刑法中的規范所指是否完全一致,乃至刑法中所言的“職務犯罪”是否全部均要劃入到監察委員會的調查范疇,仍然值得考量。
監察法實施中所涉刑法適用問題的解決思路
監察法實施之后的刑法適用銜接,已經成為現實問題。筆者認為,在充分揭示監察法后續實踐運行可能存在問題的基礎上,具體考量監察法與其他法律之間的關系,認真審查彼此之間銜接中的瓶頸及其癥結所在,合理化地提出相關建議并順利推進監察全覆蓋向縱深方向發展。就前述指出的問題來看,我們應當在類型化審視與法治化思維的基礎上提出對策。
(一)不同身份的混合性共犯并不影響監察委員會的職權行使。在不同身份混合形成的共同犯罪中,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模式。一種是涉及職務犯罪的,由監察委員會進行調查,而非職務犯罪的,則由公安機關偵查。另一種是只要涉及不同身份的混合性共同犯罪,一旦其中摻雜著職務犯罪的,則無論是職務還是非職務犯罪,都應由監察委員會調查。筆者認為,盡管不同身份的混合性職務犯罪案件有一定的復雜性,但職務主體與非職務主體共同實施的犯罪仍然屬于職務犯罪,因而應以監察委員會統一行使調查權為優先。盡管在非公權力身份主體實施的犯罪中,該犯罪的主體身份及其對應的罪名都不是典型的公權力犯罪類型,但由于共同犯罪的存在,致使非公權力身份主體與有公權力身份的職務犯罪之間的結合,此時非身份者已經融入到有身份者構成的職務犯罪之中,在規范評價層面就有了構成要素意義上的職務主體身份,所以對監察全覆蓋所要求的“公權力”正當行使來說,統一于監察委員會的調查管轄有其必要性。
(二)同一主體的職務與非職務并罰案件需謹慎區別對待。具體到監察對象的同一主體上面,職務犯罪與非職務犯罪也同樣存在,此時就職務犯罪的調查來說,監察委員會當然有權履行監察職責。問題是監察對象作為公權力人員也完全可以實施一般刑事案件,這涉及監察權如何行使的問題。筆者認為,問題解決的著眼點在于合法行使監察委員會的正當權力,以及職務犯罪調查與普通刑事案件偵查之間的有序化運行。監察委員會的成立并不意味著監察權可以替代普通刑事案件的偵查權,在監察權規范運行的框架內,仍然需要合理協調監察權與偵查權之間的關系。我們仍然要強調監察權之于職務犯罪調查的核心范疇,不能因為主體同一而以監察權替代刑事司法偵查權。因而,不能認為監察權可以一并性地代替其他刑事偵查權。
(三)監察法實施中職務違法與職務犯罪時效適用的差異審視。監察法的實施是否需要評判刑法的追訴時效,是監察委員會行使檢察權過程中需要直接面對的核心問題。因為追訴時效與國家機關的追訴權緊密相關,如果案件調查時已超過刑事追訴時效,則要么已經喪失權力啟動根據,要么欠缺追究刑事責任的必要,職務犯罪的后續程序推進必將因追訴權的根基不穩而面臨終止。筆者認為,在監察法的實施中監察委員會的職務犯罪調查必須遵守刑法追訴時效,不能因為“政務處分”沒有時效,從而否定職務犯罪監察調查中的時效。刑事責任與政務處分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法律責任,不能因為后者沒有時效而據此否定對職務犯罪的時效考察。認可時效在職務犯罪調查中的適用,其初衷并不是為了限制監察權的運行,而是因為監察委員會的調查是國家公權力的運行方式,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權力介入來查處涉嫌職務犯罪的行為人。在現有的規則層面,職務犯罪的監察調查并不等同于普通案件的偵查,但是由于二者均有求刑權的特質,在權力行使的層面仍然能找到相同點。因而在監察委員會對職務犯罪調查的追訴權客觀存在的前提下,監察委員會的調查啟動應當受制于追訴時效的限制。
(四)監察主體違法類型的刑責追究要契合刑事法治原則。監察法賦予監察委員會之下的工作人員合法的監察權限,因而監察委員會的履職人員是作為監察主體而存在的。而監察主體也有適用刑法的可能,監察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不能因為新型國家機關的類型而超越刑法。監察法實施之后的監察委員會的特殊性質會帶來刑法具體罪名適用上的非一致性,此時基于罪刑法定原則的束縛,不能為了強調懲罰而肆意用刑,也不能為了強調特殊性而法外開恩。此時,在監察法的適用中必須按照刑法基本原則行事,不能基于政策性因素或者監察權的特殊性而隨意曲解罪刑法定原則。出于對監察法實施的規范性與法治運行順暢化的考量,在監察法中列舉的監察違法類型是否全部納入刑法范疇,不能一概而論。因為監察法設置監察主體的違法類型是為了保證監察權的正當運行,而不是為了強調刑事處罰的必要性。
(五)監察實踐中職務犯罪與監察管轄的合理確定。所有的犯罪都脫離不了刑法的規范框架,在理解監察法中的“職務犯罪”時不能偏離刑法的已有規定,這是罪刑法定原則的應有之義。就現有監察全覆蓋的對象來看,顯然是以擁有國家公權力的主體身份來劃定的。如何確立監察范圍并保證監察機制的良好運行是當下工作的重心。監察權的權威與公信力一定是要通過實踐運行得以確立的。盡管“職務犯罪”的外延源于刑法規定,但溯及刑法的現有規定只是解決了“職務犯罪”究竟有哪些的問題,并不能得出刑法中所有的職務犯罪均是監察管轄范疇。監察體制的改革并不是單方面進行的,它與當下的司法體制改革及其相關機關的職能劃分同樣存在關聯。由此可見,在監察法的現實運行中,我們不能忽視監察法、刑法與其他法律之間的內在聯系,畢竟,監察體制改革中的“法法銜接”并不單純地局限于刑法這一部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