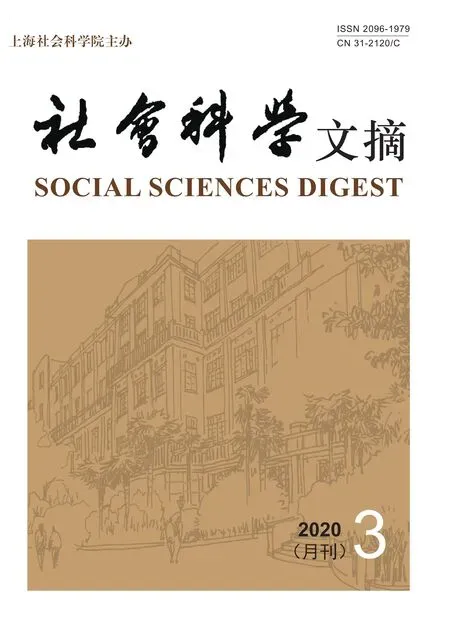論未成年人致人損害的賠償責任
《侵權責任法》第32條關于非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致人損害的賠償責任的規定,在法理和法技術上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無論采取何種解釋思路與方法,都難對它作出周全、合理的解釋。值此為編纂民法典而將《侵權責任法》修改轉變為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的立法契機,系統反思《侵權責任法》第32條并由此提出立法完善建議,顯得十分必要。
《侵權責任法》第32條規定的法理和法技術反思
縱覽現有相關研究,《侵權責任法》第32條主要存在如下值得檢討之處。
第一,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與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予以等同對待。根據《民法總則》第19條、第22條,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實施純獲利益的民事法律行為及與其年齡、智力、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民事法律行為,享有一定的意思能力。意思能力是一種內在秉賦,無論一個人置身于民事活動的哪一個領域,作為其行為基礎的意思能力,本質上是統一的、一致的。既然限制民事行為人在民事法律行為領域內具有一定的意思能力,那么當其做出像侵害他人權益之類的有意識舉動時,認為其根本不具備辨識能力,無侵權責任能力,既不符合常理常情,又違背法理與法律邏輯。第二,與有關未成年人保護的其他法律規定在內在規范體系上嚴重失衡。根據《刑法》第17條,已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在現代法律體系下,刑法與侵權責任法依公、私法理念之不同,在規制不當行為上,可以并行發揮作用。對于一種致人損害的行為,如果認定行為人應為其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對于由該行為產生的民事賠償,會被認為行為人具有侵權責任能力。由于侵權損害賠償主要是為了補償受害人受損害,所以即使行為人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但是對于其行為產生的損害后果,為救濟受害人之故,可能會被認為其具有侵權責任能力。我國《刑法》第36條、第37條對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的此種關聯關系作了明確規定。第三,在法律理解適用上存在諸多悖論。根據《侵權責任法》第32條第2款,未成年人有無財產是其應否為自己的致害行為“支付賠償費用”的決定因素。這種僅以有無財產及財產多寡決定未成年人的賠償責任及責任輕重的規定,不僅嚴重偏離現代侵權法的基本歸責思想,而且會使監護人的法律責任因被監護人有無財產而發生畸輕畸重的后果。第四,嚴重忽視對未成年人責任意識和責任能力的培養。《侵權責任法》第32條把未成年人幾乎完全當作一個不對自己行為負責的受保護者。這種不分情況地的過分保護,既不利于未成年人樹立良好的行為觀念和責任意識,又不利于經由社會交往的積極與消極磨練而使未成年人的社交能力、獨立人格得到健全發展。
未成年人致人損害的侵權責任能力規范方法
未成年人是成長中的市民,其意思能力處于漸進發展中,無法像成年人那樣理性、安全地待人接物。即使父母或其他監護人能夠給予適當的教育、照顧、引導或保護,未成年人也難免會在必要的社會交往中因一時沖動、意志力薄弱、判斷力匱乏等,做出致人損害的舉動。如何規范未成年人致人損害的舉動是一個極具一般性的法律問題。由比較法看,在規范未成年人致人損害的賠償問題上,主要存在三種規范模式。
其一,不對加害人作成年人與未成年人區分的概括立法模式。該模式的特色是,未將未成年人的責任能力作為一個特殊法律問題,統一對待未成年人與成年人的致害行為。《法國民法典》的規定最為典型,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的規定也頗具特色。其二,對加害人作成年人與未成年人區分的特別立法模式。在這種立法模式下,侵權責任能力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概念。這種立法模式可在《德國民法典》與《日本民法典》之間作出細分。《德國民法典》第827條與第828條對精神障礙者(成年人)與未成年人的侵權責任能力進行了區分規定。其三,對加害人作低幼未成年人與其他自然人區分的特別立法模式。此種立法模式的重要特色是,以年齡為標準將未成年人的侵權責任能力區分為兩類:低于特定年齡的未成年人絕對無侵權責任能力;高于特定年齡的未成年人與成年人一樣一律具有侵權責任能力。1964年《蘇俄民法典》第450條、第451條即是如此規定的,新《荷蘭民法典》第6:164條和第6:165條的規定屬于最新典型立法例。
對于未成年人致人損害的舉動,無論哪一種立法模式無不承認未成年人應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賠償責任。各個立法模式之間的差異,僅表現在未成年人應在多大程度上承擔賠償責任。《侵權責任法》第32條所采不管未成年人年齡大小、有無辨識能力原則上不對自己的致害行為承擔賠償責任的立法方法,在比較法上屬于異常類型。
未成年人致人損害的其他賠償責任機制
從規范功能上講,未成年人有無侵權責任能力僅僅解決了未成年人應否對其致害行為承擔賠償責任的問題,并不能解決未成年人致人損害所引起的所有賠償問題。需要一并思考的是:如果認為未成年人具有侵權責任能力,這種侵權責任能力是針對于所有未成年人,還是僅針對于部分未成年人。如果針對于所有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應給予特別保護的法政策應如何貫徹。如果僅針對于部分未成年人,應如何保護無法由未成年人得到賠償的受害人。調整這些法律問題的法律規定與關于未成年人是否具有侵權責任能力的規定,以未成年人致人損害問題的法律調整為中心,構成一個富有邏輯關系的規范體系。
體系地看,在對未成年人是否具有侵權責任能力作出回答之后,一些典型立法例對于未成年人致人損害的責任后果還相應地作出以下規定:
第一,父母或監護人和未成年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在法國民法模式下,未成年人應像成年人一樣就其客觀不當行為向受害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為不使未成年人承受過重的賠償責任,同時也防備發生因未成年人缺乏必要的責任財產而造成受害人無法得到救濟的后果,法國于1970年在其《法國民法典》第1384 條增補一款(第4款)規定:父與母,只要其行使對子女的照管權,即應對與其一起居住的未成年子女造成的損害,連帶地承擔責任。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第187條第1款也明確規定,有識別能力的未成年人與其法定代理人對未成年人的致害行為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同于法國民法的是,臺灣地區“民法”第187條第2款規定,法定代理人如其監督并未疏懈,或縱加以相當之監督,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負賠償責任。該規定只向法定代理人施加了一種過失推定責任。
第二,監督義務人負擔嚴格責任或過錯推定責任。這存在兩種規范方法,即法國民法的嚴格責任與德國民法的過錯推定責任。在法國,如果未成年人未與其父母一起居住且不處于父母照管權之下,根據《法國民法典》有關親權和未成年人監護的規定,行使親權的父或母及行使監護權的其他機關或個人,負有教育、保護未成年人的職責。此種監管權之下的未成年人致人損害的,除未成年人本身應按照《民法民法典》第1382條的規定對其客觀不當行為向受害人承擔賠償責任外,《法國民法典》第1384條第1款也向對未成年人負有監管義務的機關或個人強加了嚴格賠償責任。《荷蘭民法典》第6:169條第1款向對不滿14歲的未成年人行使親權或監護權的人規定的監管責任,同樣是一種不問監管人是否存在監管過錯的嚴格責任。《德國民法典》第832條對于監督義務人的賠償責任,在歸責原則上采用過錯推定原則。《荷蘭民法典》第6:169條第2款就已滿14歲未滿16的未成年人過錯致人損害而向其監管人(親權人或監護權人)施加的侵權責任,也屬于一種過錯推定責任。《日本民法典》第714條同樣向對未成年人的監督義務人強加了一種過錯推定責任。不同于《德國民法典》與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的是,《日本民法典》第714條規定的監督義務人的過錯推定責任,是以“無責任能力人不負責任的情形”為適用前提的。這一限制條件對受害人甚為不利。
第三,無識別能力的未成年人與其法定代理人的衡平責任。當無識別能力的未成年人不對其致害行為向受害人負賠償責任,而監督義務人又可以盡到監護職責而免責時,如何救濟受害人?對此,《德國民法典》(第829條)及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187條第3款)特別規定了一種衡平責任,即當未成年人不負賠償責任且監督義務人能夠舉證免責時,受害人仍然可以依據法律的特別規定,要求有財產的未成年人承擔賠償責任。臺灣地區“民法”第187條第3款也作了類似于《德國民法典》第929條的規定。對于監督義務人的賠償責任采納過錯推定責任的《日本民法典》,雖然沒有特別規定衡平責任,但日本民法學說依據《日本民法典》第709條發展出了監督義務人不管被監護人有無責任能力皆應向受害人承擔賠償責任的監護人固有責任論的解釋意見。
規范未成年人致人損害之賠償責任應注意的區分性思維
以上對未成年人致人損害問題規范方法的系統分析,為如何完善《侵權責任法》第32條提供了比較規范的法學思維方法。
首先,應區分規定民事行為能力與侵權責任能力。從比較法上看,除《法國民法典》外,鮮有國家或地區的民事立法或判例不對民事行為能力與侵權責任能力作出區分規定。侵權責任能力是在判斷一項致害行為是否構成一般侵權行為之前予以適用的。侵權法之所以對侵權行為以行為人是否具有侵權責任能力予以先行判斷,是為了對辨識能力較為薄弱的未成年人或具有精神障礙的成年人予以特別保護。這是侵權責任能力與民事行為能力制度的相似之處。但是,在落實未成年人保護政策上,侵權責任能力與民事行為能力之間存在顯著差異。概言之,無民事行為能力制度對未成年人提供了絕對保護,限制民事行為能力制度向未成年人提供了一種優于交易相對人的特別保護。然而,對侵權責任能力制度來說,雖然也存在低幼未成年人不具有侵權責任能力的立法例,但此種立法并不意味著未成年人必然會獲得絕對保護。根據一些國家或地區的民法,當受害人無法由監督義務人獲得適當救濟時,無侵權責任能力的未成年人應當依其財產狀況向受害人承擔衡平責任。侵權責任能力與民事行為能力制度之所以在未成年人保護上存在明顯不同,主要是因為這兩種制度在社會意義和適用領域上具有巨大差異。
其次,區分未成年人的侵權責任能力與具有精神障礙的成年人的侵權責任能力。近現代民法典在規定侵權責任能力上,通常在致害主體上作未成年人與成年人的區分。《德國民法典》對具有精神障礙的成年人的侵權責任能力作出規定后,把未成年人的侵權責任能力區分三種類型作了明確規定。以辨識責任能力為標準概括規定侵權責任能力的《日本民法典》,同樣采取了區分未成年人與成年人而分條加以規定的做法。新《荷蘭民法典》以14歲為標準將自然人的侵權責任能力區分規定為:不滿14歲的未成年人無侵權責任能力;14周歲以上的自然人,不管是未成年人還是成年人,具有侵權責任能力。臺灣地區“民法”第187條關于侵權責任能力的規定較為獨特,它以識別能力概念為基礎、以無行為能力人及限制行為能力人的概括表達方式,對自然人的侵權責任能力作出了概括規定。
最后,區分未成年人的賠償責任與父母或監護人的賠償責任。侵權責任能力制度僅解決了未成年人應否對自己致人損害的舉動向受害人承擔賠償責任的責任主體性問題,沒有一并解決未成年人致人損害所引起的所有損害賠償問題。因此,為實現受害人保護的規范目的,在對未成年人的侵權責任能力作出規定之后,必須進一步對未成年人負有監督義務的人的監管責任作出明確規定。如果像《德國民法典》那樣規定監督義務人僅負有過錯推定責任,仍需進一步思考:當未成年人與監督義務人皆不承擔賠償責任時,如何救濟受害人所受損害。《德國民法典》及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為此確立了衡平責任制度。
我國《侵權責任法》第32條同樣可以在區分監護人與被監護人的衡平責任的框架進行解釋。其第1款向監護人強加了一種介于嚴格責任與過錯推定責任的特別賠償責任。監護人責任的減輕,難免會使受害人得不到充分救濟。針對這一問題,以衡平責任為基礎解釋第2款規定可以取得較為合理的體系效果。因此,從規范架構上講,《侵權責任法》在規范未成年人致人損害的賠償責任上所存在的根本問題實質上表現為,沒有對未成年人的侵權責任能力這個基礎性、前提性制度作出明確規定。
未成年人致人損害之賠償責任的立法建議
在法律解決未成年人致人損害的賠償責任問題所形成的規范群中,未成年人是否具有侵權責任能力的規定是一項基礎性規范,是親權人或監護人所負賠償責任(監護責任)及未成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所負衡平責任的邏輯前提。從比較法上看,無論未成年人是否具有侵權責任能力,未成年人的親權人或監護人都必須對未成年人致人損害的行為承擔賠償責任。親權人或監護人所負賠償責任在法國、荷蘭被規定為嚴格責任,在德國、日本及臺灣地區被規定為過錯推定責任。親權人或監護人承擔的賠償責任是落實未成年人保護政策的一個關鍵環節。從親權人或監護人所負過錯推定責任根本無法明確推斷出,未成年人是否具有及具有怎樣的侵權責任能力,因為同樣規定親權人或監護人應負過錯推定責任的《德國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及臺灣地區“民法”,在未成年人的侵權責任能力這個基礎性規范上,提供了三種迥然有別的規范模式。因此,完善《侵權責任法》關于被監護人致人損害的賠償責任制度時,最為必要的舉措應當是,對未成年人的侵權責任能力作出明確規定。
在規定未成年人的侵權責任能力上,民法典應以意思能力或理性能力概念為中心,使各種有關未成年人保護的法律規定在內在體系上保持一致,同時應注意侵權責任能力在落實未成年人保護政策上的局限性,并由此顧及規范設計的多層次性。
《侵權責任法》關于未成年人致人損害的賠償責任的規定在很多方面比較類似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的規定,重構未成年人致人損害的賠償責任的規范體系時,借鑒臺灣地區“民法”第187條第1款,明確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侵權責任能力,其實是最為便宜的立法完善方法。具體建議為:在《民法典侵權責任編(草案)》(二次審議稿)第964條(《侵權責任法》第32條)增補一款作為第一款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能夠證明行為時無辨識能力的,不承擔侵權責任。《侵權責任法》第32條應相應地作出如下修改: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監護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監護人盡到監護責任,或者即使適當履行監護職責,損害仍會發生的,不承擔侵權責任。受害人不能得到損害賠償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及其監護人應根據其經濟狀況向受害人承擔全部或者部分賠償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