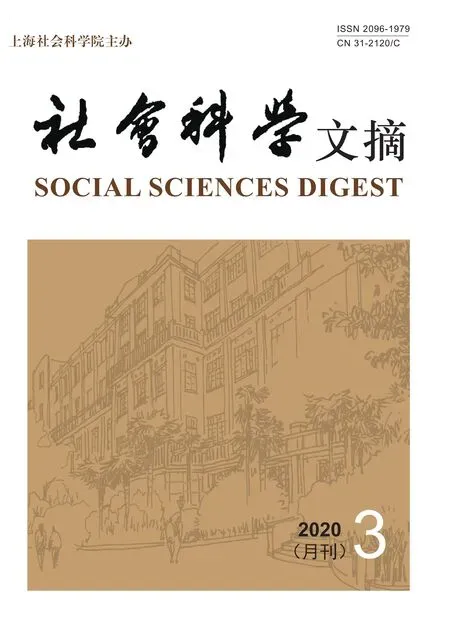簡帛文獻與中國早期史學史研究
目前已發現的簡帛文獻中,有不少與史學史直接相關的內容,如清華大學收藏的楚竹書《系年》,記錄了從西周至戰國早期的歷史,是一部帶有獨特編纂意識的史書,讓我們看到了戰國史學的某種原始形態,對中國早期史書的形成也有更為直接而深入的了解。清華大學所收藏的楚竹書《楚居》《良臣》及睡虎地秦墓竹簡《葉書》等史篇,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國早期史學中“世”類史書的某種形態,推進了關于《世本》成書及來源的認識,有助于深入思考《世本》與《史記》的關系。馬王堆漢墓帛書《春秋事語》和清華簡《越公其事》等大量“語體”類文獻,不僅對《國語》的形成背景、史學價值的認識有裨益,而且豐富了對中國早期史學中“語”類史書敘事的了解。因此,可以說,簡帛文獻中的史類文獻,從某一層面再現了戰國史學的繁榮,拓展和豐富了我們對中國早期史學史的認識。
《系年》與中國早期史書的編纂
大量簡帛史類文獻發現之前,研究中國早期史學所能夠利用的史料,不外乎《春秋》及“春秋三傳”、《國語》《戰國策》《竹書紀年》《世本》等。而《左傳》《國語》《戰國策》,滲入了戰國之后的編纂因素,很難再現春秋戰國史書的原始形態。《竹書紀年》雖是西晉時汲冢墓出土的一批竹簡,但緣于當時的保護條件,傳世的只是清人輯佚出來的一部文獻。《世本》同樣具有這方面的窘境,且有更多的爭議。在這種情況下,20世紀以來出土的簡帛文獻,特別是近些年發現的史類文獻,對于我們了解和認識春秋戰國史學的歷史面貌和史書的形成及原始形態,便顯得尤為珍貴。
清華簡《系年》是繼《竹書紀年》之后又一部新發現的戰國史書,被學界譽為中國史學史上的重大發現。的確,《系年》所展現出來的史書編撰、敘事風格、著史觀念,既反映了戰國史學的共性,又有自身的獨特性。如果對清華簡作整體性審視,更有助于認識這一點。
史書的編纂,是史學成果最便于集中體現的所在,也是傳播史學知識的重要的途徑。中國的史書編纂,多講史體和史例。從《系年》整體敘事來看,它是遵從編年記事這一早期史體的。《系年》有兩種編年記事形式:第一種是明確“表年以首事”,不過往往用某年的時間坐標書寫兩年或多年的歷史,這一現象在《系年》中是常例;第二種是以世系為序進行書寫,其中有的文中還有明確紀年。雖然《系年》沒有嚴格按照“通比其事,列系年月”或“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這一成熟編年體編纂原則進行書寫,但我們不能由此而否定《系年》為編年體史書這一判斷,只能說它是一種編年體早期史書的代表,與《漢紀》這樣成熟的編年體史書是有差距的。
如果從戰國史學的發展特點和歷史地位來看,顯然這種認識也是成立的。白壽彝在談到先秦時期史學發展特點時說:“所有這些,說明史學的一些主要方面都已經有了,但基本上都還處于早期狀態,還沒有達到成長的階段。”這就是白先生提出的“中國史學的童年”。顯然,我們不能拿成長階段的編年體編纂原則與童年時期的編年記事作對等評判。
有學者認為《系年》是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說《系年》的出土,無疑具有改寫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史的重大意義,恐怕言過其實。從史例層面言,紀事本末書寫手法(簡稱紀事本末法)在中國早期史學發展中是常見的。《國語》就提供了紀事本末法敘述歷史的范式。《左傳》關于晉文公重耳的敘述,是編年史中典型的紀事本末法。史書編纂過程中,多種書寫形式的綜合運用,早在先秦史學中已有很好的體現,開創了中國古代史學的一個優良傳統。《系年》的獨特價值就在于,“提供了戰國時期史書編纂中體裁融合的范例”。從這一點來講,《系年》有著類似《左傳》的史學創舉。
選取何種材料進行編纂,顯示出編纂者的歷史見識。據相關研究,《系年》的史料來源,一是西周王朝史官的原始記錄,二是諸國史記,三是少量的傳聞故事。從所采諸國史記的國別來看,主要以楚、晉、鄭為主,與《左傳》的鄭、晉、魏為大宗相對比,共同點是重視有關鄭國、晉國史記的選取,不同的是《系年》偏重楚國的史料采擇。這讓我們看到了戰國史學的區域特征,這也正是春秋戰國時代背景的史學反映。蒙文通曾提出晚周史學三系的認識,即南方楚人、東方魯人和中原三晉。這對我們分析《系年》,乃至整個清華簡史類文獻的史學價值,是很有啟示意義的。如果以此反觀簡帛文獻與傳世文獻有關史料選取的差異及所表達的不同的歷史觀念,也就很好理解了。
秉筆直書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也是歷代史家追求的理想目標。從史學功用角度講,史學的另一傳統就是書法不隱。需要注意的是,孔子所言的“書法不隱”與今文經學家積極追求的“一字褒貶”不能相提并論。孔子修《春秋》,追求直筆下的“微言大義”,把秉筆直書與書法不隱相融,是中國史學的重要開創。以往我們并沒有很好地注意到這一層區別。
《系年》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春秋》的這一優良傳統。雖說是以楚國為中心進行選材和記錄,但“楚師無功,多棄旃、幕,宵遁”“楚人盡棄其旃、幕、車、兵,犬逸而還”這樣的敘事,顯然是秉筆直書。這樣的事例,在《系年》及清華簡的其他史類文獻中還有很多。《系年》的敘事,不僅實現了直筆,還體現了編纂者“多聞善敗以鑒戒”的編纂意圖和敘事視角。更為突出的是,《系年》在記述西周直至戰國時期歷史發展上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事件時,不同于《左傳》《國語》的是,它并沒有選取有關卜筮的材料,也沒有記述類似《左傳》的神異預言,而是更多地從人的活動方面進行考察。這種述史的平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戰國時人著史的理性觀念。這些均說明,《系年》繼承并發展了《春秋》所開創的秉筆直書與書法不隱二者相融的史學傳統。
以《系年》為代表的簡帛史書,讓我們對戰國時期盛行的著史觀念有了很好的了解。從而使得我們對戰國史學發展有了新的認識:一是編年記事下多種敘事方法的融合是戰國史書編纂的常態,也是一種優良史學傳統;二是晚周史學三系是存在的,區域文化影響下的區域史學是戰國史學繁榮的重要體現;三是秉筆直書與書法不隱相融的史學傳統是承接相續的。
《楚居》與“世”類史書的起源
《世本》的成書年代及其性質,是中國史學史上非常重要的問題。自清人秦嘉謨根據其輯佚的《世本》提出了一個中國史學史上非常重要的命題,即“太史公書采《世本》,其創立篇目,如本紀,如世家,如列傳,皆因《世本》”。這一論斷影響很大。梁啟超就提出《世本》“為《史記》之藍本”。呂思勉也有同樣的看法。
其實,對秦嘉謨的這一論斷的質疑源源不斷,特別是學者們從史學史視野對此作新的評定,試圖糾正以往的偏識,厘清這一史學問題。對于所謂《世本》開創綜合體通史,白壽彝表示過質疑。喬治忠從史學史的學術層次考察了《世本》的成書年代及其史學價值,提出《世本》并非先秦史書,乃是劉向編輯的圖書之一。這些思考和論述,雖然推進了我們對《世本》成書年代和史學價值的認識,但還是沒有厘清《世本》的淵源和“世”類史書的原始形態,說服力不強。而簡帛文獻的發現,對此問題的深入探討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
中國史學早期,有“世”這一歷史編纂形式。《國語·楚語上》云:“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韋昭注曰:“世,謂先王之世系也。”可見,春秋戰國時期史官所書寫的“世”確實存在并有一定的勸誡意義。何以稱“世本”,《周禮·春官·瞽蒙》鄭玄注云:“世之而定其系,謂書于世本也。”所謂“世之而定其系”,就是一種歷史編纂,所成的史書就叫世本。《國語·楚語上》韋昭注引陳瑑曰:“教之‘世’,即《周官·小史》所奠之世系。”這又說明,鄭玄所言的“世本”就是楚太傅所教的“世”類文獻。
目前所見文獻最早提到《世本》這一書名的是西漢圖書整理者劉向。班固認為,司馬遷在編撰《史記》時采納了《世本》。顯然,這里的“世本”指的是劉向編輯后的一部書,與鄭玄所言的“世本”不是同一內容。從《戰國策》有多種定名來看,劉向所言的《世本》也很可能由眾多的類似文獻匯編而成。司馬遷在敘述其編纂《史記》時所采用的史料,對此已有了某種提示。《史記·三代世表》序言:“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于是以《五帝系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迄共和為《世表》。”“諜記”是記系謚之書,歷譜諜則指歷代年譜,二者似乎是有區別的。但從司馬遷整個敘述來看,二者又是統一的。諜記也好,譜諜也好,都是記世謚的,與“世”類史書的記述主體一致。
秦漢簡牘的發現,為我們認識這一史學現象提供了實例。1975年睡虎地秦墓出土一部竹書,整理者最初稱《大事記》,后又稱《編年記》。當時,有人就提出標題當定為“牒記”,但沒有過硬的史料支撐,這種看法也就沒有被學界采納。直到2002年湖北荊州印臺60號漢墓出土一批竹簡,有類似睡虎地秦墓竹簡的編年記,且標題書寫為“葉書”二字。2004年,荊州松柏1號漢墓出土一批木牘,其中有一種亦為“葉書”,記載秦昭襄王至漢武帝七年歷代帝王在位的年數。有學者懷疑“葉書”的“葉”應讀為“世”。如果這一理解不錯的話,葉(世)書應是與《國語》“世”、《周禮》“世系”以及秦漢時流行的《世本》大致類似的文獻,為記敘世系之書。
睡虎地秦簡、岳麓秦簡、印臺漢簡、松柏漢簡有關帝王年世的書寫,至少讓我們看到了“世”這一類史體的不同形態,當然還相對簡略,并未形成一定規模的成文史書。很可能,《世本》就是劉向將司馬遷曾閱讀過的“五帝德”“帝系姓”“諜記”“歷譜諜”“五帝系諜”“春秋歷譜諜”,以及出土的睡虎地《葉書》、清華簡《楚居》等文獻整理而成的一部史書,定名為《世本》。鄭玄所言“世之而定其系,謂書于世本也”,或許從中可探尋劉向命名《世本》的學術來源。
清華簡還有關于楚先世的一部文獻,記述從季連到楚悼王間的遷徙過程及相關史事,涉及32位楚先王、楚公、楚王,從傳說時代延至戰國中期。整理者命名為《楚居》,就緣于傳世《世本》中的“居篇”。簡文沒有對先祖降生進行過分渲染,也拋棄了流傳甚廣的陸終六子拆剖脅生的傳說,以更加平實而理性的視角敘述楚世系。有學者把清華簡《良臣》看作“世”類文獻的衍生。這又從另一層面說明《世本》中的某些篇章在戰國時期是存在的,也讓我們對《世本》的原始形態有了更多的了解。
雖說《世本》乃劉向編輯而成的一部史書,但從司馬遷引用的相關“世”類文獻、簡帛文獻中的“世”類文獻來看,“世”類文獻所呈現出來的以人為主、以時為軸的基本敘事方式,確實對《史記》的傳記體開創具有某種啟示意義。當然,我們不能把這種啟示有過高的評定,也不能因《世本》非先秦史書而否定這一啟示意義。
《春秋事語》與“語”類史書的繁榮
《國語·楚語上》申叔時與楚莊王在談太子教育時涉及到諸多歷史編纂形式,也說明,春秋時已有“語”一類體裁的史書。春秋時諸侯國史,其中一種形式就是記言,或以記言為主,或記事又記言。傳世的《國語》,是匯集各諸侯之“語”而形成的一部重要史書,成功地創設了記言為主的史書體裁。然而長期以來,《國語》作為“春秋外傳”而存在,被邊緣化。原因之一,就是我們沒有充分揭示《國語》何以稱為“語”,這種史書體裁為何產生于戰國前期,書中記載的“語”究竟有哪些不同的類型和寶貴的價值。而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清華簡《越公其事》等的發現,為我們了解戰國“語”類史書提供了實例。
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其體例與《國語》接近,先敘事后議論,記言是重點,最后用事件的結局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注重前后因果關系,有“綜其終始”的寫作追求,且一些篇章中的見解還是很深刻的,顯然這是經過編纂而成的,說其為戰國時的一部史書是沒有問題的。只不過,《春秋事語》敘事簡單,事件的本末記述不夠完整,內在邏輯性也不強,更符合早期史書的一些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事語》整體上反映了法家思想對史書編纂的影響,這或是戰國末期至秦漢之際史學觀念的特點以及發展狀況。這些讓我們看到了戰國“語”類史書的多樣性。《國語》只是流傳于世、帶有經學化的一部“語”類史書。故《春秋事語》的發現,使我們對戰國史學的發展狀況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認識。
清華簡《越公其事》11章,是目前所見楚竹書“語”類文獻中篇幅最長者,主要記述“勾踐滅吳”,這一敘事主題與《國語·吳語》《國語·越語上》《越語下》“語”類史篇密切相關。如果將其與《左傳》《國語》等傳世史書敘事對比,有助于我們了解戰國時期的史書形態。從具體敘事來看,《越公其事》的記述形式,沒有采用君臣問答或單純敘述的方式,而是進行了分類總結和概括,再以時間的次第分別敘述,既有政論的特點,又不失記事的大體;“五政”是作者對勾踐滅吳歷史經驗的總結,依次排列,不僅有具體的施政內容,而且有施政次序,具有明顯的史論特點。當然,就整體的越國滅吳歷程來看,《越公其事》的記載與傳世文獻相比,要簡略一些,時間線索亦不明顯。勾踐攻打吳王的背景性描述,《越公其事》略之,且其對具體戰役的記載也很少。總體而言,就清華簡而論,《系年》與《越公其事》是兩類史書的代表,前者可以視為春秋類記事文獻,后者可以視為語類文獻,是各有價值的兩篇優秀史書。
由《越公其事》、鄭國“語”書等來看,“語”類文獻的敘述主題都表達出“多聞善敗以鑒戒”的編纂意圖,顯示出戰國史學“資政”功能的特點。尤其是清華簡中為數不多的“語”類文獻帶有明顯的歷史化傾向。
就中國史學史研究而言,出土文獻,尤其是簡帛史類文獻,具有重要推動作用。西晉時汲冢出土的《竹書紀年》,就是很好的例證。清華簡《系年》等資料的發現,為我們深入了解先秦史學面貌提供了更為豐富的實例,讓我們對戰國史書編纂、歷史敘事、史鑒思想、史學傳統等有了新的認識,既看到了史學的共性,也認識到史學的多樣性,這對先秦史學研究無疑會帶來更多啟示與反思。可以說,這是繼《竹書紀年》之后再一次激發了學界對史學自身的反思,必將推動中國古代史學史特別是先秦史學的深入研究。因此,對于簡帛文獻在史學史研究中的價值和地位,我們不能以“邊角料”的態度待之,既要做減法更要做加法,要充分認識到它們對于史學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獨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