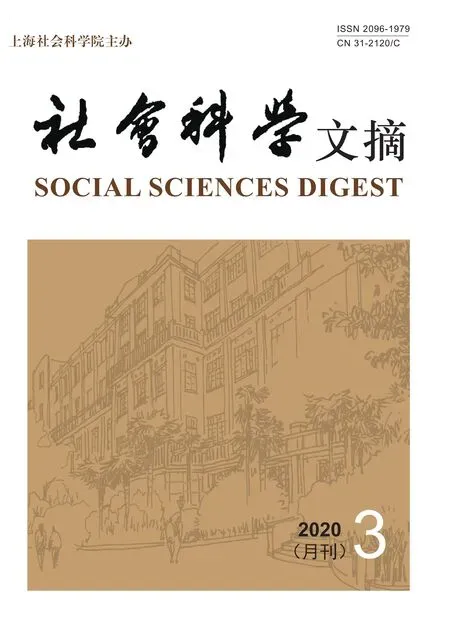“有”“無”之辨:重建近代中國歷史敘述管窺
20世紀初年“新史學”的成長,既影響史學觀念的變化,還改變著“存史”的方式。治中國近代史的學者由此需要面對這樣的問題:這既是歷史遭逢巨變的時代,也是史學觀念與史學方法發生重大轉變的時期。此所帶來的影響的是,歷史書寫所揭示的“有”,往往基于“普遍歷史”所昭示的“目的論”立說。過于關注這樣的“有”,舍棄的很可能是更為重要的“無”,況且“無”也并非不能提供信息,所呈現的實際是另外的“有”。因此,關注于歷史中“無”的一面,既可以突破“有”的樊籠,也有裨于呈現“無”所包含的“有”,重建近代中國的歷史敘述,也當在這個問題上有所突破。
從“無史”到“有史”:目的論史學的成因
柯林武德曾辨明,所有的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并且是那些在心靈里能夠“重演”的東西。晚清以降“歷史記憶”的延續,即揭示出歷史是以什么方式不斷“重演”的。清初廣織“文網”,以收繳刪禁圖書的方式磨滅人們的歷史記憶,早已埋下其“復活”的根基;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者”又喚起被“遺忘”的歷史。受此影響,中國的歷史書寫也逐漸落入“目的論”史學的窠臼。其成因及具體表現,大致可結合中國對“普遍歷史”的接納加以解析。20世紀初年梁啟超倡導“新史學”,即與此不無關系,還引發中國究竟“有史”還是“無史”的爭辯。本文探討的圍繞歷史研究“有”與“無”的論辯,也發端于此。
立足于“無”認知中國,在晚清一度甚為流行。諸如“無國”“無史”,乃至于“無學”“無社會”之類的議論,曾喧囂塵上。這自有深意在,昭示著以不同于過往的方式重新認識中國。而且,其語境既指稱當下,還指向過去。以“無史”論來看,梁啟超發表的《中國史敘論》《新史學》,即可視作“無史”論之濫觴。尤為特別的是,“無史”之說還盛行于以捍衛“國粹”為宗旨的人士中,往往與“無國”論相結合,突出這樣的意思——“無史”則“無國”,顯示出對“無史”的判定以及對“有史”的接納,另有樞機。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深厚史學傳統的國家,否認“有史”,流行“無史”之說,大有意味,表明此一時期讀書人對歷史的理解逐漸突破傳統的范疇,重新提出了“歷史是什么”的問題。與之相應,何謂“有史”,也成為讀書人思考的重心。
梁啟超舉起“新史學”的大旗,緊扣的即是對“史學”新的界說,“欲創新史學,不可不先明史學之界說。欲知史學之界說,不可不先明歷史之范圍”。重新思考“歷史之范圍”以及“史學之界說”,自是為探索歷史書寫的新體例。從“無史”轉向“有史”,明顯是中西史學會通的產物,主要涉及兩個環節的突破:其一是將中國歷史納入“普遍歷史”的架構,按照上古、中古、近世等時代進行把握(書寫通貫古今之“通史”);其二則是吸收各分科知識規劃出“專門史”,書寫各學科之“專史”。首先值得重視的是,按照不同的時代劃分中國歷史,所展示的“有史”不只具有形式上的意味,還逐漸以西方社會的演進代表著人類“普遍”的發展模式,并以此作為中國歷史演進的“目的”。這也意味著,晚清以降從“無史”轉向“有史”,主要體現在將西方社會演進所經歷的作為人類社會共同之“有”,將中國納入其中,除證明中國“有史”之外,還確立了中國歷史的“目標”。
“新史學”的基調:立足于“有史”的規劃
化解“無史”的緊張,將中國歷史納入“普遍歷史”,只是問題的一面。與此相關,“有史”的見解還有更具體的表現。最基本的,從“無國”“無史”的困惑中擺脫出來,重新確立“有國”“有史”之論述,端賴于獲得認知國家與歷史新的維度。秉持這樣的“有史”論,意味著接受“社會”“文明”的演進構成歷史的基調,并立足于從政治、經濟等因素解釋歷史的發展。從20世紀初開始,“專門史”的興起就成為史學編纂體例上“有史”的具體體現;以之為“有史”,也重新塑造了“中國之過去”。
梁啟超闡述的“新史學”,即試圖在史學編纂體例上開辟出“有史”。梁特別提到昔之史家的兩項弊端:其一,“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類以來全體之史”;其二,“徒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與他學之關系”。這正構成“新史學”關切的要點所在,當“歷史之范圍”拓展為“全體之史”,目標是立足于“有”以揭示“社會”與“文明”成長的歷史。這也成為清末歷史書寫轉變的象征。征諸各種以“中國歷史”為題名的書籍,可注意到歷史書寫的基本架構,逐漸以“文明”與“社會”為主軸。而此一時期各分科知識的成長,也構成影響史學發展的重要因素。不只梁啟超試圖在各學科中為“史學”尋求新的定位,還不乏其他學者闡述類似的看法。此所意味的是,伴隨分科知識的成長,發掘各學科之“有”而進行“專門史”書寫,也構成重塑“中國歷史”新的方向。這樣一來,除了與“斷代史”相對的“通貫古今”的“通史”之外,還產生了“通貫政治、經濟、學術、宗教等等”的“專史”。這表明,“歷史之范圍”較之過去大為拓展,“通史”與“專史”的出現,多少化解了由此產生的緊張。“專門史”的不斷涌現,也意味著中國的歷史書寫從“無史”的困惑中擺脫出來,對于“有史”的追逐,也有具體呈現。
新的史學編纂體例塑造的“歷史”
“我國史學根柢之深厚既如彼,故史部書之多亦實可驚。”梁啟超總結中國史學發出的感嘆,道出有著悠久歷史書寫傳統的中國不免面臨的困局,由此也促成史學編纂體例的不斷調整。進入近代以后,“西史”之加入,更沖擊著“中史”之編纂體例。的確可以說,近代既是巨變的時代,也是史學觀念與史學方法發生重大轉變的時期,并深刻影響到“存史”。“地方”的歷史按照新的史學編纂體例進行書寫,即是值得檢討的一環。研究者逐漸有這樣的共識,“地方”的近代史,于把握中國近代史的基調有重要意義。然而,需要面對的是,梳理地方近代史主要依憑的地方志等資料,同樣受到新的史學觀念與史學方法的影響,往往按照“有史”加以呈現,即突出“變”的一面,較為忽略地方的“不變”;最明顯的是,編纂體例與前述“通史”“專史”也漸漸趨同。
有關“地方”在歷史上的存在,常被引述的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說法;每逢激烈變動的時代,所謂“禮失求諸野”之論調也常常泛起。應該承認,遭逢巨變,“地方”也不免卷入其中。印刷書刊以及鐵路、電報的出現,使“地方”與外部世界的聯系不可同日而語;國家政權建設更是推動“地方”承擔不同于以往的角色。然而,國家政權建設的成效如何?尤其是地方如何“變”?卻值得深思。那么,以“存史”為目標的地方志又是如何書寫的呢?不可否認,這一時期地方志書的書寫也開始受到新的史學編纂體例的影響。以“今例”替代“舊例”,是重點考慮的內容。
民國時期修纂省志、縣志所制訂的體例致力于揭示地方之“變”,自不難理解。而且,除緊緊配合國家政權建設所涉及的內容之外,新的體例還接受了晚清以降所形成的新的史觀,展現出“新史學”如何“入志”的情形。耐人尋味的是,民國時期出版的省志,沿襲舊志體例的明顯占據多數。這也留下可資檢討的問題——地方志的編纂該如何“存史”?按照“有史”的方向修志,之所以難以實現,既有操作上的因素,但未嘗不是地方所發生的“變”,并不像一些方志學者所期待的那樣。換言之,按照“新例”編纂而成的省志完成不多,既是因為“近事”之難以甄別,編纂體例也不無影響。
毋庸諱言,近代以降產生了“不一樣的地方”,但如何“變”,其程度究竟如何,也難以一概而論。不可否認,進入近代以后,地方歷史的“有”與“無”或許更為突出,短時間里也難以趨同,僅結合政府行為書寫地方歷史,突出“變”的一面,未必合適。重點在于,地方近代史所揭示的是“地方”的“近代史”,而不是“近代史上的地方”。對比過往,自然有“不一樣的地方”,但各地方之“不一樣”,并不因為國家政權建設的加強而當即消除。“地方”作為更小的“歷史研究的單位”,需要以特別的方式呈現,正是因為存在著差異,對地方近代史的觀察,如致力于呈現歷史的“有”,甚至與“通史”“專史”的架構漸漸趨同,自是問題多多。消除了“差異性”的“有”,不免是放大的,乃至是牽強的,反倒是被忽視的“無”的一面,或更能展示地方的歷史。結合歷史進程所昭示的“有”與“無”,即可看出癥結之所在。
歷史進程所昭示的“有”與“無”
晚清以降新的史學編纂體例的浮現,不僅重塑了“中國之過去”,更奠定了近代中國歷史的基調。然而,史學觀念以及編纂體例的“趨新”,未必能完全反映歷史進程本身,僅僅展示與此相關的“有”,很容易遮蔽“無”所昭示的另外的“有”。結合此一時期國家政權建設“自上而下”的推進,尤其是敘述近代中國歷史至今仍沿襲的“現代化”這一框架,不難看出,歷史書寫所呈現的“現代化”之種種“有”,未必占據“主流”,或者反倒是“低音”,而被舍棄的“無”,也許才是“主調”。重建近代中國歷史敘述,或也當避免以未必有實際成效的“有”,遮蔽“無”所昭示的更具意義的“有”。
如何成長為一個現代國家,乃近代中國的基調所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國家政權建設在各個環節均有所拓展。與此相關,“現代化”問題也引起關注,而且,中國社會的不平衡一開始就成為思考的重點。這表明中國現代化甫提出,就與中國近代史結合在一起。尤其是在“國難”背景下,中國現代化之“幼稚落后”也受到重視。
結合與近代中國歷史敘述頗為相關的“現代化”論述的浮現,尤其是摻雜的各種聲音,不難發現盡管20世紀30年代“現代化”已引起重視,但還難以成為“主調”。這自是因為“現代化”在實踐層面的推進,還乏善可陳。既如此,以此作為近代歷史書寫的基本架構,自當考慮,是應該展示“現代化”之“有”還是“無”呢?此一時期所關注的“現代化”,往往以衛生、教育、法制等環節的建設作為指標,對此加以分析,可發現立足于“有”加以展現,問題不少。“有”未必構成“主調”,尤其存在嚴重的不平衡。
由此也提出值得思考的問題,對于這段歷史的研究,系按照“現代化”的“有”還是“無”來加以呈現呢?多考慮“無”的一面,而不局限于“有”,或許也是必要的。尤其應該重視,當“現代化”呈現的是“無”的狀態,則需要追問“有”又是什么?某一區域現代意義上的教育、衛生、法治等方面的建設不充分,沒有更多的“有”,則當關切這些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內容,究竟是怎樣的狀況,不能因為缺乏“有”就一筆抹殺,而有必要將“無”所涉及的實質性的“有”揭示出來。
近代中國歷史敘述秉持沿海-內地、現代-傳統等二元化分析架構遭遇諸多困難,意味著揭示“無”的一面的必要性。以圍繞“中國現代化”的研究來說,無論是基于“中國”整體還是“區域”的研究,大致都以某些“指標”為研究的基準。以此審視較為發達的中心城市,倒也能描繪“現代化”取得的進展,然而,以此觀察“邊緣”地帶,卻很可能看不到“現代化”的“有”。問題的癥結仍體現在近代中國存在著“多個世界”,意味著任何理論也好,分析架構也好,皆須立足于“有”與“無”分析這段歷史。原因在于,以中國作為“歷史研究的單位”,無論確立怎樣的維度,皆難以貫穿“自上而下”的視野,“上”之“有”很容易失落于“下”之“無”。而立足于“地方”也同樣會陷入這樣的困局中,難以確立貫穿“由下而上”之“有”。重建近代中國歷史敘述,這方面正是需要多加考慮的。
余論
近代中國歷史敘述表現出對“有”的追逐,起步于“無史”之論的流行,很明顯是闡釋中國的“焦慮”的體現,可視作遭逢巨變引發的結果。無論是將中國納入“普遍歷史”,還是在史學編纂體例中發展出“專門史”(包括“新名詞”之“入史”),皆是致力于呈現所謂“有”,以此化解中西會通后所陷入的“緊張”(包含歷史、當下與未來)。這也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較為特別的一環,重建有關近代中國的歷史敘述也須直面于此。
換言之,重建近代中國歷史敘述,須面對“現代-傳統”或“國家-社會”等架構之“得”與“失”,秉持這樣的視野,較為重視近代中國之“變”,還只是問題的一面,關鍵還在于其導致對近代中國歷史的審視,明顯存在偏向,致力于書寫種種所謂“有史”。如區域研究明顯集中于沿海及中心城市,甚至圍繞某一空間的研究也是如此,上海史研究針對“華界”即明顯偏少。對于不同的社會階層的研究也多關注讀書人、商人,較為忽視“不入流者”。當然,在“現代-傳統”或“國家-社會”的二元架構中,也更為重視前者。究其原因,皆是為追逐“有史”,以展示歷史中“有”的一面。
相應的,對此的突破也當回到“有史”所涉及的基本史實,即近代中國歷史本身的“有”與“無”,或“變”與“不變”,并重視“無”所呈現的另外之“有”。換言之,近代中國歷史既然展現出“現代”因素的不足,則表明僅僅展示與此相關的“有”未必妥當,更值得重視的反倒是“無”。當某些面向呈現的是“無”的狀態,或者只是“低音”,則不妨正視這樣的“無”,且并不因此而沮喪。地方的近代史之所以值得重視,即是因為避免按照“有”的架構進行書寫,多少更容易實現。重點在于,唯有確信“有”與“無”皆能呈現有價值的信息,方能書寫“地方的歷史”而非“歷史上的地方”。
綜而言之,結合“有”與“無”審視近代中國的歷史,尤其是展示以往被視作“無”的那些信息,對于增進對近代中國歷史的認知,無疑是大有裨益的。作出“無”的判定,也有助于提升史家對另一部分“有”的重視。重點在于,歷史敘述同樣可以選擇“無”展開,尤其是當所謂“有”是基于“目的論”立說,則更要注意過于重視這樣的“有”,舍棄的是更為重要的“無”。而對于“無”的重視,不僅可以突破“有”的樊籠,也有俾于揭示“無”中之“有”。具體來看,近代中國歷史研究所涉及的一些基本論題,無論是西學的影響還是現代性因素成長等問題,實際上皆可基于“無”立說。龐樸對“無”的辨析,曾頗有深意地道出所謂“無”,實際上有三個字——“亡”“無”“無”,包含“有而后無”“似無實有”“無而純無”等不同的情形,“表示有之失的亡,和表示失之有的無,都還不是絕對的空無”。近代中國歷史中的“無”,或許也是這樣的形態,在“無”的環節多加用心,重建近代中國的歷史敘述,或也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