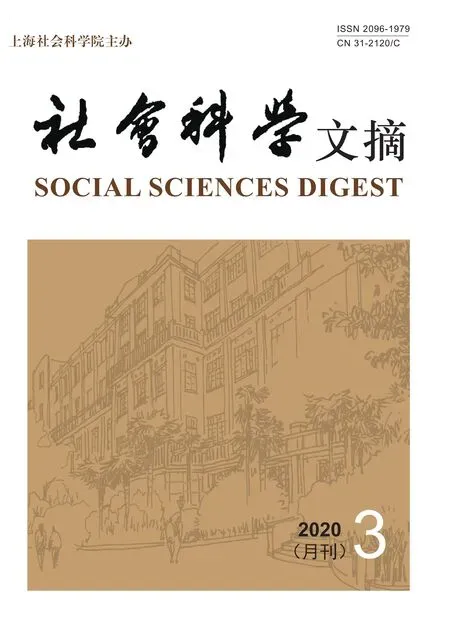論錢鍾書的舊體詩創作及相關理論
——以《槐聚詩存》《談藝錄》為主要考察對象
五四新文學運動發生后,雖然新詩在輿論上占上風,但傳統的詩詞藝術仍然以其自身的發展趨勢延續著。在現代作家的詩詞中,錢鍾書舊體詩詞流行較晚,但它際會舊體詩詞復蘇的文壇形勢,有“濟窮”之功;在詩壇上的影響,實有后來居上之勢。《槐聚詩存》出版后立即引起詩詞界的關注,對詩詞界尋求古典藝術傳統、重新提出學唐宗宋的問題具有啟發的作用。進入20世紀后,詩壇有一部分青年作者鑒于淺俗流行,嘗試模仿晚清同光體,與同光體有淵源關系的錢詩也因此頗受一部分學詩者的青睞。可以說,《槐聚詩存》是當代詩詞界有重要影響的一部詩集,值得從新、舊文學的交集,以及錢鍾書先生學術與文學創作的整體取向等多種角度進行研究。
一
新文學家的詩詞,受新文學反對摹擬古典、重視創造的觀念影響,一反舊文學重視宗派的作風。大多數作者在創作上都比較率意,不太重視于古人處取法。但也有一些作家是淵源有自的,如魯迅從科舉試律詩入手,郁達夫受黃仲則、龔自珍等清代詩人的影響明顯。但諸家與晚清以來的舊體詩派,少有直接的淵源關系。錢詩的情況與他們不同,是直接淵源晚清以來流行的同光體、晚唐體諸派,并且以宋詩為主要的取法對象,而兼融唐詩的一些特點。
錢氏家學淵源深厚,但并非從小就得到詩詞方面系統的傳授。而且傳統的所謂家學,主要是傳授經史古文,并不特別重視詩詞的教學,學詩往往是個人的興趣。錢氏在《槐聚詩存》序中對的早年學詩經歷有所交代,他說自己因讀《唐詩三百首》引起模仿的興趣,后來又看了家藏的一些清代名家詩集。“及畢業中學,居然自信成章,實則如鸚鵡猩猩之學人語,所謂‘不離鳥獸’者也。”(《槐聚詩存》卷首)所以我們論錢詩,要注意他與清詩的關系。但錢氏自認為青少年時期的舊體寫作屬于較低層次的模仿,詩學尚未成熟,所以晚年編集,“概從削棄”。
《槐聚詩存》存詩始于1934年,時錢氏已經大學畢業,在光華大學任教。集中所存本年詩作有七絕《還鄉雜詩》7首,五律《玉泉山同絳》,擬樂府體《當步出夏門行》,七律《薄暮車出大西路》《大霧》《滬西村居聞曉角》等3首。由此約略可窺青年以后詩學上的取法及門徑。
《還鄉雜詩》基本上還是清人絕句的寫法,其中龔自珍的影響比較明顯,如小標題為《梅園》的兩首:“索笑來尋記幾回,裝成七寶炫樓臺。譬如禁體文章例,排比鋪張未是才。”(其五)“未花梅樹不多山,廊榭沉沉黯舊殷。匹似才人增閱歷,少年客氣半除刪。”(其六)還有后來寫的《秋心》:“樹喧蟲默助凄寒,一掬秋心攬未安。指顧江山牽別緒,流連風月逗憂端。勞魂役夢頻推枕,懷遠傷高更倚欄。驗取微霜新點鬢,可指青女欲饒難。”這明顯地受到龔自珍哀感頑艷風格的影響。《談藝錄》第39條論龔詩及其與趙翼、翁方綱等人的淵源關系,認為蔣子瀟《春暉閣詩》中學龔氏《秋心》為近代南社等派學龔詩之開端。這些材料都能說明錢氏早年曾致力于龔詩,與其有一定的淵源關系。其擬樂府《當步出夏門行》,也是用晚清擬樂府的作法,以舊題寓新意:“天上何所見,為君試一陳。云深難覓處,河淺亦迷津。雞犬仙同舉,真靈位久淪。廣寒居不易,都愿降紅塵。”
早期存詩中,五律1首、七律3首,多學同光體。如五律《玉泉山同絳》:“欲息人天籟,都沉車馬音。風鈴呶忽語,午塔鬝無陰。久坐檻生暖,忘言意轉深。明朝即長路,惜取此時心。”此首法度上深入同光體之奧,于宋人中則最近陳師道與江西派諸家五律,蓋以白描達深雋之境,削膚存液,頗有真味,自非泛泛寫景可比。
錢詩七律,其取法也是由同光體入手的。同光體詩人,風格各有不同。陳三立悵觸時事,憂憤深廣,其詩境則縋深入幽。錢氏早年七律,風格近于散原體。如“點綴秋光野景妍,侵尋暝色莽無邊。猶看矮屋銜殘照,漸送疏林沒晚煙。眺遠渾疑天拍地,追歡端欲日如年。義山此意吾能會,不適驅車一惘然”(《薄暮車出大西路》)。此詩寫郊原的薄暮,其中融入惘然的暮愁情緒,寄托無端。其他如《大霧》《滬西村居聞曉角》,風格上都與散原體接近。
同光體的主要取法對象是宋詩,又繼承了清代以翁方綱為代表的肌理派及錢載等浙派詩人的一些因素,帶有學人之詩的特點。錢氏《談藝錄》中對清初以來各派詩人學宋詩的歷史有所梳理,對翁、錢兩家資學為詩的得失有很好的認識。其中不少內容,都可以印證其舊體寫作的取徑。他對錢載以詩人而作學人之詩,曾有特別的關注。他認為,錢載處樸學風盛之世,不自安空疏寡陋,其學問雖不見許于時流,“然其詩每使不經見語,自注出處”。錢鍾書自己的詩,也經常“每使不經見語,自注出處”,其例甚多。除中典之外,作者的詩還多識西典,像《浪仙瘦句和靖梅》這一首歌行,題目數百語,縷述其中所用英譯之典,不無炫博之嫌。另一方面,錢氏又不茍同鐘嶸所譏“文章殆同書抄”的作風,其自作詩用不經見語,多會于詩境,以清雋為旨,達到古人所說“使事令人不覺”的造詣。不僅如此,對于同光體本身,錢氏也不簡單模仿追隨。其所取于同光體者,在于詩境新雋脫俗,語言生新奇特,而對其過于奧衍晦澀、枯簡不近情等弊病,有自覺的剔除。其詩比之同光體諸家,有剔削革新之功。當然,錢氏一生并未專力為詩,加以文學革命的整體形勢的影響,所以其在舊體詩方面的整體成就,還是不如同光體諸大家的。
錢氏詩學的基本格局,是由同光體入手,上溯宋詩,并在此前提下辨析唐宋詩之變,對杜、韓以降的諸多詩家詩派,作了很精到的梳理。如《談藝錄》辨析杜甫七律,指出杜律除世人崇尚的“雄闊高渾、實大聲宏”一種外,諸如陳后山之“細筋健骨,瘦硬通神”,楊鐵崖之“以生拗白描之筆,作逸宕綺仄之詞”,也都淵源于杜律。錢氏稱前者為“杜樣”。錢氏之學杜,主要不學“杜樣”,而近于后山、鐵崖的這種取法。我們讀錢詩,印象最深的是句法之曲折變化。其中有一種即屬此類,如“搶地竹憐生節直,過枝蟬驚舉家清”(《大伏過拔可丈》),“地似麻披攢石縐,路如香篆向天灣”(《示燕謀》)。臆其詩之重句法變化,雖多出于同光體及宋人陳師道諸家,但淵源所自,未嘗不可說出于杜詩。
二
晚清至民國詩壇,在同光體之外影響較大的,還有樊增祥、易順鼎等人以纖艷為宗的晚唐體,以及黃遵憲、譚嗣同等人融會新旨的詩界革命派。錢詩在開端處是受到以緣情綺靡為主的晚唐體影響,其中不無纖艷之體的,甚至對六朝古艷也曾有所效法,如《當子夜歌》,用古調以寄新思。其法出于詩界革命黃遵憲、梁啟超諸人,風格很像晚清諸家之譯西詩。又如《古意》,則風格上近于溫李。《淚》一首,是用《西昆酬唱集》中舊題,作者自稱“試反其體”。所謂“試反其體”,大概是指不用西昆諸家之以賦法為主,鋪排典故,風格華麗;而是以白描直抒為體,又在立意上貼切主題。錢氏晚年為詩,于綺艷之體仍時一為之。1959年所作《偶見二十六年前為絳所書詩冊電謝波流似塵如夢復書十絕句》,其中就有比較典型的晚唐體。組詩除第一首為六絕外,其他6首都是七律體。他創作出悱惻芬芳、深情綿邈的一組“舊體情詩”,如“風里孤蓬不自由,住應無益況難留。匆匆得晤先憂別,汲汲為歡轉賺愁。雪被冰床仍永夜,云階月地忽新秋。此情徐甲憑傳語,成骨成灰恐未休”,“辜負垂楊綰轉蓬,又看飛絮撲簾櫳。春還不再逢油碧,天遠應難寄淚紅。煉石鎮魂終欲起,煎膠續夢亦成空。依然院落溶溶月,悵絕星辰昨夜風”。錢氏熟于詩史,對從李商隱、韓偓至黃仲則、譚嗣同等人無題、綺懷之類的詩,多有擷取,且有融會唐宋之處。
三
錢詩長于句法。其七律,置字造句,時見奇崛之氣,但又力求妥帖,追琢平淡之境。如:“緇衣抖擻兩京埃,又著庵鐘喚夢回。聊以為家歸亦寄,仍容作主客重來。當門夏木陰陰合,繞屋秋花緩緩開。借取小園充小隱,蘭成詞賦謝無才。(《返牛津瑙倫園舊賃寓》)”。錢氏七律句式不用常律,務為變化,煉字更是迥不由人,務為新險,但又能落到穩處,可以說是險處求穩,給人以很強的技巧感。1939年所作《寓意》,標志著他這種風格的成熟:“袷衣負手獨巡廊,待旦漫漫夜故長。盛夢一城如斗大,掐天片月未庭方。才慳胸竹難成節,春好心花尚勒芳。沉醉溫柔商略遍,黑甜可老是吾鄉。”作者另有《山齋晚坐》詩云:“一月掐天猶隱約,百蟲浴露忽喧呶”,句法亦極新奇。但是作者并非玩弄句法,整首詩將一段平常的夜寓情景化為詩的境界,具有很高的鑒賞價值。
1949年之后,錢氏舊體詩創作興趣減少,晚年有所回復。對于復雜的現實的變化與個人遭遇,錢詩所采取的方式,最接近黃庭堅所說“興托深遠,不犯世故之鋒”。如1954年《容安室休沐雜詠》、1957赴干校所作《赴鄂道中》5首,1974年作《老至》,乃至1961年作《秋心》,都可以是興寄無端,但微諷仍在。
作者中年以后的詩,多從日常生活、友朋交往的細瑣事物處入手,恬吟密詠,微寓感喟,整體風格較中年時期趨于平淡,但生新活法的使用有所發展。錢氏在舊詩方面所懸鵠的甚高,所作重于熔煉,但又主張自然為高。
四
在詩詞創作方面,中國古代有一個基本的理論就是“詩言志”,后來《毛詩大序》又有“吟詠情性”之說,陸機《文賦》提出“詩緣情而綺靡”。這幾條詩論,其實一直在啟示、指導著中國古代的詩人,近現代能夠卓然名家的詩詞作者也是一樣。
就近代以來的詩派來說,詩界革命比較多地體現“言志”的觀念;而以樊增祥、易順鼎等為代表的晚唐體,則明顯地側重于緣情綺靡的作風。以陳三立、陳衍、鄭孝胥等人為代表的同光體,繼承宋人黃庭堅的情性說,可以說是以吟詠情性為主。就近現詩詞創作整體情況來說,我認為言志派屬于主流。
錢鍾書對傳統的詩歌本體論及情志之說在近代以來詩學實踐中的簡單化,是有所反思的。而近代以來從西方引進的抒情理論也有這種簡單化的傾向。《談藝錄》第5條“性情與才學”一條所表達的見解,有助于了解錢詩的創作宗旨。“性情可以為詩,而非詩也。詩者,藝也。藝有規則禁忌,故曰‘持’也。持其情志,可以為詩;而未必成詩也。藝之成敗,系乎才也。”錢氏的詩論,在性情與才學兩者之間,更重視對才與學的闡述。《管錐編》第一冊“《毛詩正義》”之“《詩譜》序”條,根據《正義》引《詩含神霧》“詩者持也”一語,進一步發展其上述觀點:
《關睢序》云:“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釋名》本之云:“詩者,之也;志之所之也”,《禮記·孔子閑居》論“五至”云:“志之所之,詩亦至焉”;是任心而揚,唯意所適,即“發乎情”之“發”。《詩含神霧》云:“詩者,持也”,即“止乎禮義”之“止”;《荀子·勸學篇》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大略》篇論《國風》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正此“止”也。非徒如《正義》所云“持人之行”,亦且自持情性,使喜怒哀樂,合度中節,異乎探喉肆口,直吐快心。《論語·八佾》之“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禮記·經解》之“溫柔敦厚”,《史記·屈原列傳》之“怨誹而不亂”;古人說詩之語,同歸于“持”而“不愆其止”而已。陸龜蒙《自遣詩三十首·序》云:“詩者,持也,持其情性,使不暴去”;“暴去”者,“淫”、傷、亂、愆之謂,過度不中節也。夫長歌當哭,而歌非哭也,哭者情感之天然發泄,而歌者情感之藝術表現也。“發”而能“止”,“之”而能“持”,則抒情通乎造藝,而非徒以宣泄為快有如西人所嘲“靈魂之便溺”矣。“之”與“持”一縱一斂,一送一控,相反而亦相成,又背出分訓與同時合訓者。又李之儀《姑溪居士后集》卷十五《雜題跋》“作詩要字字有來處”一條引王安石《字說》“詩從言從寺,寺者法度之所在也”(參觀晁說之《嵩山文集》卷一三《儒言》八《詩》。)倘“法度”指防范懸戒、儆惡閑邪而言,即“持人之行”之意,金文如《邾公望鐘》正以“寺”字為“持”字。倘“法度”即杜甫所謂“詩律細”、唐庚所謂“詩律傷嚴”,則舊解出新意矣。
作者通過辨析詩之“持”“之”兩義,強調了詩之本體在于情志,而實現則在于藝術。“持”即是一個倫理化的要求,同時也是一個藝術化的過程,并且兩者是結合在一起的。最后作者甚至將“法度”引入到“持”“之”之義中,完成了他的藝術本體論與表現論的統一;在一定程度上發展了中國古代的詩歌本體論。從對錢氏詩歌創作的研究,我們發現他的這一詩歌理論的建立,與其創作實踐密不可分。或許我們可以稱之錢氏“詩持說”。事實上,與錢氏“詩持說”最接近的,應該是《毛詩大序》的“吟詠情性”之說。
錢詩產生于20世紀的多事之秋,國恨家愁,不無驚心徹骨之痛。作者的宗旨是以學術為高、藝事為尚的,但并不把學術理解為純學問、藝事理解為純藝術。其《談藝錄》自稱其書“雖賞析之作,實憂患之書也”。早年創作,多與時事相關。他中年以后的詩歌,由于某種現實的原因,抒情言志更趨于婉曲。如果用古人的創作理論來描述,我認為最接近黃庭堅的“興托深遠”之說。若以筆者上述所分的晚清以來言志、緣情、吟詠性三派來分,我認為錢詩最接近江西詩派、同光派的“吟詠情性”的作風。
錢鍾書先生精通中西詩學,深明藝事之理。其詩學溯源披流,自詩騷至唐宋元明清近代的諸家諸派,皆有辨析,尤其是對明清以來長期糾纏不休的唐宋之爭有自已獨特的見解。他的詩學可以說是博大精深的。以此深厚的詩學功底,用之于舊體詩的創作,可以說是取弘用精。其早年雖曾染跡晚唐體,晚年也時一為之;但其主要的取法,仍在同光體一派,并由同光體上溯北宋黃庭堅、陳師道諸家,用其法而不襲其跡,變化而出。受宋詩及同光體的影響,錢詩最重句法章構,多新奇之致,勁折而紆徐,瘦硬中含妍媚。其于詩歌藝術之造詣,雖不能說已臻大家之境,但足可入名家之流。
錢氏平生雖不專力為詩,但在舊體詩創作方面取弘用精,酌古以變。他的舊體詩寫作,以吟詠情性為旨,但又帶有比較明顯的逞才、游藝的特點,并且體現他博雅、機智、幽默的個性,造成比較鮮明的個人風格。研究錢詩,不僅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錢先生的學術與藝術世界,同時也可能為當代詩詞的創作上的提高與復雅提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