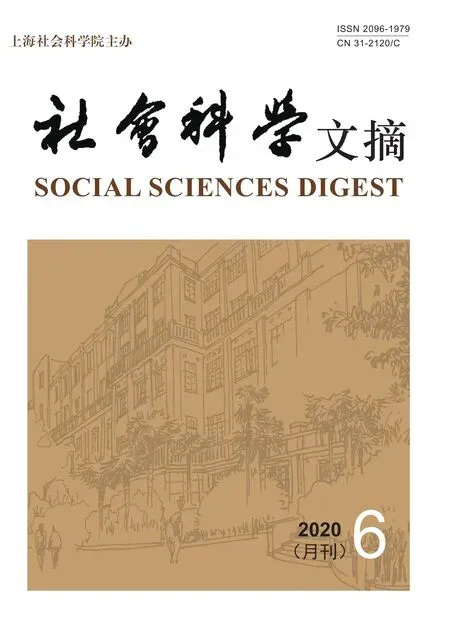鮑羅廷與孫中山1924年北上再考察
文/周利生 徐磊
孫中山1924年北上,是其晚年政治生活中的一件重大事件。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學術界圍繞孫中山北上的思想動機、北上的原因與得失以及北上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北上與日本的關系等方面展開研究。伴隨蘇聯解體而來的俄羅斯現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有關檔案資料的開放,學術界開始關注共產國際、俄共(布)以及國民黨政治顧問鮑羅廷與孫中山北上之間的關系,取得了一些成果。不過,鮑羅廷為什么會支持孫中山北上,如何看待孫中山繞道日本,國民黨出席善后會議與鮑羅廷是什么關系等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理清。
支持孫中山北上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后,鮑羅廷向莫斯科扼要通告中國局勢的變故:“政變的結果是,10月23日北京政權落入所謂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等人手中。馮玉祥發出關于發動了政變和在北京召集會議,以解決新的國家建設問題的通電。”同時,鮑羅廷指出了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國民黨應對北京政變的兩種可能之策:要么“只限于發表一般的聲明,說北京發生的僅僅是一些軍閥取代另一些軍閥的政權更迭”,要么“采取更為積極的政策”。鮑羅廷所持的是后一種態度,即積極支持孫中山北上。
其時,對于孫中山北上這一中國政治運動中的重大事情,各方看法不一。鮑羅廷意識到,“中共中央反對孫逸仙北上”。他分析認為,中共中央基于對北京政變本身的評價以及由此帶來的對革命運動的影響,覺得北京“實質上沒有發生什么特別的事情”,北京政變與“國家的解放事業”沒有關系。可是,在鮑羅廷眼中,馮玉祥“是反對‘帝國主義者’的革命的軍人”,將其視為中國革命需要爭取的對象。
當然,孫中山是否北上,關鍵取決于國民黨方面的態度。在鮑羅廷看來,國民黨內部存在反對孫中山北上的聲音,是出于國民黨本身的前途命運的考量。孫中山北上后將面臨著兩難的選擇:或者繼續“捍衛”過去頒布的“國民黨的激進綱領”,從而不可能與北京政變中的勝利者合作;或者是“拋棄”國民黨的這些綱領,那就“意味著國民黨的分裂”。鮑羅廷從積極角度看待局勢演變,認為北京政變“給國民黨提供了一個登上國民革命斗爭大舞臺并成為大政黨的極好機會”,“如不利用這一機會,不僅從策略上看是錯誤的,而且在一個長時期內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會削弱國民黨”,因此,國民黨“應該發表宣言”,孫中山“應該北上”。
鮑羅廷的觀點是有道理的。中國國民黨的早期組織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及至中國同盟會,其活動區域主要是在南方,在北方難以對革命民眾產生政治影響。“國民黨此時在北方,除了在青年學生和教授團體中蓄有一種潛勢力,表面上似尚無何種能力,所以那些軍閥巨頭,除了馮玉祥眼光比較的銳敏,極力和黨中的領袖接近外,大都不十分注意國民黨。”這種狀況既不利于國民黨組織的壯大,也無助于國民革命在全國范圍的推進。
事情的發展,正是鮑羅廷所期盼的。1924年11月1日,孫中山親自主持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鮑羅廷支持孫中山北上的觀點在會議上“占了上風”。會議決定,孫中山“離粵北上宣言為統一中國”。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提出“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的主張。
不反對孫中山繞道日本
1924年11月14日,孫中山離廣州、抵香港,改乘日本郵輪“春陽丸”號赴上海。孫中山原計劃提前一個星期即11月6日從廣州出發,乘英國或者美國的輪船去上海,但是,“駐廣州的日本人熱情地建議孫乘14日的日本輪船”。鮑羅廷對日本人的這一提議心存擔憂,提醒孫中山說:“您是否認為,他們在盡力拖延您此行的時間。即使拖延幾天也有很大意義,因為您不在北京,日本較容易利用北京的政變。”
鮑羅廷的擔心不無道理。11月10日,段祺瑞在天津會晤張作霖、馮玉祥,決定擁段為“中華民國臨時總執政”。11月24日,段在北京就職并公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制》,組成執政府。12月24日,公布“善后會議條例”十三條。馮玉祥及其國民軍受到排擠,被調離北京,前往張家口任西北邊防督辦。其結果,孫中山北上面臨的對手已經是親日的奉系張作霖和皖系段祺瑞軍閥勢力控制的北京政府。
11月17日,孫中山抵達上海。11月21日,孫中山搭乘日輪“上海丸”離開上海,取道日本赴天津。之所以繞道日本,孫中山稱:“因為在上海沒有船位,就是半個月之內也沒有船位,由上海到天津的火車又不通,所以繞道日本到北京去。”情況并非完全如此。鮑羅廷深知:“孫逸仙早就有訪問日本的想法”,“為的是試探一下對他的建立中、日、俄聯盟思想等的反應”。鮑羅廷意識到“孫逸仙取道日本的問題是國民黨代表團途中第一個暗礁”,但并沒有阻止孫中山的日本之行,而是“支持孫中山去”。在鮑羅廷看來,“在孫逸仙的腦子里對日本的幻想根深蒂固,他早就有建立中、日、蘇俄聯盟的思想”,“現在時局向他提供了訪日的機會,要阻攔他走這一步是非常不明智的。除了他從日本之行中獲得的親身感受,沒有什么能作為消除他對日本的幻想的有力的論據。此次赴日只會使他變得聰明一些”。
事情正如鮑羅廷所料,孫中山日本之行遭到了日本官方的冷遇。孫中山抵達神戶時,政府要員無一人露面,與孫中山有過聯系的各界要人極力回避,日本政府甚至拒絕孫中山到東京去。日本外務省亞洲局局長出淵勝次表示:“孫赴天津途中在日本停留,來東京與有力者會見,已為一般人所誤解。恐怕這將對孫產生不利的結果。”孫中山兩手空空地離開日本,一腔熱忱和希望化為泡影,“短短的日本訪問成為孫中山的痛苦回憶”。
為應對善后會議出謀劃策
與孫中山北上相一致,國民黨的決策中心也隨之北移。抵京后的1925年1月26日,孫中山指令將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內之政治委員會移至北京。鮑羅廷仍舊擔任政治委員會高等顧問,“作為顧問出席了所有會議”,發揮了重要作用。時為國民黨中央執委委員、青年部長、常委的鄒魯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黨權不在最高黨部之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權不在最高政治機關之國民政府,而悉集中于政治委員會。鮑羅廷乃以政治委員會顧問之資格,操縱其間”。鄒魯所言“操縱其間”,顯然帶有情緒化色彩。但是,鮑羅廷對于國民黨決策的影響力是無疑的。
國民黨應對善后會議的策略中,就不乏鮑羅廷對孫中山的影響。孫中山離開廣州前,在《北上宣言》中明確提出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并提出會議由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各省學生聯合會、工會、農會、反對直系的地方實力派、各政黨的代表等九部分團體組成。
可是,段祺瑞執意召開善后會議,并于1924年12月24日公布《善后會議條例》,對會員資格作了如下規定:“一、有大勛勞于國家者;二、此次討伐賄選制止內亂各軍最高首領;三、各省區及蒙藏青海軍民長官;四、有特殊之資望學術經驗,由臨時執政聘請或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
對于是否參加善后會議,國民黨內部“見解各殊”。“主張參加者以必須加入后方可防止其包辦國民會議,且對各省軍事財政為報告之性質,亦有益”;反對者認為,“此會與真正民意無涉,吾黨不宜參與”。孫中山起初也堅決反對段祺瑞的善后會議。段祺瑞公布《善后會議條例》的次日,孫中山就明確指出,善后會議乃“善軍閥官僚之后,非善民國之后”。
鮑羅廷與孫中山的觀點不一樣,主張有條件地參加善后會議。鮑羅廷認為,“對于是否參加段祺瑞的會議的問題,我們(加拉罕同志和我)準備建議國民黨作出肯定的決定。當然,為此我們提出了一系列條件,這樣就可以把參加善后會議變成宣傳國民黨行動綱領的最好方式。”
鮑羅廷在征得孫中山的同意后,在國民黨的政治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并獲得會議通過。于是,1月17日,孫中山復電段祺瑞,表示可以接受善后會議,并提出了兩個先決條件。一是關于參加善后會議的成員,“文不必堅持預備會議名義,但求善后會議能兼納人民團體代表”。二是善后會議討論的事項,“雖可涉及軍制、財政,而最后決定之權,不能不讓之國民會議”。但是,1月29日段祺瑞發出答復孫中山的艷電,以會期已近、時間緊張、增派代表趕辦不及為理由,拒絕接受國民黨方面的建議。鮑羅廷關于有條件參加善后會議的主張,終未實現。
與此同時,孫中山的病情不斷加重。3月12日,孫中山病逝。鮑羅廷失去了在中國革命中的一位強有力支持者。1925年5月17日,鮑羅廷在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第一次全體職員聯席會議上回憶說:“我們很痛心的,就是我們喪失了我們唯一的領袖。他奮斗幾十年如一日,去歲北京政變,他看到環境上有需要他到北京去的必要,所以他親身北上,只身去同一切惡勢力奮斗。”對于孫中山北上,鮑羅廷依然表示了贊賞和崇敬!
事實證明,孫中山北上廣泛傳播了革命理念,“喚起北方國民革命的要求,其影響實在太深刻了。北方大多數的民眾都已深印反帝國主義及打倒軍閥的決心。”孫中山晚年的這一次政治行動,鮑羅廷給予了大力支持。時人對此亦有肯定性評價:鮑羅廷“裨益于中國的革命運動”,“北京政變之后,對于孫先生北上,在國民黨內引起很大的爭論,而當時力贊其北行的,鮑羅廷之力居多”。“中山先生的北上,造成了中國全國廣大的民眾運動,是他(指鮑羅廷,引者)竭力主張與籌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