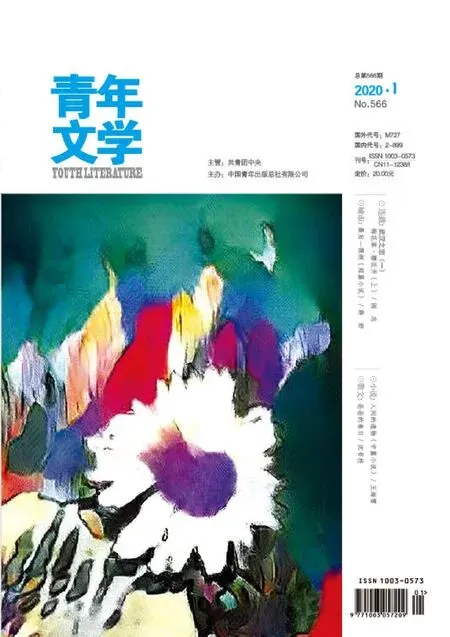落地生根
⊙文/習 習
一
他們是我的學生,多數人年歲比我大。
早課鈴響了許久,很多男生遲遲不進教室,我拿起笤帚,跑到男生宿舍門口,破門而入。用笤帚疙瘩一張張床挨個兒打過去,他們“哎喲喲”地笑。罰他們跑步,哪里跑?他們說,公園。公園就在學校后身,責罰成了歡快的溜達,我甚至混同于他們,大聲說笑,直到學校門口,調整好表情。
我第一次喝白酒是他們教的。那年新年前一晚,教室里掛滿五顏六色的彩帶,錄音機響著流行歌曲,作為班主任,我拒絕了男生的一一敬酒,答應和他們共同干一杯。這些男生,業余的一大嗜好就是喝酒,用石子兒一樣硬的炒蠶豆下酒,他們咂巴著白酒,嘴里嚼得嘎嘣嘎嘣響。女生不喝酒,只吃蠶豆。男生興致勃勃地在我周圍圍成一圈,耐心教我喝白酒的方法,不怕不怕,藥你總喝過吧?一仰脖子,哐就下去了。哐,我咽下去了,教室里掌聲雷動。
想起這些,心里就漾起些溫暖。那時我剛工作,面對的就是這樣一群進修學生。當時,農村師資緊缺,一些農村畢業的初中生、高中生被招為當地小學的民辦教師。我和他們相識時,他們有的工作快十年了,有人已經成婚,還有人在班上戀愛,進修給了他們相識的機會。
一年四季,教室里彌漫一股炕煙味,是西北農村家里特有的氣味,即便他們交來的一小片答題紙,上面也有那味道。當然,教室里還有女生的雪花膏、洗發膏和頭油的味道。女生愛美的天性在學校得以發揮,每個人額前的劉海都被發鉗燙得卷卷的。
這些學生水平不一,有的連拼音都不會讀,嚴重的方言增加了矯正的難度,有時為矯正某個字母的讀音,課堂上會哄笑成一團。而我,當然不能時時成為他們的同伙,有時會非常惱怒地狠狠把課本砸到講桌上,課堂上立刻鴉雀無聲。
彼時,我對自己的職業沒有清醒的認識,只是憑著一腔熱情,想在課堂上盡力把自己體會到的傳達給他們。我教“閱讀與寫作”課,有一次講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講到“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兒是在獄里,寫著一首呈給你的贊美詩,呈給你黃土下紫色的靈魂,呈給你擁抱過我的直伸著的手……”我讓他們做“直伸著手”的姿勢,讓他們體會這個姿勢里的情感,幾個學生流淚了。
二
我們學校是區屬教師進修學校,起初在市里的八里河區。安臥于黃河谷地的狹長城市,北部靠近黃河,南面則枕著綿延的大山。八里河區也是這樣,北部的城區緊鄰黃河,而南面,大山如屏風般矗立。大山夾著幾條深溝,山溝山腰山頂,適時的位置,分布著二十幾所小學。我們的進修生就來自這些小學,他們在我們學校一般經過兩個學期的進修。
大致在我工作的第五年,全區民辦教師幾乎輪訓完了。之后,我們有了新任務:送教下鄉。
湖灘鄉,在高高的南山山頂,翻過去就是馬家窯文化的發祥地、古稱狄道的臨洮縣。在我們干涸的家鄉,有很多浪漫的地名,比如馬灘,其實從沒有過馬匹,比如青草峪,荒蕪到寸草不生,還有靠天吃飯的湖灘,根本沒有半點兒湖的影子。
六座客貨車是學校唯一的交通工具,下鄉時,司機師傅往往載著三個老師:我們的教導主任、文科培訓教師、理科培訓教師。湖灘鄉是典型的西北二陰地區,農作物生長緩慢且產量低。那是個冬天,車在狹窄的盤山土路上攀爬,徒自拖著一個空落落哐里哐當的車兜子。前方忽然漫起霧來,車子進退兩難,只能頂霧前行。師傅的頭幾乎要抵上風擋玻璃了,我們徹底被包裹在軟騰騰的濃霧里,我覺得很新奇,霧遮擋了險峻,沒了高山和深壑,我們猶如進了仙界。直到車子破霧而出,停在一塊接近山頂的平地上,師傅跳下駕駛室,煞白的臉上虛脫一樣淌滿汗水,我們方知剛才有多危險。這時,深不見底的濃霧在腳下蠕動,仿佛什么東西落下去都能被它軟軟地接住,哪怕一個大山。而我們已在天上,湖灘就是這么高啊,湖灘的陽光異常明亮,望過去,山畔上的院落被曬得金燦燦暖烘烘的。
若干年后,我在一篇文學作品里,對印象中亦真亦幻的湖灘進行了虛構:山頂有一面大湖,湖邊有一棵幾百年的棗樹,湖水里游弋著一種鮮嫩的冷水魚,鄉里的孩子們像棗兒一樣掛滿大棗樹的樹杈,有一天,突然漫起了白霧……
那些我的成人學生,幾年前,還有著學生的模樣,盡管在課間抽旱煙喝罐罐茶納鞋底織毛衣,但在送教下鄉時,我看到了他們的另一面。
我曾經的男學生,穿著皂色棉襖,腰里扎著綁帶,儼然和當地農民沒有分別。事實上,很多民辦教師,都是一邊干農活一邊教書,農忙時,甚至顧不得上課。他們用濃重的方言和學生們對話,那些同坐在一個教室里膽小羞怯的鄉下孩子們,很可能是堂兄弟或表姐妹。而我曾經的學生很可能被孩子們稱為阿舅、姨父、姑爹,或者娘娘、舅母。這種部族式的村落在偏遠的鄉里很顯見,比如王家莊、李家溝、趙家洼,有時同一個班有近一半同姓的同學。
我曾經的學生們,工資單薄(一些民辦教師被辭退了,個別的轉正為公辦,還有一些正面臨嚴格的轉正考試),幾十年堅持下來,主要原因是能掙一份家用。高寒地區對人的面容風化得厲害,幾年過去,他們蒼老得很快。
幾乎每次送教下鄉,當我站在講臺上時,情緒都很難調整。一邊是我滿懷理想主義的備課,期望盡可能多地給他們傳達一些國內發達城市優秀的教學經驗,一邊卻是這樣的情景:上課鈴已然拉響,老師們手里倒換著爐子里剛剛烤熟的焦黑的洋芋蛋,三三兩兩慢騰騰地踱進培訓教室。
那些進教室講課的老師也如此,教室里的學生真的就像他們自家的孩子,他們可能正聞著烤洋芋的香氣聽講,也可能正啃著洋芋蛋子做作業。有的班是復式班,鄰近年級的孩子同坐一個教室,兩部分人背對背,老師給他們穿插上課。家長對孩子沒有過高要求,特別在農忙季節,學校讓他們安心,忙得顧不上做飯時,他們知道老師會給他們的娃先墊上兩口洋芋或饃饃。
面對幾年不見的我——他們曾經的班主任,他們多半顯出窘迫來,我的到來打破了他們的日常,他們還窘迫于我或許會到和學校一墻之隔的他們家里去轉轉,一不小心碰上他們的婆娘或者男人。
那時,我依舊不懂很多事情,不能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他們會宰殺一只剛才還在院里散步的公雞,表達對我這個客人的熱情。那種共同干杯的單純的歡樂已經遠去。
但無論怎樣,我一直由衷敬佩著鄉村教師,包括我的很多學生。在綿延的大山深處,每次下鄉,只要遠遠看見紅旗,就知道學校到了。這是個給人慰藉的所在,鄉村教師們像清貧的布道者,啟蒙鄉民,保護那些懵懂的孩子,他們用自己的想法和視野,讓囿于一隅的人們眺望到遠方。比如在大山之巔的湖灘鄉,人們過著幾乎封閉的日子,但學生的輟學率一直是零。有一對父母出外打工,孩子被迫放棄學業要照看患病的老人。班主任二話不說,把老人接到自己家里。這位班主任就是我曾經的學生,先前的她靜默寡言,但若有好笑的事情,她笑的時間總是最長。我的似乎已經混同于農民的學生們,他們其實個個都有深沉遠大的理想:讓鄉里的孩子盡可能地多讀些書,以后能下山進城,走進大學。
若干年后,在市區的婦產科醫院,我和一個即將生產的過去的女學生相聚在同一個病房。我很驚喜,她身上的炕煙味讓我感到親切,妊娠斑蓋滿了她的臉,但我還記得她是個面容姣好的女子,性格文靜,作文寫得很好。但是,她在盡力回避我,我的噓寒問暖攪擾到了她。傍晚,他男人帶著大包小包進了病房,他竟然也是我曾經的學生。他認出了我,禮貌地和我打過招呼后,坐在他愛人的病床邊一言不發。我們在一個房子里,但相距遙遠。我和我的女學生,偶爾會挺著大肚子在樓道相遇,她會遠遠地給我避讓,那幾天,我覺得師道尊嚴是個多么叫人別扭的東西。
三
當老師的第十一個年頭,我準備調離崗位了,像鳥籠里關久了的鳥兒,我渴望飛向別處。對從事了十年有余的教育工作我有了一些看法。無益于教學的條條框框、繁文縟節的各種檢查,看似不見硝煙的不間歇的評比和競賽,這些,我厭倦了。披星戴月、早出晚歸,工作密不透風,但整個學校,從上到下,唯獨忽視了人、忽視了學生和老師作為人的存在。那時,我時常被同一個夢境夢魘,獨自一人在荒野里,倦怠到邁不開半步。
我改行了,對過去的這段教學生涯,我只在幾年后的一篇散文《受傷的鎖具》和再若干年后的一篇散文《梨花堆雪》里提及。《受傷的鎖具》源于一件極難忘的事情,老師們終于盼到發工資的那天,但天剛亮,值班老師發現財務室的門和柜子被撬,所有教職員工的工資不翼而飛了。這是一件驚心動魄的事,那時候我們每到月底都青黃不接。財會人員失聲痛哭,那天前夜的一場大雪掩蓋了竊賊的作案痕跡,警方辦案無果。但積雪漸漸消融,在學校后身冬果園的一片殘雪里,有人發現一個被砸爛的鎖子,正是財會室的門鎖。我們的會計自那之后精神大變,經常一整天默默無言,望著那個爛鎖子發呆。那時,迫于商品經濟的發展,我們的教師進修學校已退居到了靠近鄉村的公路邊的一個院落里,“品”字形的小教學樓圍著一個很小的操場,但校園后面是一片巨大的冬果園。春天,教室窗外梨花堆雪,而今想來還有著魔幻般的浪漫和詩意。我在《梨花堆雪》里寫到,我常常站在樓道,長久地眺望,一條通向遠方的公路把我的目光帶到很遠,夏天,矚望那條公路,地面上被太陽蒸騰起的熱氣,使那條公路在視線里歪歪扭扭,顯出一種莫名的虛幻。
我告別了教學生涯,但我時常感到,過去的十年像一塊兒沉沉的黃土疙瘩。為什么?大約和我的農村學生有關,和我后來跑遍的農村學校有關。
有一年,我接到一個人電話,說他是我多年前的學生,喝多酒了,突然想起了我,很想大哭一場。我放下電話,眼睛也濕了,那個男生,他曾經的樣子歷歷在目。
其實,我從沒有忘記過那段歲月,那塊黃土疙瘩養育了我,我是在那里落地生根的。
四
我后來計劃寫一本書,寫一些最基層的女性。
在一個偏遠的村子,我和一位女鄉長待了一個多星期。寒冬臘月,我們擠在一個被筒里,深夜,能聽見鐵爐里的火苗呼呼撲躥的聲音,但房子還是冷到不敢伸頭。碩大的星斗真的會眨眼呀,那是鄉野里才有的星星。我跟著女鄉長走鄉串戶,以一個最基層的鄉村干部的眼光打量農民和農村。那些質樸簡單的人、善良溫情的人、有時又叫你無奈憤懣懊惱不堪的人,現在想來,一個個依舊活靈活現。記得在一次計生檢查中,女鄉長置身于一群劍拔弩張的村民中,她先是沖出來,讓我做好安全防范,然后義無反顧地返回人群,我親眼看著她如何苦口婆心春風化雨地解開一個又一個疙瘩。這讓我又想到我先前跑過的農村,我曾經的在鄉下執教的學生們,他們后來的境況如何呢?農民秀珍,一邊放羊,一邊趴在山坡上寫詩,寫完了念給她的羊聽,她是個多么可愛有趣的農村小媳婦兒,她粗樸的方言俚語,常常惹得我大笑不止,夜晚,在她家熱炕上熟睡,常會被她夜半歸來擠上熱炕的貓吵醒。我采訪過一個從事特殊教育的老師,她的學生都是聾啞殘障,但她的課堂生機勃勃。采訪完她的那個傍晚,在回家的公交車上,我悄悄溫習著啞語的幾個手勢——下雨:手五指分開微曲,指尖向下,上下輕輕動幾下,象征小雨點落下。車窗外正飄著小雨呢。雙手掌心向上,在胸前上下扇動,臉露笑容,這一手勢表示高興。我反復做著這個手勢,因為我心里真的高興。騰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邊緣的民勤縣,在一個干凈的黃土小院,一位七十一歲的治沙老人給我講述了她長長的重重的歷史。黃昏時,我端著大碗,坐在門檻上和她家人一起吃湯面,飛蛾噌噌撞著屋檐下的燈泡,那一天心里多么沉實安靜。
我一共寫了十四個女性,集結成了《講述:她們》一書。這本書因為她們而沉甸甸的,它有著黃土疙瘩的質地。
十年的教學生涯,我邊講課邊學習,我認識人,靠近一個個靈魂。十年之后,我還是在講,用文字講,講我領悟到的、感動到的、理解到的。雖然歷程不同,但共有一個背景,那就是我內心所能張望到的和我內心所能觸探到的大地及大地上的人和事。
五
出乎意料的是,因為扶貧駐村,我又得以回到學校。
駐村的日子,我挨家挨戶,走了每個自然村。一天傍晚,爬上村里有信號塔的最高的山頭,我坐在那里鳥瞰村子。辨別進過的每戶人家,辨認正在羊腸路上行走的農人,猜測他會去誰家串門。山下,最顯眼就是飄著紅旗的學校,在一塊兒平坦的山坎兒上,學校方方正正,三排教室整齊排列。
駐村宿舍就在學校,雖然是夏天,夜半,屋子還是很冷,好在爐子里還留著做過飯的余溫。深夜,窗外的紅旗如果被風刮得撲啦啦響,我就知道要陰天了,家遠的孩子一早可能會掛上一腳泥巴。
記得到扶貧村第一天,我找到了藏在學校門前山坡下那個長長的土廁,三條被踩踏得不長草的細白土路通向三個低矮的廁所門。正是上課時間,我隨便進了一個門,這時,我聽到幾個小腳步急惶惶地跟過來了,我知道是坐在校門口小板凳上曬太陽的幾個幼兒園同學,他們排著小隊進到廁所,一個小男孩嚴厲地說,這是男娃娃的茅廁!我說我錯了,馬上按他們伸出的小指頭的方向進到了正確的地方,我心里盛滿笑意。
在這個小學校,我依舊會想起我曾經的學生們,多少年過去了,他們的農村小學肯定也和以往大有不同。隨著城鎮化建設,現在,城區學校的班額越來越大,而農村學校的孩子數量越來越少,就我住的這個的小學,包括幼兒園孩子在內,總共也才三十多個學生。盡管學生少,但學校一定是家家村民牽掛的地方。
一天,我找到校長,請他給我兩節課,說我想給孩子們講講寫作。校長很高興,作為答謝,說晚自習后煮洋芋給我和住校老師吃。煮食洋芋,在西北農村太過普通,但那次我見識了最莊嚴的一次。厚厚的木頭鍋蓋上壓著一塊磚頭,校長和老師們不時站起,貼著耳朵聽鍋里的聲音,他們一會兒從烤箱側口添進幾塊兒炭,長長的火舌舔著鍋底,已經聞到了一股焦香,校長依然不慌不忙,他一動不動側耳辨聽著鍋里的聲音,說,正在收水,不慌,不慌。終于,鍋蓋揭開了,轟!一大鐵鍋笑開花的雪白的洋芋熱氣騰騰地盛開在我面前。
有什么能比這更打動人心?這是發生在大地上的事情,生動、意味豐富。我的寫作,正是受著這樣活生生的人和事物的滋養,才得以成長。生命是一條源遠流長的河,若要追溯,必要回到那些落地生根的往事上。
上課那天,全校學生都來了,教室里高高矮矮,目光深深淺淺。我與孩子們討論什么是作文,為什么有些作文會讓我們喜歡;我和他們討論寫作會給一個人帶來什么,我講到了快樂、愛、幸福,這都是一些深邃的詞語,但我相信他們對這些詞語會有最清澈的理解。我說,如果你愛上了寫作,你的一輩子會有著和別人不一樣的幸福,特別是當你們成了媽媽爸爸、爺爺奶奶……
孩子們都在笑,笑得那么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