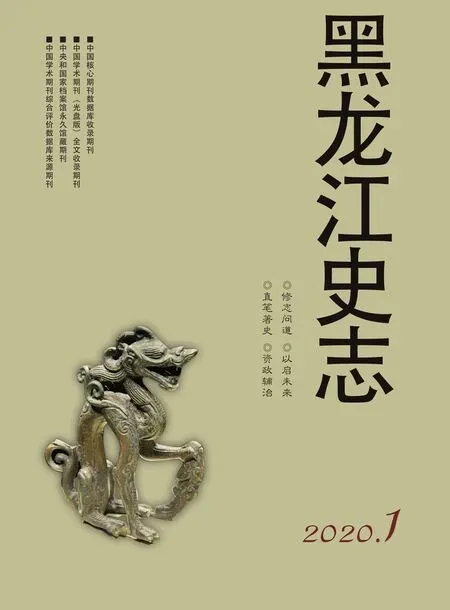把握生命里每一次感動——我和《中國地方志》歷任主編們
王 暉
今年元旦做了一個夢,讓我感動不已,一個多月過去還難遣于懷,不吐不快。2019 年第5 期《中國地方志》,發表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成員、復旦大學教授巴兆祥和李穎同志合寫的參加國際方志研討會的一篇文章,研究《中國地方志》1994—2018 年所發表的學術論文,將1687 位作者按發表的論文數量列出前50 名,本人忝居總數第一,共35 篇,其中方志基礎理論9 篇和方志編纂(14 篇)兩個單項第一。這是我始料未及的。回想《中國地方志》主編和編輯人員,一次又一次讓我感動,懷著一顆感恩的心,拾起這一片片難以忘懷的記憶。
1988 年5 月,《中國地方志》《方志研究》《史志文萃》三大公開出版的頂級方志刊物第5 期,同時發表我的3 篇文章,使我結識《中國地方志》主編孔令士、《史志文萃》主編黃德馨教授、《廣西地方志》執行副主編鄭正西等師長。1989 年第3 期,《中國地方志》發表我作為《安徽省毛尖山水電站志》編纂顧問作的序,時為副主編后繼任《中國地方志》主編的諸葛計給我來信,點贊此文并鼓勵要多寫寫文章,爭取參加全國學術年會。諸葛先生的信是莫大的動力,聞風而動寫了《論方志性質》一文,當年12 月參加了在湖南岳陽舉行的“中國地方志協會1989 年學術年會”。與會的《中國地方志》副主編劉永平看好拙作,臨別晚上他陪同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秘書長酈家駒,協會秘書長左建,副秘書長朱文堯、左開一、趙庚奇、歐陽發等一幫師長到我房間看我,鼓勵我不要改行,要潛心研究史志,晚上朱文堯設家宴熱情接待我和歐陽老師,當即邀請加入華夏地方志研究所,不久被聘為特約研究員。劉永平回京后力薦拙作以最快速度發表在1990 年第1 期《中國地方志》上。當期責編赫永清寫信告訴我,編輯部很重視這篇文章,一改過去每期之前發領導講話的習慣,將已經排版的領導講話撤下來,以首篇位置隆重推出拙作。這篇文章在全國反響強烈,爭鳴不斷,武漢市志辦主任舒練,在“2013 年新方志論壇”上的一篇文章上,稱這次爭鳴是歷史上方志性質爭論第二次浪潮,波及全國,歷時十余載。1994 年,酈家駒寫信鼓勵并作序,我主編出版了《方志性質辯論》一書,酈家駒寫信鼓勵并作序。
白駒過隙,情何以堪,上述多位良師都已作古,80 年代協會負責人只剩下趙庚奇、歐陽發兩人,參加那次年會并大會發言的也只剩下梁濱久、溫益群和我三人。現在活躍在志壇上的“大咖”們,也都是20 世紀90 年代和21 世紀初涌現出來的。酈家駒先生逝世時,我正在京參加方志學科建設規劃論證會,為了不影響會議,中指辦隱瞞了告別儀式,事后于偉平主編詢問與會者誰能寫懷念酈家駒的文章,我脫口而出能寫,后發表了《酈老教我當方志人》的文章。
2017 年8 月孔令士主編仙逝。孔老原是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是《中國地方志》第一任主編。有一次會議主持人介紹“下面請孔秘書長講話”,他一開口說我這秘書長是副的,全場肅然起敬,要知道多少副書記、副市長、副院長糾正過一個副字沒有。還有一次學術會議輪到他發言,按理他這個身份不說兩小時,隨口說說官話、套話半小時應該沒問題,可他一開口說我腦子一片空白,沒多少可說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自知之明是一種美德,孔老就是那么謙遜的人。記得在俄羅斯海參崴考察時,孔老算年高的,可一上大巴他就坐到最后一排。就他一個字、一句話、一個座,深深地影響著我。有一年我當團長帶32 人考察西藏,我就坐在后面,行在后面。滴水見陽光,小事見人品。孔老是我最尊敬的一位主編,也是最喜歡我的一任主編。1997 年昆明全國年會上,他帶我考察原昆明市志辦主任女兒開辦的“炎黃貴族學校”,目的是事后帶我去吃了一頓海鮮。每次相遇都問長問短,曾勸我來京工作,說方志出版社和理論研究室都在招兵買馬,遺憾的是那時他已經退下來了。
2019 年1 月,諸葛計先生突然走了,很意外,最后一次見面是在2017 年底《中國地方志》改版座談會上,那次他發言還是精神抖擻的,怎么說走就走了呢?剛剛80 后(歲)啊!已故的主編和編輯們,一路走好,別夢依稀不時懷念! 繼任的主編周均美,可真是大家閨秀,她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歷史學家周谷城的孫女。周大姐是最喜歡寫信的一位主編,那時候郵資比電話費便宜,故寫信多。舉個例子,有一年安徽方志學會組織評論《霍邱縣志》,我寫好評論就發給《中國地方志》,評論會后有一段時間接到M 先生電話,問我的文章是不是用了會議上他發言的觀點?周均美來信說王暉也投來相同的評論文稿。我說我的文章會前寫的以文與會,先前怎么知道你會議上什么觀點?后來我也接到周大姐來信,說先收到我的,后收到M 的,就告知他已經收到相同的評志文章……本來這件事情很簡單,認文也可,認人也可;用一篇也可,用兩篇也可,沒有必要給兩作者寫信,太客氣了!說周大姐是大家閨秀,可有一種不易察覺的女漢子性格,幾次會議看到她喜歡唱歌,喜歡游泳。2006 年在桂林召開的“志書質量標準體系研討會”上,聽她一席發言,我贊揚她從出版的角度談志書質量控制體系非常好,尤其說話語氣好,沒有女士大喊大叫那種尖利的語調。她哎呀一聲感嘆道,我是遲來了一天,不知道你們之前討論了什么,才沒有膽子大聲說,我平時說話可是高門大嗓的。我說那不行,陽剛陰柔,女人說話要柔美,男人不喜歡女強人。男人說話要陽剛,男士聲如古寺洪鐘,黃河之水天上來,汪洋肆意,滔滔不絕,即便說得不完美出點小錯都沒關系。從某種角度看,不出錯容易講官話、套話和人云亦云的廢話;出點小錯才是真話、實話,有趣有用的話。
《中國地方志》最紅火的時代,當數于偉平主編的期間。在她13 年任內,刊物由雙月刊轉為月刊,適時為二輪修志現實提供理論支撐。她團結作者,加強名刊建設,創辦新方志論壇,由開初邀請9 個人與北京市志辦聯合試辦,到后來年年與全國各地聯辦,將一些志辦領導、大學教授和專業修志人員上百人吸引到論壇中來,廣結人緣;拓展稿源,保證了一年12 期用稿質量,每年還出版一期增刊。最為稱道的是發動20 多位專家教授參與評選,編纂出版了《中國地方志30 年優秀論文選》。這些無疑與她干練的工作作風有關。她的風格給了我不小的壓力,除了逼我每年要寫兩三篇文章外,還逼我參加編輯部的諸多活動,每期論壇參與策劃選題、審稿、撰稿;優秀論文評選、藍皮書創刊、方志理論通典,都要求我參加課題組。參與起草課題方案,分配的工作任務不堪其重,如方志理論通典(當時的書名)選編參考著述目錄500 多頁,其中250 頁目錄的民國以前刊物發表方志理論文章要我責編,幾十人參編的項目,讓我一個人承擔一半目錄的任務,這也太重了!我在會上推辭,她不容置否,只是許諾在中指辦給我開一間專家房,給我一定的交通費,再配一位女博士協助完成。可我《安徽省志》編纂任務壓得透不過氣來,分身乏術,再加上哪位女博士得了重病不能上班,萬般無奈這項任務徹底停擺。
1997 年在昆明召開的中國地方志協會學術年會上,我認識了邱新立,原來他在理論研究室工作時,就經常邀請我參加他組織的學術活動。過去時興拜年賀卡,他給我賀卡都寫得特長,有的記錄了工作進程,其中一張賀卡寫了三件事:一是志書質量標準研討會,二是省志研討會,要我做些準備;三是修志立法列入一檔計劃,多年來依法修志的夢想即將成真。國務院《地方志工作條例》頒布前,他第一時間打電話告訴我,總理簽了,馬上發布,我們多年的努力終于有了結果,這可是積大功德的事。我們一同為方志事業高興。多年一起活動,許多同框記錄了我們的感情,當他還是處級干部時,合影中我們都屬于后排站派,我清楚地記得好多次我們糾結在一起,每次都互相推讓一番,我讓他站中間,他總是謙虛地將我推到中間,中央單位的靠邊站,那份情誼總讓我有些感動。后來他擔任中指辦的副主任,變成了前排坐派,合影我就挨不著他了。他接任《中國地方志》主編時,我正好被聘請在中指辦上班。距離近了,就沒了許多客套,他把我叫到辦公室,賦予更重要任務,說我有省志編纂實踐,又發過不少省志編纂理論文章,要我寫一部省志編纂業務書。為保證這個工作重點,除了繼續參與匿名審稿工作外,他沒有要求我為刊物寫論文,甚至有些年會也不邀請我參加。
《中國地方志》是國家級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一刊發表我一個人35 篇學術論文,說來原因很多。第一是參加修志實踐行當多,工作使然。主編過縣志、鄉鎮簡志、山志和省志(分志執行副主編);參評過兩百多部省志、市志、縣志、鄉鎮街道村志以及山水專志;當過網管,設計過網站《皖風網》;負責全省舊志整理,統稿清代《皖政輯要》;參與修志立法,志書質量標準制訂,《方志中國》《魅力中國》展陳文本起草;雖然沒在編輯部待過,但長期參與《中國地方志》匿名審稿工作;雖然沒在出版社工作過,受聘兩屆方志出版社外審專家及專家委員會委員,參與書稿二審工作,應該說修志工作各個行當我都從事過。有道是處處留心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勤于思考,天道酬勤,每篇文章都是工作汗水凝成,越忙思維汗滴越多。第二是參加會議多,以文參與各層次學術會議。自20世紀80 年代登上全國年會講臺后,原中國地方志協會的年會幾乎每屆都給我發出邀請函。2010 年第十屆國史研討會,中指辦選派幾個人參會,分配我的任務是寫當代省志編纂的,可我在會上發言即興講會議主題史志關系,當代研究所領導說我講得不錯,我代表小組向大會匯報全組討論情況時側重講史志關系,會后又整理出兩篇文章,一篇還了《廣東史志》的文債。第三是參加編寫理論教材工具書多。主編《方志性質辯論》,執行副主編《方志編纂培訓講義》,參編《續志編纂指南》《當代志書編纂教程》和《方志百科全書》。承擔的任務多半是難點,《教程》分配我是不能參照他人著述的一章,我在常規之外每節首創寫成一篇論文發表。《方志百科全書》聘我為專家組成員,前三次研討會的主要材料就是討論我撰寫的方志學十幾個條目,為了更廣泛地征求意見,在《中國地方志》上發表了《什么是方志——〈方志百科全書〉條目試寫稿》。百科全書編寫組先后轉來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成員、復旦大學教授鄒逸麟,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常務副組長、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朱佳木的方志、方志學與方志理論定義的爭鳴與探討文章,促我作答。編書的同時常常是引發多篇論文,只是有些發在上海、安徽等省級刊物上。第四是參加編纂業務培訓授課多。受中指辦、國家部委、20 多個省市以及寧波大學等地邀請,參加一至四屆全國地方志負責人培訓班以及省、市、縣各級各類培訓班授課,僅安徽省直機關就辦過幾十個小型培訓班。2019 年“航旅縱橫”給我繪制了近幾年的飛行圖,這是不包括我生活在合肥、北京兩個大本營周邊幾個省市乘坐火車的出行圖,飛行48 次,到了29 個城市,除了兩省市外,學術活動足跡走遍全國。山東省連續9 年不讓我換題目外,其他地方授課我都要求主辦方提出新課題,克拉瑪依市給我出了20 多個題目,一個班除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志辦廖主任作開場動員一課外,我一個人講了兩天半。一個問題一個理論生長點,講一次課激發一次靈感,自然會形成一篇篇文章。第五是觀點獨特,遵循邏輯方法。黑格爾說人是靠思想站立起來的,文章同樣是靠思想觀點問世。論文寫作不能突破,往往是因為沒有自己的觀點,總是“炒現飯”套用別人觀點補充一點本地資料而已,這樣的文章遇到資深編輯就沒戲。其次就是不懂得邏輯方法,全靠樸素思維跟著感覺走,缺乏思辨能力,停留在工作總結層面上,沒有理論升華,甚至違背哲學觀點和邏輯規則不自覺地偷換概念,此類文章特別多,一般不被高水平編輯看中。再次不懂論述文體,做官樣文章,官話套話溜熟,學術深入不進去,熱衷于情商賣面子拉關系,沒有學術性就很難笑到最后。原中國地方志協會學術會議認文不認人,不搞“官本位”,很少見到領導與會,一有領導與會就變成工作匯報會。后來各個學會協會都變成“官員俱樂部”,做真學問的只是個點綴,導致國家整頓“理事不理事、董事不懂事”現象,不許行政兼職過多。新方志論壇為了取得廣泛支持,對各省志辦領導文章網開一面,促使有的領導研究業務走向學者型。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拙作之所以能順利發表,主要是堅持觀點獨特,從不人云亦云;講究方法,依靠哲學邏輯的力量取勝。例如《論方志性質》一文,它改變了歷史上方志性質定義方法,從過去現象性比喻定義進入本質性邏輯定義方式。盡管有很多爭鳴,但誰也改變不了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只要掌握了邏輯方法,就不怕門戶之見貶低,歷史最終都得承認。拙作1989 年提出的定義:“方志是記述地方古今各個方面或某一個方面情況的科學文獻。”17 年后的《地方志工作條例》方志定義應用了這種“種差+屬”邏輯公式,與拙作的區別僅僅是將抽象概念具體化而已,如空間種差“地方”改為“行政區域”,時間種差“古今”改為“歷史與現狀”,結構種差“各個方面”改為“自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內容種差“情況”改為“資料”,質量種差“科學”改為“全面系統”,而中心詞沒有更改,直接使用了“文獻”屬概念,《條例》定義為“地方志書,是指全面系統地記述本行政區域自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的資料性文獻”。當年我跟著田嘉、邱新立等參加了這個定義的討論,當時立法指導思想只對綜合性行政區域志下定義,不考慮專志,這樣就比拙作定義少了“某一方面”專志的規定性,但《方志百科全書》中方志定義補上了。著述立說要有思想觀點,完成它還要靠充分的論證資料說話。如何組織論文資料,我的老師人民大學李文海教授(后任人大校長)曾給我們做過專題指導,受益匪淺。資料的高度決定論文的高度。我從公元前1000 多年西周開始,穿越3000 多年時空,研究歷代古文經學家的觀點,提出與眾不同的史志觀,在2008 年第12 期《中國地方志》上發表《方志與地志是歷史與地理之母》。這篇文章雖然沒有像前文那樣引起軒然大波,雖然于偉平主編將其列為當年最佳論文,雖然后來被專家們評為優秀論文,但社會上贊成者不多,地理界沒見到反應,而那些研究方志的歷史學界教授們斥為大逆不道。誰知2019 年1 月,中指辦召開方志學科建設研討會,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主編李紅巖與會提出,方志學完全可以成為獨立的一級學科,古文經學家的觀點是先有方志,后有歷史。這話唯有我最愛聽,等于說了我11 年前說的“方志是歷史之母”。2010年我出版了《方志論》一書,在封底上(見書影)我寫下理論研究的體會。理論研究的目的是立說。如果文章發表出來沒有聲響,說明觀點落后于現實, 是陳舊的理論;如果文章發表后深受歡迎,說明理論與現實同步,是成熟的理論;如果文章發表后一片嘩然,爭鳴不已,要么是荒誕不經,要么是超越了現實,人們一時接受不了,真理是時間的女兒,最終被人們接受了,這才是有重大突破的創新理論。
最后,歷任《中國地方志》的主編和編輯們對我的高度信任和厚愛,是我撰寫此文目的所在。在我未入方志門的時候,老一輩編輯給我補寄創刊以來的刊物,使我有機會私人保存一整套刊物,由當初內部出版季刊到公開出版的雙月刊,由雙月刊到月刊,再由月刊回到現在的雙月刊;由白皮封面到彩色封面,歷經《中國地方史志通訊》《中國地方史志》《中國地方志》幾次更名,應有盡有,這也許是此刊完整收藏的全國第一人。北京王瑞朗曾問我這一套刊物是拍賣還是作為鎮宅之寶,后者說對了,這份刊物是中國地方志最高學術陣地,是一部原始的方志學史,無疑對中國方志的編纂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無疑對方志人的成長賦予了豐富的知識和營養,培養了一代又一代方志人,感謝這片方志人的園地,感謝這片園地一代代辛勤的園丁,把握生命里每一次感動,必將你們銘記在我生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