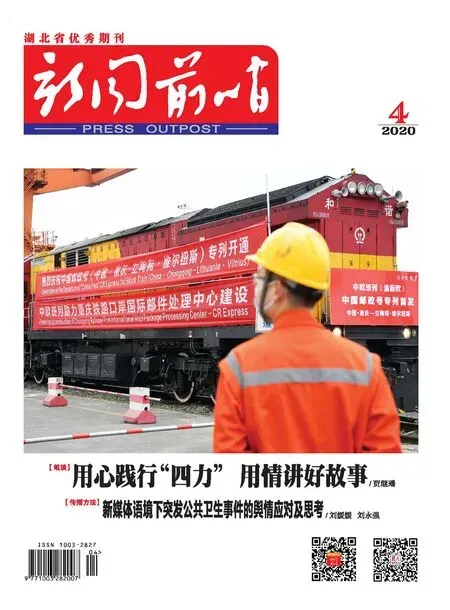電影《寄生蟲》的敘事策略分析
◎商愛笛
第92 屆奧斯卡頒獎典禮在2020年2月落下帷幕,由韓國導演奉俊昊執導的《寄生蟲》獲得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 最佳國際電影四大獎項, 這是歷史性的時刻。 《寄生蟲》動搖了好萊塢電影在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霸主地位, 成為第一部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非英語國家的電影。敘事性是電影存在的本質屬性,是使用敘述語言來講故事的藝術形式。 奉俊昊讓現實主義照進《寄生蟲》的類型化創作,同時將暴力美學雜糅進電影的敘事之中,運用多種敘事策略書寫關于社會階層、關于財富分配、關于人性的韓國故事。
一、經典線性的敘事結構
電影的敘事結構是電影的主干, 將電影編織成為兼備視聽美感的藝術品。《寄生蟲》運用經典的線性敘事結構,從貧窮的基宇得到好友推薦到富人樸社長家做家教, 到基宇一家通過一系列計謀替代樸社長家的美術家教老師、 司機和管家,到樸社長一家出門露營,原管家進入地下室找自己的丈夫,基宇一家和原管家一家的秘密被互相揭開,到基宇害怕暴露在樸社長兒子的生日派對上計劃殺死原管家丈夫,結果未遂反被傷,到原管家丈夫沖到派對現場殺死基宇姐姐,砍傷基宇母親,到基宇父親被“氣味歧視”激怒殺死樸社長,到基宇發現父親躲進地下室生活,到最后基宇幻想賺錢買下豪宅, 父親走出地下室享受陽光, 多個故事集中串聯,脈絡清晰,一氣呵成。 電影的時間、地點、情節三者高度一致,是對西方戲劇結構理論“三一律”的遵循。
但是, 這并不意味著線性敘事結構要絕對順承時間向度, 它可以在不改變線性順時基本走向的前提下運用倒敘和插敘來增添電影的光彩。《寄生蟲》中有兩處插敘,一是插入樸社長兒子半夜偷吃蛋糕看到原管家丈夫從地下室走出來昏倒的情節,這個情節推動了接下來一系列的情節發生:樸社長一家外出,原管家回來尋夫的情節。一場大雨樸家返回,小兒子不敢在屋子里睡覺跑去外面睡帳篷,樸家夫婦在客廳陪伴,而基宇一家剛好躲在客廳桌子下面,聽到了樸社長說基宇父親有窮人的味道, 樸社長的話成為基宇父親殺死樸社長的尖刀; 二是插入基宇父親殺人后跑進地下室并在地下室里的生活的情節, 向觀眾說明基宇父親沒有被逮捕的原因,同時讓觀眾感受基宇父親的絕望。經典線性的敘事結構中的兩處插敘是對主要情節的補充, 增加了情節的戲劇張力,讓《寄生蟲》精彩至極。
二、多重置換的敘事視點
當代敘事學家華萊士馬丁說:“敘事視點不是作為一種傳達情節給讀者的附屬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絕大多數現代敘事作品中,正是敘事視點創造了興趣、懸疑乃至情節本身”。敘事視點是“觀察事物的眼光”,是“創作的立腳點”,不同的敘事視點會講述不同的故事,傳達不同的思想。
《寄生蟲》在人稱和視點上選擇了非人稱敘事,不存在明確、固定的敘事人,因此敘事視點也在根據敘事的需要隨時發生變化。 《寄生蟲》的敘事視點來自于依次上場的基宇家庭的成員,并隨著故事情節變化。一組精彩的視點轉換出現在電影結尾,派對殺人事件發生后,電影出現畫外音是基宇的內心獨白, 觀眾透過基宇的視點了解了基宇姐姐的死亡、父親的失蹤,把觀眾拽入基宇的悲痛之中。緊接著,觀眾跟隨基宇的視點爬上山, 在基宇破解了父親用燈發給他的摩斯密碼時,和基宇一起重燃希望。 這時,影片嵌入了基宇父親的視角,觀眾跟隨父親讀信的畫外音回到殺人的那天,觀眾與基宇父親實現了“角色的替換”,基宇父親的驚慌和恐懼便是觀眾的驚慌和恐懼。 隨后,視點再次轉回基宇,他用內心獨白說他夢到賺錢買下了豪宅,父親走出了地下室。觀眾同基宇一起看到陽光灑落在父親身上, 一起感受到光明和幸福,但是電影結束音樂響起,觀眾被拉回現實,感同身受的是基宇夢想破碎的苦澀、無助和絕望。多重置換的敘事視點讓觀眾在觀看《寄生蟲》中獲得沉浸感,更能激發觀眾的獨立思考。
三、嚴密精致的細節把控
羅蘭巴特這樣說明細節在敘事中的意義,“一個細節即使看上去沒有絲毫意義,不具有任何功能,但這以現象本身正可以表示荒唐或無用等意義。 一切都具有意義或者無不具有意義”。 細節是電影敘事中的閃光點,實現深層次的蘊含和意味要依靠細節的處理。
《寄生蟲》中關于樓梯的描寫尤為撼動人心。 這個場景細節是對兩家人階層地位懸殊的直觀表達, 充滿了巨大的藝術張力。 基宇第一次去樸家上課,鏡頭一路跟隨著基宇。基宇從家里出來走了一段樓梯到達地上, 爬上長長的陡坡到達樸家庭院大門,再走上長長的樓梯到達樸家庭院,進入樸家客廳會見樸家夫人, 最后跟隨樸家夫人走上樓梯才到達樸家女兒的臥室。 這一系列鏡頭表達窮人和富人之間巨大的差距,以及窮人想要變為富人的艱難,尤其在基宇爬陡坡時采用了俯拍的鏡頭,更令人感受到富人的高高在上,窮人的卑如塵土。基宇一家趁樸家出門露營在樸家狂歡,樸家突然返回,基宇一家逃竄回自己家時,一路落荒向下。 他們順著往低處流的雨水,跑下陡坡,跑下長長的樓梯,穿過地下隧道后繼續跑下長長的樓梯和一段破舊的石階梯, 一步步被沖回到陰濕的地下巢穴。 這段則用了仰拍的鏡頭來表達基宇一家的渺小、狼狽和悲哀。
《寄生蟲》中的細節不勝枚舉,例如蟑螂、臺灣古早味蛋糕、司機餐廳等等,這些細節不是晦澀的符號,它們巧妙的塑造著人物, 推動著情節的發展, 給予觀眾真切的情緒體驗。 每一個微小的細節,都擁有震撼人心的強大力量。
四、弱者視角的暴力美學
學者郝建曾這樣定義“暴力美學”:暴力美學有它約定俗成的特定含義, 主要是指在電影中對暴力的形式主義趣味。 但是,奉俊昊在《寄生蟲》中體現的暴力美學,已經不是對暴力的消費, 而是成為緊密聯系現實和敘事的方式。《寄生蟲》中的暴力美學主要體現在電影的結尾,基宇抱著石頭企圖殺掉原管家丈夫, 反而被原管家丈夫從后面用套環套住脖子并拖拉, 最終沒能逃脫被原管家丈夫用石頭砸得頭破血流, 原管家丈夫沖進人群拿著尖刀插進基宇姐姐的胸膛,基宇母親見此情景與原管家丈夫廝殺,用燒烤簽刺死原管家丈夫, 基宇父親看到樸社長翻開原管家丈夫的尸體時捏住鼻子,隱忍的情緒瞬間爆發,用刀刺向了樸社長的胸膛。 場面極度混亂、血腥、暴力,情節發展讓人猝不及防。
《寄生蟲》中的暴力美學是情節的合理化呈現,不是對強視覺刺激的形式化追求, 不是作為弱者的基宇一家和前管家一家的肆意妄為,而是弱者本我的表達,是弱者本我的釋放,是借用弱者視角對社會進行諷刺、對政治進行隱喻。《寄生蟲》將基于一家和前管家一家放在極端的恐懼和絕望中,他們流露出的本性是人類對壓抑的宣泄。
敘事是電影創作的基礎和重點, 強大的電影敘事功力是《寄生蟲》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關鍵。 奉俊昊運用敘事策略在講好故事的基礎上,與人們探討社會議題。本文嘗試從經典線性的敘事結構、多重置換的敘事視點、嚴密精致的細節把控和弱者視角的暴力美學四個方面對《寄生蟲》的敘事策略進行分析, 希望從中為我國電影總結一點實踐性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