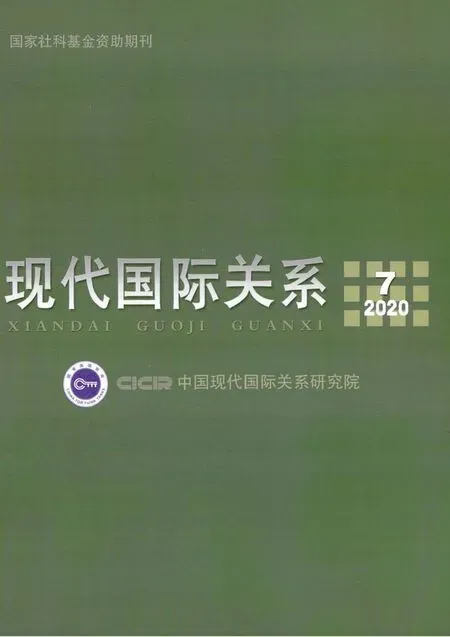印度對華示強外交的行為邏輯
胡仕勝 王 玨
[內容提要] 印中加勒萬河谷沖突使兩國關系跌至1962年邊界戰爭以來的最低谷。此次沖突看起來具有偶然性,實則是莫迪政府對華奉行示強外交、追求“高風險高收益”政策效果的一種必然結果。其后印度對華示強外交的舉措更加頻密,帶有尋機報復的直接考量,更有其深層邏輯。其中,既有印度常年追求“絕對安全”與主導地區秩序的政策慣性,也有莫迪政府有意利用外部戰略環境利好謀求對華“變道超車”的發展路徑選擇。印中關系中原有的結構性矛盾以及印國內政治生態的右傾色彩則為該沖突及莫迪政府對華示強外交預置了底色。此次沖突再次表明,兩國關系現有運行機制與架構效能衰減,難以平穩運轉兩個毗鄰新興大國之間的復雜互動,中印關系到了非重構而難以重啟的關口。
2020年本是中印關系大年,雙方為建交70周年準備了70場慶典活動。然而,先是一場猝不及防的新冠疫情打亂了一切部署,緊接著中印關系狀況迭出,及至6月15日夜爆發的加勒萬河谷流血沖突則將兩國關系推到1962年邊界戰爭以來的最低谷。印方挑釁在先,夜侵、偷襲中方控制區,重傷中方邊防官兵,中方予以痛擊實屬后發制人。印方邊防官兵遭遇大面積傷亡。從印方在沖突后明顯缺失后援救治的情況看,這次率連隊夜襲大概率是印度陸軍巴布上校的一次“獨走”式冒險邀功行為。印方不敢公開反躬自省,反而利用媒體、外交渠道在國內外大打“悲情牌”,渲染“中方霸凌”,引發印度社會群情激憤;不明真相的國際社會對印表示同情,美方政要則更是借機拱火,頻頻抨擊“中國威脅”并公開挺印,不少軍火貿易大國紛紛跟進,表白對印售武意愿。在各方哄抬之下,莫迪政府對華示強層層加碼,兩國對立情緒不斷聚積,中印關系一路下探。盡管通過雙方多層級、多機制的對話溝通,加勒萬河谷沖突引發的邊境緊張氛圍明顯趨緩,但對兩國關系造成的傷痕不易修復。這場1975年以來首現大面積傷亡的邊境沖突說明,兩國關系陷入了結構性發展瓶頸,已到了非重構而難以重啟的地步。它再現了莫迪執政以來對華關系的怪現象,即每年都在重復“高開低走止跌回升”的運行軌跡。本文擬探究印中加勒邁河谷沖突及其前后印方對華示強外交的行為邏輯,以期總結教訓、殷鑒于后,進而助益于未來兩國關系的突破。
一、絕對安全追求
印中加勒萬河谷沖突正是兩國之間新一輪軍事對抗、經濟脫鉤、民意敵對的導火索。邊界爭端只是兩國關系諸多難題中的一個(1)總體而言,中印關系長期深受五大問題困擾,簡稱五個“T”難題:涉藏問題(Tibet Issue)、領土爭端(Territory Dispute)、第三方因素(Third Party Factor)、貿易失衡(Trade Unbalance)以及互信赤字(Trust Deficit)。不同時期,不同問題對雙邊關系的干擾力度有所差異。,但自兩國先后建立現代國家以來一直對兩國關系特別是兩國民意構成嚴重干擾。
加勒萬河谷沖突雖系印度邊境駐軍部隊巴布上校率性魯莽所致,但偶然中有必然,是印度歷屆政府長期在邊境地區推行“前進政策”的必然結果。
所謂的“前進政策”,實質上,就是尋求單方改變邊控現狀的政策。早在尼赫魯時期,得益于地形的便利以及大英帝國殖民遺產的繼承,新德里大張旗鼓地實施“前進政策”,按照自身安全需求對中印邊界進行“自我修正”,不斷前插、蠶食、搶占中方主張的控制區,不斷試探中方容忍底線,直至觸爆1962年邊界戰爭。盡管印度輸掉了這場戰爭、丟掉了“前進政策”的大部分成果,但印度歷屆政府卻利用中方軍隊后撤之機,再度恢復了“前進政策”,繼續在邊境地區重施“切香腸”策略,期間還曾導致數起邊境流血沖突、軍事對壘事件。不僅如此,在兩國1980年代以來開展的各類型邊界談判中,新德里始終堅持當年尼赫魯政府“前進政策”所曾構建的“印方邊境實控線”。
如今,印軍已在中印邊界東段、中段基本上控制了絕大多數制高點。莫迪總理上臺后,印度邊防部隊著力在中印邊界西段推進“前進政策”。這也是莫迪執政以來兩國邊界對峙基本發生在西段的主要原因。以2019年為例,印度對我實控線的越線活動多達1581起,其中94%發生在西段邊境。一旦我方強勢回懟,邊界對峙乃至沖突隨即發生。邊界一出事,基本上兩國關系必受扯動。這也是2014年莫迪政府上臺以來,兩國關系總是高開低走的一大原因,形成了兩國關系年度高低變化曲線與青藏高原雪線年度升降曲線密切關聯現象:雪線升高(氣候轉暖),邊防對峙增多,兩國關系走低;雪線下降(大雪封山),邊防巡邏減少,兩國關系抬升。
印度政府之所以不惜冒著與中方發生軍事對峙乃至沖突的風險而幾十年如一日地執迷于“前進政策”,根本原因在于印度決策圈、戰略界長期存在的對追求“絕對安全”的一種迷思。此次印方挑起加勒萬河谷沖突的最大理由就是,中方在加勒萬河谷的邊防基建活動對其今年正式投入使用的達爾布克—什約克河—斗拉特別奧里地(斗拉特別奧里地機場去年10月啟用)公路構成了嚴重威脅,因為該公路是印度確保其對錫亞琴冰川(既是監控中巴喇啦昆侖公路的戰略高地,也是印巴兩軍對壘的世界最高戰場)實施有效控制的戰略要道。
印方對“絕對安全邊界”的執迷源自當年英印殖民帝國19世紀50年代起在次大陸推進的“科學邊界”計劃,意在為建立“更安全”“更具防御性”的殖民帝國,埋下了中印邊界爭端、印巴克什米爾爭端、印阿杜蘭線爭議的禍根。(2)Stuart Sweeney, Financing India’s Imperial Railways(1875-1914), Routledge, 2011, p.84.1947年獨立建國后,新德里以“大英帝國殖民遺產的天然繼承者”的身份承襲了這一理念,并不斷履踐,最終導致了印度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幾乎所有鄰國之間的邊界爭端。在中印間,遠至1962年邊界戰爭、1967年乃堆拉炮擊、1975年土倫山口槍擊事件、1986~87年桑多洛河谷軍事對峙,近至2017年洞朗對峙以及此次加勒萬河谷沖突等等,都是印度追求“更安全”“更具防御性”的“絕對安全邊界”的惡果。
實際上,對“絕對安全”的執迷是一種典型的零和博弈式行為習慣。一方所謂的“絕對安全”必然對另一方構成“絕對的不安全”,從而使兩國關系深受“安全困境”干擾。
二、保守政治的影響
外交服務于國內政治,國內政治決定外交風格。此輪中印交惡的導火線是邊境沖突,但國內政治生態的右傾化則是印度對華示強外交的政治邏輯。
2014年莫迪執政以來,印國內政治生態日趨保守。2014、2019年兩次大選,帶有印度教民族主義胎記的印人黨均強勢勝出,一舉結束1980年代中期以來長達30年的聯合政府時期。與此同時,印人黨“母體”國民志愿團(RSS)“母隨子貴”,政治影響如日中天。國民志愿團是一個以印度教民族主義塑造印度社會意識形態的右翼組織,2014年莫迪上臺之初,其基層組織“沙卡”不過4萬左右,如今擁有近8.4萬基層分支(3)根據國民志愿團發布的2019年度報告,印度全境共有84877個基層組織“沙卡”。參見“How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Is Spreading Its Footprint across the Nation,” DNA, March 9,2019.,統攝印度各層社會。國民志愿團并不直接參選,但大力支持印人黨競選,助其連選連勝。特別是2019年議會選舉中,在國民志愿團強大的基層動員力助陣下,印人黨大勝。部分地區,國民志愿團甚至繞開印人黨“建制派”,直接提名印人黨內“團干部”參選且表現不俗。
從印度兩屆政府的決策圈構成來看,政治掛帥色彩日益濃厚。莫迪第一任期里,66名部長閣僚中有41位出身國民志愿團;第二任期里,53位部長里有38位擁有國民志愿團背景。(4)Neelam Pandey and Shanker Arnimesh, “RSS in Modi Govt in Numbers — 3 of 4 Ministers Are Rooted in the Sangh,” The Print, January 27, 2020.從執政黨黨魁到國家總理再到內長、防長等重臣均出身國民志愿團。兩屆議會里,印人黨及其同盟軍的議員里幾無穆斯林代表,系印建國以來族群比例最失衡的議會。(5)本屆人民院,印人黨議員無一穆斯林,而上屆議會尚有一名穆斯林印人黨議員。穆斯林約占印度總人口的15%,2014年在議會下院席位減少至22個,僅占總席位4%,為50年來最低。2019年大選后,穆斯林議員27個,僅占比5%。(6)Eliza Griswold,“The Violent Toll of Hindu Nationalism in India,” The New Yorker, March 5, 2019.相比之下,在印人黨303位人民院(下院)議員中,出身國民志愿團的有146名,占比48%;在印人黨82名聯邦院議員里,出身國民志愿團的則有34人,占比41%。(7)Neelam Pandey and Shanker Arnimesh, “RSS in Modi Govt in Numbers — 3 of 4 Ministers Are Rooted in the Sangh.”
在印人黨與國民志愿團等右翼組織的聯手推動下,整個國家的社會與政治形態加速右轉,印度教民粹主義大行其道。追求理性、自由的傳統精英受到排擠,認同印度教特性、效忠國民志愿團等右翼團體的新精英則普遍得勢。顯然,印人黨、莫迪本人及其執政團隊出于自身政治利益考量,不得不在內政外交上特別是對華政策上要承受來自國民志愿團等右翼勢力的巨大政治影響。
中印兩國間存在的諸多結構性難題原本就使得保守派對華深懷戰略疑懼。莫迪政府上臺以來,保守勢力政治上得勢后便迅速擠壓傳統上以外交、商界精英為主的自由派生存空間,甚至印度長期堅守的在中美間“左右逢源”的戰略文化也受到沖擊。在印度教民族主義勃興的國內政治環境以及中美甚至中西方對抗的國際政治環境相互激蕩下,由保守勢力把持的莫迪政府,在對華政策的投機性與風險偏好上雙雙攀升。
僅以中資中企在印遭遇為例。以國民志愿團為代表的保守勢力長期以來反對一切外資。過去,印度右翼保守勢力特別擔心美國企業控制印度市場,敗壞印度“傳統價值觀”。國民志愿團下屬經濟組織曾多次阻撓沃爾瑪、亞馬遜等美企在印擴張業務,在美印經貿摩擦上拒絕對美讓步。近年來,隨著中國對印投資增多,特別是中資企業在印度發展迅猛。印度右翼保守勢力轉而認定中國資本威脅已迫在眉睫,遠遠大于美國資本。若不及時限制中國投資,阻止中國商品對印“傾銷”,印本土制造業將“永無翻身之日”,而且還對印度構成越來越大的安全威脅。此次邊境對峙與沖突期間,國民志愿團下屬組織“國貨覺醒陣線”(Swadeshi Jagran Manch)多次牽頭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反華”和“抵制中國貨”活動。
三、國內維穩的重壓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在其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民主國家解決國內問題的能力很弱,因為它們控制社會相對較難。為此,民主國家政府自然想把矛盾外移,外化成國際問題。(8)鄭永年:“中美之爭,我最擔心這件事發生”,https://wsdigest.com/article?artid=6995.(上網時間:2020年7月5日)這一觀點也同樣適用于解讀莫迪政府此次不斷渲染加勒萬河谷沖突的行為邏輯。
一方面,為回擊反對黨指責,莫迪政府必須對華示強。疫情防控問題早已是反對黨指責莫迪政府的“口頭禪”。面對指責,受限于各種現實條件,莫迪選項極其有限。不封城,挨罵;封城,也挨罵。對于反對黨特別是國大黨的各種指責,莫迪始終處境被動。但加勒萬河谷沖突發生后,面對反對黨的公開痛斥,特別是在面對國大黨領導人拉胡爾有關政府對華“認慫”“服軟”的抨擊時,莫迪執政團隊還是有些辦法的。只要對華示強,就能最大限度地有效回應反對黨的各種指責,而這方面的資源與選項明顯較多。譬如,大規模調動軍隊、采購更多先進軍事裝備、出臺與華脫鉤的各種經濟舉措、發表對華強硬措辭、縱容非政府組織“抵制中國貨”、在中國敏感問題上換個做法變個腔調,如此等等。盡管會冒著惡化對華關系、甚至有可能“傷敵八百自傷一千”的風險,但那又何妨。維持執政黨地位是民主國家領導人的最大政治,何況還有利好的外部戰略環境。實際上,自從莫迪不斷做出對華示強的姿態、不斷推出對華示強的舉措以來,反對黨的批判調門明顯降低。莫迪反而因種種對華示強政策而人氣攀升,進一步塑造了莫迪“安全守望者”的強人形象。
另一方面,要轉移社會矛盾,莫迪政府必須對華示強。莫迪連任以來,其一系列印度教民族主義政策,如宣布建立羅摩廟、推出統一民法典、修改公民身份法案等等,激化了印社會族群、教派、階級矛盾與沖突,社會騷亂此伏彼起。特別是2019年底印政府通過頗有爭議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以來,在全國范圍內引發持續數月的抗議活動乃至暴力騷亂,范圍之廣、歷時之長、國際負面影響之大,都是近20年來所罕見。即便是在2月底特朗普訪印期間,首都新德里還是爆發了1984年來規模最大的教派沖突,造成40多人死亡,數百人受傷。國內騷亂的政治損害已經初現。今年初,印人黨已在德里的地方選舉中慘敗;印人黨單獨或聯合執政的地方邦占全國面積的比例由兩年前的71%大幅萎縮至當前的35%。這一系列變化令莫迪執政團隊心驚肉跳。印度政治是一個超多元的生態系統,一切皆有可能。僅以2019年大選為例即可見選戰在印度的激烈程度:多達2354個政黨在中央選舉委員會登記注冊,其中450個政黨推舉了8000多名候選人,角逐543個議席。每一張選票都很關鍵。就在莫迪政府苦于缺乏應對國內騷亂的有效舉措之時,新冠疫情的暴發突然為其解了圍,使之得以冠冕堂皇地通過封城而在短時間內迅速化解此次國內政治動蕩的風險。
然而,國內騷亂是瞬間消解了,但疫情防控措施又使民生問題迅速凸顯。強制封城使打零工的“日薪”族(約占德里、孟買總人口的1/10)面臨或“病死”或“餓死”的兩難選擇。英國廣播公司(BBC)稱,封城造成印至少5000萬人失業;而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則稱,封城導致約4億非正規部門從業人員失業,“陷入深度貧困”。(9)“About 400 Million Workers in India May Sink into Poverty: UN Report,” The Economic Times, April 8, 2020.根據印度經濟檢測中心的數據,印度失業率從2月的8%一路飆升至5月的27.1%,僅4月就有1.22億人失業,即出現約1/4人口失業的嚴峻狀況。(10)Nikhil Inamdar, “Coronavirus Lockdown: India Jobless Numbers cross 120 Million in April,” BBC News, May 6, 2020.此時,席卷美國全國的“黑白大戰”騷亂更令莫迪政府惶恐。
加勒萬河谷沖突再度給莫迪政府提供了轉移視線的救命稻草。通過制造對華軍事對抗的緊張氛圍,通過出臺制華政策以及炒作懟華議題,莫迪政府在并不尋求對華戰爭相向的前提下,兩害相權取其輕,至少臨時安撫住了國內政治反對派和民眾躁動情緒與怨氣,最大限度地維持著疫情折磨下的政治與社會穩定。但這也只能奏效一時,民生問題終究將再度擾局。
四、變道超車的發展路徑選擇
莫迪執政以來,在經貿領域特別是在制造業領域“復制中國模式”一直是其孜孜以求的目的。
2014年9月,莫迪第一任期剛開始沒多久即推出“印度制造”計劃,誓言2022 年(后來調整為2025年)要讓印度制造業在 GDP 中的占比由當時的18%提升至25%,并為此推出一系列大膽的經改計劃以及以“印度制造”為主的各種眼花繚亂的發展倡議,但效果遠不如人意。據世界銀行統計,印度制造業逐季度下滑,近兩年在GDP中占比更是徘徊在14%~15%,為過去50年里之最低。(11)Vrishti Beniwal and Shwetha Sunil, “India Looks inward to Save Economy as Crisis Bites,” The Economic Times, June 25, 2020.疫情導致的中國“斷鏈”“斷供”則又暴露出印制造業對華高度依賴的脆弱性。特別是在莫迪政府非常看好的四大領域,即手機、紡織、電子和汽車零部件,因中國零部件的“斷供”,幾乎陷入停工待產狀態。聯合國3月初報告稱,“印度是受中國生產放緩影響最大的15個國家之一”。(12)印度對華產業鏈、供應鏈的依賴程度非常高。印度工業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近期(2020年5月)發布的數據顯示,印度目前電子元件、醫療設備、太陽能設備元件本地化生產程度較低,部分抗生素、維生素、汽車零配件、染料仍嚴重依賴進口。中國占印度進口總額約14%,是僅次于中東地區的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印度近25%的汽車零部件、50%的耐用消費品零部件、80% 至85%的壓縮機、95%的洗衣機自中國進口。參見“Trade Impact of Coronavirus Epidemic for India Estimated at 348 Million Dollars: UN Report,” The Economic Times, May 5, 2020.“斷鏈”“斷供”刺激莫迪政府掀起一場“自力更生”運動(這其實仍是“印度制造”倡議的翻版)。然而,莫迪政府很清楚,若按市場化與全球化的發展慣性,由于印度經濟發展嚴重受制于勞動力流、土地流、物資流與資本流“四流”之不暢,這場“自力更生”運動至少中近期內難有起色,除非另辟蹊徑,變道超車。
兩條蹊徑可供莫迪政府選擇。一條是利用印國內已有的“國貨”替代“中國造”。例如,印度政府擬對300余種“非必要低質產品進口”設置更高貿易壁壘或抬高進口關稅。這些“非必要低質產品”主要來自中國,印度國內已有替代品。再如,印方要求國有電信公司在將移動網絡升級至4G(注意不是5G)時排除華為和中興產品,這也是因為有了國產4G電信設備。
相比硬件而言,印度在軟件方面的“山寨”能力更強。特別是在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方面,由于中國企業先期多年的參與推動與培育,印度第一次站在了全民邁入互聯網時代的門檻上。例如,印度的視頻互動應用Mitron與中國的抖音在功能與用戶界面上高度相似,目前在印下載量僅次于抖音。這次禁用中國手機軟件將使該領域的“山寨”貨直接受益。其實,對于莫迪政府而言,10億級用戶的移動互聯網市場是一個世界級“金礦”,絕不會拱手相讓,更不會相讓給與之存在嚴重戰略互信赤字的中國。
由此可見,印度政府在“去中國化”時有著明顯的選擇性。莫迪政府尚不敢與中國“全面脫鉤”,因為印度不但有大量的產業領域高度依賴中國零部件和中間品供應,還有一些關鍵產業(如家庭常用藥)高度依賴中國的原材料供應,全面“去中國化”只會造成疫情背景下的更大經濟困境甚至社會動蕩,最終受損的只能是莫迪總理的“自力更生”運動,甚至擾動起民怨民憤。
另一條蹊徑就是利用中美產業脫鉤之機,吸引產業鏈向印度整體搬遷,快速實現“制造業強國夢”。為此,總理莫迪今春已要求各邦做好吸引自中國移出的跨國企業赴印投資準備,印工業和內貿促進局則牽頭組建跨部門聯委會,研擬吸引外資相關政策。與此同時,為推動全球產業供應鏈從中國撤出、建立“由值得信賴的合作伙伴組成的經濟繁榮網絡”,美也有意與印聯手推動產業鏈重構,鼓勵在華美企向印轉移,助其以“印度制造”取代“中國制造”。美國務卿蓬佩奧4月底表示,特朗普政府正設法連接美印兩國均能進入的供應鏈,尤其是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領域。(13)“US in Talks with India, Other ‘Friends’ to Restructure Global Supply Chains: Pompeo,” The Economic Times, April 30, 2020.美國務院負責南亞和中亞事務副助理國務卿瓦伊達則與在印美企代表會晤時指出,印是在華美企外遷的潛在目的地,“美印政府將為此提供便利”。(14)“Coronavirus | US State Department Supports Companies Choosing India as Alternative to China: Report,” Money Control News, April 29, 2020.此次利用加勒河谷沖突之機,印度政府第一次正式拿中國手機軟件開刀,也是為了向美方表明決心。
為了能夠在未來由美國主導的全球產業鏈中分得一杯羹,2020年4月,印駐外使領館密切接觸了逾千家美企,提出將為有意遷出中國的制造商提供優惠。為此,印已初步劃出約46萬公頃的土地,專門承接那些從中國遷出的企業,重點聚焦電氣、制藥、醫療設備、電子設備、重型機械制造、太陽能設備、食品加工、化學與紡織等行業。此外,印還有意通過開展美印軍工合作,引入美軍工技術與國防產業,軍民融合,在實現強國強軍的同時強大印度制造業。
至于印美能否最終復制中美產業鏈,則是一個天大的問號,需要時間以及莫迪政府更大的改革勇氣與措施來印證。眼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促使印度國民用“國貨”替代早已用得非常順手的“中國造”。這需要一個重大契機。加勒萬河谷悲情刺激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狂熱,乃至此前疫情催化的印度反華民意,都為印度政府此次強制禁用中國軟件、強制替代“中國貨”培育了土壤。只需稍加利用,在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大棒下,政府就可以在很短的時間里完成強制性的“替代”,至少短期內能讓印度的“自力更生”運動取得顯著進展。河谷對峙提供的機遇是有時效的。如果不能及時消費當前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緒,一旦邊境對峙消失,印度政府或可錯過這一難得的變道超車或咸魚翻身的大好時機。
由此可推定,至少莫迪政府公開渲染看似有些夸張的軍事調動、集結,不斷制造緊張氣氛,顯然并非真要“同仇敵愾”,對華動武,而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個“沛公”就是利用煽動起來的愛國狂熱,完成對中國產品的一次強行替代,部分實現印度產業大翻身。
五、地區主導權之爭
同時崛起的兩個毗鄰大國如何穩定相處一直是國際關系研究的大課題。自古至今的成功案例太少。
中印兩國建交之初雖有過一段“中印是兄弟”的蜜月期,雙方作為主要倡導者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至今仍對國際關系具有巨大指導意義。然而,兩國之間還是不可避免地爆發了邊界戰爭。冷戰末期,兩國關系逐漸走上正常化軌道,兩國通過不斷的戰略溝通,不斷擴大經貿合作,逐漸形成了諸如“兩國互不構成威脅”“兩國互有發展機遇”“兩國關系超越雙邊范疇而具有戰略與全球意義”等重要戰略共識。然而,2017年的洞朗對峙又將兩國30年正常化的努力打回原形。好不容易通過兩次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兩國關系被拉回正確軌道。特別是在2019年金奈會晤上,中國領導人提出了六條建議,旨在“為中印關系注入強勁內生動力”。然而,此次加勒萬河谷沖突及其前后莫迪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對華示強舉措幾乎又將兩國領導人的努力化為烏有:產業脫鉤卸掉了“兩國制造業伙伴關系”的建設動能;邊境地區高強度大規模軍事對峙終止了“切實提升軍事安全交往合作水平”的諸多努力;強禁中國手機APP在印使用切斷了“豐富人文交流”的重要管道。兩國關系更是下跌到196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可見,兩國關系始終未能跳出地緣博弈的窠臼。
個中原因,恐怕還要從妨礙兩個新興毗鄰大國穩定相處的諸多因素中去找尋。前述所列諸多因素更多是種種表相且具可變性,還有一個難變的因素在始終作祟,那就是兩國建國后自始至終都面對的地區主導權之爭。
中印兩國都擁有成為“有聲有色”的世界級大國、強國所必需的資源與稟賦。19世紀中葉之前,兩國就曾是全球重要級經濟體,曾富甲一方,兩國經濟實力當時即占據全球半壁江山,但當時兩國交集太少,各相隔離,相安無事。
隨著殖民主義時代的來臨,印度迅速淪為西方殖民地,中國部分淪為西方殖民地。殖民者在實現對兩國財富大劫掠的同時,更是將兩個東方經濟體強行編織進由領土主權、民族國家、勢力范圍等概念構建的殖民秩序之中。特別是,中國主導、以王道為內核的東方朝貢秩序被殖民秩序所取代。由于受殖民者的鉗制,中印兩國間的互動基本上服務于殖民者之間的地緣博弈。這種地緣博弈造成的諸多后遺癥并未隨著殖民者的離去而消失,反而轉化為新生的中印兩國之間的新問題,諸如邊界爭端、涉藏問題、中印鄰三角關系等,不斷干擾雙邊關系發展至今。
這些問題原本系當年大英帝國構建殖民秩序特別是英俄地緣博弈的產物,之所以又成為中印兩個新生國家間的問題,原因在于中印兩國對殖民歷史存在著判若霄壤的認知落差。
中華民族對于遭受殖民的歷史只有深入骨髓的恥辱感,因為殖民者不但解構了以中國王道為內核與主導的周邊朝貢秩序,而且給中國人民留下了一窮二白的爛攤子和歷史屈辱。因此,新中國對殖民秩序必否定而后快,所謂“打掃干凈屋子再迎客”。
印度恰恰相反,印度人對英國殖民統治充滿了感恩,因為英國人的殖民統治給印度的現代化國家發展搭建了底盤與骨架,這包括文官治理的軍隊、鋼鐵骨架的公務員體系、精英階層的英語、基于“自由貿易”的司法和金融體系、競賭式的民主政治文化、一個現代化工業發展的底盤(15)陳峰君:《印度社會與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5、46頁。,以及一個以印度為中心的囊括次大陸和北印度洋地區的殖民秩序。所以,印度第一代領導人尼赫魯一邊擺脫英國殖民統治,一邊卻又提出“印度是大英帝國的天然繼承者”,忙著辦理“遺產繼承手續”。
一個新生國家是殖民秩序的否定者,另一個新生國家是殖民秩序的繼承者。中印兩國由此幾乎自擺脫殖民統治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在邊疆秩序以及地區秩序的構建過程中產生嚴重的利益沖撞乃至軍事沖突。中印間的涉藏問題、邊界爭端問題因而不斷激化終至戰爭相向,至今這兩個問題仍在不時沖擊著兩國關系的穩定。加勒萬河谷沖突就是最新例證。
比涉邊涉疆問題更復雜的就是以中印鄰關系為內容的周邊秩序之爭。周邊秩序之爭主要體現為影響力與主導權之爭。隨著國力增長,兩個毗鄰大國在共同毗鄰地區會形成越來越大的利益重疊。與此同時,國力增長還不斷豐富各自構建周邊秩序的資源與手段。在“國強必始自周邊”的經略邏輯驅動下,圍繞周邊地區的秩序之爭終究難以避免,并成為兩國關系的持久干擾因素。
印度認為,其地處南亞次大陸中心,無論基于歷史還是基于現實考量都是南亞次大陸和印度洋地區的天然盟主。這片區域理所當然應為印度的勢力范圍。在該范圍內,印度負有特殊的責任和義務維護地區秩序,其他南亞各國不應、也不能挑戰印度的主導地位,更不能招引域外勢力介入次大陸; 同時,任何次大陸之外的勢力均應照顧印度在地區秩序問題上的關切與敏感度,主動避免干涉地區事務,讓該地區事務由印度主導處理。實際上,尼赫魯早在1947 年印度獨立前就指出,“門羅總統提出的門羅主義確保了美洲免受外來侵略近百年之久,現在到了將同樣的門羅主義運用于亞洲國家的時候了。”(16)Tarik Jan ed.,Pakistan’s Security and the Nuclear Option, Islamabad: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1995,p. 153.
建國后,尼赫魯即開始在南亞地區實行“門羅主義”政策,將南亞事務視為印度的“禁臠”,不容外者染指與干預。例如,尼赫魯政府加緊沿襲英國的殖民政策,與喜馬拉雅山區小國逐次重訂“和平友好條約”,先后加強了對錫金(后于1975年正式吞并)、不丹、尼泊爾的內政外交控制;此后又通過“和平友好條約”,將阿富汗、緬甸也納入到“南亞戰略統一體”中。(17)Jaswant Singh, Defending India,New Delhi: Macmillan, 1998, p.146.通過這一系列條約,印度確立了“次大陸”以喜馬拉雅山為界的戰略定義。至于西藏,尼赫魯政府及其往后歷屆政府始終對中國和平解放西藏耿耿于懷。早在20世紀50年代,特別是1959~1962年間,尼赫魯政府就曾冒險嘗試最大限度地保持并擴張英國人曾從西藏攫取的殖民利益,不斷挑戰新中國捍衛在藏主權及領土完整的底線:一方面,不斷蠶食中國邊境地區,特別是不斷推進“前進政策”,尋建“科學邊界”,甚至多地段突破殖民帝國時期的邊控主張;另一方面,圖謀實現大英帝國時期未競的夢想,即讓“西藏脫離中國,成為中印之間的緩沖區”,不斷教唆西藏上層人士反叛中國統治,并在西藏叛亂平息后主動收容達賴。尼赫魯對華頻頻示強政策的后果就是直接引發了中印邊境戰爭。
尼赫魯的“南亞門羅主義”到了其女英迪拉·甘地執政時期更是成為印度周邊外交的正式政策。早在1983 年,英·甘地即提出了被稱為“印度主義”的“英迪拉主義”,亦即“印度版門羅主義”。英·甘地總理公開表示,“印度不會干涉這一地區任何國家的內部事務,除非被要求這么做,也不容忍外來大國有這種干涉行為; 如果需要外部援助來應付內部危機,應首先從本地區內部尋求援助。”(18)R. V. R. Chandrasekhar Rao,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The Round Table, Vol. 293, No.1, 1985,p. 63;李忠林:“印度的門羅主義評析”,《亞非縱橫》,2013年第4期,第16頁。在印度統治精英看來,南亞地區復雜的地緣政治和社會文化“迫使”印度不得不擔負起“南亞的安全管理者”的角色。(19)P. Venkateshwar Rao,“Ethnic Conflict InSrilanka: India’s Role and Perception,” Asian Survey, No.4, 1988, p. 419.在這種思想影響下,南亞鄰國越過印度而與非南亞國家特別是與北方鄰國中國打交道都是“不道德的”,新德里必予以強力干預。
莫迪執政以來,新德里提出“周邊第一”外交政策,開啟了印人黨時代的“門羅主義政策”。然而,此時印人黨時代的“門羅主義政策”卻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迎頭相撞。隨著越來越多的周邊國家積極參與“帶路”建設,中印在南亞及北印度洋地區漸漸陷入越來越尖銳的地區秩序之爭。印方對中國南亞政策的過敏反應已成為印周邊鄰國政局動蕩的最大外部因素。封鎖尼泊爾邊界(2015年9月~2016年1月)、分化斯里蘭卡友華政權(2014年12月~2015年1月)、通過先后介入選舉(2013與2018年)強力遏止不丹政壇的友華傾向以及搞掉馬爾代夫的友華政權(2019年),等等,這些都旨在確保印度的地區秩序主導權不受中國影響力的侵蝕。這些國家政局變動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凡主張與華友好的政治勢力和人物均遭無情打壓。
此次邊境對峙與沖突期間,莫迪政府維持對華示強態勢,甚至不惜使用戰爭用語,既為了最大限度地逼迫中方讓步,更為了威懾周邊近國,打掉其在中印間選邊站的任何心思。而且,更重要的是,莫迪政府對華示強也是做給美國人看的。
近年來,考慮到自身并不具備單獨與中國抗衡實力,印度不得不策略性迎合美遏華戰略,并對美主導的“印太戰略”采取更加積極融入的政策。但是,美方戰略界人士認為,印度做得還遠遠不夠。要想獲得美方更大力度更大規模的支持,印度必須繼續對華示強。例如,6月24日,曾參與小布什時期美國對印政策大調整的知名印裔戰略家阿什利·泰利斯在“卡內基印度”舉行的主題為“中印邊界:升級與脫離”視頻研討會上公開表示,美國需要印度在中美間明確“站隊”,美印走深的決定權在印度;印度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對華示強,可采取一些微妙的行動明確戰略態度,如分享應對中國挑戰的意愿、提升區域國家之間的戰略互操作性等;在公開輿論上,印度應該與“印太四國”加大公開接觸、在聯合國安理會共同發聲;要在看不見的幕后采取更多實際行動。
顯然,莫迪政府7月正式邀請澳大利亞參加印美日年度“馬拉巴爾”軍演的決定很難不屬于“對華示強”的范疇。美國2017年推出“印太戰略”以來一直希望印度邀請澳軍參加“馬拉巴爾”聯合軍演,但印此前一直未置可否。
六、國際環境之利
莫迪總理執政以來,除周邊環境有點鬧心之外,印度的國際環境總體趨好。在美西方不斷增加的制華需求催化下,特別是中美對抗日趨尖銳的情勢下,印度的地緣價值陡升,達至印建國以來的歷史峰值。這使莫迪執政團隊在對華示強時有了更多底氣與自信。
隨著中美邁入全方位戰略博弈的新階段,拉印制華已成美國跨黨派基本共識。21世紀以來,美陸續將印度定性為“天然盟友”、“印度洋‘凈安全提供者’”(20)“India as a Net Security Provider,” http://www.ias4sure.com/wikiias/gs2/india-as-a-net-security-provider/.(上網時間:2020年7月5日)、“民主基石”及美戰略級別的“離岸制衡手”,視印崛起“符合美國利益”,希望在“印太戰略”框架下,與印度一起在對華、地區和全球問題上實現“戰略對接”,共當“維護安全與繁榮的戰略穩定器”。美前國務卿蒂勒森2017年10月曾公開宣稱,美國絕不會“與中國——一個非民主社會——發展猶如美印關系那樣的關系”。(21)Rex W. Tillerson, Remarks on “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for the Next Century,” US Department of State,October 18, 2017.美方這一表態既強調了在意識形態上與印度的“天然盟友”屬性,又巧妙暗示了兩國戰略走近的共同訴求,即應對中國。正是基于這兩大共同價值取向,盡管受擾于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但美印關系依舊一路高歌猛進。今年2月下旬,特朗普訪印期間更是高調宣示兩國在 “印太地區的戰略趨同”和“在全球領導上的伙伴關系”,并正式宣布兩國建立“全面全球戰略伙伴關系”。印度知名戰略家拉賈·莫漢對此盛贊不已,并認為,美印建立“全面全球戰略伙伴關系”標志著,“印度對美國的看法發生了決定性轉變,莫迪終于打破了與美國接觸的系統性偏見”。(22)C.Raja Mohan, “Explained: Reading Donald Trump’s Visit to India,” The Indian Express, February 28,2020.印度的“戰略自主”文化已經生變。正如外長蘇杰生的最新闡釋所言,所謂的“戰略自主”就是“自主選擇盟友”且“勇于冒險”。(23)Arjun Subramaniam, “The One Speech That Explains India’s New Strategic Thinking: India’s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Has Laid out Clearly and Cogently a Set of Guiding Principles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 The Diplomat, December 5, 2019.
隨著印方對美戰略拉攏的日益接受乃至迎合,美印軍事防務合作不斷深入。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在“印太戰略”推動下,美印軍事合作甚至在某些領域超過了盟友水平。當前,美印防務正從軍火貿易向聯合生產和作戰體系對接邁進;從單兵種雙邊演習向三軍聯合大演習邁進;從情報分享到態勢感知體系的共建共享轉進;從雙邊安全對話向小多邊安全合作及區域軍事安全秩序構建轉進。加勒萬河谷對峙期間,美方積極向印提供邊境局勢衛星資料,積極詢問印方軍事需求,展現出來自盟友的“安全關愛”。美方的“熱情”為莫迪政府增強了安全上防范中國的信心與能力。
在邊境對峙與沖突期間,美方政要前所未有地高調“力挺”印度。其中以國務卿蓬佩奧最為活躍,6月15日在推特上發文,對因主動尋釁中方而“陣亡”的印度士兵表示“哀悼”;6月19日在“2020哥本哈根民主峰會”上的視頻講話中談及“中國威脅”并借機指責中方“制造與印度的緊張氣氛”(24)“Pompeo Tears into ‘Rogue Actor’ China for ‘Escalating’ Border Tension with India,” The Hindu, June 20, 2020.;7月8日表示“中國在邊境采取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侵略性行動”。(25)“Pompeo Says China Took ‘Incredibly Aggressive Action’ in Recent Clash with India,” Reuters, Washington, July 8, 2020.美方“拉印制華”的居心昭然若揭。受此不斷刺激,莫迪執政團隊難免生發出對華頻頻示強的政治沖動,甚至此次在邊境問題上大玩戰爭邊緣政策。
美印關系的不斷升級還帶動了美國同盟體系不斷加大對印度的示好力度。這突出體現為“印太戰略”框架下的小多邊安全合作越走越實。兩年多來,“印太四國”(美日澳印)磋商加快,迄至2020年年中已舉辦6次,一次比一次更具實質內容。2019年9月,“印太四國”還舉行了首次部長(外長)級磋商。更為重要的是,美日澳印四國均建立起“2+2”外長防長對話機制網絡,四國后勤體系隨著2020年6月4日印澳正式簽署《后勤相互支持協議》最終“連點成網”,四國海域態勢感知、情報共享也進一步網格化。這些進展為四國海軍日后在印太地區聯演聯訓、聯合偵查、聯合巡航提供極大便利與保障。顯然,在美推動下,印太四國同盟化趨向愈發明顯。印度戰略環境利好度達至歷史峰值。
不過,莫迪政權受制于國內諸多制度性瓶頸,尚未能將這種地緣戰略環境優勢轉化為“國家振興”的強勁動力,但借重這種地緣利好使其大國外交風生水起,由此催生出其在對華政策上日益偏強硬、不妥協乃至冒險的心態。通過示強外交,印度不斷探試中方“穩東謀西”“拉印制美”的戰略底線與套利空間。有印媒甚至指稱,莫迪政府相信,在中美摩擦加劇的背景下,印越是靠美,就越能引起中方對印度的重視。(26)“Sino-India Relations Defined More by Rivalry than Partnership,” Hindustan Times, July 26, 2016.此即中印關系近年波折不斷的地緣戰略邏輯。
對比之下,在印度看來,中國的外部環境險象環生。一方面,中美對抗全面加劇。美對華進行全政府、全方位、全時段的公開打壓,甚至加快推動構建反華統一戰線。另一方面,疫情加速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重組,中國經濟面臨逆全球化進程的嚴重沖擊。
確實,當前中印關系所處環境有點類似1959~1962年間。當年,尼赫魯政府不斷在邊境地區推行“前進政策”的一個主要底氣就是,新德里自恃擁有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同時加持,而中國當年對內受困于三年自然災害,對外受困于美西方經濟與軍事封鎖,中蘇關系又初現裂痕。中國之所以后來能夠在邊境地區通過一場自衛反擊戰實現局面的逆襲與反轉,主要是中國領導人不失時機地抓住了美蘇古巴導彈危機這一轉瞬即逝的戰略契機。這從1962年中國對印邊界自衛反擊戰時間段與古巴導彈危機的時間段幾乎完全重疊可見一斑。
總之,當前中印外部戰略環境的反差至少是此次印度在對華示強道路上越行越遠的一個重要誘因。由此可見,從某種程度上而言,當前因加勒萬河谷沖突而不斷緊張的中印關系實際上也是本地區大國地緣博弈的一個強烈折射。
七、結 語
綜合看來,印中關系邁入長波動期是大概率的事。面對這樣的新常態,印中關系顯然需要“重構”。
未來印中關系可能出現兩種斗爭前景。一方面,印中將在邊境地區特別是印中邊界西段地區繼續“纏斗”。兩國邊界爭斗將大概率地由“以對話求解決”邁入“以實力強爭控”的新階段。這種邊境爭控戰必然伴生邊境對峙乃至沖突,加勒萬河谷沖突絕非是“歷史的終結”。鑒于印政府已授予邊防軍“完全自由處置權”,未來雙方沖突由冷兵器升級為熱兵器的概率在加大。盡管如此,只要能夠防止熱戰,這種常態化的邊境對峙與沖突客觀上將有助于雙方“觸碰到”對方的容忍底線。久而久之,容忍底線就會成為一條橫亙在兩國邊防軍之間的碰不得的“高壓線”。這條“高壓線”最終很可能就是雙方間真正的“控制線”。一旦有了這條“高壓線”,即便雙方仍無法從法理層面達成彼此可接受的“國際邊界”,邊境地區也能基本維持和平和安寧。但在此前,危機管控將成為兩國涉邊部門的頭等要務。如何確保雙方在邊境對峙甚至沖突成為一種新常態的情況下仍能在其他領域開展正常合作,特別是保持并拓展有利于兩國崛起的發展合作,這是對兩國政府治國理政“智慧與能力”的巨大考驗。另一方面,“一帶一路”建設特別是海上絲路建設將與美國主導下的“印太戰略”在次大陸及北印度洋地區展開持久的地緣博弈。“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國崛起的發展戰略,美國則視“印太戰略”為針對中國崛起的牽制戰略,而夾在其間的印度也視參與美國倡導下的“印太戰略”為其大國崛起的重要路徑。由此,兩大戰略體系碰撞最為激烈的地方就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陸海地帶。其中,次大陸和北印度洋是重要角逐場。可以想象,若非重構兩國關系框架,印中未來的地緣博弈只會更趨激烈。
化解大國博弈危機之道,關鍵在于視對方的大國崛起為自身崛起的助力與機遇,相互成就。兩個毗鄰的大國不可能搬開,兩國在共同毗鄰地區的利益重疊與交匯只會越來越大。兩國只有摒棄絕對排他性的舊式主權觀,只有擁抱合作共贏思維,方能走出當前的地緣安全與大國博弈的零和式困境。
印中兩國業已擁有的強大后發優勢、互補優勢和先發優勢,互為毗鄰的地緣之利理應讓這三大優勢擁有史無前例的大開發前景。即便印方認為與美合作的收益超過對華示強的代價,那也只是暫時現象,因為就在發展問題上所擁有的共同利益以及所面臨的共同難題而言,印中兩國之間遠較各自與其他發達經濟體之間要大、要難。而且,印中兩國面臨的共同威脅和共同利益不但具有高度相似性,在可預見將來都難有根本變化,這理應成為兩國持久合作的基石。這個共同威脅和共同利益就是,如何化解兩國政府面臨的主要矛盾,即兩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需求與兩國不平等不均衡不充分的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如果將兩國民眾的每一張嘴都合成一起,那會是一個140~150平方公里的無底洞。兩國政府面臨的巨大挑戰與壓力就是,如何確保每天至少兩次往這個無底碩洞里填充量足質好的食材。由此,威脅、挑戰、利益三位一體,這在世界上也難找到比這還更需要合作共處的更加充分的理由了。
印中兩國還面臨一個更加緊迫的挑戰,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雙方需要審慎謀劃和作為,才能促使這場大變局朝著有利于兩國崛起的方向演進。印中都是歷史悠久的大國,絕不甘心成為其他大國的附庸。然而,如果因相互惡斗而致在這場大變局中缺位,那只會斷送再創歷史輝煌的戰略機遇。
如果非要給中印關系未來發展設計一條行穩致遠的路徑,那就是建立一種“分行于相鄰車道的車際關系”。中印各行其道,既不強求其他車輛追隨,也不突然變道、搶行,引發禍端。更理想的是,雙方還可以不時停下來交流互動;或互伸援手,解決雙方乃至其他方的各種突發問題,平安趕赴各自的目的地。
如是,中印關系必會迎接更加順暢的下一個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