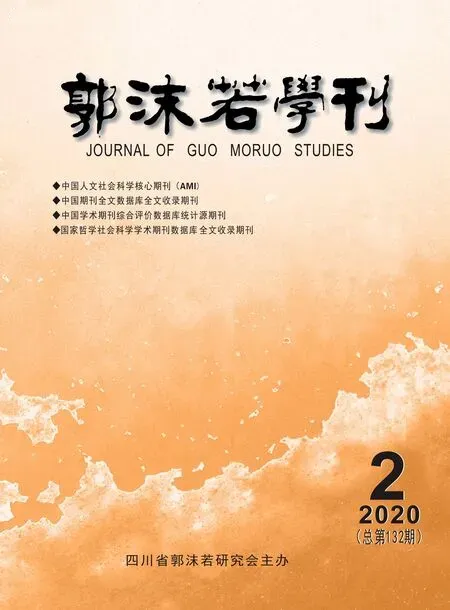郭沫若文學創作的個性氣質與兒童視角
陳 俐
關于郭沫若的個性,還有一種比較有代表性的看法,就是老舍先生的一段評價。1941年,國共兩黨曾共同為郭沫若祝五十大壽,老舍在《我所認識的郭沫若先生》中說:
沫若先生是個五十歲的小孩,因為他永是那么天真、熱烈,使人看到他的笑容,他的怒色,他的溫柔和藹,而看不見,仿佛是,他的歲數。①老舍:《我所認識的郭沫若先生》,舒濟編:《老舍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255頁。
老舍先生稱他是五十歲小孩。他認為,郭沫若性格的底色是真誠、坦率、熱情;另外還有一種看法,認為郭沫若性格復雜多變,較為典型的屬陳明遠的一段議論:
郭沫若在心理學分類上屬于一種矛盾、多元(多重性)的人格型。一方面,外向、情欲旺盛、豪放不羈;另一方面,內藏、陰郁煩悶、城府頗深。一方面熱誠仗義,另一方面趨炎附勢。②陳明遠:《湖畔散步談郭沫若》,丁東編:《反思郭沫若》,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年,第254頁。
另外,在評價郭沫若創作時,又有人認為他的作品很淺顯,意思直白,不像魯迅那樣有思想的深度,也就不那么富有“文學性”。這些看法其實包含了兩個問題:一,在郭沫若看似復雜矛盾的性格中,有沒有主導的方面,如果有,應該是什么?二,即使是在文字上淺顯直白的作品,從“文學性”的角度,有沒有他的價值和意義?
今天,我們就結合上述兩個問題進行討論。
一、郭沫若新詩創作的童心和童趣
我們最好還是從作品入手,換一個角度來認識郭沫若的個性氣質以及文學價值,那就是兒童文學。站在這一角度來讀郭沫若的文本,就會讀出另一種韻味。郭沫若在很多時候,是以一顆童心來寫詩作文,同時也不斷以“做人要一片天真”來努力實踐著對自己人格的要求。他那些被人們認為是淺顯直白的詩歌,其實是最具兒童文學特質,非常適合兒童閱讀的作品,這些作品不一定為成人所喜好,就好比當今的動漫形式的文本,成人和兒童的感受和理解,可能出現天壤之別。我們可以舉出五四時期他初入文壇時創作的一些詩歌進行討論。首先請看他的詩歌《夕暮》:
一群白色的綿羊,
團團睡在天上,
四圍蒼老的荒山,
好象瘦獅一樣。
昂頭望著天
我替羊兒危險,
牧羊的人喲,
你為甚么不見?③郭沫若:《夕暮》,收入詩集《星空》,上海泰東圖書局,1923年10月,引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211頁。
這首詩歌看起來較為單純淺顯,沒有所謂的主題和思想深度,就是兒童之眼看到的一幅自然畫面。小朋友隨意環視周圍的景色,萬物有靈的兒童思維使孩子將天上的團團白云想象成綿羊,將四周的荒山想象成瘦獅。綿羊與瘦獅,自然形成一種緊張的關系,即強者和弱者的關系。在這樣特別的想象中,兒童自然擔心羊兒的命運,油然而生出對弱者的同情。
作者完全化身為兒童,以兒童的視角來觀察事物。四周的景色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幅有兒童的主體意識參與互動的有機場景,生趣活潑、渾然天成。特別可貴的是詩歌在不知不覺中,表現出一種純真的同情心,這種同情是人類道德的基石,是人類最起碼的價值尺度,詩歌結尾在天真的反問中,不經意地完成了對兒童的道德熏陶。廢名曾盛贊這首詩說:
郭沫若有一首《夕暮》,是新詩的杰作。
……
這首《夕暮》我甚是喜愛。新詩能夠產生這樣的詩篇來,新詩無疑義的可以站得住腳了。
……
詩人的感情碰在所接觸的東西上面,所接觸的如果與詩感最相適合,那便是天成,成功一首好詩,郭沫若的《夕暮》成功為一代的杰作,便是這個原故。這首《夕暮》,不但顯出自由詩的價值,也最顯出自由歌唱的詩人的個性,也最明顯的表現著自由詩的音樂,可謂相得益彰了。①馮文炳(廢名):《談新詩》,北平新民印書館,1944年,第193頁。
在廢名看來,自然天成的詩就是詩趣和童心相融合的詩。廢名并沒有以郭沫若那些充滿了男性粗獷豪放音調的詩歌作為準繩來評價他的自由詩的成就,而是以這些具有童心童趣的詩歌來衡量自由新詩的成熟,其意味是非常耐人尋味的。再來看郭沫若的另一首詩《兩顆大星》:
嬰兒的眼睛閉了,
青天上現出了兩個大星。
嬰兒的眼睛閉了,
海邊上坐著個年少的母親。
兒呀,你還不忙睡吧,
你看那兩個大星,
黃的黃,青的青。
嬰兒的眼睛閉了,
青天上出現了兩個大星。
嬰兒的眼睛閉了,
海邊上站著個年少的父親。
愛啊,你莫用喚醒他吧,
嬰兒開了眼睛時,
星星會要消去。②郭沫若:《兩顆大星》,原載1923年《創造季刊》1卷4期,后收入詩集《星空》。引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卷,第217頁。
《兩顆大星》是一首什么樣的詩歌呢?我們完全可以看成一首搖籃曲,是成人唱給嬰兒的催眠的歌。對嬰兒,你能要求思想深度嗎?它本來就應該內容單純,詞句簡短;因為是唱詞,所以要有旋律,要回旋反復,要有音樂性。搖籃曲要求韻律舒緩、要有利于造成寧靜安定的氣氛,促使幼兒情緒穩定地進入睡眠狀態。這首詩在星星、大海、青天構成的意境中,給孩子營造一個溫馨、柔和、安寧的氛圍,引導兒童進入一種美好的夢幻狀態,使嬰幼兒的神經放松,在愛的搖籃中,逐步地進入甜美的夢鄉。
當然,這首很簡單的詩歌,其實也含有象征意義。他的象征意義是什么呢?“兩顆大星”象征著父母對孩子的愛。正是在愛心呵護下,孩子才能安然入睡。這些詩歌對于孩子而言,是愛的乳汁,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的孩子,才有健康的情緒,和諧的身心。這首詩雖然站在成人角度,但它是專門為兒童而作,最適宜兒童接受的,它是以成人視角來表現童心和愛心的詩歌。
再來看詩集《女神》中的另一首詩《光海》。這首詩1920年3月發表于《時事新報·學燈》。遺憾的是,這首詩一直沒有引起兒童文學界的注意。這是一首在詩人的本真狀態下從心底流淌出來的詩,它來自三方面的自然:
一是郭沫若幼年生活在相對封閉的四川鄉鎮,那里純樸的人情世態沒有玷污詩人的心靈。創作這首詩時,年青詩人不過是峨眉山的一滴清泉剛剛流到日本海,他仍保持著赤子之心。二是年輕的詩人在日本與日本姑娘安娜結婚后,于1917年與日本夫人安娜生下了第一個兒子郭和夫。由于生活窘迫,無錢雇保姆照顧孩子,于是初為人父的郭沫若一有空閑,就帶著兒子在博多灣的沙灘上盡情戲耍。這給他提供了在游戲中面對面、心對心觀察兒童的機會。與自己的兒子共同嬉戲的場景往往成為觸發詩情的媒介。“和兒”那天使般純潔無垢的童真,使初為人父的郭沫若大為感動。作者的童心被大大激發,即時即景,于是吟出了好些自然天成的詩。三是博多灣的美景。詩人生在蜀犬吠日的四川,對于陽光特別得敏感。博多灣千代松原的新鮮風景刺激著詩人,大海、沙灘、青松、年青的父親與稚嫩的兒子共同沐浴在艷陽普照的大海邊,詩人有如神助,一下捕捉到存在于人類中最直接、最樸素的原型經驗:對光的感受。
在人類集體的心理經驗中,光是混沌的終結,時空的起始,陰陽的裂變,生命的初始。光使世界色彩豐富,變化萬端,變得可感、可視、可知,光投射于人類的心靈,使人類的靈性被一點點激活,成為有智慧的生物。在太陽強光的照射下,詩人瞬間產生了強烈的視覺變形。山在強光的照耀下,成為一堆燃燒的火焰;海水在陽光的揮灑下,鋪成一片白銀。這片白銀居然又隨波起舞,銀波幻化為聚焦的鏡子,把天上白云和水中的帆船聚焦為競相賽跑的熱烈場面,好一幅萬類生命競自由的畫面。生命律動產生強烈的共振,充盈高漲的生命意識給詩人一種神秘的、天啟的審美感覺。詩歌寫陽光照射在自然萬物之上產生的神奇變異,寫詩人置身其中的感覺印象,如“光海”,“我和阿和/我的嫩苗/同在笑中笑”,“我們要在你懷兒的當中,洗個光之澡”。這些詞的超常組合,是客觀場景和主觀意識的交叉融合,造成了感覺畫面中的深邃意境。
《光海》的結尾,把詩歌提升到超凡脫俗的境界,“和兒”饒有情趣地把父親說成一只飛鳥。一個比喻,完全打破了成人的習慣性思維,將生命一體,互滲同構原始思維的特征表露無遺。縱觀此詩,我們不能不驚訝詩人穿透歷史時空、直抵東方思維源頭的直覺感悟能力。
由此可見,五四時期郭沫若崇尚的泛神論思想,與兒童的思維方式是相通的。在這種萬物有靈的直覺思維觀照下,萬物都和人一樣,有生命,有感情,有思想,能哭也能笑。而且,由于人和自然萬物能夠產生生命共感,其精神情緒是相通相應的,詩人和兒子在光海中洗澡的歡快情緒,與天地大海也是相通的。都處在自我與萬物同在歡笑的情態之中。①參見陳俐:《光之世界的生命律動——郭沫若詩歌〈光海〉新讀》,《名作欣賞》,2006年第4期。
我們討論以上三首詩歌,實際上是希望大家了解兒童文學可以有兩種表達的視角:一種是化身為兒童,以兒童的眼睛看世界,如《夕暮》;一種是成人用兒童理解和適合的語言為兒童營造或者講解世界,如《兩顆大星》。《光海》則是這兩種視角的綜合運用。郭沫若早期詩歌中,存在著類似表現童心和童趣的大量詩歌,如《登臨》《輟了課的第一點鐘里》《鷺鶿》《晴朝》《春之胎動》《新月》等,以及詩劇《黎明》《廣寒宮》。在小說和散文中同樣有類似的作品。比如他以動物為題材的小說和散文,就有好多篇,光是寫養雞的作品,早期就有五篇,都是很有兒童情趣的。
二、郭沫若兒童文學觀的價值取向
下面,我們由郭沫若的創作文本繼續探討他的兒童文學觀。這是郭沫若創作理念的一個重要部分。五四時期,隨著進化論在中國的傳播,“人的文學”在中國的確立,兒童的地位也進入了五四啟蒙思想家關注的視野。兒童該擁有什么樣的文學,兒童文學作品該怎樣創作,成為五四文學領域中小小的熱點。周作人從1912年開始,由對民俗學的興趣而進入童話、兒歌的研究。五四期間,應和著人道主義思想的倡導,他對兒童文學理論的研究遂成為自覺的意識。1920年1月,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學校作了《兒童的文學》的著名演講,仔細考察了不同年齡階段的兒童適宜哪些些讀物。當時的文化大師,如魯迅、胡適、葉圣陶、鄭振鐸等也都分別從理論和實踐去探討兒童文學的本質和特征。兒童文學作為獨立的學科和文學領域遂得以確立。應和這一熱點問題,1921年,郭沫若作了一篇專論兒童文學的文章《兒童文學之管見》,也發表了有關兒童文學的重要觀點。郭沫若在《兒童文學之管見》中明確提出:
兒童文學底提倡對于我國徹底腐敗的社會,無創造能力的國民,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藥。……今天的兒童便為明天的國民。②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1921年1月15日《民鐸雜志》第2卷第4號。
郭沫若首先從政治啟蒙、國民改造的角度提出兒童文學的問題。兒童是未來的國民,是具有創造的沖動,敢于“自由創造,自由表現”的優秀國民的雛形。兒童的成長與教育有關國家民族未來。這種認識,不獨是郭沫若,可以說是五四時期啟蒙思想家普遍的認識。且看五四初期兒童文學倡導者的觀點,葉圣陶呼吁:“為最可寶愛的后來者著想,為將來的世界著想,趕緊創作適于兒童的文藝品,總該列為重要事件之一”①葉圣陶:《文藝談·七》,原載1921年3月12日《晨報》副刊;引自韋商編:《葉圣陶和兒童文學》,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1990年,第439頁。;黎錦暉創建《小朋友》雜志是為了使小朋友“鍛煉身體、增加智慧,陶冶感情,修養人格,一年年長成千萬萬健全的國民,替社會服務,為民族增長”②黎遂:《民國風華——我的父親黎錦暉》,北京:團結出版社,2011年,第49頁。。
但是郭沫若在回答什么是兒童文學這一問題時,卻又強調兒童文學的自足性,他說兒童文學:
是用兒童本位的文字,由兒童底感官可以直訴于其精神底堂奧者,以表示準依兒童心理所生之創造性的想象與感情之藝術。兒童文學其重感情與想象二者,大抵與詩底性質相同;其所不同者特以兒童心理為主體,以兒童智力為標準而已。③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1921年1月15日《民鐸雜志》第2卷第4號。
這里,郭沫若又站在兒童本位的立場,強調真正的兒童文學,是照兒童心理,在自由的想象和感情中創造的文學,是把一切看成有生命的個體的文學。直到1943年,在《本質的文學》一文中,郭沫若仍強調兒童文學的境界是很高很難達到的,“頂不容易的是在以淺顯的語言表達深醇的情緒”,“要你能夠表達兒童的心理,創造兒童的世界,這本質上就是很純很美的文學。”④郭沫若:《本質的文學》,原載《戰時教育》第7卷第11、12期合輯,1943年;初收《沸羹集》,引自《沫若文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68-70頁。
在郭沫若的兒童文學活動中,《兒童文學之管見》是一篇綱領性的文章,其中的重要觀點甚至左右了郭沫若自身的文學創作方向。但這篇文章的觀點是多元博雜的,既有當時政治啟蒙的時代需求,又有由他的個性氣質所決定的審美選擇。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矛盾,也是當時新文學的一種矛盾和悖論的體現。從啟蒙和改造國民性的角度,要造就未來的國民,兒童文學便擔負著教育兒童、訓練兒童的啟蒙重任。但是從文學審美的角度,從兒童本位的角度,又必須尊重兒童的心理和思維特征。這兩種取向的融合預示郭沫若一生在兒童觀和兒童創作上努力的方向。
總體說來,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郭沫若以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以文化個體的身份自由創作時,他以自己的童心,寫著活潑的童趣。后來,郭沫若積極投身社會改造的活動之中,他的兒童文學觀更重在表達對兒童是“未來的國民”的期許。但更多地時候,他又同時強調兩種取向的不可偏廢。如在抗戰時期,郭沫若曾為組建“孩子劇團”花費了很多心血,他非常關心“孩子劇團”在抗戰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一方面充分地肯定小朋友為抗戰所作的貢獻,堅決地相信,“就要由這些小朋友們——永遠的孩子,把我們中國造成地上的樂園”。另一方面,他又反復告誡成人:“在精神上永遠做孩子吧,永遠保持敏感和伸縮自如的可塑性吧。”⑤郭沫若:《向著樂園前進》,《新蜀報》,1941年3月27日。引自王錦厚編:《郭沫若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186頁。
郭沫若在從事抗日宣傳領導工作時,常以通俗易懂的詩歌形式來宣傳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這一時期他寫了不少兒歌,以教育兒童從小就要有愛國的覺悟與觀念,從小就要養成優秀的品格和健康的精神。但他仍然注意了兒童詩歌的特征,并不生硬地灌輸教條和口號。如《七七幼稚園歌》,就以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三廳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中的物象白果樹和水牛山起興,以白果樹的高大端正和水牛的踏實堅韌來激發孩子們的精氣神,希望他們養成優秀高尚的性格和品格:
白果樹下有花園,
一群小主人。
我們大家真高興,
有志氣,有精神,
都象白果樹一根。
又高大,又端正,
我們要撐到天邊摩到云。
水牛山上有好花,
小鳥在唱歌。
我們大家真快活。
學讀書,學寫字,
都象水牛推磨兒。
不做聲,不泄氣,
我們要邁著腳步踏著地。①郭沫若:《七七幼稚園歌》,引自郭沫若:《洪波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248頁。
這一時期,郭沫若仍然把“童心”作為文學的底色,他認為在此基礎上再加以文學的本領,才能創造出真正的文學作品:
中國在目前自然是應該盡力提倡兒童文學的,但由兒童來寫則僅有兒童,由普通的文學家來寫也恐怕只有文學,總要有兒童的心和文學的本領的人然后才能勝任。因而年青的小友對于文學修養的努力是必要,而既成作家向天真無邪的心境之恢復也是必要。②郭沫若:《本質的文學》,引自《沫若文集》第13卷,第68-70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郭沫若的角色進一步發生變化,作為國家領導人,他需要從培養紅色接班人的角度來教育兒童,鼓勵兒童。1950年第一次全國少年兒童工作干部大會上的講話中講:
少年兒童工作的確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這是樹人也是建國的基礎工作。建設新國家新社會最主要的因素是人的因素,今天的少年兒童就是明天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乃至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者,我們要使今天的少年兒童能真正擔負起未來的國家主人翁的責任,一定要在他們的少年兒童時代加緊對于他們的工作。③郭沫若:《為小朋友寫作——在一次全國少年兒童工作干部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50年6月4日。
此后在每一年的“六一”兒童節,郭沫若基本上都要發表講話或寫詩來表達這些愿望。這些講話和詩歌,基本上代表國家主要領導人和紅色長輩對少年兒童殷切期望,如《獻給兒童節的禮物》《青年與春天》《永遠的春天》等。直到1963年六一兒童節來臨之時,郭沫若發表講話《長遠保持兒童時代的精神》,希望自己“還是一個兒童”,因為“兒童時代對于客觀新生事物最敏感,每時每刻在不知不覺之間都在進行著學習,”④郭沫若:《長遠保持兒童時代的精神》,《文匯報》,1963年5月31日。即使是郭沫若的晚年時期,他一旦和兒童對話,那種率真的天性便不自覺的流露出來。如上個世紀50年代的新詩《孩子們的衷心話》:
我們要去爬山,要去把船劃,
請你們也一道去吧,一道去吧!
不是說太陽是生命的源泉嗎?
多去和太陽見面,咱們不要怕。
不準爬山,怎么能夠去勘探?
不準劃船,怎么能夠去臺灣?
不準走遠,怎么能夠去探險?
不準行軍,怎么能夠去當兵?
我們不怕摔跤,不怕風吹兩打,
就只怕把我們死死地關在家;
像只籠子里的小鸚哥一樣啊,
兩只翅膀兒都要被人們關麻。⑤郭沫若:《孩子們的衷心話》,1955年郭沫若為慶祝六一兒童節所作。曾編入《駱駝集》,《沫若詩詞選》等,現引自《沫若詩詞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第8頁。
郭沫若站在孩子的角度,向成人社會表達兒童的訴求,既有時代意義,又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指導意義。聯系今天的現實,許多家長和學校只強調成績、分數,而忽視了社會大課堂對孩子們品格、意志以及知識的鍛煉和獲取。這首詩對于今天的教育仍有可貴的糾偏和救正的作用。
三、引申討論:“童心主義”以及以兒童為題材的成人作品
五四時期,與兒童本位的發現相伴隨的是“童心崇拜”。童心能夠自由地游戲、大膽地創造……童心的這些可愛品格,使得五四時期剛剛掙脫了封建綱常束縛的人們不由不對之衷心膜拜。對童心的發現,并非完全是中國現代作家自覺的行為,在很多情況下是受印度詩人泰戈兒的影響,泰戈爾的《新月集》影響著一大批中國現代作家。在這部詩集中,兒童世界被看成是與污濁的現實世界相對的冰清玉潔的理想世界。于是,在兒童文學的提倡和創作之初,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劉半農、王統照,郭沫若、葉圣陶、冰心等紛紛寫下一首首贊美詩,將兒童當作“神”來歌頌。表面上是這些作家對“童心”的吟唱,深層來看,卻寓含著作為成人的作者的生命體悟和美感追求,也寄寓著成人作者對理想社會的夢幻。如最熱烈的童心歌頌者冰心,她的《繁星》《春水》《寄小讀者》等集子中許多詩文都是被推為兒童文學佳作而載入各種兒童文學作品專集或選集。然而,嚴格看來,冰心的這些詩文只是“贊美”童心而非“表現”童心,其立足點是表現成年人通過觀照童心進而觀照理想世界、理想人格的人生態度。這些作品雖然充滿了“童心主義”的人生主張和哲學認知,但由于沒有能進入兒童的生命空間,沒有展開兒童的心靈體驗,所以只能算做以兒童為題材的成人作品,不能算做真正的兒童文學作品。
由此,我們就注意到郭沫若的創作中,還有一種類型,即以兒童為題材,卻重在表現成人的思想感情。小說中對兒童的描寫和思考,往往是作者在物質生活的困頓和事業無著的生活背景下展開。如早期的短篇小說《月蝕》記述他將自己的幾個兒女帶回國內,卻無法給他們一個健康成長環境而內疚的心境。“月蝕”是一個中心意象,是殘缺現實的象征。圍繞這個中心意象,作者以輪式輻射結構,講述了幾個故事:一是從日本回上海,去吳淞看海,卻因路費不夠而作罷,改去黃浦灘公園,又因備受歧視,備嘗亡國奴的滋味的故事;一個是由大海和月亮,想起故鄉流傳的天狗吞月的故事,由此引發的鄉思鄉愁;還有就是回憶在日本時和鄰居宇多姑娘一家的關系及變化;另一處還記敘了日本夫人一個夢境,這個夢表現了日本妻子去國離鄉的隱憂和對愛人命運的擔心。小說中一再將博多灣和家鄉的天然美景與都市的重重束縛相對比,將日本宇多姑娘父母的勢利與宇多的純情相對比,以我和夫人對家園向往與飄泊生涯相對比,以夫人夢中對丈夫隱隱的擔憂與自己對宇多姑娘的絲絲牽掛相對比。這些故事折射著作者心中交織著的多重矛盾:自然與都市的矛盾、家庭現實與純美愛情的矛盾、家園與飄泊的矛盾、科學之真與人性之善的矛盾、兒子成長的理想環境與現實生活貧困的矛盾。
上述矛盾在郭沫若的小說《飄流三部曲·歧路》中插入的一首詩歌中①原詩見郭沫若《歧路》,《創造周報》,1924年2月24日,原無標題,收入《〈女神〉及佚詩》時,添加了標題《失巢的瓦雀》,參見蔡震編:《〈女神〉及佚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第283頁。也反應出來。新月如鉤的黃昏,作者帶著兩個兒子在街樹下逍遙。兒子在歡呼雀躍中欣欣然追隨,而“我”卻在對無處躲藏的小鳥的憐憫中,哀嘆著自己的身世。在小說中,作者可以將心中種種矛盾從容地展示出來,將人性中復雜的柔弱一面暴露出來。在這些小說中,童心往往成為現實的參照,成為復雜人性的參照。那是一個告別青春的陣痛,是成人的儀式,是破繭出蛹的痛苦。
這就又回到我們最初提及的郭沫若個性中單純和博雜之間矛盾:對于兒童文學,郭沫若一種近乎本能的熱愛,一是他的個性使然,他是一個率性而為的詩人,但又是一個異常敏感、內心世界非常豐富的詩人。他向往著純真的天性,卻又發現自己永遠徜徉在物質與精神的牽扯中。在短篇小說小說《圣者》里,他一面表達著理想的兒童生活應該是與自然親近的生活的愿望,一邊又懺悔因為自己飄泊無定的生活,讓自己的孩子們在上海這種極不自然的都市中失掉健康的娛樂。他羨慕著自己的兒子無憂無慮的單純,但又意識到世界的誘力太大,自己不可能拋棄世界,拋棄社會責任隱逸鄉間。意識到要徹底地回歸兒童的天性,就必須與世事保持距離,“但是入世無才出未可”,自己并不甘心無所作為的一生,所以他把兒童看作“圣者”,將童心放在天國的位置,只可仰視追慕,不能完全踐行。
其實單純也可能和博雜聯系在一起,互相轉化,因為單純,就容易變化,而且迫不及待地將這種變化明顯地表現出來,郭沫若常常在作品和時文中,大膽地毫無保留地發表他的看法,這種看法和觀念也許是瞬間的念頭,郭沫若卻那樣強烈地、不留余地地甚至是夸張地表達。如果在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段中,這些無數個瞬間的、然而又是不同的表達連續呈現出來時,人們以全貌觀之,郭沫若就成為一個萬花筒似的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