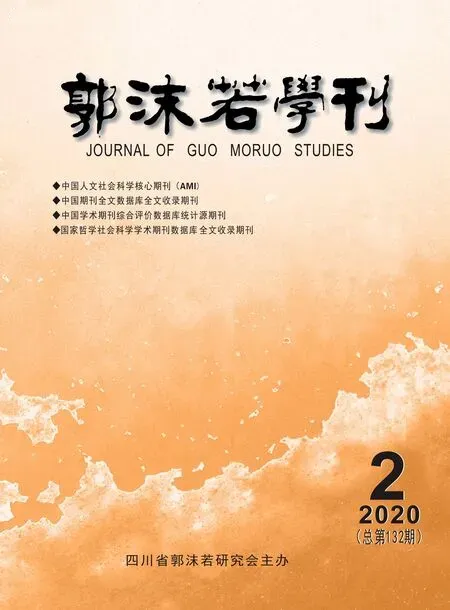論郭沫若、魯迅對梅蘭芳的不同態度
張 勇
(中國社會科學院 郭沫若紀念館,北京 100009)
那么,郭沫若與梅蘭芳同為新中國成立后不同文化領域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接續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重要踐行者和創造者,他們之間的交往又有哪些鮮為人知的史事呢?透過他們之間的交往我們又能提取出哪些隱而不彰的精神內質和文化內涵呢?特別是郭沫若對于梅蘭芳的態度與魯迅究竟有何不同、原因何在等諸多相關疑問便會隨之而來。
一、有感梅蘭芳的三件史實
郭沫若與梅蘭芳之間的交往不太為我們所關注,其主要原因在于兩者人生經歷完全不同,再加之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也大相徑庭,交集甚少,他們就如同兩條各自發展的平行線一樣,在各自軌道和領域內前行。盡管如此,根據現有史料可以知道,他們之間是有過密切交往。
(一)情真意切的書法佳作
就目前的材料來看,至少在他們相識之前,郭沫若對梅蘭芳的藝術表演能力欽佩不已,并贊賞有加。在1946年郭沫若曾為梅蘭芳書寫過一副書法作品,文字內容為:“余曾游塔什干觀烏茲白克人演奧賽洛及歌劇烏魯伯,其技藝水準甚高。歌劇中舞姿頗多平劇手法,私覺可異。一日,烏茲白克外交部長告余,渠肄業莫斯科大學時曾觀畹華博士演出,極為心醉。演奧賽洛及烏魯伯諸演員時亦求學莫京,亦具嘆為觀止。聆此乃恍然大悟,藝術之力信屬宏偉。余曾戲言,俄國人民僅知中國有二人,一為孔夫子,一則梅博士也。”①手跡見《郭沫若書法集》,四川辭書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首先,從這篇書法作品的內容來看,雖僅有百余字,卻清晰地闡述了郭沫若對于梅蘭芳高超藝術技藝的贊許與文化水準的欽佩之情。這段文字中至少傳達出如下幾個信息:一、在郭沫若書寫這段文字時他與梅蘭芳并不熟悉,郭沫若是通過與烏茲白克外交部部長交談時,得知他們的演出得益于梅蘭芳表演藝術的熏陶后,郭沫若解開了多年前在觀看西方戲劇時的疑惑,特別是使用“恍然大悟”一詞,更是非常明確地表達出郭沫若思維認知的突然性,由此也基本可以判斷出,此時他與梅蘭芳之間并不是非常熟悉,而僅僅只是因各自領域所造成的社會影響而知曉;二、郭沫若對梅蘭芳的藝術成就賦予了極高的地位,甚至將梅蘭芳放在了與孔子同等重要的位置,雖然郭沫若稱之為“戲言”,但不可否定,郭沫若對梅蘭芳藝術成就是高度認同;三、在稱謂上,郭沫若對梅蘭芳并沒有直呼其名,而是使用了畹華博士和梅博士。我們都知道梅蘭芳原名梅瀾,梅蘭芳是1910年他16歲登臺演出之際所取的藝名,而畹華是梅蘭芳的字。1930年梅蘭芳率團在美國的西雅圖、芝加哥、華盛頓等地方巡回演出72天,引起了美國各界的轟動,并因而獲得了美國波拿學院和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一般只有很親近的人才稱梅蘭芳為畹華,而以博士稱之也不常見,郭沫若以畹華博士和梅博士來稱謂梅蘭芳,也可見他對梅蘭芳既親切又尊重的情感。
再者,從書法藝術的角度來講,此段文字是使用行草方式寫就的長條幅作品,是郭沫若40年代中后期書法藝術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百余字的書寫有行有列,較為整齊勻稱,行草字體收放自如,飽含適中、恰當的抒情意味。因為郭沫若與梅蘭芳此時畢竟還不熟識,用行草的字體既避免了草書狂放不羈的濃重情誼,也可利用行書流暢的筆畫,恰當地表達出自己激情洋溢的贊賞之意。作品的前半部字體尤其工整,謹遵行草書寫的規范要求,大小比例、間距均衡,而自“聆此”一句開始,隨著書寫情緒的深入,郭沫若便開始發揮行草較為自然灑脫、隨性發揮的特性,字體便開始走出規則的限制,字與字的大小、間隔也略有不等,筆畫也長短穿插,即便是同一字,也出現了不同的樣式,如“俄國人”的“人”與“二人”的“人”在筆畫構造、大小比例都截然不同,特別是作品結尾“梅博士也”四個字的大小,基本是前面字體的兩倍,比例完全突破整個作品的限制,更加突出了郭沫若對梅蘭芳價值的認可。此作品還有畹華博士和郭沫若的款識,也有郭沫若的印文,是一幅難得的書法精品。郭沫若以一副書法作品的形式表達出他對梅蘭芳不同尋常的評價,他以藝術的形式回饋藝術人物,更是具有特殊的藝術情愫。
(二)熱情而永恒的握手
北京前海西街郭沫若紀念館的第四展廳中有一張郭沫若與梅蘭芳的彩色合影照片。照片中郭沫若身穿中山裝,左耳佩戴著助聽器,站在左側,而梅蘭芳則以戲裝入鏡,他身著古代帥服,并未卸妝,展示了英姿颯爽的穆桂英形象。照片拍攝于1961年5月31日,當晚,梅蘭芳應邀在中國科學院禮堂表演自己的代表作《穆桂英掛帥》,這是演出后在他們在舞臺中央所拍攝的一張照片。可誰曾想到,這張梅蘭芳與郭沫若握手并合影的圖片,卻成為了二人交往過程中永恒的瞬間,它記錄下兩人生前最后一次近距離的交流。
1961年5月31日,梅蘭芳應邀在中國科學院禮堂的演出《穆桂英掛帥》,這也是他留給世人最后的舞臺形象。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在觀看演出之后感嘆道:“中關村科學院的禮堂實在太小了,但有你在臺上演出,使那小小的禮堂成為了無限大的宇宙。在那兒真是充滿了光輝,充滿了愉樂,充滿了肅靜,充滿了自豪,充滿了生命,充滿了美。”①郭沫若:《在梅蘭芳同志長眠塌畔的一剎那》,《人民日報》1961年8月10日。作為曾經創作出轟動一時的《屈原》《蔡文姬》等歷史劇的郭沫若來說,梅蘭芳在舞臺上用飽滿的激情和唱腔所傳遞出對穆桂英生命意識的尊崇和敬意,恰恰與他的藝術追求高度一致。梅蘭芳的左手緊緊地握著郭沫若的右手,似有千言萬語,卻無需表達。只要藝術的精神永恒,人的生命價值也就會永遠,每當梅蘭芳的唱腔回蕩于耳畔之際,郭沫若便會堅定地認為“穆桂英永遠活在舞臺上,梅蘭芳永遠活在人們的心里”。
四是考核問責更加嚴格。這一制度明確要求將水資源開發利用和節約保護的主要指標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的主要負責人要對本行政區域水資源管理和保護負總責,并制定和實施嚴格的考核和問責制度。
對于這次握手與合影,郭沫若記憶猶新。他在梅蘭芳去世的第二天,也是梅蘭芳追悼會舉行的日子,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在梅蘭芳同志長眠榻畔的一剎那》的緬懷文章。文中,郭沫若又一次回憶到了這次握手:“你的左手緊緊握著我的右手,握得那么緊,讓我深深感受到了穆桂英的精神。你雖然沒有說話,但你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你是在說:讓我們永遠握著手并肩前進吧!”話語雖然樸實無華,卻是對他們兩人見面和握手照片最好的注解。他們雙方的握手不僅僅是禮節性的表示,而更重要的是雙方內心藝術世界的溝通和認同。②郭沫若:《在梅蘭芳同志長眠塌畔的一剎那》,《人民日報》1961年8月10日。
(三)發自心底的沉痛悼念
在西郊中國科學院禮堂演出《穆桂英掛帥》兩個多月后,1961年8月8日,梅蘭芳便走完了自己輝煌的藝術人生歷程,郭沫若對此深感悲痛是難免的。1962年為紀念梅蘭芳逝世一周年,由阿英編劇的傳記紀錄片《梅蘭芳》拍攝完成,郭沫若不僅僅題寫了該紀錄片的片名,創作了題詩《詠梅二絕有懷梅蘭芳同志》,并且用自己獨具深情的語調親自朗誦,放在此紀錄片的片頭。這在郭沫若一生中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事情了。
在郭沫若詩歌創作中悼亡詩并不多,這兩首悼念梅蘭芳的七言絕句更是難得一見。第一首四句寫到“漫夸疏影愛橫斜,鐵骨凌寒笑腐鴉。瀝血喚回春滿地,天南海北吐芳華。”這首詩不僅僅顯示了郭沫若以學問入詩的才情,還借助于傳統文化的意象表達了對梅蘭芳藝術價值的欽佩之情。“疏影橫斜”“瀝血芳華”都是古代詩作中經常用到的意象和傳說。借助于傳統文化典故,詩歌便一語雙關,既借助梅花傲然挺立的風格來贊譽梅蘭芳高尚的人格情操,也依托杜鵑啼血的典故頌揚梅蘭芳勤于創新的藝術追求,使梅蘭芳的藝術世界更加具有傳統文化的魅力。另外一首更加具象到梅蘭芳細節的刻畫,詩中寫到“仙姿香韻領群芳,燕剪鶯簧共繞梁。敢信神州春永在,拼將碧血化宮商。”直接抒發對梅蘭芳去世的悲痛之情,并借此贊譽梅蘭芳所取得傳世的舞臺成就和永恒的藝術魅力。以前我們可能更關注的是這兩首絕句本身,但詩歌必須朗讀出來,才能更加彰顯出它本有的藝術魅力,如果創作者能夠親自朗誦那更加能夠表達出無限的內蘊,而這一切郭沫若在對梅蘭芳的紀念中做到了。從現存的影像資料中,透過郭沫若低沉舒緩的語調,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他痛失好友的悲痛,及知音難覓的悲哀之情。
郭沫若與梅蘭芳究竟有過多少次會面與交流,可能并不好清晰地統計出來了,但從上述演出時的專情賞析、未曾相識時的傾情贊許、對逝者的深情緬懷等三個重要事件中,郭沫若對梅蘭芳不吝贊譽之詞便可探知他們之間彼此惺惺相惜的深厚情誼。郭沫若欣賞梅蘭芳的藝術成就,更是欽慕他的人格魅力,特別是梅蘭芳通過《穆桂英掛帥》《貴妃醉酒》等一系列經典藝術作品,所展示出對藝術美執著的表現和追求,對生命力無限熱愛和贊頌,特別是對民族傳統藝術瑰寶的弘揚,更是郭沫若對梅蘭芳心照神交情感的機緣和基礎。
二、魯迅與郭沫若對梅蘭芳認識差異原因分析
前文梳理并列舉了郭沫若與梅蘭芳之間的三件史實,能夠得到的基本認知便是郭沫若對梅蘭芳的評價充滿了“正能量”。與之相較,魯迅對待梅蘭芳的態度卻和郭沫若的截然相反,他認為梅蘭芳“未經士大夫幫忙時候所做的戲,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骯臟,但是潑剌,有生氣。”③魯迅:《論梅蘭芳及其他》(上),《魯迅雜文全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97頁。梅蘭芳在魯迅的評價話語中處處都是“負能量”。同作為中國新文化革新運動旗幟的魯迅和郭沫若,對于同一個梅蘭芳卻有著天壤之別的評價和認知,原因究竟何在呢?
(一)認知文化語境的差異導致了二者對梅蘭芳評價的根本不同。
魯迅和郭沫若與梅蘭芳的相識并評價梅蘭芳是有時間差的。魯迅與梅蘭芳一生中大約見過兩次面①徐改平:《魯迅與梅蘭芳》,《文學評論》2011年第3期。,分別是1924年5月為來中國訪問的泰戈爾舉辦的壽辰會和1933年共同接待來華訪問的蕭伯納的歡迎會。也就是在這兩次會面之后,魯迅才開始集中評價梅蘭芳的。郭沫若與梅蘭芳第一次見面究竟是在何時,目前還很難考證出來,但是郭沫若第一次提及梅蘭芳的時間是確定的,那就是上文中所提及的,1946年郭沫若專為評價梅蘭芳所書寫的一幅書法作品。魯迅與郭沫若同梅蘭芳發生關聯的時間竟然相隔了20多年,近現代中國形勢發展之迅猛超出了每個人的預期,幾乎在每年都發生著足以改變中國命運和走向各類重大事件,更不用說20年時間的間隔對中國人觀念的沖擊和認知的變革。
魯迅與梅蘭芳發生關聯的時間,主要是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期約十年左右的時間內。此時正是“五四”運動的落潮之際,轟轟烈烈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曾給進步的中國知識分子帶來了多少希望和夢想,甚至連已經37歲,沉浸于抄寫古碑的魯迅都煥發出了難得的青春熱情和斗志,他走出了已經封閉已久的心扉,飽含激情地寫出了《狂人日記》這些劃時代意義的作品。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畢竟還只是中途夭折的突發事件,它是很難從根本上撼動兩千多年傳統舊文化體制的根基。魯迅在激情的吶喊過后,便很快清醒地認識到這場文化運動的走向,憤然地寫出“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肩余一卒,荷戟獨彷徨”的詩句,可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于魯迅的文化心理產生了重要影響。最明顯的一點便是,魯迅認為用所謂改良的方式是不足以對抗如大山一樣堅固的傳統文化糟粕,唯一可行的就是不得不采取更加激進的,甚至是矯枉過正的辦法,那就是用“拿來主義”去除所有現存的一切封建文化,在全新的基礎上重建中國文化的秩序。在魯迅看來凡是傳統的就是應該否定,而作為傳統藝術重要代表的京劇藝術,便順理成章納入魯迅所認為的傳統文化范疇,而梅蘭芳作為傳統文化中典型代表的京劇藝術順理成章地成為魯迅否定的對象。
“魯迅的兩度談及梅蘭芳,著眼的都是梅蘭芳身后的中國社會大舞臺”。②徐改平:《魯迅與梅蘭芳》,《文學評論》2011年第3期。事實的確如此,在魯迅所撰寫的涉及梅蘭芳的文章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論照相之類》《給文學社的信》《略論梅蘭芳及其他》等,的的確確都沒有對梅蘭芳本人有任何褒貶,而是直陳針砭梅蘭芳所飾演的人物,比如林黛玉、天女等。魯迅對事物批判采取的方法多是以“類”為單位進行含淚的批判,而不是對單一“個體”進行指責。對梅蘭芳的批評也依然延續了此種方法,在魯迅批判范疇中他將京劇藝術、梅蘭芳和傳統文化劃上了等號,所以魯迅真正意義上并不是在否定作為個體人而存在的梅蘭芳,而是借助梅蘭芳的象征符號表達出他對傳統文化堅決否定的立場和決心。
20世紀40年代中期郭沫若與梅蘭芳發生了關聯,此時文化環境與30年代初期已經截然不同了。1937年日本悍然發動了盧溝橋事變,全面侵略中國。中日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救亡與啟蒙的雙重主題又有了新的轉向,無疑“救亡”的時代命題已經全面超越了“啟蒙”的緊迫性和必須性。為了投身到民族救亡的大潮之中,郭沫若“又當投筆請纓時”,做出了“別婦拋雛斷藕絲”的時代抉擇,他此時希望的是“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在他內心中認為,在民族危亡之際必須凝結所有中國人的力量才能取得民族抗戰的勝利,而此時無論是延續古典精神的傳統文化,還是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革新文化,甚至是西方文化中對中國抗戰革命有價值的部分,只要是能夠煥發起民族抗爭精神的都應該屬于此時中國文化建設和發展的范疇。這些復合型的文化模式,成為最大程度發掘并喚醒民眾抗敵斗爭情緒的動力與源泉。
上文提到的郭沫若在1946年所寫的稱贊梅蘭芳的書法作品中,對于梅蘭芳的稱呼有兩個,一是畹華博士,二是梅博士。之所以對梅蘭芳的稱呼如此在意,并非僅僅出于對對方尊重的原因,更主要是“博士”代表著更高文化層次上的認同,是對傳統文化學理化的提升,而非簡單程式化地把梅蘭芳僅作為一個表演藝人來看待,由此也可以看出,郭沫若把以梅蘭芳為代表的藝術表演形式納入戰時文化體系之中。
郭沫若對梅蘭芳認知的初始判斷,影響并決定了他延續性的認知。甚至在梅蘭芳去世多年后的1967年6月10日,郭沫若曾在回答如何看待紀錄片《梅蘭芳》時說:“我們看待人,評論事,不能抓住一枝一節。人民不會忘記做過好事的朋友。梅蘭芳在抗戰期間拒絕演戲,是有民族意識和氣節的”①葉伯泉:《記和郭老的一次談話》,《文藝百家》1979第1期。。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梅蘭芳在抗戰危亡的關鍵時刻如何保持高尚的民族節操的史事,并將其與反面典型周作人相互對比。可見,不同文化發展體系的要求決定了魯迅與郭沫若對梅蘭芳認知和評價的基礎與差異。
(二)戲劇創作與舞臺表演的互通性有利于郭沫若與梅蘭芳間具有天然認同感
如果說不同時代文化命題的差異,從外在直接導致了魯迅與郭沫若對待梅蘭芳價值判斷方向有所不同的話,那么魯迅和郭沫若文學創作領域的差異,也造成了二者內在心理上對梅蘭芳認同度的親疏程度。魯迅文學創作主要集中在小說與雜文上,而郭沫若的文學創作則主要集中于詩歌與歷史劇。特別是郭沫若在歷史劇創作過程中,注重于對傳統文化創造性的改造,構成了郭沫若與梅蘭芳認同與交往的文化基礎,雖然一個致力于歷史劇的創作,一個投身于舞臺藝術的表演,但是他們創作和演出的作品多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經典之作,精深之事。借助于戲劇藝術表演舞臺所搭建的橋梁,郭沫若與梅蘭芳的交往具有了厚重的文化內涵。
郭沫若除了是高揚主體性的詩人,也是將史事、詩情與戲劇完美融合的劇作家,他在1941-1943年先后創作完成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筑》(后改名為《高漸離》)《南冠草》和《孔雀膽》等六部歷史劇的創作。以上幾部歷史劇無論是劇作的創作手法,還是美學內涵,也無論是劇作的主題內容,還是歷史價值來講,都是繼郭沫若“女神時期”詩歌創作高潮之后又一次文學創作的高峰。郭沫若在抗戰期間所創作的六部歷史劇,都是以中國古代歷史上的某一事件或歷史人物為原型,并融入現代的文化內涵和時代特征后創作出來的。他運用了“借古鑒今”、“借古喻今”、“借古諷今”、“失事求似”的創作原則和手法,借助中華民族文化歷史上廣為人知的歷史人物及相關事件,如信陵君竊符救趙,屈原愛國故事等,從而達到映射抗戰時期社會時局的鮮明創作目的。
梅蘭芳是現代中國為數不多的戲劇表演大師,他一生致力于京昆表演藝術,他的藝術人生也恰如郭沫若一樣跨越了新中國成立前的各個歷史時期,將《貴妃醉酒》《黛玉葬花》《霸王別姬》等傳統經典劇目進行了創造性的改編,特別是他在長期的戲劇舞臺表演實踐中自成一家,形成了獨特的“梅派”表演體系和藝術特色。總體來講,梅蘭芳善于利用有限的舞臺空間,通過自己獨特的服飾、身段、手法和唱腔等方式,將所展演的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并把劇中人物的文化魅力和精神內涵完美展現出來。
郭沫若與梅蘭芳,一個作為戲劇劇本的創作者,另外一個作為戲劇藝術的表演者,他們之間雖有藝術分工的不同,但創作者和表演者之間天然的關聯,有了藝術承續間的默契。因此,相較于魯迅對梅蘭芳文化視角的單一評價,郭沫若對梅蘭芳的評判更有同行者之間互相融會貫通之情,具有了客觀性和親近性。正是這一方不大的舞臺,成為郭沫若與梅蘭芳文化藝術創作的交匯點和契合點,同時也定格了他們留在歷史長河之中的絢爛畫面。
(三)“天才型”精神氣質生成了郭沫若與梅蘭芳的“互粉”動力
魯迅曾經說過“世界上哪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用在工作上了。”這雖然是魯迅的自謙之詞,不過也可以從其中推測出魯迅不是屬于天性聰慧類型的感性創作者。魯迅通宵伏案寫作的艱辛,抽煙思索的愁容等諸多生活細節,以及《吶喊》《彷徨》等作品,都能看出魯迅是擅長于深刻哲思的理性判斷者。此種推斷無任何刻意貶低魯迅的意思,只是為了說明他與郭沫若和梅蘭芳等聰穎型的人物,在內在精神氣質上截然不同的特質。
郭沫若被贊譽為“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的學術領域涉及文學、歷史、古文字學、翻譯、書法等各個方面,幾乎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他都有所涉及。他之所以能夠超越常人取得如此全面的成就,與其敏感多變的個性和聰慧敏銳的創作心理機制有關。郭沫若曾說過:“詩人底心境譬如一灣清澄的海水,沒有風的時候,便靜止著如像一張明鏡,宇宙萬匯底印象都涵映著在里面;一有風的時候,便要翻波涌浪起來,宇宙萬匯底印象都活動著在里面。”②郭沫若:《致宗白華》,《三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7年版,第7頁。這可以看出他對于外界事物敏捷的觀察能力和強烈的表達欲望。
郭沫若的創作天分令人欽佩,僅僅文學創作領域,他就有詩歌、戲劇、小說、散文、自傳文論等多體裁作品問世。郭沫若的第一首白話新詩《鷺鶿》發表于1919年9月11日的《時事新報·學燈》上,此時他還不到28歲。而近三十而立之際,就出版了石破天驚的中國現代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白話新詩集《女神》,令國內文壇諸多名流為之贊譽,實在是“在當時未見可與對壘者。”①茅盾:《我走過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頁。
郭沫若的天賦還表現在文學作品創作的速度上,僅以歷史劇創作為例,五幕劇《屈原》是他在1942年1月2日至11日,用了十天的時間完成的,時隔一個月之后,五幕史劇《虎符》在2月2日至11日,也用了十天的時間完成,五幕劇《孔雀膽》更是僅僅用了五天時間。郭沫若談到歷史劇創作時的狀態時,說自己“提筆寫去,即不覺妙思泉涌,奔赴筆下。”試想除了平時知識和素材的積累外,天才的心理創作機制恐怕也是不可否認的重要因素。
與郭沫若頗為相似,梅蘭芳成名之早,所獲得業界認可程度之深也大大超出常人所及。1904年,年僅11歲的梅蘭芳就初登舞臺。憑借超出常人的天分,在他25歲左右的時候,就已開始與年長他兩輩的伶界泰斗譚鑫培唱“對兒戲”,并且一舉成為旦行的中堅。更不可想象的是到了“1921年時的梅蘭芳……已經躋身于京劇大家之列,其時他的聲望,若用‘如日中天,紅得發紫’八個字來形容一點不為過。”②吳開英《梅蘭芳若干史實考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5年版,第60、64頁。與郭沫若成名的年齡大體一致,梅蘭芳也是在30歲時便已經享受到傳統戲劇界的最高殊榮,得到了別人可能一輩子也難以取得的成就,成為了中國戲劇藝術的領軍人物。當然這一切成績的取得,還需要梅蘭芳日復一日的刻苦努力和不懈練習,但是作為藝術表演形式,如果沒有一定的天才稟賦可能他也僅僅只能停留在一般的水準吧。
得到了如此高的贊許,并不僅僅是因梅蘭芳過人的表演藝術,還得益于他對于戲劇表演藝術不懈地探索。像京劇這樣傳統的劇目要想創新是比較困難的,但是梅蘭芳“吸取昆曲、話劇等多種藝術的營養,創造性地發展了京劇藝術”③王在梅:《梅蘭芳傳》,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6年版,第19頁。,尤其是“在古裝歌舞戲里,將青衣、花旦、閨門旦、貼旦、刀馬旦等幾種表演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表演形式,且在表演、舞蹈、唱腔、念白、音樂、服裝、化裝等方面均有創新。”。④吳開英《梅蘭芳若干史實考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5年版,第60、64頁。在此理念的基礎上,他改編或新編的《黛玉葬花》《嫦娥奔月》和《天女散花》等京劇劇目,都成為梅蘭芳保留和經典作品,也是社會各個階層觀眾競相熱看的傳統劇目,以此也形成了他特有的“梅派藝術”體系,梅蘭芳作為創造性的天才氣質展露無遺。
郭沫若與梅蘭芳特有的創新天才型氣質,使他們之間更易于形成惺惺相惜的認同感。當梅蘭芳去世后,郭沫若用顫抖的聲音,悲傷誦讀為其所撰寫悼亡詩時所流露出失去琴瑟之誼的傷感,更是表達了他從此知音難覓的巨大悲痛。
魯迅與郭沫若基于時代文化命題、各自創作體裁以及內在心理構成等諸多不同的原因,導致了對現代戲劇大師梅蘭芳認知上的巨大差異,當然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差異是必然存在的,我們探究如魯迅、郭沫若和梅蘭芳等現代文化大家們之間的交往,并不僅僅是為了厘清彼此是非恩怨,了斷塵封已久的歷史公案,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這些紛紛擾擾的言行中欣賞到現代文學和社會化發展的多彩風景,也正是由于這些差異的存在才形成了現代文學獨有的闡釋張力和研究動能,各個歷史人物才因這些友情和分歧具有了活生生的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