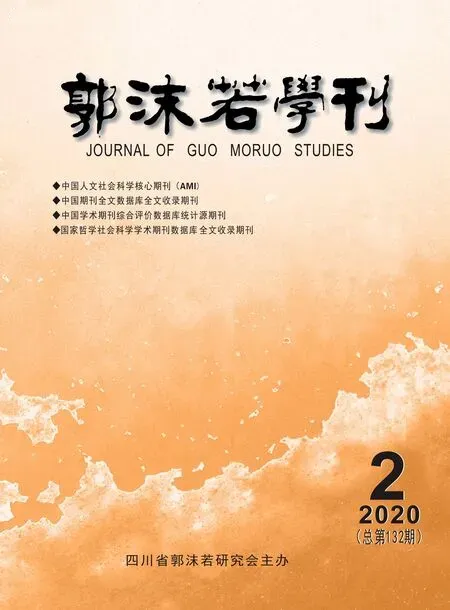郭沫若歷史劇《屈原》域外翻譯與搬演的“全景圖”
何 俊
(西南交通大學 外國語學院,四川 成都 611756)
時下,國內學界的郭沫若研究在告別了一段相對沉寂的時期之后,迎來了復興的春天。就郭沫若的作品體裁而論,歷史劇重新受到的關注尤為矚目,特別是其代表作品《屈原》。近幾年涌現出來的相關研究,一個最大的亮點是不再沿襲一直以來的抗日呼聲造就的政治啟蒙劇這一視角,而是呈現出回歸戲劇本體及其藝術特色、進行文本解讀和美學思考的趨勢,角度新穎別致。除了從多種角度出發的文本研究之外,也有研究關注該劇引發出來的詩詞唱和及其催生的《屈原》經典化問題①咸立強:《“〈屈原〉唱和”與話劇〈屈原〉的經典化》,《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屈原》的經典化不僅包括國內的影響和接受問題,而且可以涵蓋域外的相關維度。
一、進入異域和他者接受視野的《屈原》
郭沫若的翻譯與創作從一開始就是雙管齊下,他的戲劇創作與外國戲劇翻譯之間也存在著較為密切的關聯,這一因緣已成為學界的探究話題②張勇:《郭沫若早期歷史劇創作與詩劇翻譯鉤沉》,《北方論叢》2017年第1期。。以各種形式的翻譯為表征的中外文學關系,很多時候都不是單向道,而是在很大程度打上了雙邊進行的烙印。一方面,作為翻譯家的郭沫若翻譯了諸多國家的文學和社會科學作品,并從中汲取靈感和滋養,以此構建自身思想和文學的大廈;另一方面,郭沫若其人其作也進入了世界各國漢學界的研究視野,其作品在各個語言世界的翻譯與研究、接受與傳播問題,已經不是一個新鮮話題。迄今,國內學界已分別對英語、日語、韓語、德語、法語、俄語、意大利語等語言區域的郭沫若翻譯與研究成果進行了梳理,郭沫若在域外的影響力在某種程度上超出了國內學界預料①魏建:《近十年來走向世界的郭沫若研究》,《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
這一出乎意料的接受熱度尤其體現在《屈原》上面:《屈原》譯本不僅涵蓋上文提及的主要大語言區域,另外還進入越南語、尼泊爾語、捷克語、匈牙利語、波蘭語、羅馬尼亞語、冰島語等相對小眾的語言世界。戲劇的特殊性在于它既包括作為劇本的文學范疇,又涵蓋作為舞臺實踐的表演藝術,《屈原》在世界各地的接受與傳播,就包括翻譯和搬演兩個不可或缺的維度。這里面既有劇本《屈原》進入各種語言的迻譯,也有戲劇《屈原》在當地的改編和搬演,進而造就了郭沫若作品進入異域和他者視野的一道獨特風景線。無論是《屈原》的翻譯還是搬演,學界已經針對特定的語言區域做過不同程度的相關探究,本文嘗試著在此基礎上勾勒出《屈原》在異域接受與傳播的“全景圖”。
二、《屈原》在世界各地的翻譯和搬演史實
一個有趣的史實是,最早的《屈原》譯本并非譯成了最為通行的國際語言英語,而是郭沫若負笈之國,也是他“第二故鄉”——東瀛的語言。眾所周知的是,1942年1月,僅僅耗費了郭沫若10天的時間,《屈原》就橫空出世。整整十年半之后的1952年7月,郭沫若的《屈原》被須田禎一(1909-1973)譯成日文,由東京未來社出版,收入《戲劇叢書》系列(Thespis Series);第二版則在1956年由巖波書店發行,收入“巖波文庫”系列,郭沫若在1956年5月21日還特地為這個版本寫了序言②戈寶權:《郭沫若的著作在日本》,《文獻》1979年第1期。,此版后面還附有其他形式多樣的譯文“副文本”,包括日本“前進座”劇團1952年12月在全國開始公演的照片③戈寶權:《郭沫若的著作在日本》,《文獻》1979年第1期。。根據相關考證,該譯本初版依據的底本是20世紀40年代上海群益出版社的版本,第二版則依據1950年以后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修訂本。④曾嶸《郭沫若〈屈原〉如何走入日本——須田禎一的翻譯過程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0期。除了單行本以外,須田禎一的《屈原》譯本還跟郭沫若其他作品的日譯文一起,被收入各種選譯本。1955年,河出書房付梓《現代中國文學全集》第二卷“郭沫若篇”,收入小野田耕三郎譯的《少年時代》和松枝茂夫譯的《正續創造十年》,以及須田禎一翻譯的初版《屈原》。1966年,東京海燕社出版了須田禎一譯的《棠棣之花》和《屈原》。同年,同一出版社又出版了須田禎一譯的《郭沫若史劇全集》第一卷,內收《屈原》和《虎符》。到了1972年,東京講談社再版須田禎一全譯的四卷本《郭沫若史劇全集》,第一卷為《屈原》和《虎符》,正文前面同樣附有多種“副文本”,包括郭沫若在1955年8月為譯者寫的《屈子行吟處,今余跨馬過》一詩的長條幅,以及1962年前進座上演《屈原》的劇照。⑤戈寶權:《郭沫若的著作在日本》,《文獻》1979年第1期。從1972年起,京都的雄渾社開始推出17卷《郭沫若選集》日譯本,其中的第六卷《史劇 I》在1978年底出版,收入《棠棣之華》和《屈原》。⑥戈寶權:《郭沫若的著作在日本》,《文獻》1979年第1期。
除了《屈原》劇本翻譯,日本劇壇對《屈原》的搬演同樣可圈可點。日本劇壇曾四次公演《屈原》,郭沫若甚至還對某些演出做過相關指導。《屈原》在日本的首次搬演是在1952年,由著名演員河野崎長十郎飾屈原,這次演出一直延伸到次年為紀念屈原逝世2230周年而進行的紀念公演,其主要目的是回應世界和平會議理事會將屈原列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的提案決定⑦轉引自:[韓]權五明:《郭沫若歷史劇〈屈原〉在日本的上演與影響》,《重慶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如前所述,1956年再版的《屈原》譯本就將首演劇照作為譯文“副文本”收入其中,足見劇本翻譯與戲劇搬演之間的緊密關聯,也再次印證了戲劇兼有劇本文學與表演藝術的“二元一體”特征。1962年,“前進座”再次進行巡回公演,在演出之前還跟出訪東瀛的中國電影代表團進行了交流⑧轉引自:[韓]權五明:《郭沫若歷史劇〈屈原〉在日本的上演與影響》,《重慶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巧合的是,1962年5月,時任蘇聯駐日大使,自身也是屈原研究者和郭沫若歷史劇《屈原》譯者的費德林也在日本觀看了《屈原》的公演⑨轉引自:[韓]權五明:《郭沫若歷史劇〈屈原〉在日本的上演與影響》,《重慶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時舉行第三次公演。在演出之前的1971年冬,郭沫若還專門賦詩一首:“滋蘭九畹成蕭艾,桔樹亭亭發浩歌。長劍陸離天可倚,劈開玉宇創銀河。”⑩[日]河野崎長十郎撰、徐迎新譯:《日中友好〈屈原〉訪華公演團訪問報告》,《郭沫若研究》1988年第4輯,第41頁。1979年郭沫若逝世,日本國內進行第四次公演。另外,河野崎長十郎還曾于1980年率團來華,在天津、南京和北京三大城市演出《屈原》,而且取得了較為轟動的接受效果。被編譯搬演到他國舞臺上的中國戲劇得以返回母國上演,這一事實本身就印證了原劇在他國文化中較為成功的接受與傳播,頗類一國作品被翻譯成他國語言后又再度“回譯”至原文。引人注意的是,就日本學界前兩次《屈原》公演的評價而言,可以窺見一個明顯的轉變:從凸顯當時國內的政治社會癥候,到關注作為文本內容和舞臺藝術的戲劇本體。①轉引自:[韓]權五明:《郭沫若歷史劇〈屈原〉在日本的上演與影響》。
同為我國一衣帶水鄰邦的韓國,對郭沫若作品的翻譯起步較早,但比之打上了一定意識形態烙印的后期作品,郭沫若的早期作品比如詩歌等受到的關注則要大得多②梁楠、李曉虹:《郭沫若著作韓文翻譯概述》,《郭沫若學刊》2012年第4期。。就郭沫若的戲劇而言,梁白華從1923到1931年間譯出《棠棣之花》《王昭君》和《卓文君》③李曉虹、梁楠:《梁白華與郭沫若早期作品的韓文譯介》,《郭沫若學刊》2010年第1期。,此后韓國對郭沫若戲劇的翻譯便一直陷入沉寂。直到2005年2月,泛友社才出版了郭沫若《屈原》的韓語譯本,翻譯捉刀者為姜姈妹。④梁楠、李曉虹:《郭沫若著作韓文翻譯概述》,《郭沫若學刊》2012年第4期。同年10月,學古房出版社發行了一套中國話劇韓譯本叢書,由河炅心、申振浩兩位譯者合作完成,收郭沫若歷史劇一卷,包含《屈原》《虎符》《蔡文姬》。⑤梁楠、李曉虹:《郭沫若著作韓文翻譯概述》,《郭沫若學刊》2012年第4期。在序言中,譯者指明了翻譯這套話劇作品叢書的原因,即彌補近20年來中國話劇翻譯勁頭不足的弱勢,而且翻譯選材標準定位于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其中也不乏旨在宣傳特定意識形態而創造出來的作品。⑥梁楠、李曉虹:《郭沫若著作韓文翻譯概述》,《郭沫若學刊》2012年第4期。
鑒于地緣文化政治的原因,《屈原》還被譯成其他亞洲各國的語言文字,并在一些亞洲國家的舞臺上搬演。另外,作為中國文化戰線上的一面光輝旗幟,郭沫若新中國成立后頻繁出訪,在中國與國外的對外文化事務中發揮了不小作用,其作品在國外的接受與傳播也因此得到某種程度上的推廣。20世紀50年代,越南中央改良劇團和越南南方改良劇團就將《屈原》改編成了古典戲劇,多年來一直在公演;此外還有歌劇形式的改編,同樣好評如潮。⑦[越]范秀珠撰、田小華譯:《作家郭沫若與越南》,郭沫若故居、郭沫若研究會編;《郭沫若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949頁。1960年,河內文化出版社發行《屈原》的越南語譯本。⑧[越]范秀珠撰、田小華譯:《作家郭沫若與越南》,郭沫若故居、郭沫若研究會編;《郭沫若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949頁。與中國一直交好的尼泊爾也在20世紀60年代推出了《屈原》譯本,譯者為烏帕德亞,由尼泊爾皇家學院出版。⑨秦川:《國外郭沫若研究述略》,《郭沫若學刊》1994年第4期。尼泊爾大戲劇家勃克瑞施納·夏馬還打算將《屈原》搬上舞臺,親自擔任導演,并扮演其中主要角色。⑩秦川:《國外郭沫若研究述略》,《郭沫若學刊》1994年第4期。1966年,緬甸也出版了《屈原》的相應譯本,譯者為覺萊倪(又名“敏覺”)。[11]李謀、姚秉彥:《淺談中國文學在緬甸》,《國外文學》1983年第4期。
接下來把目光投向全球最大的語言區——英語世界:《屈原》的英譯本并非在英語本土國家出版,而是在1953年由北京的外文出版社推出,譯者就是當時剛剛調任到該社任專職翻譯的楊憲益及其夫人戴乃迭(Gladys Yang)。巧合的是,同年夫婦倆還合譯了屈原的《離騷》。后來,楊、戴的《屈原》英譯本還于1955、1978和1980年再版。跟日語譯本一樣,這個英譯本也曾被收入英文本的合集之中。1984年,外文出版社發行由彭阜民和澳大利亞漢學家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合作編選和翻譯的《郭沫若劇作選》(這也是四卷英文本《郭沫若選集》的第二卷),其中收錄的《屈原》選用楊、戴夫婦的譯本。相關研究發現,楊、戴譯本很好地傳達了該劇的“可表演性”[12]解晶晶:《屈原中“可表演性”的英譯研究》,南京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英語是國外讀者接受中國文學作品時所仰仗的最重要的語言,這不僅體現為英語母語人士這一群體的人數眾多,而且還要加上以英語為二語或外語、數量更為龐大的讀者群體。但除了楊、戴譯本,作為國際通用語言的英語再沒有催生《屈原》的第二個譯本,也沒有英語國家的出版社再版那個唯一的英譯本。
相較之下,法國則為《屈原》貢獻了多個不同譯本(包括片段)。1953年,在《思想》(La Pensée)雜志第12期的《向屈原致敬》一文中,法國漢學家讓·謝諾(Jean Chesneaux)首次譯出《屈原》第二幕。[13]Chesneaux,Jean.Hommage à K’iu Yuan.La Pensée,1953 12(52).1957年,法國華裔學者梁佩貞女士又譯出《屈原》的全譯本,收入漢學家艾田蒲(René Etiemble)主持的《認識東方》叢書中國系列[14]Kuo,Mo-jo.K’iu Yuan.Trad.,pref.et notes de MIIe.Liang Pai-tchin.Paris:Gallimard,1957(Coll.“Connaissance de l’Orient”).。相比之下,德語區在郭沫若作品的翻譯方面則反應平平,尤其是參照德語區方興未艾的魯迅翻譯和研究來看的話:①何俊:《德語世界的郭沫若譯介與研究》,《郭沫若研究》2018年第14輯,第172頁。《屈原》德譯本到1980年方才姍姍來遲,譯者是生活在瑞士的漢學家梅德(Markus M?der),譯本由外文出版社發行②M?der,Marcus.Qu Yuan.Ein Schauspiel in fünf Akten.Beijing:Verlag für fremdsprachige Literatur,1980.。再把眼光轉向南歐的意大利,該國的諸多文化名人及其作品,比如但丁、意大利未來主義詩作以及作家鄧南遮等,都對郭沫若的創作產生過較大影響。有趣的是,意大利漢學界對郭沫若作品的譯介和接受也有目共睹。對中國文化頗感興趣的佛羅倫薩法學家、作家和政治家皮埃洛·卡拉曼德雷(Piero Calamandrei)曾于1955年參加意大利官方派出的第一個經濟文化代表團訪華,次年就在自己所創刊物《橋》(Il Ponte)的中國專號上發表了郭沫若《屈原》第四幕的譯文③[意]安娜·貝雅蒂)、晨雨譯:《郭沫若及其著作在意大利文化中》,《郭沫若研究》1996年第11輯,第303頁;。1957年,另一本期刊《幕》的中國專號上刊載了馬利亞·馬莫翻譯的《屈原》全劇④Mario V.Zallio.Some Italian Books on Communist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58 18(1),p.127.。
蘇聯在《屈原》翻譯和研究方面同樣表現不俗,這也生動地體現在郭沫若與譯者費特林的互動上。后者是屈原研究專家,曾就屈原和劇本《屈原》向郭沫若多次請教。1951年10月,費特林譯的《屈原》單行本發行,郭沫若還曾為它作序。1953年,莫斯科國家文學藝術出版社發行了三卷本俄文版《郭沫若選集》,郭沫若還曾為這個版本作序⑤郭沫若撰、劉亞丁譯:《俄文版〈郭沫若選集·自序〉》,《郭沫若學刊》2016年第2期。,第二卷收入《卓文君》《王昭君》《棠棣之花》《虎符》《高漸離》《屈原》等戲劇譯本。1956年,莫斯科又出版了一本中國戲劇集,內收包括費特林所譯《屈原》在內的五部中國戲劇譯本。⑥于立得:《郭沫若歷史劇〈屈原〉在前蘇聯的翻譯及傳播》,《郭沫若學刊》2020年第1期。1990年,蘇聯藝術出版社又出版了由費德林主編的《郭沫若集》,戲劇卷收入《棠棣之花》《虎符》《屈原》。⑦秦川:《國外郭沫若研究述略》。1954年1月31日,莫斯科葉爾莫洛娃劇院首演《屈原》。⑧于立得:《郭沫若歷史劇〈屈原〉在前蘇聯的翻譯及傳播》,《郭沫若學刊》2020年第1期。另有烏克蘭學者提到《屈原》也曾以烏克蘭語單行本的形式發行,但并未說明具體年份,只是籠統地說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⑨[烏克蘭]娜塔利亞·伊薩耶娃:《中國文學在烏克蘭》,《岱宗學刊》1998年第1期。1957年,安達·鮑勒杜爾(Anda Boldur)和弗勒依庫·伯樂納(Vlaicu Birna)合作翻譯的《郭沫若文集》羅馬尼亞文譯本出版,收入《屈原》和《棠棣之華》兩個劇本。經過一年的排演,1958年9月28日,《屈原》在羅馬尼亞斯大林城的國際劇院首次上演,并獲得極大成功。⑩[羅馬尼亞]伐倫汀·錫爾維斯特魯:《屈原在羅馬尼亞首次演出》,《戲劇報》1959年第3期。這出戲的演出是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九周年獻禮,而且參加羅馬尼亞戲劇節的演出。
《屈原》在東歐的翻譯和搬演也是一個亮點:1952年,《屈原》波蘭語譯本[11]Kuo,Mo-jo.Czü Jüan.Dramat w 5 aktach,prze?.z j?z.chiń.i przypisami opatrzy? Olgierd Wojtasiewicz,Czytelnik,Warszawa 1952.由沃伊塔謝維奇(Olgierd Wojtasiewicz)譯出,1955年再版。1958年,《屈原》的匈牙利語譯本問世,譯者為漢學家米白(Miklós Pál),1961 年再版。[12]https://www.tkbe.hu/emlekoldal/miklos-pal-1927-2002;[斯洛伐克]高利克撰、王巍譯:《中國文學翻譯在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1919-1989)》,《漢學研究》2000年第 7輯,第 391頁。《屈原》還曾被捷克漢學家米列娜(Milena Dolezelová-Velingerová)譯成捷克語,未出版。[13][斯洛伐克]高利克撰、王巍譯:《中國文學翻譯在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1919-1989)》,《漢學研究》2000年第7輯,第391頁。不過,1957 年春天,《屈原》先在捷克斯洛伐克廣播電臺所舉辦的“戲劇晚會”的節目中播送,然后又在布爾諾國立劇院上演;隨后,布拉格的軍隊中央劇院也演出了這出戲,改用“愛情和叛逆之歌”來作劇名。[14]朱觀海:《〈屈原〉演出在捷克斯洛伐克舞臺上》,曾健戎、王大明編:《〈屈原〉研究》,重慶地方史資料組1985年版,第236頁。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也進入了北歐國家。1954年,《屈原》被譯成芬蘭文,該劇于1959年初在芬蘭國家劇院公演,演出多達二十場以上。[15]佚名:《芬蘭戲劇季節演出我國劇目》,《世界文學》1959年12期。1958年,《屈原》的冰島語譯本問世。[16]秦川:《國外郭沫若研究述略》。郭沫若的創作中也存在一些阿拉伯國家比如埃及的文學景觀和意象,有趣的是,《屈原》也走進了阿拉伯語世界,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推出相應譯本。另外,世界語專家李士俊的世界語《屈原》譯本1987年由中國世界語出版社付梓。
三、《屈原》翻譯和搬演的相關思考
考量《屈原》在域外翻譯和搬演的“全景圖”,不難發現一些比較有意思的維度,這既關涉譯者或改編者的個體因素,也與支持翻譯和改編的官方機構或曰贊助人有著密切聯系,當然還受制于當時的宏觀政治和社會大環境。作為一部歷史劇,借古喻今的《屈原》仍然在較大程度上遵從了基本的歷史事實,即便在創作過程中對史實進行了大量“借古喻今”和“失事求似”的藝術加工。作為歷史劇的《屈原》,自然要重返當年的歷史場域和空間,圍繞歷史人物屈原及其政治遭遇和生活境況展開,于是不難想象,為什么這部劇作會引起一批以中國歷史為研究方向和重點的國外漢學家的關注。比如《屈原》片段法譯文的譯者謝諾即是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先驅,其扛鼎之作是四卷本的皇皇巨著《中國現代史》。無獨有偶的是,翻譯《屈原》全本的華裔學者梁佩貞也是歷史系出身,1929年畢業于燕京大學歷史系,后來轉向中國古詩詞的翻譯和研究。從該譯本的序言可以看出,梁將郭沫若的詩歌和劇本放在一起分析,試圖構建二者之間的關聯,①胡嫻:《郭沫若歷史劇〈屈原〉在法國的譯介》,《安徽文學》2016年第9期。這跟以《屈原》為代表的郭沫若歷史劇雜糅詩歌和對話元素、詩意充盈的特色不謀而合。
時代背景和政治癥候也是《屈原》域外翻譯和搬演過程中值得重視的因素。上文提及的謝諾本人就是法國共產黨員,他把《屈原》的創作和在國統區的上演看作是一樁政治事件;之所以專門譯出第二幕“受誣”,而且加上了“被權貴驅逐的屈原”這一標題,更是執念于該劇對國民黨陰謀的揭露和批判。②胡嫻:《郭沫若歷史劇〈屈原〉在法國的譯介》,《安徽文學》2016年第9期。另外,出于域外漢學對中國文學“厚古薄今”的翻譯和研究傳統等原因,中國現代文學在域外的譯介往往都要在中文作品產生多年以后才能進行,類似日本國內兩者近乎同步發生的現象,即郭沫若作品問世后的短短幾年內就能被譯成日語,實在是非常少見。正因如此,包括郭沫若作品在內的中國現代文學,其譯介很多都是發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后。這樣一來,譯介國與新中國的外交關系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現代文學在該國的翻譯狀況。
《屈原》在東南亞和東中歐國家的翻譯和搬演,無疑跟當時剛成立的新中國的政治和文化意圖有著緊密關聯,也就是急于同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建立友好關系,以便聯合起來對抗當時冷戰和鐵幕時代背景下虎視眈眈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當然還有一樁世界政治和文化舞臺上的大事直接助推了20世紀50年代《屈原》在世界各國的接受與傳播:1953年,郭沫若以中國和平理事身份參加世界和平理事會,在當時的西柏林召開的會議推舉屈原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有學者認為,屈原走向全世界、成為世界級的大詩人,多多少少還得益于具有較高政治地位和國際知名度的郭沫若的推崇和引介。③[韓]權五明:《郭沫若歷史劇〈屈原〉在日本的上演與影響》。也就是說,除了宏觀政治背景,原著者的對外文化交流使者身份及其和譯者、改編者之間的雙向互動也充當了《屈原》翻譯和搬演的推手。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郭沫若和日本、蘇聯、尼泊爾等國家學界的交流層面。頗有意思的是,在郭沫若短暫造訪過的國家中,比如波蘭、挪威、西德、奧地利、捷克、羅馬尼亞、古巴、印度、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埃及等等,其所在語言區大多都存在相應的《屈原》譯本。如前所述,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個雙向道的問題。作為腳踏中西文化的文學巨匠,郭沫若在自己的創作中吸收和化用了他國文學的符碼和意象;作為一種有意無意的“反向交流”,包括《屈原》在內的郭沫若作品也在相應國家或語言區域得到接受和傳播,由此構建了一種“你來我往、互相成全”的文學和文化交流關系,這在日語、德語、意大利語、阿拉伯語等區域體現得尤其淋漓盡致。在郭沫若逝世多年以后的今天,得益于國家宏觀政治、經濟和文化戰略,這種雙邊交流得到進一步傳承乃至發揚光大,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近年來“郭沫若中國海外研究中心”在埃及的落戶以及相關活動的蓬勃開展。
就譯作的出版等實際操作層面而言,《屈原》譯作的發行也跟翻譯機制息息相關,直到今日還可以為我國大力倡導的“中國文學走出去”提供些許啟示。新中國成立后,包括《屈原》在內的作品就在一種特殊的翻譯機制下迻譯付梓,多個語種(英語、德語、阿拉伯語、世界語)的《屈原》外譯本都在作為翻譯贊助人的外文出版社發行。這家成立于1952年、隸屬于國家外文局的出版社是我國主要的對外出版機構,一直以來擔負著對外宣傳和“國家譯介”的任務。另外,就翻譯文本而言,郭沫若的作品一向以經常改動而知名,包括《屈原》在內的著譯作品的文本譜系一直是國內學界的研究對象;如前所述,底本問題在日本學界的《屈原》翻譯中也有折射。
拋開《屈原》作為抗戰名劇在國內引發的轟動效應以及影響中外文學關系的政治癥候不論,劇本《屈原》本身的文學價值和美學意象也不容忽視,在此還應注意中外學界評價和接受《屈原》過程中出現的審美旨趣的同一性和差異性問題。國內學界長期以來對《屈原》推崇有加,這從1942年元旦陪都文藝界或多或少打上了溢美之詞烙印的預言即可窺見——“今年將有《罕默雷特》(《哈姆雷特》)和《奧賽羅》型的史詩出現”①田本相、楊景輝:《郭沫若史劇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頁。。這一極高的評價在后期的相關研究中也一再得到強化,比如當時就有文化界人士認為《屈原》躋身世界名劇之林也毫無愧色,除了以上提及的兩部莎劇,還有人將它與荷馬的《伊里亞特》《奧德賽》、歌德的《浮士德》、②周務耕:《從劇作〈屈原〉想起》,《新民報》1942年4月18日。索福克里斯的《俄狄浦斯王》相提并論③柳濤:《談〈屈原〉悲壯劇》,《文藝生活》1942年第5期。。國內學界的《屈原》研究熱度也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其地位:搜索知網論文數據可知,有關《屈原》的研究論文數量長期以來在郭沫若戲劇的相關研究中位列榜首。但就英語世界而論,1974年面世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草鞋腳》(Straw Scandals)中收錄的郭沫若戲劇片段并非出自《屈原》,而是《卓文君》;此外,著名華裔美籍漢學家夏志清則認為郭沫若最好的歷史劇是《棠棣之花》,而非《屈原》。④[美]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頁尾注5。斯洛伐克著名漢學家高利克也曾經坦言:“波蘭和匈牙利等國家的譯者對歷史上的屈原比對《屈原》劇本本身更感興趣,況且那也并非一部優秀的劇作,但或許譯者做出這樣的選擇另有原因吧。”⑤[斯洛伐克]高利克撰、王巍譯:《中國文學翻譯在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1919-1989)》。高利克所言的“另有原因”無疑是指政治癥候,至于國外部分漢學家緣何對《屈原》作為劇本的價值進行了某種程度上的忽視或消解,這里面當然有著語言和文化翻譯帶來的美學價值被無奈遮蔽等客觀原因,但也從側面證明中國文學作品真正走出去確實“道阻且長”。
四、結語
時至今日,郭沫若作品在域外的譯介與研究已經成為國際“郭沫若學”的組成部分。從這個角度來看,郭沫若其人其作也可被視為一種“鏡像和資源”⑥李斌:《作為鏡像和資源的郭沫若》,《東岳論叢》2018年第12期。。就史劇《屈原》這一較有代表性的具體作品在域外的接受與傳播而言,由于政治場域的作用,《屈原》譯介和搬演的黃金時期都集中在20世紀50年代,其意圖更著眼于該劇發出的政治呼號。從歷時的角度來看,21世紀以來,《屈原》各個語種的譯本都很少見到再版。盡管如此,英語世界對郭沫若歷史劇《屈原》的研究并不缺席⑦參見:楊玉英:《郭沫若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9-193、294-295、301-304頁。,也不乏探究蘊藏在《屈原》中的陰陽之道這一易學思維模式的別出心裁之作⑧參見:Chen,Rose Jui-chang.Human Hero and Exiled God:Chinese Thought in Kuo Mo-jo’s Chu Yuan.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Detroit,1977;楊玉英,2015,第 488-497 頁。,對郭沫若創作頗有微詞的夏志清同時也首肯《屈原》等歷史劇里穿插的幾首歌詞,認為它們才是郭沫若最好的詩歌⑨[美]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頁尾注5。;與之相應的是,近年來國內學界對《屈原》戲劇文本的關注也重新抬頭,大有再度迎來春天之勢。從域外接受與傳播史的角度來看,就已經掌握的資料而論,《屈原》催生了18個語種的譯本(外加一個未出版的捷克語譯本),并以話劇形式在六個國家多次上演⑩《屈原》在尼泊爾的搬演是否成行,尚未可知,故而沒有統計在內。,深入當地觀眾之心。在《屈原》經典化這個問題上,該作品在域外主要以翻譯和搬演形式呈現的接受和傳播也可以納入研究視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