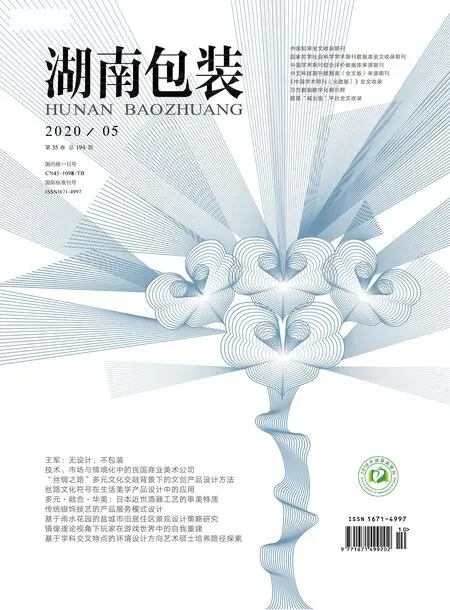多元·融合·華美:日本近世酒器工藝的審美特質
張夫也 劉粟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北京100084)
日本的歷史分為原始時代、古代、中世、近世、近現代5個時期,其中近世是指安土桃山時代(公元1573—1600年)和江戶時代(公元1603—1868年)。這一時期,是日本歷史與文化不斷變革與發展的階段,正是處于多元與融合的年代,從織田信長使用“天下布武”之印就開啟了日本新的歷程。之后豐臣秀吉結束日本戰國時代的亂世,經濟逐漸發展起來,一方面工商業的發達和海外貿易的隆盛,與繪畫關系密切的工藝特別是建筑裝飾物,以及武士階層的裝劍器物,日常使用的陶瓷器、漆器、染織工藝等等,都開始與西方世界接觸,西方文明與日本疏根蔓枝,西學東漸,作為日本西學之先驅的“南蠻文化”開始滲透于日本傳統文化的各個領域,擁有財富的商人和以町人為代表的庶民階層,從開始與武力背景為依托的武士階層形成對抗,到江戶時代德川家康將日本帶向幕藩和平體制下的“町人”安居樂業之中,由于社會安定有序,近世酒器及酒文化的發展也成為當時社會繁榮的重要標志。
日本近世酒器的發展,不僅是從近世歷史與文化的角度去思考,更重要的是從酒器本身的藝術審美特征去演繹,近世酒器主要是安土桃山時代到江戶時代這個時期的酒器,是沿著祖先歷史長河一脈相承下來。從原始時期的繩文、彌生時代的各種土器也就是酒器雛形,到古墳時代平瓶、提瓶、環形瓶、皮袋形瓶、橫瓶,奈良時代正倉院酒器,平安時代延喜式酒器,再到中世鐮倉室町幕府時代的古瀨戶、漆塗酒器,之前的每個時代都會對日本近世酒器的設計產生深遠的影響,如同瑞士心理學家榮格形容人們的“集體無意識”[1]一樣,酒器被制作的人賦予生命,每個人的生命意識與藝術觀照都被隱射在酒器之中。文章所分析的審美特質功能美、形式美、技術美不是相互割裂的,每個部分所闡述的內容也是互相包含,也可能會互相轉化,希冀通過文中理性與感性相結合的分析,去體驗日本近世酒器帶給人們的不一樣的感受。
1 功能美:造型體現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觀念
從實用的角度出發,設計要先解決人類的生活需求,也必然反映當時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觀念。酒器的發展涉及到飲酒文化,酒器離不開酒,不懂得欣賞酒,也不會真正理解酒器對日本人生活的重要意義。當時的酒按制作工藝大致可分為蒸餾酒、釀造酒和配制酒3類。其中從室町末期一直到今日的日本酒都被稱為“諸白酒”的清酒屬于釀造酒,“精米步合”是日本清酒釀造的術語,指的是磨過之后的白米,占原本糙米的比例,精米度數字越小,代表清酒的品質越好,日本后來又出現了延長酒保存期的“低溫殺菌法”[2]等一系列提高釀酒水平的技術。還有從東南亞經琉球傳入的燒酎屬于蒸餾酒,從日本各種酒的釀造工藝來看,糙米的比例象征著自然屬性,這里更多反映日本人尊重自然、崇拜自然的意識。
從安土桃山時代的《お湯殿の上の日記》[3]一書中可以看出“居酒屋”經常被提及,由鐮倉時代的酒館發展而來的“居酒屋”也逐漸成為反映日本時代與文化的產物,居酒屋最早是在江戶時代晚期出現,后來隨著時代變遷,居酒屋逐漸成為日本人生活方式發生改變的最好見證,從居酒屋之中的酒器的變化可以看到日本人內心深處的生存觀念和審美意識。從著名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公元1724—1804年)在《判斷力批判》一書中,對審美經驗的性質所涉及的質、量、關系等角度去尋找日本酒器的功能美。
1.1 形式追隨功能,展示的是酒器生產領域中美與善的關系
所謂功能美,是美學的概念,酒器造型是形式,同時也是功能,形式追隨功能是一種設計理念。19世紀美國著名建筑師路易斯·沙利文曾提出“形式追隨功能”的觀點。日本酒器到安土桃山時代和江戶時代,傳承發展很好,酒器的器型美觀,令人賞心悅目,外表形式美觀是美,實用功能便利是善,經過歷史長河,百姓日用為道,真正融入日本酒文化與生活之中才是美與善的體現。比較常見的徳利、片口、豬口、桶口、盃等日本特有的“居酒屋與禮儀文化”[4]酒器,出現了多種多樣、造型優美,豐富形態的酒器,從功能上分類,有瓶子、片口、銚子、提子、燗鍋以及酒的搬運具(各種的樽類)、德利、酒盃、盃洗等。這與中國古代青銅器觚、觥、觶、角、爵、斝、杯、舟等酒器相類似,不僅典籍中有記載,使用者有身份與等級制度的區別、盛酒器也有專門細致的使用方法與分類原則。比如說其中銚子就是體現日本酒器的形式追隨功能,造型從早期的飲食器轉變而來,起初有煎藥、煮水的功能形狀一般是高大的壺,口大有蓋,旁邊有柄,用沙土或金屬制成。到近世逐漸被人們用來溫酒、燙酒,隨著身份與等級制度的不同,銚子作為酒器,造型上也開始精致起來,由原來的高大逐漸向扁平發展,口大有蓋便于溫酒保留,旁邊的柄開始變成從上面跨越的弧線形提手,整體造型富有裝飾性,更加令人賞心悅目,也很好地詮釋了酒器生產領域中美與善的關系。
1.2 從質的特征來看,酒器造型內在的美是超功利的
質是本質,是內在的,日本近世酒瓶子和樽的造型是經過歷史演變過來的,能體現一種內在美,歷史悠久,底蘊深厚。從日本古墳時代公元4世紀左右就已經誕生,瓶子有平瓶、提瓶、環形瓶、皮袋形瓶、橫瓶等各種美的造型樣式,樽以太鼓樽為典型,也有受中國唐代時期北方游牧民族影響的胡瓶、胡樽造型的影響,從正倉院寶物中可以看到具有顯著中國西域風格的漆胡瓶,帶有濃郁的異域情調,可以看出,瓶子的造型樣式雖千差萬別,但基本特征都是比較相近,從瓶肩部到上半身比較渾厚飽滿。下半身到瓶底逐漸纖細,后來這種束腰式造型成為近世漆塗瓶子的基本形。從這些基本形里不僅僅看到飲酒、注酒、裝載酒等功能作用,也要超出酒器的社會文化、等級制度、道德觀念這個范疇,去體會一代代工匠的手如何制作,如何經過更多使用過的酒器的人來傳遞情感。
1.3 從量的特征來看,酒器的造型具有日本社會文化的普遍性
量作為事物存在和發展的數量與規模,也是審美對象。片口、提子、銚子、燗鍋等酒器都是具體的審美對象,造型比較接近,這種美體現日本酒文化,都是圍繞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展開的。在江戶時代,無論是貴族還是庶民都在大量使用片口、提子、銚子、燗鍋,這些近世酒器造型來源于古代繩文時期的深缽形土器,外形像缽,但在口緣處有注口,用于注酒。在各種宴會和祭祀活動中經常使用,和酒壺、瓶子、小型太鼓樽一樣適合于盛放或搬運較小容量的酒。除了片口之外,提子、銚子、燗鍋不僅可以注酒,還有專門用來溫酒的功能,這些酒器都能反映日本近世社會文化的日常,造型特征非常具有普遍性。
1.4 從關系特征來看,酒器的造型是合目的性的形式
人們欣賞日本近世酒器“德利”就是審美關系特征的最好體現,只要談到德利(日語稱為:德利,發音:とくりtokuri),就會形成自己的主觀判斷,即意識到是日本的清酒瓶樣式,與日本清酒相關聯。帶有目的性去翻閱各種日本酒器的圖片資料,初步了解到原來“德利”是清酒壺,進一步深入了解后,發現日本古代是作為放佐料和醬油的瓶子來使用的,提子、銚子、燗鍋最初也不是專用于酒器,也是從飲食器、炊煮器演變而來,德利發展到安土桃山時代一般器型是細長的頸,類似花瓶的造型。日本“德利”酒器之中的器型設計受中國古代陶瓷文化影響,同時又有日本自身民族文化的淵源,之所以產生現在這樣的造型也是非常合目的性的形式的體現。來自于古代和中世寺院使用的水瓶和花瓶,不是為了尋找起源而產生這樣的聯想,臺裹的元德二年(公元1330年)觀心寺的金銅蓮花瓶,是德利形花瓶的典型代表,飲食器與德利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也就是以古瀨戶為中心的中世諸窯都有著像中國陶瓷盛產那樣的宏偉目標。德利的器型各式各樣,特別是玉壺春秋形的德利讓人印象深刻。除了上述提及的日本近世的本土酒器之外,還有受到中國和西方文化影響的玻璃酒器、七寶工藝酒器等,它們的功能美也展現了日本融入外來文化的特色。
2 形式美:酒器的色彩是不同材質的節奏與韻律
形式美是事物的形式因素本身的結構關系所產生的審美價值。研究日本近世酒器的形式美,其形式因素有很多,對審美形式的知覺感受存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選取“色彩”這一感性質料及形式因素作為典型,對不同時期、不同工藝種類的酒器工藝作品進行分析。
2.1 日本人在創造德利酒器的活動中不斷地探索各種色彩的民族因素特性
日本近世酒器的色彩首先要根據不同材質來區分,由于制作工藝不同,漆工藝、陶瓷工藝、金屬工藝、玻璃工藝等不同材質的酒器色彩呈現的形式也不相同。“德利”就是體現日本酒器民族特色的重要代表,不僅器型來源于酒盃和酒瓶等造型樣式,包含銅、錫等金屬元素,且玻璃、陶瓷、金屬、漆器等各種材質兼有,這其中也有受歐洲金屬工藝的影響。色彩也呈現出藍色、黃色、金色、銀色、紅色、黑色等不同材質特有的顏色,大約16世紀,日本歷史的中世時期,隨著各種燒制陶瓷的窯業興起,“德利”最早的記載來自于《親俊日記》天文十一年(公元1542年)八月十日條“淵田入道后家德利一持來之”。從文字上看,除了“德利”,還有“陶得利、云具理、止久利、土工李”等不同表達名稱,也相應產生不同色彩的酒器。后來到日本江戶時代中期以后,逐漸統一為“德利”這個名稱。“德利”一詞用于酒器在中國很難讓人理解,著名收藏家馬未都將“德利”解釋為是日本人的清酒壺,認為從漢語字面上理解,“德”是道德品行,與中國陰陽五行之中“水”色彩的理解相通,一般對應的黑色或者深色,可以引申為恩惠,“利”為利益好處,可以引申為順利,德利的解釋應該是內在的美與外在的美之結合,這與日本人崇尚自然,在生活中重視內外結合的存在有關,與西方把外部和內部對立起來理解的價值觀不同,德利酒器的色彩寧靜與鮮麗并存,更好地體現了日本人內外融合的一種審美觀,從中可以感受到德利酒器色彩的民族因素特性。對于德利酒器色彩的認識使人們能深切感受到其獨特的審美與內涵。
2.2 色彩在陶瓷制酒器的發展中最易令人感受到節奏與韻律
色彩變化最為豐富的酒器要屬陶瓷器,酒器的發展一直是伴隨著陶瓷器的發展而不斷變革,進入安土桃山時代(公元1573—1600年),茶文化盛行,得益于茶文化陶瓷器窯業的繁榮發展,酒器亦開始大量使用陶瓷制品。古瀨戶類型的窯依然作為窯業中心,從中世以來,陶器中施釉陶成為了古瀨戶唯一的品種,一直采用的色彩以黃、褐色為主。到江戶時代初期,也就是17世紀40—50年代,日本瓷器的出現帶來了色彩的變化。新型裝飾手法的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繪等技術逐漸普及,最早體現這種青花的青藍色彩為主風格的是有田(田賀縣)一帶燒制的瓷器——“有田燒”和“伊萬里燒”,后來在柿右衛門燒制成功后以紅色的赤繪為主,結束了過去只是鐵繪、吳須(燒在藍色上的釉料)的歷史,在釉面上自由施展紅、黃、藍、紫等釉色,這些稱之為赤繪、錦手色繪的裝飾手法給彩繪陶瓷帶了絢麗的色彩,色彩非常豐富,且畫面很和諧。江戶時期誕生了柿右衛門、古九谷樣式(見圖1、圖2)在內的伊萬里燒、鍋島等瓷器生產的發展。另一方面在京都,以野野村仁清和尾形乾山為代表的色繪陶“京燒”的發展,擺脫了對中國陶瓷的模仿,特別之處就是裝飾上表現出漆器“蒔繪”般黑地上閃爍金光的裝飾效果,確立了“京燒”及地方窯業在日本陶瓷制酒器中的地位,色彩很有繪畫寫意性,感覺有音樂旋律。人們可以從伊萬里琉璃釉捻溫德利、伊萬里色繪牡丹紋酒注、鍋島色繪松竹梅紋瓶子、京燒酒樽等酒器作品中去感受那個時代色彩的節奏與韻律。
2.3 把色彩從玻璃酒器的形式中抽象出來,對形式美作了比較和概括
形式美是客觀事物外觀形式的美。包括線、形、色、光、聲、質等外形因素,色彩就是形式美的因素其中之一。日本近世興起的玻璃酒器映入眼簾之后,給人的直觀感受一定是色彩與形式美、抽象美的關聯,當時最負盛名的玻璃酒器當然離不開發源于江戶時代末期的“江戶切子”(見圖3)這種玻璃器皿,在東京三德利美術館收藏的“切子”的制作的重要代表有薩摩切子酒杯、酒瓶(見圖4、圖5),隨著時代與審美的進程,“江戶切子”和“薩摩切子”的花紋演變出越來越多的樣式,豐富的質感讓切子充滿魅力。江戶切子就是在江戶時代末期的江戶(今東京)逐漸形成的加工工藝。天保五年(公元1834年)日本橋附近的小傳馬町經營硝子(玻璃的別稱)制品的“加賀屋久兵衛”,仿英國制的切割玻璃的技術來完成;薩摩切子,來自薩摩藩(今鹿兒島),為日本江戶時代的國家實行“殖產興業[5]”重要藩屬地,“切子”關鍵詞是切,用金屬砂盤或磨石切割加工硝子,再進行雕花玻璃制作色彩視覺效果極為豐富,猶如萬花筒般呈現出不同層次的美,常見的顏色有黃、藍、紫、棕褐色等,形態萬千,賦予玻璃生命與光彩。“江戶切子”的著名傳承人川井更造,把“廣田硝子”株式會社作為平臺,不斷地追求手工玻璃品質上的成長,這是色彩在玻璃工藝形式美的一種綻放。

圖1 古九谷樣式

圖2 柿右衛門

圖3 江戶切子

圖4 薩摩切子酒瓶

圖5 薩摩切子酒杯
3 技術美:結合時代與文化的特質考量裝飾
日本近世酒器的技術不僅是酒器設計的形式,也是不同材質、外形、裝飾等技術的表達,所產生的技術美,一定要結合時代與文化的特質去分析,它的審美價值主要體現以下3方面。
3.1 日本近世酒器帶有日本統治者的“黃金藝術”審美意識
從安土桃山時代開始,隨著金銀礦開采業的發達,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到德川家康,統治者們崇尚黃金意識增強,幾十年間在日本修筑了100多座城郭,都是用金箔涂瓦,內部貼金泥,用金碧輝煌來形容絕不為過。在酒器的裝飾技術層面,黃金裝飾必不可少,其中漆工藝的技法以壓倒性的優勢占很大比重,用蒔繪、螺鈿、雕漆、漆繪、密陀繪、沈金等異樣的技法來制作的各種精美德利酒器,一直是本土文化的重要審美象征。漆工藝酒器之中用蒔繪裝飾技術的德利酒器非常有名,根據江戶時代著名漆藝家幸阿彌家十代長重家傳書記載,慶安二年(公元1649年)池田光政的女兒(德川家光的養女)整套婚禮嫁妝調度(家具和日用器物),就有獅子牡丹葵紋蒔繪德利(見圖6),是日本近世德利酒器歷史上非常豪華絢爛的重要代表作品。

圖6 獅子牡丹葵紋蒔繪德利
3.2 作為日本人的傳統工藝的物化
安土桃山時代除了以“黃金技術”代表皇室高貴的審美價值取向,還有以千利休為代表的受禪宗思想引導而產生的草庵式茶室“空寂的茶禪一味”審美思想,草庵式茶室用原木結構,草,土墻,竹格或由葦編等接近自然的原料與素材,盡可能按照自然規律來完成“空寂茶”和“閑寂美”的自由創造,也成為日本酒器工藝文化的一種表現和自我確證。這種簡素和非對稱、保留天然原貌的裝飾技術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約1 300年前,在盛產黏土的美濃地區開始生產一種名為“須惠器”的土陶器。進入江戶時代,美濃燒作為平民的日常酒器開始進入千家萬戶,為了守護傳統工藝,工匠們不斷創新,將流行元素與古老技法巧妙融合,形成了現代實用兼具觀賞的和風酒器。美濃燒燒窯溫度達到了1 240—1 260℃,而非通常700—800℃。胚體經過充分氧化,可令其中的金屬含量大大降低,這種尋求天然環保的態度,至今仍反映日本人通過技術體現對自然的尊重和保護的態度。
3.3 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技術作為一種知識體系
玻璃酒器的技術引導因素一定伴隨著日本近世時期,與西方文化的最初傳入及其影響有關的是西方的先進技術和知識。天文十二年(公元1543年),葡萄牙人是近世最早來日本的西方人,除了帶來槍炮和火藥制造技術,冶煉技術等一系列工業生產技術也走入了這個時代,在當時日本政府的政策支持下,以長崎為首,大阪、江戶、萩、佐賀、薩摩等各藩的玻璃制造產業也非常盛行。如果看到這些酒器,其特征與歐洲的酒瓶和玻璃酒杯很相似,銚釐(ちろり)[6]和三重盃、盃臺,長崎玻璃暖酒杯(見圖7)等日本特有的酒器品種很多,因為熱水燙酒的器具,原本都是金屬制作而成。近世玻璃酒器的重要角色除了上文提到的“江戶切子”,還有來自青森縣的津輕玻璃(見圖8)。津輕玻璃源自中國的玻璃制品,3世紀左右傳入日本后,經過幾代日本手工匠人的努力,將津輕玻璃(津軽びいどろ)發展為工藝文化品牌。其玻璃制作技術“宙吹”(宙吹き)技術是津輕玻璃產業發展的關鍵。需要玻璃工匠在溶解爐達到1 400℃高溫的狀況下,按照個人意識和審美要求來吹制玻璃胚胎的形狀。在日本NHK拍攝的系列紀錄片《日本匠人》可以感受到這種傳統手工藝已經形成一種體系而發展,依然延續生命的氣息。

圖7 長崎玻璃銚釐

圖8 津輕玻璃
4 結語
研究日本近世酒器的發展,除了功能美、形式美、技術美等設計美學范疇,必然要拓展到日本的歷史、文化、民族、宗教、生活等領域,要真正理解日本近世酒器,進入美學層面理解其審美特質,需要深入了解日本人的審美意識,從日本著名建筑設計師黑川雅之[7]的《日本的八個審美意識》,去真正體會其中微妙的內涵,感受“一期一會”,珍惜每一個美好的瞬間,領悟日本人對自然的敬畏和崇敬,秩序感與和諧共生,才能真正理解日本的器物設計為什么盡量避免引導或者刺激別人,而是給人充分的想象空間。雖然表達有所不同,但心靈相通,這就是日本近世酒器帶給人們審美的心靈震撼,從酒器的藝術美之中可以領悟出具有陶冶性情、凈化靈魂的作用。
被德國國立美術館列為“日本現代漆器12人”之一,日本當代漆藝家赤木明登從手藝人的角度詮釋了制作器物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他手中制作的漆器造型并非獨創,創作靈感來自于江戶末期的漆碗,深植于長久以來大眾的日常生活之中,他的兩部著作《美物抵心》和《造物有靈且美》,以手藝人的視角去發掘和論述真正的美物。他認為真正的美物可能是無心之作,是手藝人本性的自然流露。物件是否美,可能取決于手藝人的技藝,也可能是他們用手給物滲入的心魂或生命[8]。從赤木明登的手工藝創作思想中可以看到日本人獨特的藝術審美思想。日本金澤美術工藝大學的辦學理念是“以手思考,用心造物”,日本近世酒器很多看起來平淡樸素,但卻會讓人在不斷接觸中越來越驚嘆于工匠們對細節的考究和對使用者的呵護。通過相關資料整理,對日本近世酒器工藝的審美特質的理解,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4.1 傳承有序,雖然源于中國、朝鮮,但形成了自己獨立的文化體系
通過對日本近世酒器的了解,追溯歷史,從原始時期繩文時代開始,到近世桃山時代、江戶時代,一直與中國酒器文化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這其中不乏有受中國唐代青白瓷、宋代官窯瓷器均窯影響的優雅酒盃,也有與朝鮮李朝粉引德利等酒器神韻相似的德利清酒瓶,但從平安時代開始,“唐風化”向“和風化”轉變之后,不但名稱上有本國的技術性、地域性特點,審美和功能上也有其獨特的文化意蘊,最終形成了德利酒器、陶瓷酒器、玻璃酒器、酒杯等各具特色,并相互轉化融合的酒器文化體系。
4.2 德利酒器不能簡單歸納于工藝種類,是跨領域的酒器類型
德利酒器幾乎出現在所有的工藝種類之中,陶瓷之中德利酒器很多,備前德利和斑唐津德利在日本近世聲名顯赫;漆器之中蒔繪德利尤為光芒耀眼,并且與南蠻蒔繪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玻璃和金屬工藝酒器中也經常出現作為溫酒器、燗鍋之類的德利酒器。德利酒器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是日本傳統工藝重要的文化符號,日本近世酒器的研究之眼。
4.3 原始神道文化體系的影響
日本近世酒器雖然呈現多樣性的發展趨勢,但始終圍繞原始神道為核心,以崇拜自然、尊神敬祖等諸要素構成的原生文化一直貫穿日本整個社會、文化、宗教之中,無論是神道神社、佛教寺廟的神佛文化,還是到江戶時代形成的町人文化,酒盃有其特殊意義,這是傳統古代習俗的傳達,清凈的尊崇神道的神饌具都是酒器發展的見證。經歷了神人融合、尊崇天皇之后,開始回歸大眾化,走入尋常百姓生活之中,寄托著日本人的自然情懷,處處滲透著原始神道文化體系的精髓。
4.4 受南蠻文化影響的酒器是日本近現代工業設計的萌芽
日本近世開始的南蠻文化主要是受以葡萄牙、英國、荷蘭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影響,酒器之中以漆塗酒器和玻璃酒器為代表,漆塗酒器的重要代表即為南蠻漆器;玻璃酒器由于受歐洲以意大利穆拉諾玻璃文化的影響,其特征與歐洲的酒瓶和玻璃酒杯很相似,薩摩切子酒瓶、酒杯和江戶切子已經逐漸走入西方國家的視野。這些都是本土化和國際化,東西方文化的完美結合,也是從傳統工藝到日用器具設計成功轉型的典范,為以后日本的近現代工業設計發展奠定了基礎。
綜上所述,鑒于目前中國對日本酒器的研究還是停留在文化旅游、商業、廣告宣傳等淺層文化層面,并沒有就酒器的歷史淵源和工藝美術設計研究角度展開較為深入的學術分析,筆者通過整理相關日文資料,以日本近世為時間節點,以點帶面,剖析酒器及酒文化,也是冀望引起更多研究者的關注,對日本傳統工藝文化歷史及相關領域作全面細致的分析。古人云“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研究日本近世的酒器不僅僅著眼于酒器,酒器只是一個切入點,可謂冰山一角。對整個日本傳統工藝歷史的濃縮作更多關注,也是對當下的傳統工藝及現代工業設計發展拓寬視野,帶來更多的研究方法與思考,正如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教授,著名生物學家琳·馬古利斯等[9]的《神秘的舞蹈》一書的結尾“我脫去的是肉體,留下的是整個宇宙”謹以此句與更多關注日本傳統工藝歷史與發展的學者與研究人員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