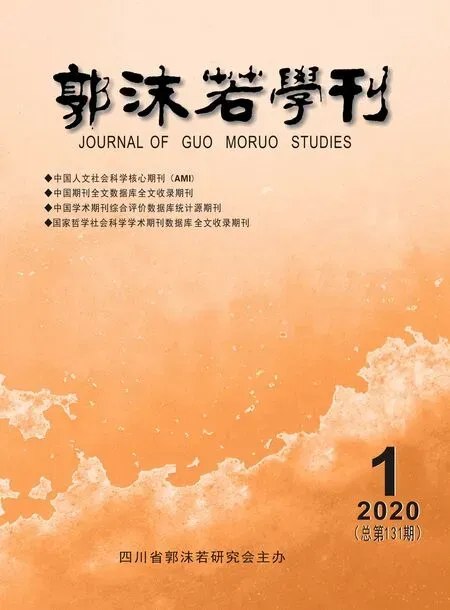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的版本與修改
喬世華 喬雨書
(遼寧師范大學 文學院,遼寧 大連 116081四川大學 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 成都 610211)
作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理論的重要文獻,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最早對“兒童文學”做出界說并明確提出“兒童本位”,同時闡述了兒童文學本質及建設路徑。該文最初發表在1921年上海《民鐸》雜志第二卷第四號上,后又收錄在郭沫若第一部文藝批評論著《文藝論集》中。《文藝論集》在不同時期出版單行本或并入合集時,郭沫若均對書中具體篇目和文章內容做過程度不同的增刪修改,因此該書先后有過多個版本,如上海光華書局1925年初版本、上海光華書局1929年訂正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沫若文集》第十卷等。以不足五千字的《兒童文學之管見》來說,也因多次修改而實際上先后形成了《民鐸》版、光華初版本、光華訂正本和《沫若文集》本這樣四個文字表述不盡相同的版本。我們恰可以透過這篇文章歷次修改而形成的諸種“異文”,發現郭沫若三十多年間在諸種人事尤其是文藝相關問題認識上的歷時性變化。
一
《兒童文學之管見》在《民鐸》雜志最初發表時,文章開篇有這樣一句話:“國內對于兒童文學,最近有周作人先生講演錄一篇出現,這要算是個絕好的消息了!”①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民鐸》,1921年1月15日第2卷第4號。顯見此文的寫作是對周作人1920年10月26日在北平孔德學校的演講《兒童的文學》的一種積極回應。但在1925年光華初版本以及此后的各種版本中,這一句話均被刪掉。個中緣由值得細細推敲。
據咸立強《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翻譯問題論爭探源》(《中山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一文可知,郭沫若在翻譯問題的認知上與周作人、沈雁冰、鄭振鐸等發生齟齬正是在寫作《兒童文學之管見》前后。《時事新報·學燈》1920年10月10日在刊發周作人譯作《世界的霉》、魯迅小說《頭發的故事》、郭沫若歷史劇《棠棣之花》、鄭振鐸譯作《神人》等幾篇作品時是依照周作人、魯迅、郭沫若、鄭振鐸的順序排列先后的,這引起了郭沫若的不平,遂在1921年1月上旬(略早于1921年1月11日《兒童文學之管見》的寫作時間)致編者李石岑的信件中有“我覺得國內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處子;只注重翻譯,而不注重產生”的感慨,并主張“處女應當尊重,媒婆應當稍加遏抑”①郭沫若:《通訊》,《民鐸》1921年2月15日第2卷第5號。。可見,寫作《兒童文學之管見》時,郭沫若已經因翻譯問題對周作人等心存芥蒂了。當1921年6月10日鄭振鐸在《文學旬刊》上發表《處女與媒婆》一文認為郭沫若的這一說法“未免有些觀察錯誤了”,郭沫若即迅速反應,在致鄭振鐸的信件中表態:“有的說創作不容易,不如翻譯(周作人《兒童的文學》一文中有這么意思的話);有的說中國人還說不到創作,與其囂囂焉空談創作,不如翻譯(耿濟之《甲必丹之女》序文中有這么意思的話);像這樣放言,我實在不敢贊可。”②“郭沫若致鄭振鐸信”,《文學旬刊》1921年第6期,轉引自咸立強《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翻譯問題論爭探源》,《中山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1925年前后正是郭沫若思想發生巨變時期,正如其在《〈文藝論集〉序》中所表示的那樣:“我的思想,我的生活,我的作風,在最近一兩年之內可以說是完全變了”,“這部小小的論文集,嚴格地說時,可以說是我的墳墓罷。”③郭沫若:《文藝論集》,上海:光華書局,1929年,第1頁。1924年,郭沫若翻譯日本早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著作《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這書的譯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一個轉換的時期,把我從半眠狀態里喚醒了的是它,把我從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從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對于作者是非常感謝,我對于馬克思列寧是非常感謝。”郭沫若由是“成了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了”,并認為“馬克思主義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是唯一的寶筏”④郭沫若:《孤鴻》,《創造月刊》,1926年1卷2期。。職是之故,獲得思想新生的郭沫若不愿意再在自己文章中提到周作人,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與此可相印證的是郭沫若對《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于創作上的態度》一文的修改。該文最初在1922年8月4日《時事新報·學燈》發表時,篇末曾有一段長文字介紹了寫作緣起,其中特別點明此文與沈雁冰之間的精神聯系并對沈雁冰表示出相當敬意:“我這篇文字的動機,是讀了沈雁冰君《論文學的介紹的目的》一文而感發的。雁冰君答復我的這篇評論的態度是很嚴肅的,我很欽佩”,“雁冰君的答辯,本來再想從事設論,不過我在短促的暑假期內,還想做些創作出來,我就暫且認定我們的意見的相違,不再事枝葉的爭執了。我們彼此在尊重他人的人格的范圍以內,各守各的自由。”⑤郭沫若:《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于創作上的態度》,見黃淳浩校《〈文藝論集〉匯校本》,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0頁。但在《文藝論集》1925年光華初版本以及后來的各版本中,這段說明文字也同樣被刪掉。再聯系稍后倡導革命文學的創造社、太陽社對被他們視為落伍的魯迅、周作人兄弟以及沈雁冰等人的批評和攻擊這一事實來看,郭沫若自從初步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之后,就已經不愿意再在文中和周作人、沈雁冰等落伍的新文學權威出現思想互動了。
不過,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與周作人《兒童的文學》實際上所發生著的密切精神聯系,是無可否認的。比如,周作人《兒童的文學》中有如是表述:“以前的人對于兒童多不能正當理解,不是將他當作縮小的成人,拿圣經賢傳盡量地灌下去,便將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說小孩懂得甚么,一筆抹殺,不去理他”,“誤認兒童為縮小的成人”,“我們承認兒童有獨立的生活,就是說他們內面的生活與大人不同”⑥周作人:《兒童的文學》,《新青年》1920年12月1日第8卷第4號。。郭沫若在文中也有類似說法:“兒童與成人生理上與心理上的狀態,相差甚遠。兒童身體決不是成人之縮形,成人心理亦決不是兒童之放大。”⑦郭沫若:《通訊》,《民鐸》1921年2月15日第2卷第5號。再者,周作人在《兒童的文學》中實際上為中國兒童文學建設開出了創作、收集和翻譯這三種方法,比較而言,他更看好收集和翻譯這兩種方法,并用大量篇幅論及此,如:“童話也最好利用原有的材料,但現在的尚未有人收集,古書里的須待修訂,沒有恰好的童話集可用。翻譯別國的東西,也是一法,只須稍加審擇便好。”①周作人:《兒童的文學》,《新青年》,1920年12月1日第8卷第4號。郭沫若在《兒童文學之管見》中也同樣依次提到了“收集”、“創造”和“翻譯”這三種方法,只是他并不像周作人那樣看好翻譯:“太偏重翻譯,啟迪少年崇拜偶像底劣根性,而減殺作家自由創造底真精神。翻譯亦不可太濫。歐人底兒童文學不能說篇篇都好,部部都好,總宜加以慎重的選擇。并且舉凡兒童文學中地方色彩大抵濃厚。譯品之于兒童,能否生出良好的結果,未經實驗,總難斷言。所以我的主張還是趨重于前的兩種。”②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民鐸》,1921年1月15日第2卷第4號。
二
《兒童文學之管見》中提到了華茲華斯、泰戈爾、梅特林克、霍普特曼等一些外國作家或其作品,如舉說華茲華斯《童年回憶中不朽性之暗示》、泰戈爾《嬰兒的世界》等以說明“兒童文學不是些鬼話桃符的妖怪文字”,“兒童文學底世界總帶神秘的色彩”③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民鐸》,1921年1月15日第2卷第4號。等。《沫若文集》本全部刪去原來所引的華茲華斯的詩歌和泰戈爾詩歌的外文部分而只保留中文譯文,這應該是考慮到方便讀者閱讀的因素。至于《民鐸》版譯文中“位置”、“束縛”等詞語在《沫若文集》本譯文中改作了“地位”、“羈縛”等,或可顯示出郭沫若在翻譯時措辭上的用心。
當然,在涉及到對華茲華斯、梅特林克、霍普特曼等外國作家作品的“評價”時,《沫若文集》本做出的些許改動,是可以顯示出郭沫若在1949年之后對上述作家的新認識的。
比如在談到收集童話童謠的必要性的同時,郭沫若提到了兩首令自己印象深刻的謠曲:
大家必吟誦起這兩首謠曲起來,那時底幸福,真是天國了!如今呢,回憶起來,不容不與瓦池渥斯起同樣的哀感!(《民鐸》版)
有時會順口唱出這些兒歌來,那時候的快樂,真是天國了!(《沫若文集》本)
郭沫若早期對華茲華斯是甚為欣賞的,譬如其在《三葉集》中對詩歌有這樣的看法:“我自己對于詩的直感,總覺得以‘自然流露’的為上乘,若是出以‘矯揉造作’,只不過是些園藝盆栽,只好供諸富貴人賞玩了”④郭沫若:《郭沫若致宗白華》,《郭沫若全集·文學編》1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第47頁。。這與華茲華斯在《〈抒情歌謠集〉序言》中的認知正相吻合:“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⑤劉若端編:《十九世紀英國詩人論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22頁。刪掉與華茲華斯有相同感受的文字,保持和他的情感距離,這應該與華茲華斯等詩人在社會主義國家被貼上“消極浪漫派”的標簽有關。高爾基《我怎樣學習寫作》中對消極浪漫主義和積極浪漫主義有嚴格的區分:“在浪漫主義里面,我們必須分別清楚兩個極端不同的傾向:一個是消極的浪漫主義,——它或者粉飾現實,想使人和現實相妥協;或者就使人逃避現實,墮入到自己內心世界的無益的深淵中去,墮入到‘人生的命運之謎’,愛與死等思想中去,墮入到不能用‘思辯’,直觀的方法來解決,而只能由科學來解決的謎之中去。積極的浪漫主義,則企圖加強人的生活的意志,喚起他心中對于現實、對于現實的一切壓迫的反抗心。”⑥高爾基:《我怎樣學習寫作》,戈寶權譯,上海:讀書出版社,1946年,第7-8頁。1949年以后,國內學界也都緊緊跟隨這種說法,如卞之琳《開講英國詩想到的一些體驗》(《文藝報》1949年1卷4期)、晴空《我們需要浪漫主義》(《詩刊》1958年6期)、朱光潛《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吉林大學學報》1963年3期)等,都普遍認為作為消極浪漫派的華茲華斯站在與歷史相抗衡的立場上迷戀過去生活,“厭惡革命”⑦朱光潛:《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吉林大學學報》,1963年第3期。是他的標簽。在革命浪漫主義被肯定和提倡的1958年,郭沫若雖說敢于坦白承認自己是浪漫主義者了⑧郭沫若在《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紅旗》1958年第3期)中表示:“比如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認:我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了。”,但是不愿意再和華茲華斯這樣的消極浪漫主義者保持聲氣相通,也是情理中事。
同樣的,梅特林克的《青鳥》、霍普特曼的《沉鐘》等象征派戲劇在1949年之后聲名不佳,郭沫若也要避免和他們發生關系。在《民鐸》雜志版、光華初版本、光華訂正本等20年代幾個版本的《兒童文學之管見》中,郭沫若還對他們有這樣不加掩飾的贊賞:“梅特林底《青鳥》、浩普特曼的《沉鐘》最稱杰作”①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民鐸》1921年1月15日第2卷第4號。,其1920年與宗白華、田漢三人之間通信集成的《三葉集》中就多次提及帶有典范色彩的梅特林克《青鳥》、霍普特曼的《沉鐘》,表現出明顯的稱賞態度來:“你若果能把我們做個Model,寫出部《沉鐘》一樣的戲劇來,那你是替我減省了莫大的負擔的呀!”②郭沫若:《郭沫若致田漢》,《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第66頁。而在《沫若文集》本中,郭沫若將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正面評價換成不動聲色的客觀事實的描述:“我看過梅特林克的《青鳥》、浩普特曼的《沉鐘》”③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第154頁。,以此與這些不入時人眼的作家及作品保持著謹慎的距離。
三
在談到兒童文學的效用時,《民鐸》版如是說:
文學于人性之熏陶,本有非常宏偉之效力,而兒童文學尤能于不識不知之間,導引兒童入于醇美的地域;更能啟發其良知良能——此借羅素語表示時,即所謂“創造的沖動”,——達于自由創造,自由表現之境。是故兒童文學底提倡對于我國徹底腐敗的社會,無創造能力的國民,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藥。
光華初版本、光華訂正本都與《民鐸》版保持一致。《沫若文集》本則將原先對社會和國民顯示著強烈絕望和批判色彩的詞語如“徹底腐敗的”、“無創造能力的”等盡數刪除:
文學于人性之熏陶,本有宏偉的效力,而兒童文學尤能于不識不知之間,導引兒童向上,啟發其良知良能——借羅素的話表示時,即所謂“創造的沖動”,敢于自由創造,自由表現。是故兒童文學的提倡對于我國社會和國民,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藥。
雖說這種改動可能會令后面的“起死回春”顯得突兀和失去依據,但整體表達在語氣上和緩了許多,不再帶有強烈的批判色彩,這更容易為讀者所接受,也許還意味著郭沫若在解放后文化精英立場的某種退隱。
而與此相關聯的是,郭沫若也一并矯正了早期對民間文藝的輕視態度。《民鐸》版在談到兒童文學的“創造”這一路徑時,對在民間流傳的童話、童謠等的藝術價值和收集者所能取得的成效是抱持懷疑態度的:
此種作品有待于今后新文學家之創造自無待言,如童話、童謠等體裁,我國舊有的究竟有多少藝術上的價值,尚是疑問,采集的人更要具有犀利的批評眼才行。將來的成果如何,究竟不能預料;那么還是有待于新人底創造了!不過創造的人總不要輕于嘗試,總要出諸鄭重,至少兒童心理學是所當研究的。
光華初版本和訂正本的有關表述除了個別文字有變動外,也都和《民鐸》雜志版相同。郭沫若彼時之所以期待新人創造,實在緣于其對民間文藝的信心不足。《沫若文集》本則刪除掉此類表態:
此種作品有待于今后新文學家的創造。童話、童謠,除舊有的須迅速采集而嚴加選擇外,還是有待于新人的創造。創造的人希望出諸鄭重,至少兒童心理學是所當研究的。(《沫若文集》本)
《民鐸》版中,郭沫若在提到自己印象深刻的兩首謠曲時,毫不留情地對其他謠曲給出了負面評價,《沫若文集》本則力避感情用事般的評價:
我所能記憶的謠曲,有價值的只上兩首,此外雖還記得些,但都鄙陋無可言。(《民鐸》版)
我所能記憶的兒歌,比較有價值、留在記憶里的只這兩首。(《沫若文集》本)
郭沫若對《兒童文學之管見》做修改的1958年,正值這樣一個大背景:“全面搜集民歌及其他民間文學藝術,是一件必須全黨、全民動手的工作,同時必須動員和吸引全體文藝工作者來參加這個工作”,“我們的詩人一定要深入工農群眾,和群眾一同勞動,一同創作,向民歌學習,向優良傳統學習”①周揚:《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新道路》,文藝報編輯部編:《論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13頁。。更何況,郭沫若對民間文藝的態度早在這之前就已有變化。1950年,其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如是說:“說實話,我過去是看不起民間文藝的,認為民間文藝是低級的、庸俗的。直到1943年讀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才啟了蒙,了解到對群眾文學、群眾藝術采取輕視的態度是錯誤的。”因為意識到了“中國文學遺產中最基本、最生動、最豐富的就是民間文藝或是經過加工的民間文藝的作品”②郭沫若:《我們研究民間文藝的目的——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苑利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民俗學經典·民俗理論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41頁。,所以郭沫若在修改涉及到民間文藝話題的舊作時,就竭力消除太多的個人感情色彩而對事實進行客觀陳述。
四
在正式進入對兒童文學的論述之前,《民鐸》版首先談到了對文藝上功利主義和唯美主義之爭的看法:
文學上近來雖有功利主義與唯美主義——即“社會的藝術”與“藝術的藝術”——之論爭,然此要不過立腳點之差異而已。文學自身本具有功利的性質,即彼非社會的Antisocial或厭人的Misanthropic作品,其于社會改革上,人性提高上有非常深宏的效果;就此效果而言,不能謂為不是“社會的藝術”。他方面,創作家于其創作時,茍兢兢焉為功利之見所拘,其所成之作品必淺薄膚陋而不能深刻動人,藝術且不成,不能更進其為是否“社會”的或“非社會的”了。要之就創作方面主張時,當持唯美主義;就鑒賞方面言時,當持功利主義:此為最持平而合理的主張。
光華初版本和光華訂正本也都對此沒有做什么大的改動。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甚至其后更長一段時間里,郭沫若都聲明“我更是不承認藝術中會劃分出甚么人生派與藝術派的人”③郭沫若:《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于創作上的態度》,《文藝論集》,上海:光華書局,1929年,第267頁。。在他看來,文學本身是兼有功利性與唯美性的,即使是包括“非社會的”和“厭人的”作品等在內的那些唯美主義作品,也都會因為有益于社會改革或人性提高而具有功利性。顯然,郭沫若有要調和融通這兩種看似水火不容的文藝觀念的意圖。因此,20年代的郭沫若主張就作者一面而言,創作時要以唯美為追求,這樣才能創作出“深刻動人”的作品;主張就讀者一面而言,鑒賞時要持功利主義態度,如是方能受益。
《沫若文集》本中,郭沫若對此段文字做了較大程度的修訂,將“社會的藝術”與“藝術的藝術”之爭置換為了更為明確的“人生的藝術”與“藝術的藝術”之爭:
文學上近來雖有“人生的藝術”與“藝術的藝術”之爭,這是強加分別的,究竟誰是人生派,誰是藝術派?文藝是人生的表現,它本身具有功利的性質,即是超現實的或帶些神秘意味的作品,對于社會改革和人生的提高上,有時也有很大的效果。創作家于其創作時,茍兢兢焉為個人的名利之見所囿,其作品必淺薄膚陋而不能深刻動人。藝術且不成,不能更進論其為是否“人生”的或“藝術的”了。要之,創作無一不表現人生,問題是在它是不是藝術,是不是于人生有益。
顯見,郭沫若修正了自己早先關于藝術和人生關系的認知,他更愿意強調文學的“人生”性,強調藝術之于人生的意義,而不愿意再像早年那樣做一個藝術觀念的調和派。
五
比較而言,光華初版本、光華訂正本和光華改版本對《民鐸》雜志原刊文章的修改都不太大,這可能同《文藝論集》出書時間與文章發表時間相去不是太遠、郭沫若思想變化還不是很大有一定關系;而在經過了時間的沉淀、世事的變化之后,已是花甲之年的郭沫若在修訂編輯《沫若文集》時對于文學藝術的認知和表達更加趨于沉穩。更何況,1950年代以后的郭沫若是身兼數職的重要領導人,先后擔任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等重要職務。身份的變化,使得其在對文學藝術的言說上必須要更加慎重,不可能太隨心所欲了,因此《沫若文集》本在措辭上所發生的變化,有不少都是為了表達的圓滿穩妥。
早先《兒童文學之管見》成文時確實有不夠縝密的地方,如對宗教畫中耶穌肖像的描述容易造成讀者的誤解,《沫若文集》本遂有了更精準的表達:
歐洲古代畫家未解解剖學之重要,宗教畫中之耶穌肖像大抵皆為成人之縮形,吾希望我國將來的兒童文學家,勿更蹈此覆轍。(《民鐸》版,光華初版本)
歐洲古代畫家未解解剖學之重要,宗教畫中之幼年耶穌肖像大抵皆為成人之縮形,吾希望我國將來的兒童文學家,勿更蹈此覆轍。(光華訂正本)
歐洲古代畫家未解解剖學之重要,宗教畫中的嬰兒耶穌大抵是成人之縮影,我國畫家和雕塑家也有這樣的毛病。(《沫若文集》本)
而且,郭沫若早先并未對我國畫家雕塑家有所批評,《沫若文集》本中則指出中國畫家和雕塑家也都存在這種藝術上的通病,這可能意味著此時郭沫若對本土精英的繪畫和雕塑作品有了更多了解,產生了新的認識,才會下此斷言。
又如《民鐸》版認為“兒童文學中采取劇曲形式底表示者,在歐洲亦為最近的創舉,我國固素所無有也”①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民鐸》1921年1月15日第2卷第4號。,《沫若文集》本則改為“兒童文學采取劇曲形式,恐怕是近代歐洲的創舉”②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第154、148、155頁。,不再就我國是否有劇曲進行判斷,如是避免了無謂延伸有可能帶來的表達上的疏漏。再如在談到人的改造要從兒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做起時,《民鐸》版最初是這樣申說的:“所以改造事業底基礎,總當建設于文藝藝術之上。這決不是故意夸張,借以欺人弄世之語。”③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民鐸》1921年1月15日第2卷第4號。光華初版本、光華訂正本也都沒有變化,《沫若文集》本則刪削了一些冗贅文字,直接將這段話改作:“因而改造事業的組成部分,應當重視文藝藝術。”④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第154、148、155頁。《民鐸》版中,郭沫若對兒童文學翻譯這條路徑顯得不是特別看好,因而說“譯品之于兒童,能否生出良好的結果,未經實驗,總難斷言”⑤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民鐸》1921年1月15日第2卷第4號。,在《沫若文集》本中則改為“尚難斷言”⑥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第154、148、155頁。,雖只是一字之易,但在表達上更無懈可擊,至少對翻譯并非毫無信心。
事實上,郭沫若在不同時期對《兒童文學之管見》的修改,不但反映著他一個人思想或性情上的變化,更是有代表性地反映著“五四”時期一部分知識分子在波詭云譎的時代浪潮中左突右進時的心靈掙扎。值得提及的是,歷經世事滄桑的郭沫若對諸種文藝事項在認知上發生了那么多變化,但其對兒童文學概念的界定幾乎沒有發生變化(幾個版本只是在個別字詞上略有差異):“兒童文學無論其采用何種形式(童話、童謠、劇曲),是用兒童本位的文字,由兒童底感官可以直溯于其精神堂奧者,以表示準依兒童心理所生之創造的想像與感情之藝術。”⑦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民鐸》1921年1月15日第2卷第4號。赤子之心的詩人也許唯有在面對至為質樸本真的兒童文學時,才心無掛礙、沒有那么濃重的人間煙火氣,而本位的兒童文學觀遂成為郭沫若對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莫大貢獻,影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