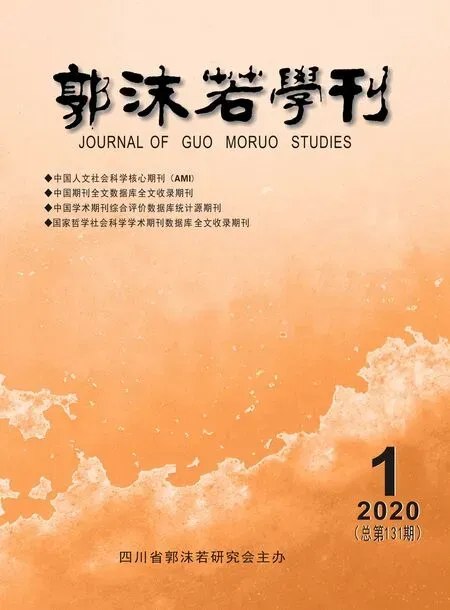《郭沫若年譜》訂補二則
李紅薇
(中國社會科學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9)
一
龔濟民、方仁念編著《郭沫若年譜》①龔濟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龔濟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譜》(增訂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1930年4月23日:
作《“矢令簋”考釋》,并附《追記》。考定此為“周初之器”,其制作年代“必在成王之世”。收《文集》十四卷《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附錄。
5月:
發表《明保之又一證》,以“新出一卣”復證明保確系“周公之子”。……收《文集》十四卷《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附錄。②龔濟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譜》(增訂版)增“現收《全集》歷史編一卷”。
王繼權、童煒鋼編著《郭沫若年譜》③王繼權,童煒鋼編:《郭沫若年譜》,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1930年4月23日:
作《“矢令簋”考釋》,并作《追記》。收《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附錄”。又收《沫若文集》第14卷。
5月:
發表《明保之又一證》……收《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上海圖書館編《郭沫若著譯系年》④王訓昭等編:《郭沫若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年。“矢令簋考釋 附追記(論文)”注:
1930年4月23日補志;初收1930年5月20日上海聯合書店三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再版書后》;又收《沫若文集》第14卷。
“明保之又一證(論著)”注:
初收1930年5月20日上海聯合書店三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再版書后》;又收《沫若文集》。
林甘泉、蔡震主編《郭沫若年譜長編》①林甘泉、蔡震主編:《郭沫若年譜長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1930年4月23日:
作《“矢令簋”考釋》《追記》,考釋成王時一尊一卣。
兩種《年譜》《郭沫若著譯系年》及《年譜長編》均將《“夨令簋”考釋》②多誤成“矢令簋”。的寫作日期定于1930年4月23日,即《“夨令簋”考釋》文末“追記”部分的“補志”時間。《明保之又一證》歸入是年5月,是由于該文未注明寫作時間,即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聯合三版的出版月份為準。
蔡震先生不同意這一看法,他認為《夨令簋考釋》《明保之又一證》等6篇文章,“著者于第6篇《夏禹的問題》文末署‘1930年二月七日補志’。這個日期當然應該是全部6篇補遺文章最終完稿的時間。”③蔡震:《〈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寫作與出版》,收入《郭沫若生平文獻史料考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也就是說,蔡先生認為《夨令簋考釋》《明保之又一證》皆作于1930年2月7日之前。
我們認為上述兩種看法都是有問題的。
《夨令簋考釋》開篇即言:
與《夨彝》同出之《令簋》,近蒙容君希白以拓墨見示,與《令彝》確系一人之器,并饒有相互發明之處。
《明保之又一證》言:
《令彝》之“周公子明保”,余以為乃周公之子名明保。近新出一卣,復得一證。其銘云:“隹明保殷成周年,公錫作冊鬯貝,揚公休,用作父乙寶尊彝。□”
由上可知,《夨令簋考釋》的寫作,緣于容庚(字希白)寄贈的《令簋》(即夨令簋)銘文拓本,《明保之又一證》亦由于見到一件鑄有“隹明保殷成周年”的卣。也就是說,兩篇文章的寫作一定晚于郭沫若見到二器拓本之后。《郭沫若致容庚書簡》1930年2月16日記:
如南宮中鼎……,其文例為“隹+subject+predicate+年”此之“隹明保殷成周年”,正當以明保為名詞主格,殷為動詞,成周為賓語……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聯合三版的《三版書后》有一則“按語”,“這本是《再版書后》,因寄回國時沒有趕及,只好改成《三版書后》了。”“按語”寫于“四月十日”。《夨令簋考釋》《明保之又一證》等6篇文章,本作為《再版書后》,后收入聯合三版,故這6篇的寫作時間不會晚于4月10日。④蔡震:《〈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寫作與出版》,收入《郭沫若著譯作品版本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年。
揆諸上述細節,《夨令簋考釋》《明保之又一證》的寫作時間當在1930年2月9日之后,且不晚于4月10日,其中《夨令簋考釋》追記部分標明“1930年4月23日補志”自當與正文非同時所作,應是“再版書后”改為“三版書后”時另加。
二
王繼權、童煒鋼編著的《郭沫若年譜》1947年“初秋”記有為郭墨林題跋事:
文中所謂“郭若愚未刊稿”,已于1990年正式發表于《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五期,該文首次公布了郭沫若為樊季氏孫中鼎所作題跋的手稿照片。②郭若愚:《郭沫若佚文〈樊季氏鼎〉跋小記》,《上海博物館集刊》(第5期),1990年,第103-107頁。《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六卷《金文叢考補錄》亦收錄了這篇題跋。③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六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56頁。此事龔濟民、方仁念編撰《郭沫若年譜》,上海圖書館編《郭沫若著譯系年》,林甘泉、蔡震主編《郭沫若年譜長編》皆失載。
郭若愚在《郭沫若佚文〈樊季氏鼎〉跋小記》一文中對郭沫若《樊季氏鼎跋》的手稿作了釋文,落款時間記作“民紀卅六年初秋”,即1947年。文章開頭云:
一九四六年至四七年,郭沫若先生旅居滬上,他寫了《詛楚文考釋》《行氣銘釋文》等研究古文字的文章,已為郭老學術思想研究者所注意。就我所知,他還寫過《樊季氏鼎跋》,文字不多,但對于研究樊季氏鼎及樊國地望,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可以看出,郭若愚認定該文乃1946-1947年郭沫若旅居上海時所作。值得注意的是,郭若愚漏引了跋文末“墨林先生囑題”六字,卻稱“我曾手拓全形墨本,郭沫若先生跋云……”,全文對“墨林”只字未提,這很容易讓讀者誤以為此跋是為郭若愚所作。《郭沫若全集·考古編》收錄這篇題跋時,亦脫“墨林先生囑題”一行,落款時間也作“民紀卅六年初秋”。
細審題跋手跡,筆者認為所謂的“民紀卅六年”,實應作“民紀廿六年”,即1937年。
跋文中“墨林”即郭墨林(1906-1986),嘉興人,回族,抗日戰爭前,子承父業,隨父經營“聽濤山房”古玩店,④葛壯主編:《長三角都市流動穆斯林與伊斯蘭教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5年,第196頁。曾收藏過甲骨,⑤嚴一萍:《甲骨學》(上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 年,第 230 頁。對文物頗有研究。1986年任上海文史館館員,擅長文物鑒定。曾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顧問。⑥嘉興市志編纂委員會編:《嘉興市志》,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7年,第2259頁。鄭國賢:《歷代嘉興書畫名人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44頁。不少史料均記載了郭沫若曾為郭墨林收藏的《樊季氏銅鼎拓文》題跋注釋的經過。⑦蘇菲:《郭老與回民的一段情》,收入《成都少數民族》編委會編:《成都文史資料第三十輯:成都少數民族》,1997年。中華文化通志委員會編:《中華文化通志第3典民族文化:回族文化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邱樹森主編:《中國回族史》(修訂本),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
郭沫若為郭墨林題跋的具體時間,《中國回族文獻庫》“郭墨林”條稱:
民國二十六年,郭沫若在滬時曾為他所藏的《樊季氏銅鼎拓文》題詞注釋。⑧參中國回族文獻庫http://www.huizu360.com/huizu/news_view.asp?tid=16&id=1554
上海市文史研究館網站“郭墨林自傳”,有更為詳細的記載:
郭沫若曾為其藏戰國時代銅鼎拓片題字注釋。1937年7月29日,郭沫若自日本歸國抵滬后的第三天,墨林攜《樊季氏孫中鼎》拓片去滄州飯店請教,郭沫若題字如下:“此鼎有銘蓋文,凡廿一字,曰:‘佳⑨“佳”當為“隹”的誤字。正月初吉乙亥,樊季氏孫屯中鼎鼎共告金,自乍石池’。古鼎銘有自名石池者,如大師錘,伯侯鼎即其例。其石字稍沮力但固無可疑也。文尚未著①“著”當為“著”。錄,而蓋紋取制與壽春楚器頗相似,時代當屬于戰國。樊季氏如細考之,或當有得。墨林先生囑題。民國廿六年初秋,郭沫若”。數十年來,墨林將其收藏身邊,1990年,其次子良能與北京郭沫若故居紀念館聯系,同年9月,該館館長,郭沫若之女郭平英信稱:“能在《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的《金文叢考》卷發稿前增補這一遺散題跋,可謂意外收獲”。②參上海市文史研究館網站http://www.shwsg.net/d/96/78.html
郭沫若歸國日期,見諸當時報刊,如《申報周刊》“時事一周”辟有專欄報導“郭沫若返國”一事:“于七月二十五日自神戶乘日本皇后號輪返國,于二十七日下午安抵上海”。③參《申報周刊》1937年第2卷第31期。“1937年7月29日”確為“郭沫若自日本歸國抵滬后的第三天”。王繼權、童煒鋼編著《郭沫若年譜》1937年7月27日記“下午,船抵上海……到達上海后,由黨組織給他安排了住所,暫住滄州飯店”,龔濟民、方仁念編《郭沫若年譜》則記1937年7月27日“下午,抵達上海。……然后由郁達夫作東,在來喜飯店設宴洗塵,直到深夜。”1937年7月28日“搬至滄州飯店。”兩種記載雖略有差異,但至少可以肯定,7月29日郭沫若已下榻滄州飯店了。另郭成美在《回族學者金祖同》一文中稱“1937年7月底金祖同帶兩個妹妹德娟、淑娟和侄女金頤拜見郭氏。……祖同還帶回族表兄郭墨林攜一古鼎訪郭氏。”④郭成美:《回族學者金祖同》,《回族研究》,2008年第2期,第138-144頁。郭成美《國學大師致回族學者金祖同之書函、為其著作序文》亦有類似說法,“1937年秋祖同還帶回族表兄郭墨林攜‘樊季氏孫中口鼎’拓片拜訪郭老,郭老題字如下:‘此鼎有銘蓋文……民紀廿六年初秋,郭沫若’。”⑤郭成美:《國學大師致回族學者金祖同之書函、為其著作序文》,《甘肅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第22-29頁。
揆諸上述史料,可以肯定:樊季氏鼎拓本的主人是郭墨林,郭沫若為之題跋時間當是“民紀廿六年初秋”。是年郭若愚僅16歲,而據文獻記載,郭若愚與郭沫若相識當始于1947年6月,⑥郭偉亭編著:《文博專家郭若愚》,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6年,第14頁。故可肯定此事與郭若愚無關。
王繼權、童煒鋼編著《郭沫若年譜》對此事記載有誤,應將郭沫若“為郭墨林所藏樊季氏孫中鼎題辭”這一事件移至1937年。龔濟民、方仁念所著《郭沫若年譜》《郭沫若著譯系年》《郭沫若年譜長編》等也應補收此事。《郭沫若佚文〈樊季氏鼎〉跋小記》誤奪“墨林先生囑題”,將題跋時間錯識為“民紀卅六年初秋”。《郭沫若全集·考古編》因襲了這一錯誤。為體現題跋原貌,釋文當補入“墨林先生囑題”一行,且落款時間應訂正為“民紀廿六年初秋”。《郭沫若全集》若有機會再版,應修訂這一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