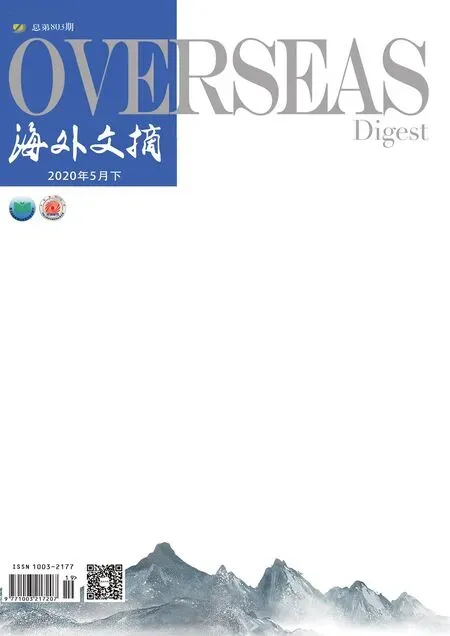國有企業海外訴訟中國家豁免問題研究
毛萱
(武漢大學法學院,湖北武漢 430072)
1 問題的提出
隨著我國“一帶一路”深入推進,走向海外企業的數量也越來越多,隨之而來的便產生各種海外安全風險,如恐怖主義風險、社會動亂、違法違規帶來的安全風險等。其中,違法違規的安全問題主要是指由于包括企業自身在內的各種主體未按照當地法律規定或合同約定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使企業卷入海外訴訟爭端之中,從而對企業海外長久的經營以及財產安全構成威脅。在涉及訴訟的企業中,也不乏一些國有企業。而由于國有企業與國家的聯系密切,一旦國有企業在海外卷入有關的訴訟,除了對企業自身的財產和經營安全產生影響外,還涉及國有企業在訴訟中是否能夠援引國家主權豁免進行抗辯的問題,從而對國家安全以及國家海外利益產生重要影響。
國家豁免是國際法上的一項基本制度,是指一國的行為和財產不受另一國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方面的管轄。狹義的國家豁免僅指一國的行為及其財產不受另一國的司法管轄,即非經一國同意,該國的行為免受所在國法院的審判,其財產免受所在國法院的扣押和強制執行。在有關豁免問題上,不同國家采取的立場不同。具體而言,有的主張絕對豁免原則,如我國在剛果(金)案中就重申了絕對豁免的主張;有的采取限制豁免原則,如美國1976 年《外國主權豁免法》中則采取的是限制豁免原則。此外,不同國家的法律對于具體概念的認定也不甚相同,因而,有必要對于依據不同法院地的不同法律來判斷國有企業在訴訟中主張國家豁免的可行性及其影響的問題予以討論,以更好地維護國家海外利益和保障企業海外安全。
2 不同依據下國有企業取得國家豁免主體資格的界定
2.1 以《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為依據
《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是統一國家管轄豁免適用國際條約的嘗試。雖然該公約尚未生效,但不論是WTO 爭端解決機構、ISCID 還是主權國家均普遍承認規則的指引作用①,它代表了對于主權管轄的國際權威表述②。
對于國有企業是否能夠主張國家豁免抗辯,首要問題在于國有企業是否被包含在“國家”的含義之中。《公約》的第2 條第1 款明確定義了“國家”包括國家及其政府的各種機關;有權行使主權權力并以該身份行事的聯邦國家的組成單位或國家政治區分單位;國家機構、部門或其他實體,但須它們有權行使并且實際在行使國家的主權權力;以國家代表身份行事的國家代表。雖然從條文內容上看,該條并沒有明確指出國家是否包括國有企業,但在1991 年國際法委員會對公約草案的評注中寫道:“國家機構或部門或其他實體的概念可能包括國有企業”。③其隨后又說明“為了該條款的目的,一般假定,這種國家企業無權執行政府職能,因此,通常無權對另一國法院援引豁免”。《公約》第10 條第3 款也有“國有企業一旦卷入與其從事的商業交易有關的訴訟時,國家享有的管轄豁免不應受影響”的規定。由此可見,在通常情況下,國有企業不能被預先推定為國家豁免的主體,“須他們有權行使并且實際行使國家的主權權力”時才有豁免的主體資格。
因此,在《公約》視角下,國有企業不當然具有管轄豁免資格,其享有國家豁免根據和國有企業的性質無關,而是由其所實施的國家主權權力行為決定的④。繼而,在國有企業涉及海外訴訟時并不會對國家在該國境內的財產安全造成威脅,但對于企業而言,海外訴訟對其自身的經營及財產安全的損害依然存在。
2.2 以美國《外國主權豁免法》為依據
國家豁免規則體現在國際法和國內法兩個層面⑤。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第2 條第3 款規定:“關于本公約用語的第1 款和第2 款的規定不妨礙其他國際文書或任何國家的國內法對這些用語的使用或給予的含義”。這表明了在“國家”等用語的定義上,國內法規定具有比國際法優先,因而對于國有企業是否享有國家豁免,還需要尊重國內法的相關規定。由于在所有涉及我國國有企業的訴訟中,有很大一部分案件的法院地在美國,而《外國主權豁免法》是美國法院處理有關外國國家主權豁免的依據,有必要考察在此依據下國有企業的國家豁免問題。
2.2.1 國有企業是否屬于“外國”的界定
《外國主權豁免法》對于“外國”的定義,并非僅局限于傳統意義上國家的概念,其第1603 條規定了“外國”除外國的政治分支機構外,還包括外國的代理機構或媒介,其中“外國的代理機構或媒介”是指下列任何實體:(1)獨立的法人、社團或其他;(2)隸屬外國或其政治分支的機關,或其多數股份或其他所有權屬于外國或其政治分支的實體;(3)既非美國某州公民,亦非依照任何第三國法律設立的實體。因此,依據該條規定,對于外國的國有企業是否能夠被納入“國家”的范疇應考察其是否屬于外國的代理機構或媒介的三項條件。對于第一項和第三項條件,大多數依據外國法成立的國有企業都較容易滿足。對于我國的國有企業而言,其是依據我國法律規定設立的獨立法人,能夠以自己名義參與訴訟。《公司法》《企業國有資產法》等法律規定也主張政企分開,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因此,我國國有企業是否滿足“國家”的條件,主要在于對第1603 條的第二項規定的考察。
對于第二項條件,美國最高法院在Dole Food Co.v.Patrickson 案中進行了具體解釋。法院認為“外國的代理機構或媒介”必須是外國必須擁有該公司大部分股權或所有權,相反,通過一個或多個公司與國家分開,作為間接子公司不滿足第二項條件。⑥對于我國的國有企業而言,其在種類上包括了由國資委或地方政府投資控股的企業,還包括了政府參股的公司以及政府直接控股公司的子公司等。對于國資委和地方政府直接控股的公司而言,其大多數股份由政府持有而享有《外國主權豁免法》中的國家管轄豁免的主體資格。例如,在2015 年中航集團的案件中,美國聯邦第六巡回上訴法院推定中航集團具有管轄豁免資格;⑦在2016 年中國建材集團案件中,美國法院推定中建集團享有管轄豁免,并且因為并沒有在美國從事行業活動不屬于商業行為的例外,最終認定法院對于中國建材集團沒有管轄權。⑧而對于國有企業下的子公司,由于其與國家政權間不存在直接的控股關系,因而不具有主權豁免的主體資格。例如在Ocean Line Holdings Ltd.v.China Nat.Chartering Corp. 中,美國法院認為中國租船公司屬于中國外運長航集團的子公司,其股份并非由國家直接持有,因此其不能被認為屬于代理機構或媒介。
2.2.2 法院因存在例外而具有管轄權
然而,雖然國有企業經過初步證明能夠被預先推定具有國家豁免資格,但至于企業的國家豁免主張最終是否能得到支持,還應判斷其行為是否屬于豁免例外的情形。實踐中,原告主要是通過證明國有企業存在商業行為的例外而主張其不享有國家主權豁免。正如美國法院在1992 年Republic of Argentina v.Weltover,Inc.中提到商業行為例外是FSIA 最重要的一項例外。它是《外國主權豁免法》對外國主權豁免的限制性理論進行編纂的核心。在2003 年的Grabar 案中,美國法院認為本案中沒有存在商業例外以及放棄豁免的情形,因此,中國遠洋石油公司仍具有主權豁免。在2007 年Orient Mineral Co.v.Bank of China 案中,法院認為毫無疑問中國銀行屬于外國的代理機構或媒介,在1998 年Voest-Alpine Trading USA Corp.v.Bank of China 中也是如此認定的,因此中國銀行已經初步享有豁免權。但是銀行在中國的商業行為對美國產生了直接影響,即從Wil-Bao 的賬戶向Saren Gaowa 在猶他州銀行賬戶轉款40 萬美元,該行為屬于商業例外行為。基于此,中國銀行并不享有主權豁免。
總結而言,在依據《外國主權豁免法》的背景下,國有企業如果能夠證明其是依據中國法成立具有獨立的法律人格,能夠以自己的名義參與訴訟,并且由政府直接控股的國有企業,在實踐中能夠被預先推定國有企業享有管轄豁免,而國有企業的子公司理論上不享有國家豁免主體地位。但至于最終是否能真正免除法院對事項的管轄,還需要考察其行為是否屬于例外情況。
3 國有企業海外訴訟中主張國家豁免的影響
3.1 國家并不必然對國有企業的行為承擔責任
國有企業與國家存在緊密聯系,國有企業在國家豁免問題上可能帶來的影響一方面體現在國家對國有企業行為的責任問題上。具體而言,即國家是否需要對國有企業的行為負責。由于國有企業獨立于政府的法律人格,在通常情況下國家的管轄豁免不會因國有企業的豁免受到影響。這在《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第10 條的規定中就有體現。根據第10條,國有企業卷入與商業交易有關的訴訟時,并不會對國家的管轄豁免構成影響。因此,此時國家并不需要對國有企業的行為承擔連帶責任。但公約草案評注中對第10 條第3 款進行了補充,即當涉及“掀開公司面紗”的問題時,國家仍可能與企業共同承擔連帶責任。
3.2“國有企業國家化”的潛在風險
2014 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對Republic of Argentina v. NML Capital Ltd.一案的判決中,通過判例形式在執行豁免相關問題上的修改。這對于對國有企業在訴訟中主張國家豁免抗辯的問題也產生重要影響。在案件中,法院認為由于《外國主權豁免法對于查詢豁免沒有明確的規定,根據規定對于外國財產的查詢問題需要適用《民事訴訟規則》的規定。一旦適用該法的規定,法院就有權頒布寬泛的判決查詢令,而過于寬泛的查詢令可能會導致披露一些在任何國家都必然享有豁免的財產。但美國最高法院認為查詢令只是為了解財產的屬性,并不必然導致財產被執行,查詢和執行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財產是否能被執行需要另行考量。換句話說,如果不通過查詢令的方式,無法了解財產的位置和屬性,則將無法判斷財產能否依豁免法被執行。由此可見,基于美國最高法院的理解,雖然依據《外國主權豁免法》的規定,外國國家財產享有執行豁免,但這并沒有免除這些財產基于寬泛的查詢令,在判決后被查詢的可能。
依據該規定,如果在涉及國有企業的海外訴訟中,該國有企業滿足“外國的代理機構或媒介”的地位,并且不存在例外情況而成功主張國家管轄豁免,就會出現“國有企業國家化”⑨的情況。即如果一國企業提出對于國家的訴訟,并且出現需要承擔責任的情況時,其在美國境內經營的國有企業財產就會面臨被查詢的可能,這會使得國有企業的財產以及國家機密面臨被披露的危險,對于企業財產安全以及國家安全造成損害。由此可見,在有限豁免原則下,國有企業在海外訴訟中主張國家豁免,在其之后的經營中就存在“國有企業國家化”的隱患,從而使得財產安全和國家財產處于潛在的風險中。
對于我國而言,雖然我國在2005 年簽署了《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開始了有限豁免的立法進程,但在剛果(金)案中,我國又再次重申了絕對豁免的立場,并且我國一貫主張國有企業不享有國家豁免主體資格。然而,實踐中仍然有很多國有企業在訴訟中主張國家豁免,并獲得了法院的支持。雖然這些企業一時免于責任的承擔,但長此以往可能會我國國有企業在美國的競爭環境造成影響。例如在美中經濟安全評估委員會在其2016 年6 月的《貿易投資監測月報》中,重點關注了涉及中航工業和中國建材集團在美國主張主權豁免的問題,并對中國國有企業利用FSIA 獲得不公平競爭優勢的問題表達了擔憂⑩。與此同時,即使企業主張國家管轄豁免,也可能因為商業行為的例外被否定,此時企業不但要面臨承擔責任的風險,也會引起交易方的反感,影響企業在海外的形象。如果企業在訴訟中頻繁主張國家管轄豁免免于責任的承擔,長此以往,會引起企業合作方的擔憂,對今后海外企業的經營和業務的擴展造成不利影響,最終不利于維護國家的海外利益。
4 對于我國國有企業的啟示
4.1 積極維護自身權益,加強企業的合規經營
對于國有企業在海外訴訟中的國家豁免問題,首先,不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不論企業是否享有國家豁免的主體資格,在海外經營的中資企業面對訴訟時,企業自身首先還是要積極應訴,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在Walters 案中,因為中國北方工業公司和中國政府在收到傳票后一直未出庭,美國密蘇里西區地區法院1996 年作出缺席判決,要求中國政府賠償1000 萬美元。原告后來多次申請強制執行,相關部門為此付出巨大的資源投入去處理后續問題,代價是巨大的⑩。其次,在限制豁免的趨勢下,國有企業并不當然就享有國家豁免主體資格,其仍需對自己是依據國內法律規定設立的獨立法人并由政府享有大部分股權承擔證明責任。因此,在訴訟中國有企業仍應認真承擔證明責任。最后,在訴訟中取得的國家豁免資格,國有企業仍然可以通過明示或默示的方式予以放棄。即使如前文所述,國有企業在訴訟中主張主權豁免會在企業海外長久的經營等方面產生負面影響,但如果能夠通過主張主權豁免符合自身利益訴求,或是能夠在訴訟中取得優勢,不妨可以選擇主張。但歸根到底,需要建立在維護企業自身海外安全以及國家海外利益的基礎上。
與此同時,從根源上看國有企業在訴訟中的國家豁免問題與國有企業海外涉訴息息相關。因而,還需要從根本上加強企業海外的合規經營。這里的企業不僅僅是指被卷入海外訴訟風險的企業,而是指整個“走出去”的企業群體都應重視和提高自身合法合規經營的能力。而這需要國家、行業協會以及企業自身的共同作用。首先,發揮國家、行業協會等對國有企業海外經營的監督和引導作用。在2018 年12 月,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外交部等多個部門印發了《企業境外經營合規管理指引》。其目的在于規范海外企業的經營行為,通過對照《合規指引》,企業能夠結合自身實際,來加強境外經營相關合規制度建設,不斷提高合規管理水平,使其經營符合國際條約、東道國法律法規等的要求。其次,企業加強自我監督,加強對營業地相關法律法規的學習認識,促進企業的責任意識以及國際競爭力的提高,保障企業經營在海外合法合規。
4.2 加快國家豁免立法進程,促進相關國內法的完善
在國家層面上,一方面要修改完善相關法律規定,明確國有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以及其法律地位等核心問題。應當認識到國有企業對自己的財產享有所有權,國家僅作為出資人享有股權,國有企業在承擔法律責任的時候不能以國家利益為借口逃避責任11。與此同時,也要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的進程促進政企分開,從根本上體現轉變國企與政府關系,改善國企應對海外訴訟時的問題。
另一方面針對于國家豁免問題。目前我國有關國家豁免的立法尚處屬空白,不能為我國當事人對外國有關主體提起訴訟提供依據。除此之外,我國在國家豁免所采取的原則也需要通過法律來予以明確,消除實踐與理論不一致的情況。目前而言,我國堅持的是絕對豁免的立場,而絕對豁免原則導致的不利情況就是中國對于外國國家、國家所有的法人、財產沒有任何有效的控制。反之,中國及其國有企業、國有財產卻極有可能在其他采取限制豁免的國家被訴,在被訴的時候我們就很難以絕對豁免的主張獲得該國法院的支持,因為是否賦予外國國家、國有法人、國有財產以豁免完全是該國自身決定的12。而如果采取限制豁免的立場,我國法院就具有了涉及其他國家、國有財產的管轄可能,就可以在互惠的基礎上確定豁免的條件與方式。這種互惠的基礎就能夠使得我國有權對外國財產進行制約,以此能夠在國際交往中更好地維護我國國有企業在海外利益的維護。由此可見,從更好地保障海外企業的經營,維護我國海外利益的角度出發,限制豁免原則更有利于維護國家利益。
總之,應加快我國關于國家及其財產豁免的立法進程,推動限制豁免原則在我國的發展,這不僅能夠在法律層面規定和表明我國對此問題的立場,為我國法院在處理外國國家豁免問題的時候提供足夠的法律支撐,更能夠從專門立法中看出我們國家對于國家豁免的立場,為我國國有企業在國外的訴訟提供法律支撐。
注釋
①梁一新.論國有企業主權豁免資格:以美國FSIA、英國SIA和UN公約為視角[J].比較法研究,2017(1):82-94.
②趙海樂.論國有企業“政府權力”認定的同源異流:國家責任、國家豁免與反補貼實踐比較研究[J].人大法律評論,2015(2):348-375.
③UN,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on the work of its forty-third session.
④齊靜.中國國家管轄豁免立法具體問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⑤王蕾凡.美國國家豁免法中“恐怖主義例外”的立法及司法實踐評析[J].環球法律評論,2017(1):168-178.⑥Dole Food Co.v.Patrickson,538 U.S.468(2003).
⑦Global Tech., Inc.v.Yubei(Xinxiang) Power Steering Sys.Co.,807 F.3d 806(6th Cir. 2015).
⑧Chinese-Manufactured Drywall Products Liability Litigation,168 F.Supp.3d 921(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E.D.Louisiana,2016).
⑨紀林繁.不得援引國家豁免的商業交易訴訟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⑩李慶明.中國國家財產在美國的執行豁免:以沃爾斯特夫婦訴中國工商銀行為例[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4):60-65.
11崔航.國家豁免中的國有企業問題研究[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3):61-66.
12何志鵬.主權豁免的中國立場[J].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5(03):6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