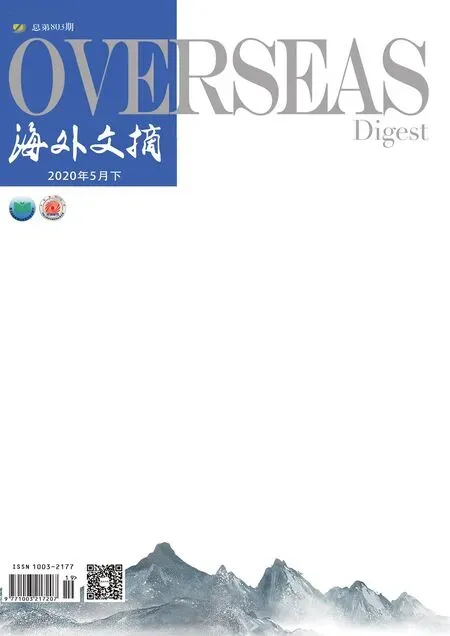從文化形態史觀探析中國翻譯史上的第一次翻譯高潮
張鳳
(青島大學,山東青島 266701)
1 文化形態史觀
文化形態史觀是在20 世紀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種歷史理論。這是由德國歷史學家斯賓格勒(Oswald A.G.Spengler,1880—1936)最先提出,隨后由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深入發展的一套關于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的宏觀分析理論。其中湯比因在批判繼承基礎上形成的文化形態史理論,影響更為深遠。他認為應該對人類進行全方面的研究,并在其著作《歷史研究》提出了文明興衰的四階段論,即每一種文明都要經歷起源、生長、衰落和解體四個階段。
西方的形態史觀對中國史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于20 世紀40 年代出現了以林同濟、雷海宗為代表的“戰國策派”。雷海宗認為中國歷史可以分為兩大周,在他看來,外來文化的融入促進了中華文化的再生,并進一步做出了比喻:“我們可說文化如花,其他的文化都是草本,花一度開放,即告凋死;中國似為木本花,今年開放,明年可重開,若善自培植,可以無限地延長生命”。[1]可以看出,雷海宗強調了文明的可延續性,結合其對中華文明的解讀,文明延續性的關鍵是要接受外來因子,不斷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2 文化形態史觀與翻譯
2.1 文化與翻譯的關系
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身是一種符號或者象征系統,蘊含了豐富的文化內涵。而翻譯則是語言間的轉換過程,是促進文化間交流的過程。文化想要廣泛傳播,翻譯是重要的傳播介質。而翻譯理論家一直將翻譯的研究重點放在語言層面,直到20 世紀70 年代開始,翻譯理論家開始關注翻譯中的文化因素,而隨著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的發展,出現了一門新的翻譯研究學派——翻譯文化派。巴斯奈特和勒弗維爾(Bassnett & Lefevere)提出要從廣闊的歷史文化角度研究翻譯問題,1990 年,二人合著出版了《翻譯、歷史與文化》一書,正式提出了“翻譯的文化轉向”的概念。翻譯的文化轉向為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維度,意義十分重大。
柏默(Palmer)說:“語言的歷史和文化的歷史是相輔而行的,它們可以互相協助和啟發。”[2]鑒于翻譯是語言間的轉換過程,可以得出結論,翻譯和文化之間也是互動關系。一方面,翻譯作為對外傳播文化和引進外來文化的重要途徑,可以豐富民族語言文化,促進本民族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文化又制約著翻譯過程:民族心理開放程度越高、對文化的需求越高,那么翻譯活動越容易開展;雖然文化之間存有共性,但是不同民族間的同一文化意義卻大相徑庭,這就對譯者的翻譯活動造成了阻礙。這種文化和翻譯之間的互動關系,對譯者提出了要求,譯者在翻譯的時候,必須要深刻理解兩種文化的深厚內涵,更要注重語言表達,同時要克服主觀因素,盡量減少譯者自身因素對翻譯結果產生的影響。
2.2 基于文化形態史觀的翻譯價值
基于文化形態史觀,談翻譯與文化的關系,季羨林曾表示:“倘若拿河流來作比,中華文化這一條長河,有水滿的時候,也有水少的時候,但卻從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數大大小小是頗多的。最大的有兩次,一次是從印度來的水,一次是從西方來的水。而這兩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中華文化之所以能長葆青春,萬應靈藥就是翻譯。翻譯之為用大矣哉!”[3]由此,可以看出,任何一種文化,不管曾經取得了多么光輝燦爛的成就,都不可避免地要與外來文化相互交流,互通有無才能得以無限發展。新鮮的外來文化的注入過程中,翻譯的作用至關重要,翻譯促進了文化的空間發展,豐富了民族文化的內涵。
許鈞曾提出:“翻譯具有社會性、文化性、符號轉換性、創造性和歷史性這五方面的根本屬性,這五個方面既是對翻譯的基本理解,也是對翻譯價值的基本認識。”[4]翻譯的價值是多方面的,但不管從哪個方面研究,翻譯終歸是與文化緊密相連。文化形態史觀強調將文化看做一個有機體,而作為一個有機體,新陳代謝是生命活動最主要的形式,如果新陳代謝停止了那么有機體也將不復存在。也就是說,文化要不斷與外來文化交流,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的營養部分,這樣本民族文化才能不斷進步和實現自我革新。而翻譯就是促成文化新陳代謝和自我革新的最主要的途徑,這就是翻譯的文化價值。
3 中國翻譯發展史
語言作為文化的一部分,翻譯活動與文化息息相關,翻譯史其實就是文化史。中國漫長的翻譯發展史蘊含了各民族文化之間的文化交流史。馬祖毅在其著作《中國翻譯簡史》中提到:“我國是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國內各民族,也包括在歷史上已經融合一起的民族,都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創造、繁榮和發展作出過自己的貢獻。而在創造,繁榮和發展中華民族文化的過程中,各民族的翻譯活動也起過一定的作用。因此,在撰寫中國翻譯史時,便不能單純著眼于漢語的翻譯活動。”[5]按照馬祖毅的觀點,中國的翻譯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時期,并且周代便有清楚的口譯記載歷史。在隨后漫長的中華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國內各民族之間相互交流,深入融合,翻譯歷史不可湮滅。
對于中國歷史上的主要翻譯階段的劃分,翻譯界有多種觀點,本篇論文采用了馬祖毅先生的觀點,他在《中國翻譯簡史》中指出:“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三次翻譯高潮:東漢至唐宋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和鴉片戰爭至“五四”的西學翻譯。”[5]這種劃分方式,可以更好地從文化形態史觀的角度分析翻譯與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本論文著重分析第一次翻譯高潮。
4 第一次翻譯高潮
東漢時期佛經傳入我國,唐朝時佛經翻譯達到鼎盛于北宋進入衰落期,而到了元代幾乎沒有任何發展。佛經一開始傳入中國時并沒有引起強烈反映,因為梵文并不能被大眾接受,必須譯成漢語才能被漢人閱讀、理解。如此一來便誕生了第一批佛經翻譯家,最早的有迦葉摩騰、竺法蘭、安世高、支謙等人,后來涌現出了有道安、鳩摩羅、玄奘等著名的佛經翻譯大師。
佛經翻譯在中國得以盛行更多的是得益于當時的社會環境。東漢時期,政治動蕩,社會混亂,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急需借助宗教抒發內心的愁苦之情,以求得到精神安慰。而東漢統治者看到了這一點,利用百姓對佛教的崇拜之情以鞏固其統治,這為佛經翻譯的發展做了鋪墊。在統治者的大力支持以及諸多佛經翻譯大師的努力下,越來越多的人接觸到佛教文化,而佛教文化也給中國文化帶了深遠的影響。
佛經的譯入,帶來了漢語語言上的變化,影響至今,例如:漢語詞匯增多,出現了許多“眾生“浮屠”“因果報應”等佛教用語表達;帶來了漢語的音韻和詩歌音律的變化等等。前面提到過的佛經翻譯家都秉承了自己的翻譯理論,在翻譯的時候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和處理方法,例如:支謙主張“曲得圣意,辭旨文雅”,翻譯時多采用合譯和譯注的方式;玄奘主張忠實于原文風格,并提出了“五不翻”的音譯規則等等。這些翻譯理論對后世的佛經翻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經過1000 多年的發展,佛經翻譯極大了促進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豐富了中華文化,同時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哲學思想和藝術繪畫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佛教在中國的地位也日益根深蒂固。中國文化中第一次注入了外來文化,就已泛起如此巨大的波瀾。
5 結語
從這第一次翻譯高潮中得以窺見,翻譯是文化交流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化形態史觀將文化看做是一個依靠新陳代謝的有機體,而外來文化的注入是本民族文化實現自我革新的重要步驟。翻譯引進新思想、新觀念、新技術,開闊人們的視角,豐富了語言表達,從而為文化注入活力,推動社會文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