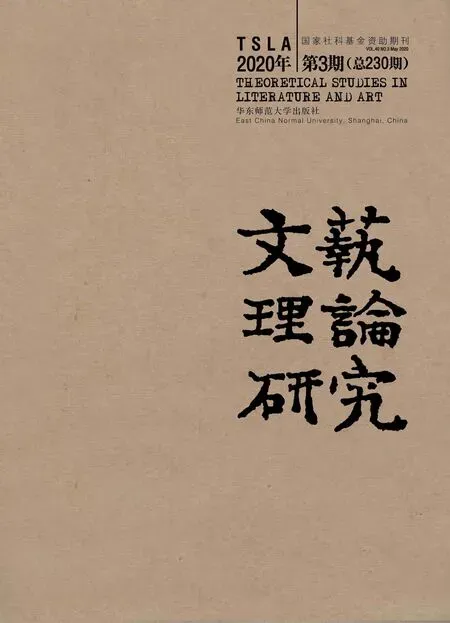“地方”終結了嗎: 空間理論的辯證思考
朱 軍
人類的美學經驗離不開“地理感”。“地理感”因“人”之具有評價選擇機能而對環境有不同的“感的回應”,同時任何回應也都具有理性意義、價值意義(潘桂成8)。“空間”(space)與“地方”(place)是人類地理感的來源,也是文化地理學和空間研究的邏輯起點。無論是文化生態主義(韋伯、西美爾、斯賓格勒、芝加哥學派等)、人本主義(段義孚、雷爾夫等)還是馬克思主義(列斐伏爾、卡斯特爾、大衛·哈維等)立場的空間研究,“空間”往往是自由、開闊與全球化的符號,而“地方”是封閉、寧靜與本土化的象征。全球化時代地方感的重構集中體現了“空間”與“地方”的辯證關系,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空間視域下的地方思想,試圖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雙重背景中,有針對性地回應全球化的諸多文化癥候。自列斐伏爾以來,都市往往被想象為一個濃縮的全球或世界,同時世界被想象為一個都市(Shields141)。面對“逆全球化思潮”,馬克思主義對于城市空間社會性、辯證性、開放性的強調及其實踐,具有強烈的現實指導和糾偏的意義。
一、 地方的終結
全球化時代,地球是平的。那種李帕德筆下“內在于一個人生命地圖里的經緯”(Lippard7)消逝了,“地方”看起來越來越呈現出雷同的面貌,社區、購物中心、商店、旅館差不多同一個模樣,地方感變得非常淡漠,“地方”正在加速被侵蝕,這為全球化時代的人類提出一個嚴峻的質問:“地方”是否即將終結?
雷爾夫《地方與無地方性》表達出人文地理學家深深的憂慮,這種憂慮來自全球化時代地方“本真性”的消逝。海德格爾從“棲居”發展出“本真性”的概念,“本真性”意味著“作為一種存在形式,真實性乃是替自己的存在負責的完整體認和接納”(Relph78)。這種對“地方”的完整體認,往往被稱為“圈內人”意識,即內在于一個地方,意味著歸屬與認同,你越深入內在,地方認同感就越強烈,相反,“圈外人”意識則意味著與地方的疏離,是一種存在的外部性。
現代人為“無地方性”所纏繞,普遍淪為存在的“圈外人”。現代交通、媒體、大眾文化及其制造的“流動性”,鼓舞了“無地方性”,進而傳播了對于“地方”的不真實態度,削弱了地方認同,地方不僅看起來很像,而且感覺也雷同,提供了同樣枯燥乏味的經驗可能性。譬如高速公路、鐵路、機場橫越并強加于地景之上,它們“從每個地方出發,卻不通往任何地方”(Relph90),僅僅促成人群大量移動,搬家變得家常便飯,家園不再有歸屬感。再譬如城市建設的日益主題公園化、奇觀化、博物館化和未來化,極大助長了“無地方性”的擴散:
“迪斯尼化”的場所是一些荒唐的、合成性的地方,它將歷史、神話、現實和幻想進行了超現實的組合,這些景觀與某一特定的地理環境沒有什么關系。(20)
迪斯尼是“無地方性”的代表,艾柯、哈維、詹姆遜、鮑德里亞、索亞、迪爾、段義孚、雷爾夫、柏林特等人多有論述。迪斯尼集中體現了后現代文化中的拼貼、復制特質,對全球各種地域和歷史文化的模仿呈現為“主題化”的景觀美學,其中似乎表達出對地方性及其過往的依戀,甚至流露出一種感傷的現代主義情調,但卻是超真實的“仿真圖像”,本質上架空了地方性,或者說體現了一種沒有歸屬感、虛偽的地方性美學。它們是外地人或“他者”的創作,并不是本土文化真實的表現,其象征意義也是“面向他者”的。用雷爾夫的話說,迪斯尼是一種“無地方”(placeless)的地方:
一種欺騙的建構展開,這種欺騙盡管擺出一副熟悉的幸福面容,卻在不斷地使自己遠離(它周圍的城市)大多數基本的現實性。這一城市的建筑幾乎是純粹符號性的主題公園建筑,玩弄著嫁接意義的符號游戲。無論此類設計代表著一般的史實性還是一般的現代性,都是基于與廣告相同的演繹,即純粹的可想象性這一觀點。(Sorkinxiv)
迪斯尼美學在全球的風行,帶來了城市的主題公園化。伴隨著上世紀50年代“建筑波普”運動,強調“表演和奇觀”的“布景”景觀模式從起先的主題公園、娛樂總會、購物中心,逐漸向城市真實生活的街道、廣場、公園、新城等各個層面滲透,從波士頓濱水地區擴展到巴爾的摩、紐約、舊金山、倫敦、悉尼港區、拉斯維加斯乃至上海的環球港、泰晤士小鎮等等。在哈貝馬斯看來,消費主義的興起、媒體的商業化、媒體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勾結,造成了公共空間的衰弱。城市的迪斯尼化“從而可以營造這樣的地方: 它提供了一種身為‘公共’的一部分的感覺,但事實上它們卻是經過校準和煞費苦心編制的制造利潤的機器”(艾倫·萊瑟姆164),同時它帶來了千城一面的“普世一律的城市主義”(urbanism of universal equivalence)(Sorkin217)。
哈貝馬斯哀嘆公共空間的衰弱,但他把原因歸結為內在的消費主義美學的崛起,雷爾夫則強調存在的“圈內人”性質,但他認為“地方”正變為“他者導向”。事實上,“無地方性”的美學不能簡單認為是外部資本積累需求,也不能歸結為對內在歸屬感的無望追逐,而是內外雙重原因的結果。
不可忽視的是,媒介與技術的無界性也構成了對地理空間的消蝕,橫越地球的短暫連接變得越來越像,移動性和大眾文化導致了非理性、膚淺的地理景觀和空間美學。后現代美學狀況讓都市人普遍處于無家可歸狀態,梅羅維茨《無地感》指出技術會重組社會環境,這會最終降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人類迫切需要思考如何立足于“消失的地方”,梅羅維茨說:
現在,你可以在不親歷現場的情況下成為一場社會表演的觀眾;你可以不與別人在同一個地點會面的情況下與其“直接”交流。其結果是,那些曾經將社會分為許多截然不同的互動空間環境的物理結構,其社會重要性已大為降低。(Meyrowitzvii)
對于“地方”是否終結的探討似乎又回到海德格爾有關棲居本質之思考。面對人的人類性和物的物性在全球化空間中的消解,商品、市場和媒介制造了普遍的“無距離”狀態,帶來了自我建構和身份認同的危機。在無數歷史和文學作品中,“地方”曾經作為自我存在的隱喻,而今自我存在的形成難以依賴內生的、剝離了流動性與距離體驗的地方,這造成了普遍的無根基狀態——人的無家可歸狀態。
二、 “地方越來越重要”: 地方的多重變形與再結構
海德格爾的無地可棲顯然太過“多愁善感”了,因為過度地去資本化和去市場化,只能落入狹隘的地方主義信仰,忽視了現實的經濟與資本流動對建構現代性地方的社會作用(BetweenSpaceandTime418-34)。就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而言,外在的社會關系建構與內在的本真性追求之間并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相反,過度強調內在的、本真的、感官的體驗,會導致“地方”演繹為意識形態的想象,因為這會掩蓋地方和世界的物質和社會聯系,進而模糊社會聯系中的權力關系。
因此,哈維特別強調“地方越來越重要而非越來越不重要”(Justice296-98)。“地方”的重構一直并且持續地內在于資本積累之政治經濟學: 其一,1970年代以來,時空關系被徹底重構,并且改變了“地方”在資本積累的全球樣態中的相對位置。底特律、謝菲爾德、利物浦、里爾等城市被拋棄,地方的安全普遍受到威脅,造成了人們擔心“地方”的一般意義以及自身所在地方的特殊意義被消解。其二,交通和通訊落后于時代,由于距離的摩擦作用,地方免于競爭,擁有一種高水平壟斷力量,但是如今地理流動更加容易,地方固有的壟斷權力大大削弱。其三,那些扎根于一個地方的人強烈意識到,他們正在與其他地方競爭高度流動的資本,這迫使他們出售“地方”,運用各種廣告和形象包裝來提高本土的可區別性。其四,近20年,吸收過剩資本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其中相當大部分陷入投機性地方建設。養老和旅游勝地、新生活社區、文化中心、特色城鎮、休閑城市、主題公園和主題公園化的城市投資變得愈發積極,這些集中于消費景觀的投資,意在出售地方形象,爭奪文化和象征資本,恢復消費的吸引力以及本土傳統文化。不遺余力營造的地方形象及其特定品質往往呈現出“奇觀與戲劇性的組合”(TheConditionofPostmodernity92-93),但這一競爭過程也呈現出負面效應,創造了同質的復制品,也就是“無地方”的地方。
“地方”由此終結了嗎?在哈維對海德格爾的反駁中,“地方”出現了諸多變形,海德格爾和雷爾夫現象學視野下的“無地方”具有負面的道德意涵,而“地方”并沒有真正終結,而是變幻為各種“非地方”(non-places)或者“類地方”(almost-places)。鮑德里亞、哈維、歐莒、史瑞夫特等人的解讀更強調地方與移動、瞬間、短暫相連,是將各種移動性安置于彼此的關系之中。歐莒與鮑德里亞一樣認同,對于旅行的迷戀,已經將“非地方”理解為在世存在的方式,后現代社會有別于傳統社會的重要特征便是新的移動的思考方式,作為“非地方”的旅行者空間似乎比有根的地方更讓新生代有歸屬感。史瑞夫特進一步認為,這種移動性應該被看作一種新的“感覺結構”:
在之中(in-between)的世界里,“地方”是什么?簡單的回答是——折衷: 永遠處于發聲狀態,介于不同地址之間,總是推遲不定,充滿移動、速度和流通的蹤跡,我們可能讀過“類地方”的描述[……]按照鮑德里亞的術語,這是第三級的擬像世界,入侵的虛假地方終于完全消除了“地方”。或者,“地方”是策略性的裝置,捕獲交通的固定地址。或者,最后,我們可能將它們解讀為各種空間、時間和速度實踐的框架。(Thrift212-13)
人本主義地理學將“地方”看作感覺結構,馬克思主義者將“地方”看作社會結構,他們都試圖在時空壓縮的全球化空間中重新把握“地方”。不過列斐伏爾、德波等人認為,無論借助旅行獲取地方經驗,還是借助圖像走向日常經驗,重新獲得“地方感”的努力都是徒勞的。譬如現代旅游名城疏離了家鄉和歸屬地,而是赤裸透明的符號。拉斯維加斯和迪斯尼制造的巴黎、羅馬的幻境,成為孤零零的景點、盆景,變成了僅供觀看的圖像,世界萬物也不再神圣,而是工業體系和市場體系所控制的資源、圖像和符號。城市化的隔離進一步制造了集體性的孤獨,隨著城市公共性的衰落,景觀和圖像開始占據公共性退卻后的空間,在無所不在占統治性地位的圖像中,“景觀信息填滿了孤獨,而景觀恰好從這一孤獨中獲取了它們全部的力量”(Debord172)。
“消失的地方感”意味著媒體傳播促成了空間實際距離的瓦解,單向度的信息流創造了馬爾庫塞所謂“單向度的人”,導致了文化認同的全球同質化。當然這一觀點也遭到了一些學者的批評。譬如庫爾德里和麥卡錫認為,正在顯現的畫面不是“地方”的瓦解——實際上,由于媒體將我們聯系在一起,所以我們前往遠方旅行的理由是增加而非減少了——而且我們與其他地方和當事人的互動被更加細致地整合進了我們的日常經驗流中(Couldry9)。
也就是說,媒體將世界聯系在一起,可以增加“規模效應”,地方與全球化、消費與空間分布之間的差異,會將地方經驗重新整合進我們的日常經驗流之中。“我們或可稱之為經驗性非地方的東西不斷擴增,乃是當代世界的特色。流通空間(高速公路、航空)、消費(百貨公司、超級市場)與傳播(電話、傳真、電視、網絡),在當今全球占據了更多空間。它們使大家不必生活在一起,就可以共存或同居于空間。”(Augé110)庫爾德里《加冕街》拍攝地的參觀者研究也試圖說明,觀眾在媒介化空間中扮演關鍵因素,觀眾有可能走向圖像,或者讓圖像走向自己。重要的是要認識到觀眾借助媒體可以得到定位——在過去、未來和空間中的定位。
在后現代文化中,“地方”不再是固定的位置,從此意義上說,地方終結了,但是正如李帕德所言,“心理的地理有必要歸屬某處,這是普遍疏離的解藥”(Lippard20),恰恰在普遍的“非地方”和“無地方”的孤獨情境中,“地方”更加凸顯為人類互動的意義核心和彼此觀照的基礎領域。在社會空間結構的分析視野下,全球化強化了資本主義“抽象空間”的擴張,也讓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得以彰顯,促使人們回歸“保衛地方”的美學實踐,甚至激發出一種威廉斯式地方性的“戰斗的特殊主義”。換言之,“地方”并未真正消逝,而是具有了多重面貌,并且因其推動了后現代都市感覺結構的轉型,顯得越來越重要。
三、 “退回地方”: 對一種敵意立場的批判
“空間”原本與開闊性、自由性聯系在一起,而“地方”多與歸屬感、封閉性聯系在一起。馬克思主義和人本主義地理研究都認同“空間”和“地方”內涵的辯證性。人本主義地理學雖更強調“地方”的庇護性和家園感,但同樣贊同神學家伊曼紐·史威登堡所言,“天使愈多的地方,愈多自由空間”。天使本質并不占有空間,而空間因天使的無私而被創造。相反,人群的擁擠常成為我們產生挫敗感的重要原因,特別是西方工業社會的工人階級家庭常因為擁擠而喪失隱私權,乃至生存權益被剝奪,盡管擁擠的空間也代表了對地方性的親密、溫暖的偏好。
里爾克《朝圣書》“機器隆隆效人欲,未見送來真幸福;金屬懷著鄉愁病,生機渺渺無處尋。欲離錢幣和齒輪,離開工廠和金庫;回歸敞開山脈中,山脈納之將門閉”,為海德格爾及其追隨者提供了重新想象“地方”的路徑。(海德格爾297—98)從現代性的批判激發出人們回歸地方、家鄉的渴望,這是空間研究的一條重要理論路線圖。哈維甚至追溯到莫爾《烏托邦》中神話、完美小鎮所代表的黃金時代,在技術成為“世界新主人”的時代“離開工廠和金庫”,意味著對靜態精神秩序以及和諧社會模式的懷舊。
在全球化時代,空間與技術的全球化聯系更緊密,然而“機器隆隆效人欲,未見送來真幸福”,“地方”也可能退行為一種“本土”的信仰。曼紐·卡斯特爾在《城市問題》中批評道:“有關‘都市社會’的著述正是直接建基于神話的基礎上,并反過來又為現代性的意識形態提供了關鍵詞,種族中心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合二為一了。”(Castell83)此言隱藏著新馬克思主義城市學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對列斐伏爾尖刻的批判,在卡斯特爾看來,不論是作為“空間”、整體的、全球化的“都市文化”還是作為“地方”、差異的、區域性的亞文化,都既不是一個概念也不是一種理論,而可能淪為一個虛構出來的神話、一種意識形態的流行敘事,列斐伏爾“作為現代化進程的真正頂峰‘都市社會’”同樣潛藏著地方性的種族中心主義和空間性(全球性)的自由資本主義的合流。
究其緣由,“地方”之所以獲得圖騰般的共鳴,是因為其象征價值往往被過度征用。“地方”指向著日常、真實、有價的實踐領域,成為意義的地理源泉,在全球流動時代不斷編織的陌生化網絡中,緊緊抓住它至關重要(“回歸敞開山脈中”)。在風靡各地的“都市文藝復興計劃”中,“地方”再次成為吸引力的來源,譬如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館、倫敦的千禧穹頂、亞特蘭大的波特蘭中心,以及世界博覽會、奧林匹克運動會和世界杯,都成為推廣地方形象的資源。與此同時,地方的文化遺產也在重新被開掘,城市中心正在經歷重新“士紳化”,譬如倫敦考文特花園、圣地亞哥的煤氣燈區、波士頓的法尼爾廳地區,以及上海的新天地、武康路等地,這些“舊世界”中的歷史標記被重溫,人們試圖尋找過往的自豪感和歸屬感,懷念銘刻在地方深處的本真性和根源性。
對另一些人來說,“退回地方”代表一種防御性的做法: 拉起吊橋,緊閉城門,以抵御新的侵略(“山脈納之將門閉”)。按此解釋,“地方”是拒絕之所,是嘗試性地從進攻/差異中撤離。這是一個政治與文化上保守的安樂窩,一個日趨本質化的(且最終不可行的)作出反應的基地,它沒有表明正在運作的真實力量。譬如民族主義和區域性地方觀念的復活,其本質特征是鼓吹排他主義,肯定本土的特殊性具有土生土長、根基深厚的本真性。
哈維回到巴爾的摩,以吉爾福德(Guilford)作為地方研究的起點,原因在于這里正體現了“地方”從敞開到封閉的退化。吉爾福德曾經代表“最佳和最現代的城市規劃”,是20世紀初城市郊區化運動的產物,20年代這里已經形成了多種建筑風格混合而成的建筑和街區,開放式的設計沒有柵欄和圍墻,建筑分布在小公園中間寬大曲折的街道上,儼然新教徒權貴們僻靜的世外桃源。不過,隨著1960年代以來貧富分化的加劇,隔離墻開始興建,幾起兇殺案的曝光讓吉爾福德徹底變成了一個被門禁隔離、警衛森嚴的社區。當地《太陽報》將它命名為“可防御的空間”。盡管兇殺案最終證明是夫婦家人的自相殘殺,但對外來者“不受控制的空間性帶菌者”的刻板印象已經成形,空間的邊界固化為種族、貧富的界限。吉爾福德最終驗證了資本主義地方建構的政治經濟學。
“門禁化的地方”并非個案,而是全球化時代一種典型的空間意識形態。在個體層面,不同城市堅守另類生活風格的亞文化群體,利用“地方”來抵抗全球資本主義勢力;在民族國家乃至全球化層面,通過“地方”的再神圣化,地方主義信仰正在成為宗教和民族國家強化自我認同的手段。以英國工黨政府推動的千禧穹頂為代表,國家熱衷于投資紀念性的雄偉建筑,以穩固他們的權力和權威,從集體記憶中喚回榮耀,并將之投諸未來,這往往是資本主義換取救贖希望的唯一美學愿景——奠基于認識地方、根著于地方乃至獻身于地方。這一新自由主義經濟社會救贖自身的迫切需要,也導致“逆全球化”正呈現為地方信仰的回潮。
四、 全球地方感: 超越權力區隔化
如上對于“地方”的祈望和拒斥呈現出對立的美學立場,這通常是因為共享一種根深蒂固的假設:“地方”是封閉的、連貫的、完整的、本真的,像“家”一樣,是一個安息之所;“空間”則是多少原本被區域化的,通常總是被分割開來的。馬西《保衛空間》指出,“空間”與“地方”構成了一種敵意的立場,一種對于諸如抽象對日常等等二元理論層面的想象——“地方”是有意義的、生命的、日常的(8—10)。
圍繞“地方”的闡發既是空間研究的基礎,也與日常生活批判緊密勾連,是海德格爾、列斐伏爾、哈維等人思想的重要理論落腳點。問題的關鍵還在于:如何拋棄對“地方”偏執的理解并依然保留對特殊性和獨特性美學的欣賞?如何以一種更“進步的”方式重新想象地方(或本土性,或地區)?換言之,我們如何可能介入“本土”“地區”,而同時堅持國際主義?正是在這一語境中,不少空間論者都強調需要重建“全球地方感”——既胸懷天下又依戀地方的全新的后現代視野。
馬西提出“全球地方感”命題,起源于對哈維“時空壓縮”理論的批判。在她看來,“時空壓縮”的特性描述表達了濃厚的西方和殖民者觀點。譬如曾經熟悉的本地小街道,如今布滿一連串文化輸入品,通常的解釋認為時空的壓縮與文化的侵入由資本的行動所決定,但事實上,這也與性別、種族和文明優越論有關。通過對哈維和索亞的批判,馬西強調“新自由主義新父制”(Neoliberalism Neopatriarchy)不應該被空間研究所忽視。
因此,“全球地方感”需要重建理解空間與地方的“權力幾何學”——時空壓縮的權力幾何學。地方的封閉性和空間的流動性不應該對立起來,人群的復雜移動的過程充滿了權力,不僅是資本的議題,也牽涉無所不在的社會關系形式。
不要將“地方”想象成周圍有邊界的地區,而可以想象成社會關系與理解網絡中的連結勢態,但是這些關系、經驗和理解中,其實有很大的比例,是在一個比我們在那個時刻界定的地方還要大的尺度上建構出來的,不論這個地方是一條街,一個區域,甚至是一個大陸。而這么做,便容許地方感是外向的,覺察到與廣大世界的關聯,并以積極正面的方式整合了全球和地方。(Massey315-23)
“地方”不應該被權力區隔化,而應該被觀照為一個“社會關系星叢”,一種超越區域的連結勢態,它們匯聚在一地“會遇地方”。這將導向一種全球地方感——外向、進步和全球的地方感。其具備的特征包括: 一、“地方”絕不是靜止的,而是一個“過程”;二、“地方”是由外界定義的,不必要封閉地方的分割邊界;三、“地方”是多元認同和歷史的位置,因此充滿內在沖突;四、地方的互動界定了“地方”的獨特性,地方文化的特殊性被不斷再生產;五、“地方”是廣大社會關系本身,空間無法脫離社會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地方的建構亦將立足于社會-空間的再造。總之,“地方”是一種社會關系構造,其社會性和人與人的關系有關,不斷處于編碼和解碼、協商和爭議之中,并且具有激進的特質,承認身份和差異政治的重要性。
正是源于“地方”的上述特征,馬西定義的“地方”——吉爾本(Kilburun)與哈維定義的“地方”——吉爾福特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吉爾本位于倫敦市中心西北,這里張貼著紀念絕食抗議的海報,莫里斯在劇院上演著獨角戲,國家俱樂部安排沃爾夫的戲劇,在黑獅子劇院上演《芬尼根的守靈夜》,櫥窗展示著印度模特,溫布利圓形劇場舉辦著音樂會……這里有自己的性格,但絕對不是一種沒有縫隙、連貫一致的認同和單一的地方感。文化和美學的多元認同造就了此地和其他地方的關聯。
馬克思主義地方觀何以進步?因為享受一種美學化的差異——他們從人群中抽離,以多樣性為樂,擁有一種文化資本的獲得感,因為有能力欣賞差異而產生了自我價值感。列斐伏爾認為“都市革命”的歷史貢獻在于,城市創造了一種情境——都市情境。在那里,差異的事物一個接一個地產生且并不孤立地存在著,按照它們的差異性而存在。空間是冷漠的,但城市卻能把差異統一并連接起來。大都市呈現為一種合理性的譫妄——一種庸常的日常生活、科層體制、權力意志與詩性的瞬間、節慶、靈機、奇跡的結合體。劉懷玉以“詩創實踐、瞬間奇遇、欲望造反”總結都市情境美學譫妄與解放相疊合的特征(393)。
譬如蒙特利爾便是列斐伏爾的審美烏托邦,一個被情境化塑造的空間。每個地方變成多功能的、多價的、超功能的,并且伴隨著連續不斷的功能的轉換。這是一個大型的展覽化的地方,日常性被節慶所吸納,瞬間性的“剎那美”從變幻的地方中產生,身體、街道、空間向節奏化的詩性體驗敞開,都市因其華麗與奇跡而變得晶瑩剔透。陸揚指出:“‘奇跡’的要害在于將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事件陌生化,從而通過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批判,醞釀日常生活的革命。人必須首先變成‘日常的人’,然后才能變成‘完全的人’。”(陸揚66)在此意義上,美學精神可望治療現代理性獨斷、精神分裂、階級分化的城市病,而城市的建構應確定并傳達社會關系的本質: 源于或導致沖突的互惠性存在與差異的美學。
進而言之,單純而顯著的多樣性并不必然導致進步的地方感,而面向歷史的尋根沖動也不必然是反動的。“全球地方感”作為一種都市情境美學,希望超越權力的區隔化,將都市觀照為社會關系的星叢并重新結構為一個詩性的整體,這一都市情境美學的生命力在于: 在差異性中保持特殊性。
五、 辯證、開放的時空美學重構
當代馬克思主義空間辯證法強調靈機、奇跡及其代表的開放性,這正是列斐伏爾“三元空間辯證法”、卡斯特爾結構主義城市空間觀、哈維“時空(過程)辯證法”和“希望的空間”、索亞“第三空間”的共同理論訴求。其底蘊在于,現代工業城市的象征物將會讓位于未決性,這種未決性構成了對城市的不同理解。具體到“空間”與“地方”的辯證思考而言,列斐伏爾、哈維、馬西的空間美學“以馬克思、柏格森、海德格爾等現當代重要哲學家的思想為基礎”(Saldanha44),同時他們進一步致力于挑釁并批判海德格爾式的地方浪漫主義詩學,建構馬克思主義“更進步的”、開放的地方批判,一種新的全球化時代的空間辯證法。
值得注意的是,馬西“全球地方感”的直接靈感來源于約翰·萊希特,和列斐伏爾、情境主義者一樣,他們都渴望召喚一種驚奇——“不期而遇之上的不期而遇”——這正是波德萊爾一樣的浪蕩子所遭遇的那種驚奇。
浪蕩子的軌跡不引向任何地方,也不來自任何地方。它是一種沒有固定空間坐標的軌跡。簡言之,沒有任何的參照點以便對浪蕩子的未來做出預測。因為浪蕩子是一個沒有過去或未來、沒有同一性的實體: 一個偶然性和未決性的實體。(Lechte102-103)
依據對波德萊爾的重新詮釋,列斐伏爾、索亞、哈維、馬西引申出“空間靈機觀”,通過重申“普遍的形而上的不確定性”,意在對海德格爾的地方詩學展開挑戰和糾偏。海德格爾將空間重新構想為“地方”,從原理上為空間研究指出了正確的方向,但卻遇到了真正的難題: 海德格爾的地方信仰過于根深蒂固,很少向外部的相互關聯的東西敞開。當代馬克思主義空間研究者大多具有左派海德格爾主義者特質,他們也認同“都市首要的優先之事乃是讓人棲居”(LaRevolutionurbaine122),但他們不只堅持詩化、身體化的美學實踐和地方性棲居,而強調辯證、開放的社會空間實踐。譬如列斐伏爾使用“棲息”(habitat)而非“居有”(dwelling),哈維認為海德格爾的有機地方觀一定會導致民族主義、反移民、反都市化的不良傾向(張一兵29)。馬克思主義空間論者要求立足“都市化-民族國家-全球化”三位一體的整體視野展開社會空間實踐。
有關全球化地方的辯證時空構造還得益于巴赫金的啟發。“地方”是時間與空間的結合體,巴赫金曾經將眾生喧嘩、復雜多變的時空體賦予小說和語言的分析。巴赫金分析小說之“具體整體”在哈維看來便類似于“地方”,“地方”是“時間和空間指示器”,不僅“時間密集了,豐富了,變得在藝術上可見了”,同時“空間對時間、情節和歷史的運動變得敏感,并對其積極回應”,這就是“地方”在人類歷史地理學中得以構造的方式。文學想象總是從一個具體的地點出發,從具體到整體,從一隅到世界,“這是人類世界的一隅,濃縮在空間中的歷史時間”(Justice294)。“地方”因此得以超越一個純粹的、永恒的方位(position)和地點(location),而成為被“想象的”時空點,進而是制度化社會關系的構型、物質時間、權力運行以及話語策略,其中隱藏著全球化社會過程的認知地圖。哈維總結說:
最終,我把“地方”理解為整個社會生態過程時空動態之中那些相對的“永恒”所具有的內在的、異質的、辯證的和動態的構型。(294)
“地方”的辯證構造正是哈維轉向馬克思立場的重要標志,標志著空間研究轉向“過程”而非“物”的辯證法。借助對《資本論》的深刻領悟,空間研究旨在打破資本主義的物化景觀和意識,把開放性、流動性和異質性重新還給空間及其歷史,并嘗試在社會過程的動態諸關系中探索一個“可能的世界”。這一嘗試集中體現于哈維“從空間到地方,再回看”之中,意味著從全球尺度落腳于地方再返歸空間周而復始的現象學循環,這一意向性體驗過程不再單純賦予特殊地方尋根式的懷舊,而是從根源處追溯連接不同地方的社會關系,進而探尋“地方”如何被建構和體驗為物質的、生態的人造物,以及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地方”作為“過程辯證法”的凝聚物,呈現為部分與整體、歷史與未來、生成與永恒的相互構造,“可能的世界”也是辯證法的有機組成部分,“社會過程”最終決定了空間形式。
以“地方”及其社會過程時空動態的辯證思考為軸心,列斐伏爾、哈維等人作為“都市社會”的審美烏托邦,轉向以“地方(場所)精神”和空間正義為核心的差異地理學和生態批評,為馬克思主義的美學與文化理論開拓了唯物主義的空間維度,對當下各種形式的“審美主義”傾向有糾偏作用。(閻嘉)這一歷史-地理唯物主義視野下的都市美學實踐也塑造了“空間轉向”的基本旨趣,譬如讓·鮑德里亞以符號學解碼的方法闡釋超空間、類象與仿真之間的關系,居伊·德波圍繞巴黎經驗建構出心理地理學和情境主義美學,展現出地方性、切身性經驗對全球化抽象空間的批判力量。卡斯特爾以結構主義立場重新闡述了地方與媒介文化、亞文化、城市草根社會運動的關系,與哈維一樣,“時空壓縮”時代“流動性地方”的畸變與重塑是其關注重點。另外,索亞、馬西、迪爾等借助對“第三空間”和后現代地理學的深入描繪,強調開放、辯證姿態對待正義、自然、地方和傳統,一種文化和美學視野下的“全球地方感”具有強烈的當下指向。
結 語
總體而言,馬克思主義視野下的空間理論,主張“空間-地方”視野下辯證、開放的時空美學重構,推進了全球化時代社會空間的批判與實踐,因其對后現代都市狀況的針對性而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其一,對于“地方終結”的探討喚醒了對城市本土性與原真性美學的思考。“地方”既是具體的居住地和家鄉,更是抽象的、先驗的、超越的存在真理之場所。海德格爾的“作為存在場所的地方”理論是空間研究的重要根基,但是海德格爾式的“地方信仰”以及空間拜物教卻是需要警惕的對象。
其二,面對后現代都市地方性的消逝,強調在“都市化-民族國家-全球化”的維度上重新思考“地方”。其核心的路徑在于追溯連接不同地方的社會關系,而不是單純賦予特殊地方尋根式的懷舊。空間的生產是最具包容性的社會關系的再生產,將身份認知置于為斗爭、自由與解放而選擇的空間之中,開啟了全球化時代差異化兼具特殊性的都市美學實踐。
其三,受益于波德萊爾瞬間性詩學和巴赫金時空體理論,宣揚“地方”充滿機遇并具有未決性。面對工人被豪斯曼式建筑排擠到城市邊緣的現實,空間的情境主義強調節日的瞬間革命性質,“節日”創造的“生活方式”顛覆了對傳統空間的習慣性使用方式。節慶、狂歡、革命是“理想”的變式,波德萊爾審美現代性的二元“憂郁與理想”演進為“節慶與革命”,城市詩學導向城市革命,日常生活批判也最終轉向了空間的生產。
最后,當代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具有高度的理想主義色彩,是“想象的”空間美學。從列斐伏爾的詩性烏托邦創想到哈維作為時空烏托邦的“希望的空間”、蘇賈的“第三空間”、馬西的“全球地方感”等,都旨在重構一個未來的、世界性的、平等化的空間。理想城市是超越資本主義工業城市的未來存在,而回溯城市發展史,“城市”這個形式本身一直是流動和暫時的,唯有它的藝術形式是永恒的,如列斐伏爾所言,城市作為藝術作品而存在(WritingsonCities173)。在此,空間研究及其“過程辯證法”似乎呼應了馬克思“反城市”的立場,唯有城市消融于藝術形式之中,文明最終才能取代野蠻(譬如城鄉二元對立),形成人類命運的共同體。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ugé, Marc.Non-Places:IntroductiontoanAnthropologyofSupermodernit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9.
Castells, Manuel.TheUrbanQuestion:AMarxistApproach.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Couldry, Nick, and Anna McCarthy. “Introduction.Orientations: Mapping MediaSpace.”MediaSpace:Place,ScaleandCultureinaMediaAge. London: Routledge, 2004.9.
Debord, Guy.TheSocietyoftheSpectacle. Trans. Ken Knabb. Canberra: Hobgoblin Press, 2002.
Harvey, David. “Between Space and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AnnalsofAssociationofGeographers. 80.3(1990): 418-34.
- - -.Justice,NatureandtheGeographyofDifference. Oxford: Blackwell, 1996.
- - -.TheConditionofPostmodernity:AnEnquiryintotheOriginsofCulturalChange. Oxford: Blackwell, 1989.
海德格爾: 《林中路》,孫周興譯。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
Heidegger, Martin.OfftheBeatenTrack. Trans. Sun Zhouxi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7.
艾倫·萊瑟姆等: 《城市地理學核心概念》,邵文實譯。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年。
[Latham, Alan, et al.KeyConceptsinUrbanGeography. Trans. Shao Wenshi.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3.]
Lechte, John. “(Not) Belonging in Postmodern Space.” Eds. Sophie Watson and Katherine Gibson.PostmodernCitiesandSpaces. Oxford: Blackwell, 1995.102-103.
Lefebvre, Henri.LaRevolutionUrbaine, Paris: Gallimard, 1970.
——.WritingsonCities. Trans. Elizabeth Lebas and Eleonore Kofman. Oxford: Blackwell, 1996.
Lippard, Lucy.TheLureoftheLocal:SenseofPlaceinaMulticulturalSociet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77.
劉懷玉: 《現代性的平庸與神奇——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哲學的文本學解讀》。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
[Liu, Huaiyu.MediocrityandMiraculousnessinModernity: A TextologicalInterpretationofHenriLefebvre’sCriticalPhilosophyofEverydayLife.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6.]
陸揚:“列斐伏爾: 文學與現代性視域中的日常生活批判”,《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5(2009): 66—74,159。
[Lu, Yang.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View of Literature and Modernity.”JournalofTsinghuaUniversity5(2009): 66-74,159.]
Massey, Doreen.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Barnes, Trevor. and Derek Gregory. eds.ReadingHumanGeography. London: Arnold, 1997.236-323
多琳·馬西: 《保衛空間》,王愛松譯。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年。
[- - -.ForSpace. Trans. Wang Aisong.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3.]
Meyrowitz, Joshua.NoSenseofPlace:TheImpactofElectronicMediaonSocialBehavio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Relph, Edward.PlaceandPlaceness. London: Pion Limited, 1976.
Saldanha, Arun. “Power-Geometry as Philosophy of Space.” Eds. David Featherstone and Joe Painter.SpatialPolitics:EssaysforDoreenMasse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3.44.
Shields, Rob.Lefebvre,Loveand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Sorkin, Michael. “Introduction: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VariationsonaThemePark:TheNewAmericanCityandtheEndofPublicSpac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2. xiv.
——. “See you in Disneyland.”VariationsonaThemePark:TheNewAmericanCityandtheEndofPublicSpac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2.205-233.
Thrift, Nigel. “Inhuman Geographies: Landscapes of Speed, Light and Power.” Ed. Paul Cloke.Writingtherural:FiveCulturalGeographier. London: Paul Chapman, 1994.212-213.
閻嘉:“不同時空框架與審美體驗: 以戴維·哈維的理論為例”,《文藝理論研究》6(2011): 36—41。
[Yan, Jia. “Different Spatio-temporal Structure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Harvey as an Example.”TheoreticalStudiesinLiteratureandArt6(2011): 36-41.]
張也:“空間、性別和正義: 對話多琳·馬西”,《國外理論動態》3(2015): 2—8。
[Zhang, Ye. “Space,GenderandJustice: A Conversation with Doreen Massey.”ForeignTheoreticalTrends3(2015): 2-8.]
張一兵: 《照亮世界的馬克思: 張一兵與齊澤克、哈維、奈格里等學者的對話》。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Zhang, Yibing.MarxWhoIlluminatedtheWorld:ZhangYibin’sInterviewwithZizek,Harvey,NegriandOtherScholar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