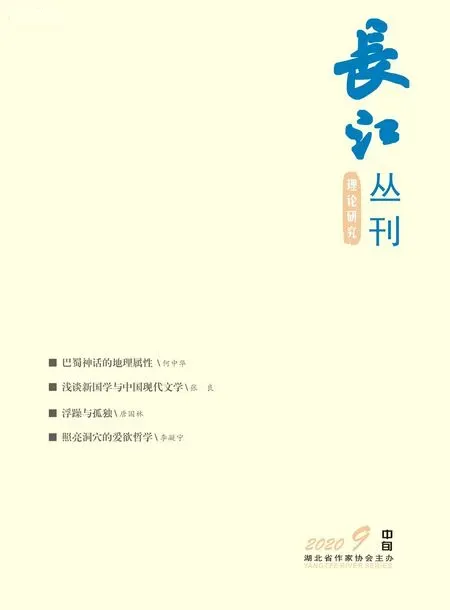淺談新國學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
■張 良/日照職業(yè)技術學院
一、前言
新國學作為一個全新的學術概念,并不是一個新的學術研究方法論,也不是一個學術研究的指導方向與新的學術流派,而是有關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國學術的一個觀念。新國學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固有“國學”這個概念的基礎上,促進中國現(xiàn)代文學全新發(fā)展而作出的新的定義。
二、新國學提出的意義概述
關于新國學提出的意義概述及背景研究,從李繼凱教授發(fā)表的《新國學與新文學》學刊中可以了解到:“新國學的倡導,對持續(xù)發(fā)展新聞學必將產生深刻且重大的影響,新國學的曲折命運折射著新文學坎坷的發(fā)展歷程。”嚴家炎先生認為:“新國學的內在精神與提出異議,便是要以革新國學為目的,積極創(chuàng)新與改革傳統(tǒng)國學,努力推進國學現(xiàn)代化發(fā)展,才能使國學符合中華民族的現(xiàn)代發(fā)展需求,實現(xiàn)對國學的傳承與弘揚,將國學發(fā)揚光大,而不是打倒國學。”這一結論的提出,源自于我國文學界的廣大學者對“五四”以來發(fā)展出的文化存在一定誤解、缺失和認知偏差,多數(shù)學者認為國學具有調和性、綜合性特征,更具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方法論意義。還有學者認為新國學具有較高挑戰(zhàn)性,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提出新要求,要求中國現(xiàn)代文學要堅定自身立場定位與定性,探索新國學意義與概念,在此基礎上,實現(xiàn)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與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進行碰撞,進而探索出全新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理念和方法新變。新國學與傳統(tǒng)國學相比,觀念視野開闊,內涵豐富,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提出更具科學性、合理性的理性思路,進一步推進中國現(xiàn)代文學創(chuàng)新發(fā)展。新國學概念的提出,是為滿足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的實際需要,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抓住改革契機,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提供新出路。新國學概念的提出,即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新發(fā)展指出面臨的困惑與學科建設問題,也進一步幫助中國現(xiàn)代文化發(fā)展梳理和清晰認識,為其創(chuàng)新、可持續(xù)性發(fā)展指明道路。
三、淺談新國學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
(一)新國學是中國現(xiàn)代文化的新概念
嚴格來講,新國學的提出不僅是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創(chuàng)新發(fā)展指明道路,同時也是中國現(xiàn)代文化史上的一個新概念,源自于二十世紀初期,是中國文化發(fā)展的產物。但是,由于新國學概念產生于“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要早于“五四”新文化進入中國文化時期,所以更受中國現(xiàn)代文學界關注。早在新國學概念提出之前,中國便有了“中學”與“西學”之爭,在那個時期,“中學”不論是在復古派官僚那里,還是在洋務派官僚那里,都是指儒家倫理道德學說,并且是經由古時期學者系統(tǒng)改造過、順從異族政治統(tǒng)治的知識分子所接受并運用的倫理道德系統(tǒng)。在那個時期的“中學”和“西學”之爭,不僅是現(xiàn)代科技與西方文化的分化,同時也是清朝統(tǒng)治集團內部兩條政治路線的分歧與斗爭,其爭論內容主要是以在面臨具有更先進科學技術水平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侵略我國清王朝情況下,所采取的各種政治策略問題。在這個爭論背景下,“中學”與“西學”爭論政治意義要大于文化意義。“國學”作為一個學術概念,早在章太炎主持的《民報》編務期間,便于明確提出“國學”這一學術概念。正是因“國學”概念的提出,不僅促使他與當時同盟會的大多數(shù)革命者產生一個嚴格的區(qū)別,還促使其越加受我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界所重視,為其發(fā)展帶來新出路。在《民報》中對“國學”的解說,認為新國學屬于一種固有學術,但又能跟隨時代變化而推陳出新,它包括有中國古代哲學、文學、語言學三個主要部分,不僅包含儒、道、釋等各家各派的思想哲學,同時也是中國古代高雅文化的總稱。
(二)新國學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組成部分
在新國學發(fā)展初期,雖然備受爭議,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界中,也受到排斥。但是,其實這個被排斥的“新國學”學術概念,是屬于中國當代學術系統(tǒng)之內的學科,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新國學也應占據(jù)自己應有的位置。無論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科、中國現(xiàn)代科技文化,還是中國現(xiàn)代翻譯文化,在發(fā)展過程中,都沿用了中國當代學說中新國學的學術概念,并借助其概念發(fā)揮和正在發(fā)揮自身獨立的作用價值。新國學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是對中華民族的民族語言進行創(chuàng)作和創(chuàng)新,將海外華人文化與華人文學有機融合,同時對促進中國當代文化,進一步發(fā)展起到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并且體現(xiàn)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對世界影響的擴大。所以,新國學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的融入與發(fā)展,是沒有任何理由受到廣大學者排斥和排除在外的。在中國當代文化與當代文學快速生成、快速變化和發(fā)展過程中所產生的文化與文學,不論在這整個過程中還會發(fā)生何種曲折、遇到怎樣的困難,都難以打破中國文化凝固不變的整體,也無法改變中國文化萬古不變的抽象觀念和生生不息的結構整體。而新國學作為一個學術性的活體系統(tǒng),在發(fā)展中并不屬于一成不變的固體,也是需要跟隨時代變遷進步和革新的。雖然這樣看起來,新國學成為了一個“無邊無沿”的學術概念,對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并沒有什么實際意義。但是,從實際上來看,新國學就應當是一個既包括中華民族古往今來,所有文化現(xiàn)象的研究及其成果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界各個研究學者都要具備的一個明確整體觀念,它既不等于整體,但卻是整體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三)新國學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新發(fā)展
之所以說新國學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新發(fā)展,是因為在新國學生成初期,雖受到廣大學者所排斥和產生諸多爭議。但是,當新國學這個學術概念,重新返回大陸學術界,逐步滲透到中國現(xiàn)代文學當中,并且成為在中國學術界中唯一具有整體性、概括性和超學科性,并且影響巨大的學術概念時,不僅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帶來新機遇和新轉機,同時也促使中國大陸的學術結構發(fā)生重大變化。而這一重大變化的產生,對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界的廣大學者而言,其中一個最無法忽視的變化就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學科的存在和發(fā)展。尤其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中國現(xiàn)代文學產生之時,中國大陸學術界尚未存在新國學這一概念,所以便致使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與新國學這個學術概念失之交臂,導致中國現(xiàn)代文學被“歷史地”遺留在新國學之外。但是當新國學這一學術概念重回中國大陸學術界,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化研究學科的地位就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尤其是作為新國學重要載體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科,在新國學學術概念盛行發(fā)展期間,不僅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提供新出路與指明新思路,同時還進一步完善,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化整體,填補中華文化精華,促進中國現(xiàn)代文學創(chuàng)新發(fā)展。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新國學學術概念,在盛行發(fā)展期間,不僅成為整個中國社會推進文化改革的一種希望寄托,特別是魯迅研究上,同時還激活了“國粹”,促使中國固有文化與文學門類,在“國粹”的名義下,努力克服現(xiàn)實困難,獲得全新發(fā)展。中國現(xiàn)代文學也在這一發(fā)展形勢下,擔負著其他學科所不能擔負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工作,充分體現(xiàn)其獨立存在的必要性與價值意義。
四、結語
綜上所述,新國學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是一個永久性的學術概念,同時也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新概念、新出路,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指明思路與方向。但是,當人們都以這樣的觀念理解“國學”的時候,新國學這一學術概念就沒有實際存在的必要,經由其發(fā)展和演變,便只有“國學”,而沒有“新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