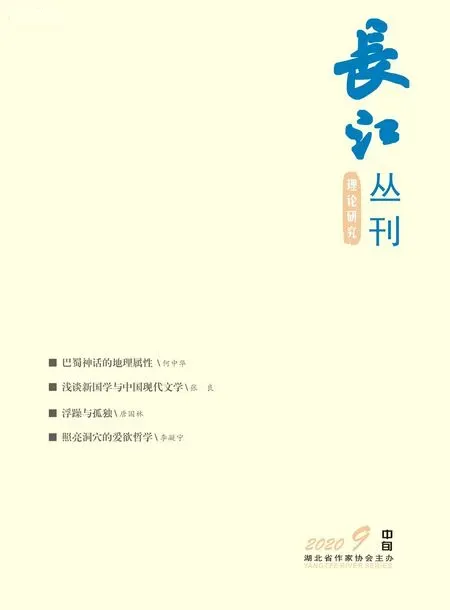從社會認可度析視聽翻譯譯者的“隱身”
■劉大燕/重慶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
一、前言
視聽翻譯(AVT)作為翻譯研究的新興領域,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發展得如火如荼。視聽翻譯實際上是一個比較龐大的領域,涵蓋了二十幾種模式,其中為人所熟知的是電影翻譯的兩種模式,即配音和字幕翻譯。
在該領域從事翻譯工作的人員統稱為視聽翻譯譯者(audiovisual transl ator),但具體各種模式也有專屬的稱呼。法國翻譯學者Gouadec把從事視聽翻譯的人員分成三大類:字幕翻譯人員、配音人員和本土化人員。在具體模式中,還有更詳細的分工,如在字幕翻譯中,Díaz Cintas與 Remael提出三分法,指出整個過程涉及時間軸制作人、譯者和改編者。視聽翻譯作為一種特殊的翻譯,所涉人員眾多,可以“視聽翻譯譯者”概括論之。
視聽翻譯譯者如今面臨諸多困境,如對專業技能的重重挑戰。困境之一是其社會認可度較低,用Diaz Cintas與Remael的話說,“視聽翻譯譯者作為整體——尤其是字幕譯者——并沒有得到社會認可。” 這樣的處境造成了視聽翻譯譯者的“隱身”,而這種“隱身”主要表現在版權和版稅方面,以及電影片尾的致謝名單上。本文剖析這些“隱身”的表現,并探討一些改善措施。
二、版權與致謝名單
(一)版權與致謝署名問題的一般原則
一部作品的版權實際上由兩種權利構成:一種是使用權,通常根據達成的共同協議或與客戶簽訂的合同行使;另一種是精神權利,用以保護作者的作品不被篡改。使用權可以出售或轉讓,前提是各方達成明確的一致意見,但精神權利不可轉讓,版權持有者不必也不應放棄對作品的精神權利。
視聽翻譯譯者的版權源自譯者的版權,而譯者的版權則來源于對著作權的保護。國際上簽訂了兩大公約確認了對著作權的保護,一是1886年在瑞士伯爾尼擬定的《伯爾尼公約》,另一個是1952年在日內瓦簽訂的《世界版權公約》。根據兩大公約,譯者與作者享有同樣的版權,所以有權因自己所做的工作而獲得認可。
此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 CO)也肯定了譯者的權利,在1976年的一份文件中,如此規定:
譯文作者的名字應該出現在如下場合的顯眼位置:所有出版的翻譯著作、劇院海報、廣播電視節目的預告、電影的片頭字幕和其它所有推廣宣傳材料。
兩大公約規定的譯者版權也延至影視翻譯領域(視聽翻譯領域),該領域的譯者也享有與作者同樣的版權。例如,譯者的版權也適用于字幕譯者,若字幕譯者無異議,其名字應該出現在影片的致謝名單上。字幕譯者的版權并不排斥某些必要的改動,如客戶有權糾正影視作品的明顯錯誤、改進計時、改變字幕行的分布,以及其它必要的改動。這些變動都是在字幕譯者版權允許的范圍內。
(二)署名問題的例外情況
在版權與致謝署名問題的一般原則下,也有一些可以不署名的情況。例外之一,某些特定節目,如電視節目不到10分鐘的內容、新聞節目的譯文等,除非有特殊原因,原則上譯者不署名。
例外之二,某些視聽翻譯模式的版權問題有爭議。視聽翻譯模式眾多,情況紛繁復雜,版權署名問題并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對某些模式的版權問題有學者提出了質疑,如針對有耳疾的人的字幕翻譯(SDH),其版權狀況并不明朗。但Ivarsson與Carroll仍然認為這種模式“也是一種創作活動,這就意味著,該模式的字幕譯者也應該署名”。
另一種常見情況是,譯者自己謝絕在致謝名單上署名。Kuo對字幕譯者做過這方面的實證調查,結果顯示,受試者中,6.5%不想署名,19.1%希望“只是在某些情況下”署名,而所謂的“某些情況”,僅限于如下情況:完成翻譯任務時間充足、能夠確認修訂過的版本、個人喜歡影片、未通過中介公司直接與客戶合作。Kuo得出的結論是,字幕譯者對自己作品的信心大大影響了對待受不受認可的態度。對自己作品越有信心,就越期待得到認可,越沒信心,就越不熱衷于署名問題。
字幕譯者謝絕署名的原因多樣,也因譯者而異,但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字幕翻譯這種模式有其特殊性,譯者的譯文隨后出于語言或技術等原因會被其他人改動,尤其在修訂階段,而譯者本人不贊同這些改動,更有甚者,字幕譯者根本沒有機會確認修訂過的版本。如此一來,動搖了字幕譯者對自己作品的信心,不愿在上述情況下擔保最后成品的質量,由此而謝絕署名。以上均為可接受的不署名的情況,但也造成了譯者無版權無署名的事實。
(三)行業版權實際狀況
字幕譯者原則上與其他譯者一樣擁有版權,但實際上在不少國家,如西班牙和希臘等國,字幕譯者并沒有自己作品的版權,也不會獲得版稅。如果這種最常見的視聽翻譯模式尚且如此,可以想象其它模式所面臨的囧境。
造成字幕譯者沒有版權還有版權轉讓的原因。字幕翻譯行業的常見做法是,譯者把版權轉讓給承接翻譯任務的公司,一般是翻譯公司或專業字幕翻譯公司。大多時候這種轉讓是譯者與翻譯公司簽訂合同時所要求,譯者不得不同意。在芬蘭,一般要求字幕譯者把版權轉讓給翻譯公司,例如不少做此工作的大學翻譯專業的學生與知名翻譯公司Giddyup Text簽訂合同,就會宣布放棄版權。在克羅地亞,Nikoli?對克羅地亞公共電視臺(HTV)的字幕翻譯狀況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字幕譯者與電視臺所簽合同剝奪了其作為作者擁有的所有權利,包括版權。以上種種證實字幕翻譯行業譯者沒有版權是比較常見的現象。就整個視聽翻譯行業而言,所面臨的實際困難也大同小異。
(四)致謝名單署名實際狀況
按照致謝名單署名的一般原則,字幕譯者有署名的權利。Kuo對字幕翻譯的實證研究指出,字幕行業人員有強烈愿望提高其社會和職業認可度。Kuo的調查顯示,74.4%的受訪譯者稱“總是”希望在電影字幕版的致謝名單上署名。而行業的實際情況事與愿違,Kuo的調查結果是,所有受訪者中,只有24.7%的人“總是”能夠署名致謝,而14.7%的人“從未”署過名,5.1%的人對自己是否署了名一無所知。不僅字幕譯者,也包括字幕翻譯公司,很多時候沒有出現在電影字幕版片尾的致謝名單上,這被認為是“想要隱身的一種做法”。
譯者署名與否國與國之間區別較大,有些國家比其它國家對字幕譯者更尊重,因此署名的比例更高,如Kuo提到的丹麥、芬蘭、挪威、瑞典等北歐國家,這些國家有自己的國情,部分原因是法律明文規定字幕譯者擁有致謝署名權,部分原因是字幕譯者得到強大的行業組織的支持。在我國,電影字幕版一般會署上譯者或翻譯公司的名字,取決于影片是內部翻譯的,還是外包給翻譯公司完成。筆者留意過幾部進口大片,有時有譯者的名字,有時是翻譯公司的名字。
而在某些國家,字幕譯者的署名比例并不高,例如Nikoli?對克羅地亞公共電視臺(HTV)的調查顯示,字幕譯者并不在片尾致謝名單上署名。受訪的一位譯者表示,字幕譯者和字幕校對人的名字均不會出現節目末尾,沒人知道他們是“節目播放之前制作文本的人”,這位譯者認為這是該行業的弊端之一,剝奪譯者的署名權,奉行這種“愛干不干”的工作原則,對字幕譯者不夠尊重。
此外,署名的位置也影響到譯者的受關注度。署名致謝既可以在片頭,也可以在片尾,目前最常見的做法是放在片尾。致謝署名放在片尾的不利之處是大多數觀眾都看不到,畢竟沒有多少人有耐心在電影放映完畢后還待在影院,等致謝名單放完后才離開,除非特意想要了解譯者的名字,看看誰該為翻譯得糟糕透頂、錯誤連篇的字幕負責,或者又是誰翻譯得如此妙語連珠。
簡而言之,字幕譯者的署名狀況并不樂觀,遠遠比不上文學翻譯的譯者,畢竟在文學翻譯領域,大多數出版著作都署上了譯者的名字。字幕譯者如果不署名,則把其地位置于文學翻譯譯者之下,也側面反映出視聽翻譯不如文學翻譯受重視。署名問題造成了負面影響,降低了字幕譯者的社會認可度,Diaz Cintas與Remael因此把字幕譯者描述為“被迫隱身”,也影響到其版權,“這種負面影響表現最明顯的是字幕譯者對自己的作品沒有版權”。可見版權與致謝署名息息相關,互為掣肘。
三、版稅問題
除版權、致謝署名外,視聽翻譯譯者的社會認可度還表現在版稅方面。一般情況下,有版權就有權獲得版稅。但如前所述的種種情形,視聽翻譯譯者(尤其是字幕譯者)實際上很多時候沒有版權,所以也沒有版稅。Kuo曾評論道,無論是分享所配字幕的節目的版稅,還是享有自己作品的版權,這些對于字幕譯者來說都是“罕見的”情況。在這方面,視聽翻譯也遠不及文學翻譯,文學翻譯的譯者不僅可以在大多數出版著作中署名,更有可能簽訂合同,確認其獲得版稅的權利。
Kuo對字幕譯者的版稅情況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受訪譯者(84.2%)表示“從未”因所配字幕的節目的再次出售而獲得過版稅。Downey解釋了部分原因:
電影的字幕翻譯一般在影片拍攝完之后進行,逐條制作,由承包該任務的公司或個人完成,他們與最初的電影拍攝過程并無關聯,也不會從之后影片的發行中獲取版稅。
從以上解釋可以看到,字幕譯者沒有版稅,主要是因為字幕翻譯與電影拍攝本身沒多大關系,是在影片拍攝完畢之后才做的工作,因此與電影相關的利益沒有多少瓜葛,自然不會從影片的發行中獲利,包括版稅。
雖然視聽翻譯譯者獲得版稅的機會不大,但某些國家或客戶會保障譯者的此項權利。Jankowska對波蘭視聽翻譯行業進行了調查,指出視聽翻譯譯者的很大部分收入來自版稅,由波蘭戲劇作家與作曲家協會(ZAiKS)支付。不僅如此,波蘭還對此以法律明文規定,根據1994年2月4日頒布的《版權與相關權利法案》,波蘭視聽翻譯譯者協會(STAW)建議,每次采用其作品,譯者都應該獲得報酬,包括在電視上和影院重播重映、各種DVD版本、在公共汽車和飛機上放映。
除國別差異,對版稅的保障更多來自客戶的意愿。Kuo的研究顯示,字幕譯者獲得版稅的權利較少依賴任何法律上的保障,而更多取決于公司的意愿,這些公司多設立在特定國家,如對版稅狀況比較樂觀的受訪者中,有2.8%的人認為獲得版稅是“理所當然的”,2.6%的人聲稱“經常”獲得版稅,這些譯者的客戶和委托人一般來自芬蘭、挪威、丹麥、法國、澳大利亞、斯洛文尼亞、泰國和美國等國。這些國家的傳統做法較好地保護了譯者的權利。
而某些情況正好相反,即使在波蘭,有法律保障此項權利,視聽翻譯譯者沒能獲得版稅也是常態,如Jankowska對波蘭視聽翻譯譯者的調查中,近一半(48%)的受訪者表示沒有獲得版稅。Jankowska不無遺憾地指出,很多時候,雇主侵犯了譯者的合法權利,沒在合同中包含版稅這一項,甚至沒讓譯者簽訂版權轉讓同意書。其它某些國家的版稅狀況也比較耐人尋味,如西班牙一般不認可字幕翻譯這種活動擁有版權,卻認可配音可以獲得版稅。
總而言之,像字幕譯者這樣,視聽翻譯譯者實實在在做了翻譯工作,但無論是名還是利,似乎都與其無緣,心中不免忿忿不平。Jankowska對視聽翻譯譯者進行的訪談中,一位譯者解釋了對工作不滿的原因,包括翻譯工作不穩定、譯者招聘沒有明確標準、編輯對譯文的更改,其中明確指出沒有版稅是主要原因之一。
四、結語
早在二十年前,我國著名影視翻譯家錢紹昌教授就曾說過:“如今譯制片受眾(觀眾)的數量遠遠超過翻譯文學作品受眾(讀者)的數量,影視翻譯對社會的影響也決不在文學翻譯之下”。[8]如今視聽翻譯的發展勢頭更加迅猛,主要得益于國內外蓬勃的電影產業。根據中國影協發布的《2019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中國已經成為北美之外的世界第二大票倉,拉動全球電影業整體增長了1.2%,有望在全球電影市場與美國和中美之外市場三分天下。
在此背景下,視聽翻譯的潛力無可限量,而且隨著技術的發展,更多視聽翻譯模式涌現,視聽翻譯早就應該取得與文學翻譯同等的地位。而與此大勢相悖的是對該領域譯者的認可度,以各種理由剝奪譯者的版權和版稅,剝奪其在電影中署名的權利,使對視聽翻譯作出巨大貢獻的譯者始終默默無聞,“隱身”于臺前幕后,加劇了其艱難的處境。視聽翻譯行業要更健康地發展下去,要采取積極措施,如加強對該行業的重視、提升行業地位、創建行業協會,使譯者“顯形”,能夠無比自豪地與影視作品的主創人員、其他類型的翻譯人員一起比肩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