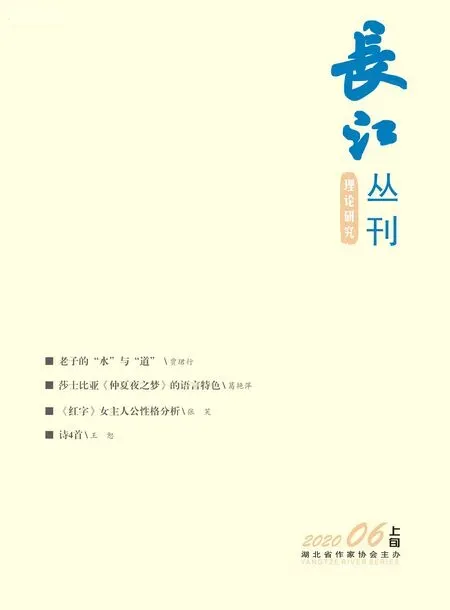孤獨者的頌歌
——評楊光詩集《我們的悲哀由來已久》
■馮 晶
孤獨是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一個永恒的主題,它貫穿于整個人類社會及個體的生存狀態中。隨著孤獨意識的不斷自覺,“孤獨”逐漸成為哲學乃至文學的關注點。在眾多作家的筆下,“孤獨”日漸成為人類特別是現代個體精神困境的表征。從屈原、魯迅到莫言,從卡夫卡、薩特到馬爾克斯,古今中外從來都不乏借由文學來表現人類孤獨體驗的作家。因此,優秀的文學作品,總是要關注社會、關注人的精神狀態,給人獨立、警醒的先鋒力量,尤其是詩歌。對于一個詩人來說,正如楊光在一篇博客中所言,他是“黑夜中醒著的人之一,用自己獨特的詩歌來喚醒沉睡的心靈,讓迷失的人返回自己,返回我們和諧的家園。詩人作為自然的一位守護者,他們在詩歌中聆聽自然、撫摩鄉土、反思人自己、贊頌真善美、歌唱人與自然的和諧。他們抒寫世間萬事萬物,他們頌贊世間萬事萬物的互惠共存。”誠哉斯言!我以為他本人正是這樣一位書寫人生及其孤獨的詩人,翻開他的詩集,似乎滿滿只有兩個大字——“孤獨”。作為一個沉思者、預言者、啟迪者以及行動者,他關注那些個體的“人”的生存狀態,從而參悟人生價值和意義,同時,當然也為我們這些讀者選擇以何種姿態存活于當下提供了一種精神指引。
“尋找孤獨”——進退維谷的生存困境
“孤獨”究竟源于何處?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每個生命個體都難以避免在人生的某個時刻、某個階段感受到自身與周圍環境的異質,或是感覺到外部世界的陌生感,亦或是與他人溝通的距離感,這些都會讓我們產生孤獨的體驗。孤獨作為現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已被從叔本華、尼采到薩特等哲學家所揭示,他們都覺察到因“上帝死了”而導致的現代人的價值真空和無可皈依感,在這種失衡的時代大背景下,孤獨已成為人類乃至整個現代社會都無法擺脫的病癥。
閱讀《我們的悲哀由來已久》這本詩集,撲面而來的都是這樣一些意象——深黑的井、布谷、蝙蝠、烏鴉、老鼠、黑夜、棺材等等,這些意象共同的情感指向都是“孤獨”。在詩歌中,詩人將個人生命感悟轉化為與客觀外物“靜默”的交流,在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隔膜、理想和現實的矛盾中,描摹孤獨、思索人生,在《蝙蝠》一詩中,詩人就借“蝙蝠”這樣一位“黑夜的攜帶者”展現了空虛孤寂的人間世態。
詩的開頭是一幅靜止的畫面,夕陽未落,萬物塵埃落定,樹木“靜止、抽象”,這里樹木像是沒有實體,“抽象”意即一種虛幻的存在,靜止得仿佛只是鏡花水月般的幻影。這種彷徨而無所依托的自然現象象征著的即是人的一種生存困境。人如果在光明與黑暗當中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便成了一個“彷徨于無地”而無所依托的生命存在,孤獨之感油然而生。
蝙蝠飛過醬色的天空/巨型的翅膀攪動強大的氣流
從“紅”到“醬色”,天空顯然黯淡了不少,夜晚來臨,萬物沉睡,清醒著的只有孤獨者和夜間活動的生物。蝙蝠飛過,“強大的氣流”打破了原本的靜止。未被人類教化的蝙蝠顯然是獸性未泯、充滿著自然的野性。在我國民族傳統心理中,蝙蝠因同“福”諧音,通常是用以象征福氣、富貴、快樂、長壽,古人常在銅器、陶器、寺廟壁畫等等器具或建筑中飾以蝙蝠,寄托美好、祥瑞的愿望。這里的蝙蝠,以一種“巨型”“強大”的狀態出現,既不同于象征福氣的祥瑞,也異質于靜止、抽象的樹木,它充滿了蓬勃的生命力和原始的野性。
這夜晚的飛行利器,這黑夜的攜帶者/它落下的地方,仿佛砂石撒進漆黑的樹林/讓我聆聽到世界的動靜
到了此時,醬色的天空已經完全變黑,蝙蝠“仿佛砂石撒進漆黑的樹林”,“巨型”“強大”的蝙蝠在這里變得如砂石一般渺小,作為夜晚的飛行利器、黑夜的攜帶者,它們的力量仍然不足以與“漆黑”“靜止”的樹林抗衡。在其他一些詩中,作者也同樣寫到諸如烏鴉、老鼠等生物,與這些黑夜的生物不同,人儼然沒有野生動物的這種野性,喪失了掙扎的本能,生活在喧鬧的都市里,人作為自然的一部分已日益與自然隔絕,更像一群都市動物。壓力、焦慮、困惑,人類在不斷去征服過程中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方向,從而陷入一種孤獨的恐懼,陷入一種無序的生存困境。
在另外一首《回答》中,對于人類生存困境的暗喻則更加明顯:
如果你問這個世界上最多的是什么,/我回答:“是人。”/如果你以同樣的話去反問另一個人,/這個世界最缺的是什么,他會回答:“是人。”/因此,當有人問,/為什么在大白天也點著燈走路,他回答:/“找人。”
這首詩副標題是“致第歐根尼”,詩中的“他”也正是這位鼎鼎大名的“犬儒”哲學家。相傳第歐根尼有一次大白天在雅典街上點著燈籠走來走去,像是在尋找什么。當有人問他在找什么,他回答在找人,意即在當時的社會中很難找到他認為是真正的人。這首短詩頗具哲學意味,第一個問題是“這個世界上最多的是什么”,回答“是人”。早在古希臘時期,普羅泰戈拉就提出了“人是萬物的尺度”的說法。作為有自我意識的高級動物,“繁衍”和“發展”是人的本能,人通過不斷征服其他生物,決定并支配著整個世界的活動,逐步成為了萬物的主宰。第二個問題“這個世界最缺的是什么”,這里以哲學家的身份回答“是人”,為何不以“我”的口吻回答,或許是出于作者的自省意識,作為普通人,我們每一個人都擺脫不了身份的限制,在社會文明不斷的發展刺激下,人逐漸成為了資本的附庸,人與人的關系已經疏遠,以市場交易來衡量一切,作為有思想的社會性動物,人已經失去了自我意識和個性,內心充滿了空虛與恐懼,世界上人很多,卻缺少真正有思想和意識的人。第三個問題,“為什么在大白天也點著燈走路”,回答“找人”。“第歐根尼的燈”很顯然是在尋找真理,在腐朽的社會中尋找真正的人。詩人的這種自省意識正是他孤獨的來源,現代的孤獨已逐漸從一個私人性質的生命體驗上升為一種廣泛而具有普遍認同的文化符號,這就是現代人對孤獨的自覺。
在這本詩集中,詩人不斷地探尋著底層世界和蕓蕓眾生的精神困境,審視著人類乃至萬物的生存困境,通過日常的生命體驗,道出了簡單深刻的生存哲學。
“直視孤獨”——向死而生的生命意識
“死亡”從生物學意義上來說,是每個生命個體必須面對的階段,是無法擺脫的生命歸途。作為哲學永恒的話題之一,死亡的不可避免與生命的空虛感、孤獨感簇生在一起。人對于世界的感知始于生而止于死,因而“死亡”可以說是人類最孤獨的存在。自古以來,人們大部分從否定的一面看待死亡,認為死亡是對生命的戕害,是一種無奈的生命決絕。而存在主義哲學卻認為,“死”是另一種人生價值。海德格爾認為人應該“向死存在,就是先行到這樣一種存在著的能在中去,這種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就是先行本身。”人只有真正領會和懂得了死,才能領會和懂得生的意義。在楊光的詩中,他同樣以這種“向死而在”的生命意識,大膽直視生命的孤獨。翻開這本詩集,《名字》《葬禮》《從星空下走過》《花朵》……不得不訝異于其中死亡以及與死亡相關的字眼的大量出現——墳墓、墓碑、墳頭、亡魂、遺像、遺容等等,死亡被詩人頻繁地描寫。對于詩人來說,死亡并不意味著否定、消失,而是帶有一種坦然、贊美的姿態。在他看來,真正的孤獨者,不管他處于什么樣的環境都能讓自己安然并且自得其樂,哪怕他面對的是死亡的恐懼。詩集開頭《深夜的咳嗽》便是一場惡疾的描繪:
穿過墻,像把鋤,朝我挖來。/我不知他害的什么病,咳了多少年。/每咳一下,仿佛空氣在顫抖。/咳嗽的間隙,是他擂胸的沉悶聲/和床板咬牙切齒的詛咒。
首先,在人們潛意識中總是對深夜懷著一種自然恐懼。深夜本身便是黑暗、神秘、肅殺的象征物,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也是各種鬼魅妖狐出沒游走、興風作浪的時刻,死亡就像黑暗深沉的夜空一樣凝視著人類畏怯的靈魂。“穿過墻,像把鋤,朝我挖來。我不知道他害的什么病,咳了多少年。”隨著墻的建立,詩中的二人有了清晰的空間劃分,作為客體的“他”害了咳嗽,并且咳嗽聲打破了二者靜止的狀態,用鋤頭般的力量朝“我”挖來。“每咳一下,仿佛空氣在顫抖。咳嗽的間隙,是他擂胸的沉悶聲和床板咬牙切齒的詛咒。”這段以“我”作為感知對象,“我”聽到的聲音是顫抖、沉悶和詛咒,這些灰暗的象征詞正是“我”的一種聯想,外部的聲音被內化成心理感受,可見墻的兩側都存在孤獨的個體,“他”患著重病無以療救,而另一空間的“我”也同樣感受著這份痛苦。
爾后,咳聲又起,像把鋤,挖在我的心上。/我感覺,他的肺都要咳出來了,/像只茄子,砸在地板上,/他提起腳,用力,踩,跺……
這里第二次提到咳聲像把“鋤”朝“我”挖來,并且直接點明“挖在我的心上”,不同于第一句的隱晦,這里描寫得更加深入,孤獨和疾病的痛苦折磨著不同空間的兩個人。“我感覺,他的肺都要咳出來了,像只茄子,砸在地板上,他提起腳,用力,踩,跺……”,這里仍然是“我”對于另一空間的想象,在“我”的想象里“他”的肺就像茄子一樣,被砸在地上,用力的摧毀,一連串的動詞“砸”“提”“踩”“跺”,殘忍的暴力場景與奇異的意象聯系在一起,用一種近乎荒謬的冷靜,展示出一種極其殘忍卻又冷靜的畫面。“他”摧毀的是肺、是疾病、是生命,是處在死亡邊緣的“用力”的掙扎。
絕癥使死亡成為可見,它迫使人們意識到個人的存在是可以隨時隨地被毀滅的,死亡的瀕臨會使他失去自我與世界。正因為這種面對死亡的無奈、恐懼以及末日感,使人的孤獨和自省得到強化,從而加劇了人們對于未知恐懼的發難和挑戰。作者在這首詩中用一道墻隔開不同空間的兩個人,一人遭受著疾病的痛苦,另一人卻也聯想著這份孤獨,一個是疾病的激發,一個是自覺的釋放,二者所處境遇不同,但在敏感孤獨、遺世獨立上是相通的。這首詩對于疾病或者說死亡的威脅,兩人沒有去哭天搶地的吶喊,而是主動地去面對、去迎接,甚至于去用力的掙扎,承受著生命盡頭的痛苦折磨,這是一種坦然的主體選擇,用與死神的頑強搏斗來捍衛人的生存尊嚴。
如果說在這首詩中,詩人對死亡的態度還比較隱晦的話,在另一首《銀杏頌》中作者對于“死亡”則大加贊美:
最媚人的花,是罌粟/最美麗的活著,是死亡/上蒼賜予我們的只有一次生/我卻用它幻想各式各樣的死亡/包括像銀杏一樣飄落/多么美,在風中沉醉/金色的鱗甲覆蓋衣襟,手臂,把我埋葬/你來的時候,正是黃金堆積的山中
“罌粟”因其具有生命力勃發和加速生命消亡的雙重表征,在文學作品中總是帶有精神陷落的隱喻,其毀滅性力量又始終聯系著衰敗與死亡。詩人認為罌粟是最媚人的花,旋即贊美死亡是“最美麗的活著”。詩人毫不避諱自己對于“死亡”的贊美,他把死亡比作像銀杏飄落。銀杏作為“公種而孫得食”的長生樹,其葉邊緣一分為二,歷來也有陰陽、生死的象征意。死亡是人生必然的結果,死未必是件壞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種生命的解脫。落葉紛紛,一年將盡,金色的銀杏葉把人覆蓋、埋葬,覆蓋了一切,也促使人與殘酷現實的隔離。而且從色彩的象征意義上講,金黃色象征“光明、希望”。詩人看似在贊頌銀杏葉,毋寧說更是在贊頌“死亡”,“藝術是以人為中心的,死亡是人的最高限定,是生命歷程的終點,又往往是精神運動的最高點和情緒波動的峰巔。”詩人從飄落的銀杏葉中看到了死亡的意義,通過死亡去直視孤獨,直視人生的價值。
“生存還是毀滅”一直是始終困惑人類的哲學命題。隨著十九世紀末尼釆一聲“上帝死了”的高呼,人類步入孤獨的深淵而無所適從。深陷于孤獨泥沼中的人們,雖然孤獨的體驗各不相同,但最終結局都是被無情地毀滅,“死亡”可以說是最根本的孤獨。詩人在詩中熱烈地描寫“死亡”,實則也是在審視和思考人類的生命意識,這并非消極的悲劇意識,而是超越了對某一人或某一物的慨嘆,所進行的哲理性思考。詩人以無畏的勇氣來直面無法改變的悲劇,以審美的人生態度來對待死亡,界定了人生的意義,從而思考如何去打破這種孤獨的生命存在。
“超越孤獨”——知黑守白的生活態度
孤獨從另一方面來說又意味著隔絕與封閉。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在對物質和技術無止竟的追求中,放棄了個體精神的訴求,每個人都生活在自我的孤島中孤立無援。如何超越孤獨,或者說我們該以何種姿態度過余生,詩人也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愛”,希望通過“愛”的力量來獲得情感的補償。這是個可以說俗套但是行之有效的辦法,作為歷史序列中的每一獨立個體來說,人生究竟有何意義,這是個渺茫、模糊的問題,但人生若有一切值得熱愛的事物,才能走向自我實現。在《愛之什》這首詩中,單從字面組接來看,并沒有多么絢麗多彩的語詞,但卻是詩人復雜深刻的人生感受。“愛”是很抽象的概念,它是我們所共有的具體生活經驗,尤其從情感的基礎上甚至與“惡”的對立角度看待它。“一個人走在深切的夜晚,沒有恐懼,/沒有孤單,滿天星光照我去荒蕪大地。”這是一句以自我觀照外界的生活敘述,同樣是夜晚的荒蕪大地,沒有恐懼和孤單,這里的“滿天星光”是一種愛的隱喻,愛是對人類生存問題的完美解答,在“愛”的世界上,人可以自由的生存、生活,沒有孤獨的困境,哪怕是一個人,也可以感受到世界緊密的聯系。“我看見石頭發出低迷之光,猛獸溫柔的舐犢之情……”這兩句是全詩的點睛之筆。在中國古代,素有“石能言說”的傳統,人們刻立石碑、石像來表達對于自身乃至萬物的感知,而“野獸”由于其原始的本性和極大的破壞性,自古便是邪惡的化身。詩人把“石頭”與“野獸”這兩個并不搭配的意象組接起來,野獸是有限生命的象征,而石頭則是無限生命的象征,可以說整個自然界都是愛的結果,這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世界最本真的倫理關系。
在全面異化的世界里,我們得到了“愛”的處方,可是到底該如何去“愛”,在詩歌《所謂愛》中,詩人有著這樣的見解:
所謂愛,是一種情懷,/就像清晨的露珠,落日的悲憫。/但不是同情,更不是憐憫,/一切有關憐憫的詞匯,都是對愛的不恭和褻瀆。
很多人認為人性本善,“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義”,作為高等生物的人對于愛的理解自然更加深入。而在現代社會中,愛卻失去了原有的崇高感與道德感,逐漸流于表面,人們往往吝于表達自己的感情,陷入了愛的匱乏當中,自我隔絕的同時也被社會孤立。“愛是行動,愛是布道”,在詩人眼中,愛是給予、奉獻,在給予別人愛的過程中,自己也能明白生命的真正價值所在。德蕾莎修女一生為窮人服務,她用誠懇、行動的愛,救助苦難中的人,對她而言,給予愛和尊嚴比給予食物和衣服更為重要。這是德蕾莎修女對愛的理解,同時也是詩人對于人間愛的祈愿。
愛是堅守。/愛是虔誠。/愛是承受。/愛是那些在孤獨中熱望的靈魂。/再說得樸素一點,愛是——/愛好你的愛人,孩子,和你身邊的每一個人,/包括那些細微的事物,塵埃……
生存在荒謬的世界中,一些不安于或者不甘于孤獨存在的靈魂,一直都在尋找救贖之路,“愛”作為人類信仰的核心,需要人們虔誠去堅守心中的信念,承受生命孤獨的原罪。詩人甚至認為,愛其實很簡單,就是愛好自己的愛人、孩子、身邊每一個人,包括細微的事物。作為社會的一員,我們是自我人際圈子的核心,親人、朋友,包括身邊的每一件小事都值得我們去關懷,這是愛最簡單也是最直接的需要。如果說德蕾莎修女的愛是“大愛”,這種關懷身邊的“愛”便是小愛,是每個人都應該具有的生活責任感,是一種日常的生活方式。詩人自身即是如此生活,“我信奉萬物有靈。真正守護自然的詩人首先是將自己領回家;然后將孩子領回家;再然后是將一粒土一塊石領回家;再然后是將花草樹木領回家,將小小的細菌,將蟲魚鳥獸和人領回家,為人找尋一條返鄉的路,為自然找尋一條返鄉的路(也許他們已有自己的路),也許土石花草、細菌昆蟲和動物及神,我們都在努力向神性智慧靠攏,不是么?”愛是關切、尊重和責任,哪怕身邊一草一木都應該去愛,只有懂得愛的真諦的人才能夠在愛人與愛己中走向自我實現。
人生的孤獨無可避免,就像人擺脫不了生存的困境和死亡的威脅,這不是個人獨有的缺陷,而是整個社會的病癥。關于“愛”的療救,魯迅先生也曾有過如此感慨:“人間都很寂寞。我單能這樣說了就算么?你們和我,像嘗過血的野獸一樣,嘗過愛了。去吧,為要將我的周圍從寂寞中救出,竭力做事吧。我愛你們,而且永遠愛著。”盡管孤獨是人類社會永恒的主題和普遍現象,是作為現代的個人無法回避的生存經驗,期待愛的救贖也是人類共同的決心和意志。我們能做的就是愛身邊每一個人,每一個值得熱愛的事物,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從而超越孤獨。
“逃離還是回歸”——關于孤獨意識與現實關切的思考
弗洛姆曾說,“現代社會結構在兩個方面同時影響了人:它使人越來越獨立自主,富有批判精神,同時又使他越來越孤立、孤獨、恐懼。”從生命源起,孤獨便在每個個體身上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或是主體潛意識的心理狀態,亦或是對于生命狀態的現實經驗。總之,人在形成獨立人格的基礎上,難免會對所生存的外部環境產生批判意識,也可以說,對現實的本質了解越深,人就會越感到自身與周遭環境的異質,從而產生孤獨。
現實是切實的,也是殘酷的,它享有至高無上的控制權和操作權,隨時會給普通的小人物考驗和打擊,甚至是摧毀。作為現代社會獨立的人,人原本學會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舊制度所帶來的束縛,但是在社會的發展進程中,科技進步和物質文明造成了物欲橫流的人生狀態,人們不斷呼喊精神存在,卻又彼此之間相互懷疑。進步與墮落,成為現代人的生活的兩面。詩人認為“在科技文明繁盛無比的今天,自然、人心已經荒漠得太久了。人本是自然的守護者,是地球家園的守護者,但人越來越偏離了人性,偏離了人的本職。”面對千瘡百孔的世界,我們該保持怎樣的姿態,或者說,我們還該不該保持對現實社會的關切。“逃離”還是“回歸”,同樣也是一個恒遠的主題。
在這本詩集《我們的悲哀由來已久》中,我以為,“回歸”才是詩人的選擇。對生存困境的沉痛反省和冷靜回顧,對于人的生存意義、理想生活方式的追問和探索,他感悟到了世界的荒誕與人的孤獨,卻并未沉淪于絕望之中,而是做著自我拯救的不懈努力。詩人楊光便是這樣一位孤獨者,他從個體生命體驗出發,反思時代,追問人生,唱出自己孤獨的頌歌。孤獨是人生常態,人雖然注定要承受數不清的艱難險阻和看不見的冷漠孤獨,但只要用“愛”的處方堅定不移地走向不知盡頭的苦難,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也就在奮斗和掙扎中體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