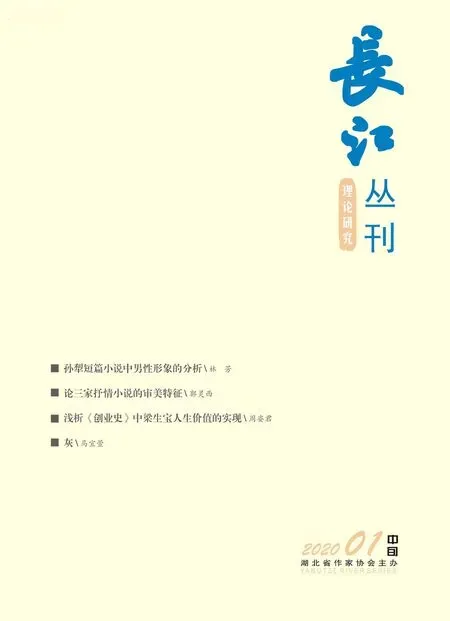中國藝術品價值的人類學解讀
■
/中國藝術研究院
一、前言
2004年之后,中國藝術品產業迎來了增長的爆發期。而2008年之后,隨著西方金融危機,以外國藏家為主的當代藝術品市場一蹶不振,而此時中國的市場異軍突起,中國經濟持續增長,越來越多的富裕階層進入藝術品投資的領域,傳統書畫古玩市場占據了80%以上的市場份額。2015之后市場趨于理性,但是藝術品市場每年仍在增長,投資藝術品仍然是最主要的投資渠道之一,只是這時候的藝術品投資已經不是“資本的狂歡時代”,而冷靜下來思考哪些藝術品和藝術家是值得投資的。這需要從藝術價值的系統以及具體的藝術品環境來判斷,我們可以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解讀藝術品的價值取向。
二、藝術品的背書系統
藝術價值的建構需要哪些因素參與,這些因素的參與將決定藝術創造力與再生產。如果沒有這些因素的參與,藝術就沒有進入信息交互的通道,那就不能稱為藝術。根據對一些藝術家事跡的觀察,筆者列出了四個價值構建的要素:時間、資本、權力、共識。
權力,包括政治權力、藝術界權威、藝術共同體話語權以及媒體權力等。這一點很好理解,藝術價值是一個比較沒法量化的問題,不管是政治權力還是藝術家共同體,實質是一套解釋系統,給予藝術價值以可量化的認可。比如,劉海粟有意在幫國外文化機構編寫中國歷代畫作選時,把自己的作品和歷代名家放在一個體系里,從而獲得國際認可。傅抱石更是因為國慶10年周年,與關山月創作了《江山如此多嬌》,并受到毛主席手書畫名,從此名聲大噪。
資本,是最直觀的價值構建因素,特別是在當今的市場環境中,藝術越來越表現出其金融產品的屬性,由于其價值的不穩定,用資本背書價值的保值與增值,是較為穩妥的方式,也是短平快的方式。比如吳冠中,90年代,吳冠中的作品也就是幾千元左右,這時,剛在房地產業嶄露頭角的萬達集團,以敏銳的藝術和商業洞察力對吳冠中作品的宣傳與運作進行了全方位的戰略布局,吳冠中與萬達集團建立了良好的關系,2004年,萬達聯手中法文化年組委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出吳冠中作品世界巡展,這讓其作品引發了國內外的轟動。
時間,我們也可以理解成歷史或者故事。在關系的維度中,時間是最微妙的影響因素,這里的時間特指藝術創造在關系網絡中的再生產歷史。比如西方美術的后印象派,其發生之初并沒有受到當時藝術界的認可,也超出了大眾審美的過往經驗。但是隨著西方現代主義文化的不斷衍化及資本主義文化的自我反思,后印象派開啟了整個現代主義美術的時代,進而影響了后現代文化及先鋒藝術,開辟了一條藝術價值生產的康莊大道。時間因素是最具穩定性的因素。
共識,指的是公眾的文化共識、藝術共識,或者是特定文化圈子內的價值共識。共識雖然和時間有密切的關系,但是,共識的建構還是有一定的系統可控性的,也就是可能在所見的時間范圍內完成關系的再生產。比如在專業藝術家眼里,藝術有很多的表達方式和門派,但是在普通中國人眼里,不管藝術家如何表達,水墨畫總是更容易被認為是有價值的,而“當代”藝術就顯得非常陌生,基本不會讓人與藝術扯上關系。所以共識不僅代表了藝術家的技藝水平,也代表了不同文化圈層的認可。
三、當代藝術“困境”的原因
人類學看藝術品的基本原則是:不拘泥于藝術本體,不迷信藝術的美學闡釋,而是從文化整體觀的角度來看藝術品。把藝術品放在歷史與當下實踐的角度來看,有些事情自然就變得清晰起來。
比如,80年代中期在中國開始崛起的所謂的“當代藝術”,從85新潮之后,人們的主體意識開始自覺,這種自覺獲得廣泛的時代共鳴,在美術作品上表現的比較極端。而藝術品創作不僅可以摒棄傳統的創作思路,還可以顛覆藝術品的邊界,比如先鋒藝術、波普藝術、行為藝術、觀念藝術等等。需要注意的是2004年之前,這些在中國本土長出來的西方現代主義“怪胎”雖然受到追捧,但是這些作品并沒有在國內獲得太多的藏家,而大部分的藏家是西方的畫廊或藝術商人,但這些作品并沒有在更大范圍內獲得文化和資本上的認可。更多的是西方資本和權威藝術機構為這些作品做價值背書。其本質是藝術體制的價值炮制,利用的是“國外權威”和“境外資本”。
在改革開放的頭二十多年,中國的文化權威一直是需要“別人認可”的狀態,這在其他的藝術門類中表現的也很突出。比如張藝謀、陳凱歌、姜文等導演的作品最先在國外的電影節拿下大獎,然后國內藝術界才以此為風向,確立藝術品質的高低。方力均、張曉剛等人的作品其實是在西方現代主義的創作框架內完成了藝術的本土表達,與其說是這些藝術家走上國際,不如說是境外藝術體制選擇了中國的個別藝術家,因為他們的作品是國外人“可以看懂”的,這就是文化的相對性的問題。
但是在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前后,市場遇冷一直持續到今天,而當代藝術缺少資本與權威機構的認可,這個游戲很難進行下去。另一方面,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使得這十年,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整個社會都出現了后現代主義的解構風潮,民粹和犬儒主義的浪潮也是此起彼伏。也就是說,西方的價值背書系統本身都出現了嚴重的危機,更沒辦法來為中國的當代藝術做背書,中國的當代藝術危機必須靠自身的文化系統來化解。
相反,2009年,中國經濟在強刺激下,更多本土富豪進入藝術品投資,但是中國富豪投資的藝術品重點是古玩字畫和現當代書畫名家,中國的藝術品投資市場異軍突起,成為了世界第三大藝術市場。而2015年之后,隨著金融政策的收緊,中國的藝術品投資市場趨于理性。但是,中國市場依然在上升的通道,而這些錢大部分投向了古玩字畫及現當代名家字畫市場。當代藝術里,除了少數名家有藏家和境外畫廊為其站臺之外,其他年輕的畫家鮮有人問津,這就是當代藝術的“尷尬”。
其實從四個藝術品的價值背書因素,我們就很好解釋上面的現象,當代藝術的“困境”就在于四方面背書系統的全面崩塌,這種解構的速度是可怕的,藝術品往往只有兩個極端,一文不值與平步青云。而當代藝術不管是在話語權,還是資本方面,都已經遇冷。當代藝術也沒有中國本土文化的與大眾共識的背書,所以,這種困境短時間內是沒有辦法逃脫的。
四、建立背書系統的藝術價值生態
當代藝術的遇冷與中國本土文化市場的崛起,這些現象必須從文化整體觀的角度解讀,才能發現藝術品的真實價值是來自何處。而藝術品的價值背書系統又可以決定藝術品投資的方向,所以藝術品的投資者應理性選擇。藝術是一種精神產品,其美學層面比較抽象,有很強的主體性和自主性,如果藝術僅僅定義為一種美學感受,我們可以完全不用考慮藝術品的價值問題。但是,藝術品既然進入了市場流通和資本軌道,這個藝術品產業如果想更好的發展,必須要建立一個價值的參考系,這個是產業發展的基礎。
從產業規劃的角度,藝術品市場必須從歷史和社會經濟現狀出發來思考藝術品產業的健康發展。在藝術價值的評價體系中,必須綜合考慮權力、資本、歷史和共識等四個維度,在定價策略上也應該盡量在可以量化的平臺上“擠泡沫”,而不能陷入合法化危機和合法化泛濫的泥潭。權威評價機構和評價體系的介入是這個市場健康發展的前提。
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我們要全面認識藝術品的價值維度,引入更多的評價系統,尋求價值背書因素的平衡考量。藝術品投資進入理性階段,意味著投機炒作者將被淘汰,更多的藝術界精英、藝術鑒賞家、藝術金融專業人士進入這個場域,藝術價值的相對量化是在權威人士和市場表現的不斷權衡過程中產生的。
而對于藝術家來說,不能埋頭于自我的想象世界。藝術品的價值在于它與外在世界的匹配度。這并不意味著當代藝術、實驗藝術、觀念藝術就沒有價值,而是藝術家要知道自己的創作到底有哪些價值系統內會發光,能和整個藝術界產生哪些關系的連接。
只有建立良好的藝術價值生態,藝術品產業才能良性的發展。這需要藝術界不同背景的精英共同來打造并維護一種全面、合理、可操作性的價值生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