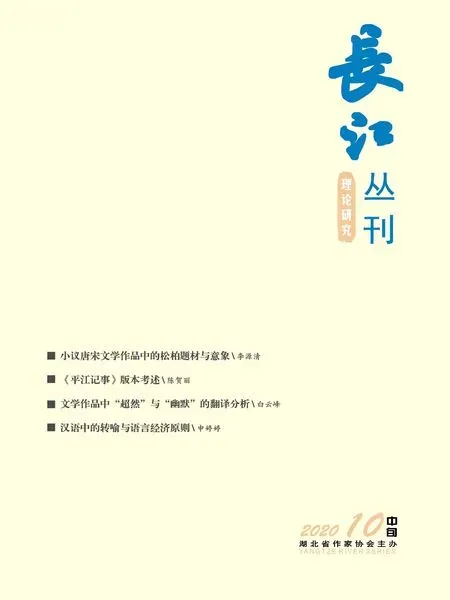漢語(yǔ)中的轉(zhuǎn)喻與語(yǔ)言經(jīng)濟(jì)原則
申婷婷/四川大學(xué)
一、語(yǔ)言的經(jīng)濟(jì)原則
語(yǔ)言的“經(jīng)濟(jì)原則”也就是“經(jīng)濟(jì)機(jī)制”,最早由法國(guó)語(yǔ)言學(xué)家馬丁內(nèi)在《普通語(yǔ)言學(xué)綱要》中提出。經(jīng)濟(jì)原則以盡可能少的消耗言語(yǔ)活動(dòng)中的支出來(lái)提高語(yǔ)言交際的效率,即減少重復(fù)和冗余,在最短時(shí)間內(nèi)以最簡(jiǎn)潔的形式實(shí)現(xiàn)最大量信息存儲(chǔ)和傳遞。
經(jīng)濟(jì)原則體現(xiàn)在不同時(shí)期漢語(yǔ)的音、形、義上。語(yǔ)音方面,如《廣韻》三十五個(gè)聲母發(fā)展到現(xiàn)代漢語(yǔ)普通話的22個(gè)聲母,古全濁聲母變?yōu)槿缃衿胀ㄔ捜簦烈簦牌铰曌纸褡x送氣清音,古仄聲字今讀不送氣清音。像“幫[p]、滂[p]、并[b]”中“幫”母為普通話聲母b,“滂”為普通話p,但全濁聲母“并”仄聲演變?yōu)槠胀ㄔ捖暷竝,平聲演變?yōu)槠胀ㄔ捖暷竍。此外中古不同的聲母“非[pf],敷[pf‘],奉[bv]”全部演變?yōu)榻衿胀ㄔ捖暷竑。字形方面,如隸變,漢字簡(jiǎn)化。“愛(ài)-愛(ài)”,“龜-龜”,“復(fù),復(fù)-復(fù)”等。經(jīng)濟(jì)原則在字形上的體現(xiàn)方便了人們的書(shū)寫(xiě)也節(jié)省了時(shí)間成本和識(shí)別成本,但也因此為后輩閱讀古籍造成了一定的阻礙。詞義方面。漢語(yǔ)有這龐大的詞匯系統(tǒng)有了詞義的聚合,基本詞匯成為整個(gè)詞匯系統(tǒng)的核心,以滿(mǎn)足我們的日常表達(dá)需要。此外還有一詞多義也體現(xiàn)了語(yǔ)言的經(jīng)濟(jì)原則。
經(jīng)濟(jì)原則雖然能夠節(jié)省語(yǔ)言和言語(yǔ)成本,但經(jīng)濟(jì)原則也存在一定的劣勢(shì)或缺點(diǎn),也非常依賴(lài)語(yǔ)境或者是談話雙方的共識(shí)。如:“你看過(guò)了嗎?”到底看過(guò)什么了?這里省略了賓語(yǔ)。要弄明白到底看過(guò)什么,必須補(bǔ)充問(wèn)話前面的語(yǔ)境或賓語(yǔ)。其次,由于”能量守恒定律“,說(shuō)話人如果表達(dá)簡(jiǎn)潔,那就意味著聽(tīng)話人需要耗費(fèi)更多的”能量“去理解說(shuō)話人所說(shuō)的話。越是經(jīng)濟(jì)的話就越消耗聽(tīng)話者的”能量“。這就是“語(yǔ)言經(jīng)濟(jì)原則的負(fù)相關(guān)性”。比如魏曉斌在《關(guān)于語(yǔ)言經(jīng)濟(jì)原則的反思》中所舉的例子:“秦始皇乃始燒書(shū)”改成“政俶燔典”,只節(jié)省三個(gè)字就意味著聽(tīng)話人必須弄明白“政”,“俶”,“燔”,“典”指的是什么意思,而且每一個(gè)字又含有其他的義項(xiàng)。聽(tīng)話人要真正弄懂這四個(gè)字的意思還必須從眾多義項(xiàng)中經(jīng)過(guò)一番篩選才行,這就違背了當(dāng)初使用經(jīng)濟(jì)原則進(jìn)行省略的初衷了。而且有時(shí)強(qiáng)行遵守經(jīng)濟(jì)原則還會(huì)帶來(lái)負(fù)面影響。如,我們?cè)谡?qǐng)求別人借筆給我們用時(shí),說(shuō)“請(qǐng)把你的筆借我用一下。”“可以把你的筆借給我用一下嗎?”等方式比相對(duì)經(jīng)濟(jì)的“筆用一下”更為禮貌。
總之,經(jīng)濟(jì)原則雖然省力,也有某些特殊效果,但只有語(yǔ)言足夠清晰地傳達(dá)意思和必要情感的情況下經(jīng)濟(jì)原則才能發(fā)揮其預(yù)期的效果,否則溝通失敗。
二、轉(zhuǎn)喻及類(lèi)型
轉(zhuǎn)喻(metonymy)在漢語(yǔ)修辭學(xué)文獻(xiàn)上又被稱(chēng)為“借代”,卽在同一認(rèn)知領(lǐng)域中,借用相關(guān)事物的名稱(chēng)來(lái)代替所要表達(dá)的事物。20世紀(jì)80年代以后,隨著對(duì)轉(zhuǎn)喻本質(zhì)和機(jī)制的研究,認(rèn)知語(yǔ)言學(xué)家認(rèn)為轉(zhuǎn)喻和隱喻(metaphor)不光是一種語(yǔ)言表達(dá)方式或是修辭手法,更是人類(lèi)的思維方式和認(rèn)知過(guò)程。陸儉明在《隱喻、轉(zhuǎn)喻散議》中認(rèn)為有隱喻,轉(zhuǎn)喻是“一個(gè)認(rèn)知域可以激活另一個(gè)認(rèn)知域”,其中激活又分為單一激活和疊加激活。單一激活,如:“見(jiàn)義勇為救兒童,不愧時(shí)代活雷鋒。”(崔喜躍,高洪順《一“名”驚人》)雷鋒在人們的心中是做好事不留名的代表,可以用“雷鋒”來(lái)激活樂(lè)于助人的精神。疊加激活,如:“他嘗試以毛澤東用理論指揮‘槍桿子’的辦法指揮‘筆桿子’。”(翟墨《藝術(shù)家的美學(xué)》)“槍桿子”是槍的一部分,用“槍桿子”這個(gè)部分來(lái)激活整體“槍”,再激活配備槍的人,卽士兵,軍人,泛指軍隊(duì),武裝力量。同樣,“筆桿子”是筆的一部分,用作為一部分的“筆桿子”激活整體“筆”,又由用筆激活用此進(jìn)行協(xié)作的人。
(1)整體—部分:“他說(shuō)他這輩子走遍了五湖四海從來(lái)是肩膀上站得人大腿上跑得馬,想不到老了會(huì)落下這樣一個(gè)名聲,睡到天亮還睜著眼睛拉了泡尿在床上“(陳世旭《喧囂與騷動(dòng)》)“五湖”“四海”是中國(guó)疆土中的一小部分,由此來(lái)激活全國(guó)各地這個(gè)概念。
(2)容器—內(nèi)容:“山雨欲來(lái),滿(mǎn)樓寂靜。”(《中國(guó)青年報(bào)》)“寂靜”不光指的是環(huán)境,更只處于“樓”這個(gè)處所的人無(wú)聲。
(3)領(lǐng)主—屬物:“我和奶奶在草坪的石凳上坐下,說(shuō)著,笑著,觀看一群紅領(lǐng)巾做游戲。”(倪立青《奶奶的牙齒》)用“紅領(lǐng)巾”激活配戴者少先隊(duì)員。
(4)物體—形狀:“然而圓規(guī)很不平,顯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國(guó)人不知道拿破侖,美國(guó)人不知道華盛頓似的,冷笑說(shuō):‘忘了?這真是貴人眼高……’”(魯迅《故鄉(xiāng)》)因?yàn)闂疃┱咀藰O像圓規(guī),故用“圓規(guī)”轉(zhuǎn)喻楊二嫂。
(5)事物—處所:“所謂農(nóng)村實(shí)行新生活運(yùn)動(dòng),據(jù)蔣介石說(shuō):‘各縣紳耆服務(wù)桑梓,協(xié)助‘剿匪’”。(榮孟源《蔣家王朝》)因古代人們習(xí)慣在住宅周?chē)N植桑樹(shù),梓樹(shù),后就用嗓梓借代故鄉(xiāng)這個(gè)處所。
轉(zhuǎn)喻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語(yǔ)言更加生動(dòng)有趣或者簡(jiǎn)潔,甚至于使某些詞增添新的義項(xiàng),比如說(shuō)“狐貍”“諸葛亮”等等,當(dāng)然使用過(guò)度的轉(zhuǎn)喻也會(huì)使人產(chǎn)生厭煩心里。
三、轉(zhuǎn)喻與語(yǔ)言經(jīng)濟(jì)原則
轉(zhuǎn)喻可以用舊詞轉(zhuǎn)喻獲得更多的所指,或說(shuō)使一個(gè)詞的意義得到擴(kuò)展、引申,在加強(qiáng)表達(dá)效果之上滿(mǎn)足了語(yǔ)言的經(jīng)濟(jì)原則。但不是所有轉(zhuǎn)喻都要用經(jīng)濟(jì)原則去固定衡量,只是某些轉(zhuǎn)喻是與經(jīng)濟(jì)原則密切相關(guān)。袁毓林在《漢語(yǔ)的概念轉(zhuǎn)喻及其語(yǔ)法學(xué)后果》中卻否認(rèn)了轉(zhuǎn)喻的“省略說(shuō)”。
首先袁毓林設(shè)定了“的”字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喻模式之一“S的M”,M是“S的”所修飾的名詞性中心語(yǔ),并否定“S的”不是“S的M”的省略形式,即否定“用較短的符號(hào)串代體相關(guān)的較長(zhǎng)的符號(hào)串,并且喚起較長(zhǎng)的符號(hào)串的意義”。他轉(zhuǎn)引了朱德熙的幾個(gè)例子,贊同說(shuō)其賓語(yǔ)位置上的“S的”后面補(bǔ)不出合適的中心語(yǔ)“M”。
先看其中的例a:孩子們有的[ ]唱有的[ ]跳。對(duì)比于袁毓林在前文所舉例子“紅的花”來(lái)說(shuō),“有的唱”“有的跳”根本就不是“S的M”的形式,而是“S的V”形式。再者,“有的”是指前文已經(jīng)提到的“孩子”,如果在“[ ]”后面再補(bǔ)出賓語(yǔ)“孩子”那句子就變成了“孩子有的孩子唱有的孩子跳”是不符合語(yǔ)法的。也就是說(shuō)這里所謂的補(bǔ)不出來(lái)賓語(yǔ)并不能證明省略說(shuō)在這里不成立,而是前文已經(jīng)給出了對(duì)象,再補(bǔ)出來(lái)就不符合語(yǔ)法或者說(shuō)是語(yǔ)用習(xí)慣了。最后,“S的M”只是“S的”中的一個(gè)類(lèi)型而已,也不能因?yàn)橥品恕癝的M”的省略說(shuō)而確定的認(rèn)為轉(zhuǎn)喻的省略說(shuō)不成立。
再看例子b:他年輕力壯,所差的[ ]是眼睛不太好。這根本就不是“S的M”形式,而且“[ ]”在袁的文中自己也點(diǎn)出來(lái)了可以補(bǔ)“方面”一詞,且說(shuō)了理由。但袁的理由是在讀者或者交際對(duì)象在看到或聽(tīng)到這個(gè)句子之前就已經(jīng)明了“眼睛”是身體的一部分,在看到這個(gè)句子時(shí)腦子里會(huì)有共識(shí),自動(dòng)補(bǔ)出“他所差的方面是眼睛不太好”,而不需要一定要把后面的東西補(bǔ)出來(lái),這就符合省略說(shuō)。袁轉(zhuǎn)引的其他例子同理,都正好可以證明轉(zhuǎn)喻與語(yǔ)言的經(jīng)濟(jì)原則是有關(guān)系的。
因語(yǔ)言的經(jīng)濟(jì)機(jī)制的作用使語(yǔ)言無(wú)可避免要受到時(shí)空的限制,而語(yǔ)境則可以對(duì)這種時(shí)空限制提供適應(yīng)和超越的條件,即語(yǔ)境是語(yǔ)言經(jīng)濟(jì)原則得以實(shí)施的保障。如依袁所說(shuō),把“S的”指稱(chēng)事物的語(yǔ)義功能歸結(jié)給底層的“S的M”,就是把“S的”存在的語(yǔ)境直接省略不計(jì),而“S的”到底指什么又需要依賴(lài)于語(yǔ)境,如果否定或省略語(yǔ)境,就無(wú)法使“S的”結(jié)構(gòu)表義準(zhǔn)確。再者像“有的唱”中“唱”這個(gè)動(dòng)作本身是指向人的動(dòng)作,只是需要前面的“孩子們”來(lái)確定或縮小“人”的范圍,可見(jiàn)在“孩子們有的唱有的跳”里面并沒(méi)有把“S的”指稱(chēng)事物語(yǔ)義功能歸結(jié)到“S的M”上,而是在前面的信息當(dāng)中。至于“跳”和“唱”則是人動(dòng)作的轉(zhuǎn)稱(chēng)或者是擬人修辭時(shí)采用的動(dòng)詞,也并不是“S的M”形式。
雖不是所有的轉(zhuǎn)喻都能體現(xiàn)語(yǔ)言的經(jīng)濟(jì)原則,但也不能因此否定所有的轉(zhuǎn)喻與語(yǔ)言的經(jīng)濟(jì)機(jī)制無(wú)關(guān)。而且某些轉(zhuǎn)喻不光能使語(yǔ)言更省力,還能達(dá)到不一樣的效果,比如說(shuō)網(wǎng)絡(luò)詞“囧”,本來(lái)囧指的是“窗戶(hù)”,引申為“光明”。因?yàn)椤皣濉钡淖中蜗駱O了人難堪,尷尬時(shí)的表情,所以用以轉(zhuǎn)喻“郁悶、悲傷、尷尬“等境遇。由此“囧”舊詞增新義,符合經(jīng)濟(jì)原則,而且把人的境遇表達(dá)得更加形象詼諧。總之,筆者認(rèn)為轉(zhuǎn)喻與經(jīng)濟(jì)原則的關(guān)系是不可否認(rèn)忽略的,需要我們用更多的實(shí)用語(yǔ)料對(duì)這個(gè)問(wèn)題進(jìn)行更多的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