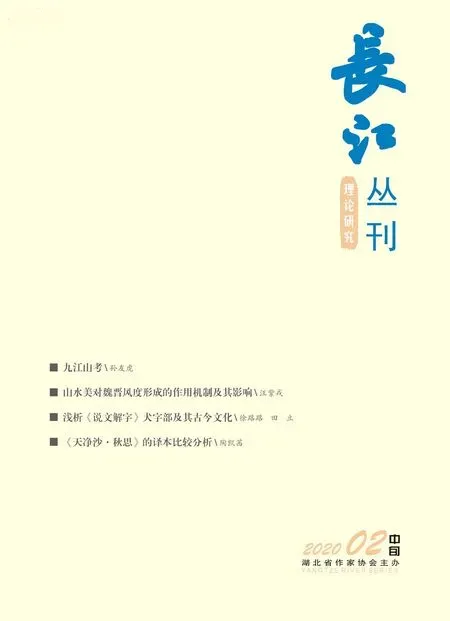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祿豐縣高峰鄉火把節大刀舞形態變遷研究
■陳 蕊 李索菲 周海韻 王 旭 李 穎 思 思/吉首大學
一、前言
本文主要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相關理論對大刀舞與楚雄州高峰鄉彝族火把節的關系、儀式中傳統舞蹈文化的變遷進行闡釋分析,擬通過文化現象本身的表現形式、象征主題、價值功能等,反思優秀傳統文化自身的生命力,與舞蹈文化變遷背后隱藏的權力、歷史、文化等種種力量間的博弈。
二、文化表演
通過在羊街鎮與高峰鄉兩個田野點的考察,我們了解到,傳統的民間儀式現在已經轉變為由有關部門主辦或與民間合辦的形式,且整個儀式的流程受經費等各方因素影響而越來越趨于簡單化,大刀舞在這樣的條件下雖然在儀式過程的演變中“存活”下來,但其已由展演的形式進行表演,其排練過程、表演人員的構成、表演的具體動作等均發生改變,因此,大刀舞的形式、內容與意義其根本已發生變化。
由于天氣與交通的原因,我們未能到達羊街鎮平安村進行大刀舞的考察,因此我們把大刀舞的研究重點放在了高峰鄉的火把節上。高峰鄉節日氣氛濃厚,群眾廣泛參與。節日在遵從傳統習俗的原則之下由有關部門進行主導。除了每三年的大過火把節之外,在小過時大刀舞就成為展演。有關部門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儀式的完整與順利進行,但這種權力關系也間接的影響了大刀舞的進行,在現代展演中大刀舞動作與調度的語義已經缺失,其實質變成了一種表演;而隨著女性的介入,可看出其儀式及舞蹈原有的嚴肅性、神圣性已然被打破。
三、同源異流背后的博弈
據普順發老人介紹,解放后在高峰鄉、廣通縣、武定縣的倉底村都有大刀舞遺存,現在除了祿豐外其它地區都已失傳。據本小組搜集資料粗略考證,倉底村、平安村、高峰鄉的大花菁、小花菁村目前均有大刀舞遺存。
據羊街鎮文化站站長楊光華介紹,當地平安村大刀舞保存較完整,且平安村應為大刀舞的發源地,其他地區是之后才傳過去的。高峰鄉文化站站長李美紅則認為,羊街鎮的三個面具上全部畫有龍圖騰,正是說明其不夠“純”,因為紅彝族的圖騰是虎,而普順發所繪制的代表“天、地、人”的三個大面具上,只有代表“地”的面具上畫的是龍,而代表“天”的面具上畫的正是紅彝族圖騰——虎。在之前所查的資料中顯示,大刀舞的起源主要有三種說法,而在當地進行進一步考察、訪談之后,我們可以看出,有關大刀舞起源的說法均不一致。我們可以追究的是,大刀舞在當地造成了一種文化資源所有權的競爭,權力背后所代表的地方文化在新的層面展開了博弈。
四、外界環境的制約與民族傳統儀式和精神信仰的傳承之間的關系
外界環境對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精神信仰的制約原因如下:
(一)經濟方面
當地家庭平均年收入3000元左右,經濟形式較為單一,以種植玉米等農作物為主,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自給。當地的經濟來源以烤煙為主,但如果烤煙收成不好,一家人基本的生活就無法保障。物質基礎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如果基本需求都無法得到保障,那大刀舞的傳承就產生了阻礙,民族傳統的儀式就難以得到延續。近些年過節的經費基本都由有關部門承擔,兩年小過要幾萬,三年一大過就得耗資幾十萬之多。我們在高峰鄉的火把節上了解到,本次文化站文體宣傳組舉辦的火把節總共花費14000元。一方面原因是國家提倡節約,但另一方面還是可看出這一地方的經濟能力已經很難再支持大型的活動。活動的舉辦需要經費的支持,由于經費的縮減,所以火把節上的很多活動儀式都在簡單化,盡管工作者在努力將最核心、最傳統、最具代表性的儀式活動保留下來,但還是無法控制大刀舞和火把節文化傳統的逐漸“凋零”。由于地方的信息、交通閉塞,拉動經濟能力較慢,人民生活水平不高,35歲以上的人都不愿留在當地,紛紛外出打工,這樣導致傳承大刀舞的人越來越少。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對于處于較為貧困的鄉鎮來說,要促進和發展當地經濟,改善落后局面,最快捷的方式就是發展旅游事業。但旅游業是一把無形的雙刃劍,當這一地方旅游業發展起來之時,當地的文化也會隨之商業化。民間的許多優秀傳統文化都會為了迎合旅游業而改變來滿足現在人們的需求,如此想感受“原汁原味”的大刀舞和火把節氣氛就更難了。
(二)人為因素
最具話語權的普順發老人生於1936年,今年已79歲高齡,而大刀舞的套路共有72套,傳到老人這里只剩下12套。這12套中有兩套高難度的動作普順發已完成不了,在采訪老人時他堅持為我們表演了兩套大刀舞,每表演完一段老人都需要歇一會兒。因膝蓋不靈便,老人在表演時動作較緩,其中快速的蹲下、出腿、換腿的動作,老人在完成時較為困難,因此我們大部分只采取口頭采訪的形式,并沒有繼續讓老人進行表演和錄制。老人的徒弟共有40余人,但由于個人資質、毅力、興趣程度、經濟情況有別,到目前為止,只有老人的大徒弟掌握套數最多,其可跳八套大刀舞。由此看,對于大刀舞套路的傳承將會日趨漸弱。隨著社會的發展,鄉村社會、地方文化絕不是封閉狀態,當地人享有網絡等與外界同樣的資源,在現代化的沖擊下,人們的獵奇、盲從心理可能導致優秀傳統文化被冷落,導致大刀舞在沿承道路中異常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