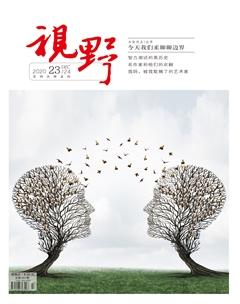在古代當(dāng)捕快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體驗(yàn)?
李媛
影視劇中的捕快跟歷史上的真實(shí)情況是一樣的嗎?在古代當(dāng)捕快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體驗(yàn)?
捕快那些事
要當(dāng)捕快,得先弄清捕快的“職位描述”“日常工作”和“任職要求”。
古代的捕快,屬于衙役,是衙門里少不了的跑腿辦事的勤雜人員,負(fù)責(zé)當(dāng)?shù)匦姓?quán)力的執(zhí)行,算是執(zhí)法和行政的主力。從重要性來看,衙役名列前茅,但從地位看,衙役基本是地位最低的一群人:沒有官方身份, 即沒有編制,只算是為衙門服役。
以明清州縣衙門為例,衙役分四班,即皂、捕、快、壯班(也有學(xué)者稱分為三班衙役,不包括捕班,或捕、快合一)。各班都有班頭,也叫頭役,統(tǒng)領(lǐng)本班。《水滸傳》中的武松在陽谷縣就是擔(dān)任這種班頭。四班之外,還有零星雜役,包括門子、禁卒、仵作、庫丁、倉夫、斗級(收糧掌斗)、轎夫、傘扇夫、鳴鑼夫、吹鼓手、燈夫、更夫、伙夫、馬夫、鋪兵(郵驛)等等。
這么多種類的衙役都對應(yīng)著什么樣的工作職責(zé)呢?
皂班的職責(zé)是前驅(qū)護(hù)衛(wèi)和儀仗,知縣升堂辦案時執(zhí)行刑訊拷笞;
快班分為馬快和步快,職責(zé)是巡夜、傳喚、逮捕,問案時到庭供長官驅(qū)使,還會被派出到鄉(xiāng)下催征賦稅;
捕役的職責(zé)是偵查案件,緝捕盜賊,也同快班一道巡夜,押運(yùn)官銀時充當(dāng)護(hù)衛(wèi);
壯班的職責(zé)是守衛(wèi)糧倉金庫和監(jiān)獄,護(hù)送官銀或罪囚時,也充當(dāng)雜差;
門子掌管儀門(衙門中正門與正堂之間的門,正官升堂辦公,須關(guān)閉儀門),叫升堂,喊人犯,掌管發(fā)令竹簽。
其余零散衙役的職責(zé)大多從名字就可以判斷出來。
了解捕快的“職位描述”和“日常工作”后,我們來看看衙門對捕快的要求。古代生活史專家倪方六曾說:“只要是手腳利索、腦子好使的都能當(dāng)捕快,從目不識丁的農(nóng)民到有前科的小混混,都能做,因此捕快的素質(zhì)整體來說是不高的。”
此外,衙役的身份分兩種:良民和賤民。民壯、庫丁、斗級、鋪兵為良民,皂、快、捕、仵、禁卒、門子為賤民。可以看到,這些身份為賤民的衙役才是我們所認(rèn)知的捕快主力,所以,捕快一般是由素質(zhì)并不很好的賤民擔(dān)任。而賤民身份的衙役一旦從業(yè),其三代不能參加科舉,也不準(zhǔn)捐納買官,所以有些家庭嚴(yán)禁子孫從事衙役。
但是,除了官戶和縉紳外,其余百姓都要服役納稅,而衙役可以豁免或逃避徭役,在官府辦事還可以照顧本家和三親六故。
行文至此,也許你會有個問題——為什么對衙門來說這么重要的職位,要由賤民來做?
因?yàn)椴犊旄傻幕顑海诠湃丝磥恚且环N得罪人的活計(jì):總是要抓人拿人,總是跟壞人壞事打交道,所以只能讓賤民做。
在古代,當(dāng)捕快大概是一種美夢逐漸破滅的體驗(yàn)吧。沒有編制福利不說,工資還不高;工資不高就算了,至少能庇護(hù)家人,但卻影響了長遠(yuǎn)發(fā)展,成了賤民,家人三代不能入仕。有選擇的情況下,大家應(yīng)該還是會選擇科舉和從軍,衙役說到底是無路可走的人去混口飯吃而已。
捕快的生財之道
也許有人會問,捕快待遇這么差為什么不辭職呢?而且感覺在老百姓眼里他們很厲害,看起來也沒那么窮?
那再來說說捕快為什么不辭職,答案其實(shí)就在后兩個問題里:他們被百姓畏懼,就可以借機(jī)搞自己的生財之道,有錢自然就不愿意辭職了。
為什么老百姓怕他們?他們的錢怎么來的?對百姓而言,可以不認(rèn)識遠(yuǎn)在天邊的皇帝,但近在眼前負(fù)責(zé)縣里日常治安的捕快大家必然都是知道的。
百姓對捕快的感觀還來源于其具體職能。皂班負(fù)責(zé)刑訊拷笞;捕役緝捕盜賊的刑罰權(quán)力讓人們不自覺地畏懼;再者,捕快的整體素質(zhì)并不高,像無賴一樣無常的捕快來負(fù)責(zé)刑訊和緝捕盜賊,總有種一言不合就會套罪抓人的既視感,老百姓定然也深怕自己觸了霉頭被抓。
說到捕快怎么獲取錢財,其實(shí)就是詐百姓、收賄賂。
宋人沈夢溪說:“天下吏人,素?zé)o常祿,唯以受賕為生。”一般州縣認(rèn)為,衙役辦差向當(dāng)事人收取的車費(fèi)、驢費(fèi)、鞋襪費(fèi)和飯費(fèi)茶水錢都屬于“正常收費(fèi)”,只是不準(zhǔn)借機(jī)勒索敲詐,這說的就是一般的收費(fèi)由頭了,多數(shù)衙門的規(guī)費(fèi),屬于書吏和衙役分享。
只要派差,就能得到規(guī)費(fèi)或賄賂。舉個例子,一樁殺人案,從勘查現(xiàn)場到審結(jié)案件,各種規(guī)費(fèi)可達(dá)數(shù)萬錢。捕役由于發(fā)案不規(guī)律,沒有案件時就沒有額外收入,所以主要從娼妓戶和宰牲戶收取陋規(guī)。這樣一來,小地方的捕役,缺乏規(guī)費(fèi)來源而生活像乞丐,而大城市的捕役,則因收費(fèi)花樣繁多而十分滋潤。有的衙役,陋規(guī)收入一年甚至能有數(shù)千上萬兩銀子。
再舉個例子,清朝方苞在《獄中雜記》中稱:同樣三個人受刑,一人花了三十兩銀子,被打傷骨頭,躺了一個月才好;另一個人花了六十兩銀子,打傷的是皮肉,二十多天恢復(fù);第三個人花了一百八十兩銀子,挨打的當(dāng)天晚上就能像平常一樣散步。方苞問這些衙役:既然都花了錢,為什么挨打輕重不一樣?衙役回答說:如果一樣,誰還會多給錢?
即使進(jìn)了班房,有錢和無錢的待遇也大不一樣。所以,不管地方政府有什么公務(wù),到衙役手里總能生出撈錢的法子來。可以說,收陋規(guī)的方式和理由只有我們想不到?jīng)]有他們做不到。
此外,衙役之間,或者說是衙門的上下級之間也存在私相授受,基層貪腐總會有個上下庇護(hù),不然貪污者早就被揭發(fā)了。《歷代判例判牘》第三冊《四川地方司法檔案》中記載了一個普普通通的官場弊案,案子規(guī)模不大,案情也不復(fù)雜,但正因?yàn)樘^平常,反而具有普遍意義,成為窺探盛世王朝全貌的青萍之末。案件發(fā)生在大明嘉靖年間,成都府下轄的彭縣,節(jié)選的一小部分故事的主角是吏和衙役。
先說一下明朝時縣衙的組成:縣衙里最大的是知縣,叫主官;縣丞和主簿是他的副手,都是佐貳官。三人之下有位首領(lǐng)官,負(fù)責(zé)辦公室典史,是個書吏;再往下就是衙門內(nèi)最重要的行政機(jī)構(gòu),三班六房。三班就是指皂班、壯班、快班,有時候還會多一個捕班,和快班合在一起,就是老百姓熟悉的“捕快”;六房對應(yīng)的是朝廷六部,分為禮、吏、戶、工、兵、刑六個部門,各有主管業(yè)務(wù)。除此之外,還有承發(fā)房和架閣庫等辦公機(jī)構(gòu)。在這些機(jī)構(gòu)里辦事的人,統(tǒng)稱為吏,也叫胥吏或吏胥。
故事的開始是一個叫陶成的當(dāng)?shù)厝诉M(jìn)入彭縣縣衙,成為吏房的一位書手。這個職位顧名思義,就是負(fù)責(zé)各類公文檔案的書寫、抄錄。聽起來挺枯燥瑣碎,但里面有很大的門道——古代公文全靠手寫,狀紙、官職申報材料等等,他筆一揮墨一灑,改幾個字就會影響別人的命運(yùn)。
四年之后,陳佐也加入了彭州縣衙,他在戶房擔(dān)任算手。戶房主管錢糧賦稅,和吏房書手差不多,也是只需在賬簿上做一點(diǎn)點(diǎn)手腳就能讓農(nóng)戶生不如死。比如在納稅時,將田地等級改一改,農(nóng)戶要繳納的田稅就不知道翻了幾番,農(nóng)戶想避免這種事,基本只能指望銀子。書手和算手都是胥吏的一種,沒有官身,工資少得可憐,他們摸清衙門的門道之后,就利用這些見不得光的路子大量斂財。他們作為本地人,比上官更熟悉地方情形和法令文牘,又把持著具體的政務(wù)事項(xiàng),很容易從中做手腳,有時候日子過得比主官還滋潤。
兩人為了能放心操作,不約而同地拜了縣衙的二把手屠主簿當(dāng)靠山,尋求庇護(hù)。之后陳、陶兩人很快勾結(jié)到一起,“各結(jié)攬寫法,討錢使用”。
陳、陶二人是衙門里衙役的上一級胥吏,雖然沒有編制,但是比較穩(wěn)定,因?yàn)轳憷敉鞘来嗬^的。胥吏索賄就是從僉派人員填補(bǔ)役期已滿的衙役開始。這個行動由戶房負(fù)責(zé)查詢戶籍輪值表,確定應(yīng)役人選;吏房負(fù)責(zé)登記造冊。也就是說工作被交由陶成和陳佐兩人完成。
僉派名單里有一個叫劉選的平民,他被安排去做快手,就是前面提到過的快班,巡夜、傳喚、逮捕還要去鄉(xiāng)下催收賦稅的衙役。劉選不想做快手,因?yàn)榭傄甲咛^勞累,但是又不能拒絕服役安排,于是他找到了陶成、陳佐二人想尋求其他解決辦法。這基本就是送上門來的索賄人選,陶、陳二人協(xié)調(diào)后讓一個叫劉本敖的閑漢替劉選去做這個差事。作為給劉本敖的報酬,劉選每個月要出三斗米、三錢白銀;至于陳、陶二人,雖然沒有記載,但可想而知他們一定收了不少賄賂才會愿意為劉選奔走。
對劉本敖而言,快手是他撈錢的好機(jī)會:衙門發(fā)現(xiàn)某戶人家牽涉官司后會發(fā)下牌票——一張寫好事由和日期,簽好押、印好官印的執(zhí)法憑證。劉本敖拿著這張牌票,就可以去農(nóng)戶那訛詐錢財。《官箴書集成》里的記錄更加直白:“每一快手一二十兩,賄買戶書寫就。蓋快手借票催糧,原非為催糧計(jì),不過借印票在手,無端索害鄉(xiāng)人。農(nóng)民多不識字,又多良善之人,彼即有完票在家,快手欲無端害之,幾十里外向誰分訴?一張票,乃一快手幾年生活也。”
此案件苦主(原告)是一位農(nóng)民,因其他農(nóng)戶與書吏快手等的私相授受,被坑到一個人承受好幾倍的賦稅,被逼無奈越級上告縣衙的衙役和官員,最后,縣衙內(nèi)的貪污者都被徹查得到了應(yīng)有的懲罰。礙于篇幅,不再贅述其情節(jié)。
總而言之,在古代,除非是服役需求,普通百姓一般都不會去做捕快。如果真要回到古代謀職,考科舉做正兒八經(jīng)的官可比捕快香。說白了,捕快并不是一個實(shí)現(xiàn)抱負(fù)的好職業(yè)。
十三摘自微信公眾號“國家人文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