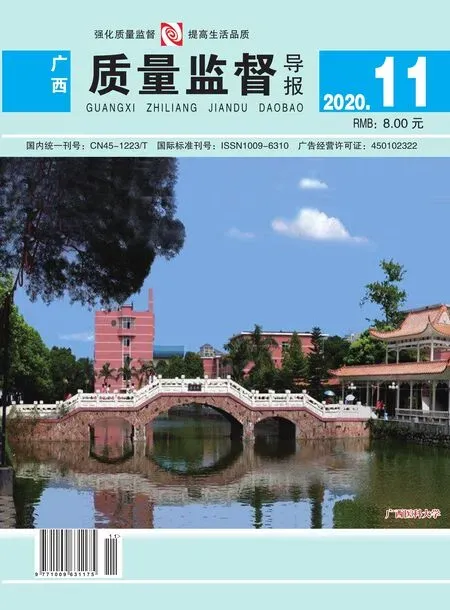金融化文獻綜述
于 根
(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 北京 100081)
一、1970到次貸危機前的西方金融化研究
西方經濟實務一直在自由化和國家干預二者之間循環。自從亞當斯密《國富論》出版以來,西方倡導自由經濟政策,直到1929年大危機和凱恩斯1936年《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發表,西方改為實現國家干預政策,并在二戰后迎來了一段黃金時期。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方經濟出現滯脹危機,在商品市場上,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高漲,使西方實體經濟受到重創;貨幣市場上,1971年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不再兌現黃金,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經濟金融風險迅速擴大。這時,自由主義重新抬頭,力求走出滯脹危機,此時,麥金農和肖1973年提出的金融抑制理論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理論。他們認為1929年危機后開始的國家干預政策,對金融管制過嚴,被嚴重束縛的金融對經濟支持不足,拖累了經濟的正常發展,他們主張金融業放松管制(deregulation),實行金融深化政策,為經濟提供更多支持,是自由化政策的當時代表。他們提出的具體政策是反對利率管制,提倡金融自由化,實現利率出清。較高的利率可以促進儲蓄,抑制企業投資低收益項目進而提高投資的質量,投資效益提高促進經濟增長。
伴隨著自由化、信息業等新經濟形態和各種金融創新的出現,西方走出了滯脹危機,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一詞在學術界廣泛出現,戈德史密斯1994年構造了金融相關率FIR=金融資產總值/經濟活動總量這一指標,王廣謙1996認為經濟金融化指一國國民經濟中貨幣與非貨幣性金融工具總值與經濟產出總量的比值提高的過程,即FIR提高的過程,這是對宏觀層面的金融化的主流學術定義。他統計發現,不論是美英法德日五個發達國家,韓國泰國等比較發達國家,印度巴基斯坦等欠發達國家,經濟金融化的趨勢都在增強(見表1),金融化是世界上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象。秦曉2000年提出麥金農和肖提出的金融深化是金融化的濫觴,本文支持這個觀點。王芳2004提到度量金融化不僅有規模指標,還有結構性指標、滲透度指標和效率指標,提出不僅要探究金融化的數量指標,還要研究質量指標。

表1 各國金融化趨勢
至于金融化的動因,早在1966年,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在《壟斷資本》中已經提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實體經濟中盈利性的投資機會日益減少,剩余利潤需要尋找投資機會,而金融創新創造的諸多金融產品成為了投資場所,因此金融化趨勢不斷增強,這個觀點可以追溯到卡爾·馬克思的理論觀點,總結起來是實體和金融業利潤率的剪刀差導致了金融化不斷加強。和自由化基本同時,美國公司治理領域發生了股東價值革命,過去可能以追逐利潤為公司經營目標,股東價值革命指股東是公司的所有者,公司經營目標應該是為股東創造價值,在這種思想指引下,公司普遍出現從“重積累輕分紅”到“重分紅輕積累”的轉變,這無疑會進一步促進金融化的增強。
至于金融化對經濟的作用,學界并不一致。宏觀層面,戈德史密斯1969使用35個國家的樣本發現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一般同時發生。King和Levine1993較早的分析了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在控制其他效應的情況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顯著正相關。微觀層面,Rajan和Zingales1998使用交叉項檢驗發現對外部資金依賴度越高的行業金融發展對其發展的促進作用越顯著。Wurgler2000引入了行業投資額對行業規模的彈性—投資彈性這一新概念,顯然彈性越高的行業投資水平更高,更有利于經濟增長。他的研究發現金融發展顯著提高投資彈性。Love2003發現金融發展顯著改善中小企業融資狀況。
持相反觀點的研究也十分豐富。金融發展領域的權威學者Levine2003對“金融體系更發達的國家經濟增長更快”持懷疑態度。譚儒勇2004認為盡管現有實證研究大多支持金融有利于經濟增長的觀點,但由于假設條件過于嚴格、實證方法和數據的缺陷,金融發展必然促進經濟增長的觀點過于絕對。本文認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很難說清,即使有因果關系,誰是因誰是果也難以確定,不可武斷認為金融導致經濟發展。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難以確定,但金融過度膨脹導致泡沫放大進而引發金融危機的危機制造者的嚴重后果基本得到普遍認同,2008危機是最近的證明。
二、次貸危機后的西方金融化研究
亂后思治是人類的通常行為,對于次貸危機的重創,西方學術界顯然要研究危機的原因和應對之道,危機中破產的幾家金融巨頭眾所周知,因此,金融化問題的研究在危機后理論上應該變得更為豐富。學界普遍認為金融化,金融部門的過度膨脹,過度金融創新,金融風險的積聚是2008年危機的重要原因。
更微觀地研究金融化,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部門的金融化:金融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居民部門。金融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膨脹,可以算是金融化最經典的形式;居民部門將大量財產投資于金融領域,也是當代很明顯的現象;非金融企業部門的金融化是一個比較新穎的問題,也是一個學術爭議的焦點。非金融企業金融業占企業總經營的比重不斷提高,是這種金融化的表現。鄧迦予2014把這種金融化用三個指標量化出來;從資產負債表的角度,金融資產占企業總資產的比重,是金融化的度量指標,這是一個存量的指標;從現金流量表的角度,金融投資占據企業投資資金總量的比率,也可以表示金融化的程度,這是年度的流量指標;從利潤表的角度,金融經營利潤占公司總利潤的比例,這個流量指標是第三個度量金融化的指標。
金融部門的擴大,居民資產中金融產品占比的擴大,和宏觀經濟關系緊密。金融業的高利潤率是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當然實體經濟疲軟是這個問題的反面。而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的原因,更加復雜。金融實體兩大部門利潤率的剪刀差是一個主要原因,而70年代以來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創新,實體經濟創新乏力、增長疲軟是這個剪刀差的背后原因。第二,股東價值革命和委托代理問題使企業傾向于裁員高分紅而不是留存再投資,看中短期利益而不是長期發展,這必然導致金融活動的擴大。從資金來源角度,美國等發達國家可以實現產業轉移,控股海外企業,利用發展中國家的低廉成本維持高利潤率,這樣發達國家積累了大量剩余利潤,而實體企業優良投資機會日益罕見,進入金融業購買各種金融工具成了這些國家企業的重要選擇,金融化因此不斷擴大。
至于金融化是好是壞,它對經濟社會的作用如何,是一個重點問題。金融部門和居民部門的金融化,學界普遍用適度原則解釋。金融業的適度發展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率,管理風險,服務實體經濟。而過度發展,積累金融風險,一旦出現最后壓垮駱駝的那根稻草(比如2008年的雷曼兄弟公司破產),爆發金融海嘯,必是一場災難。而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可以分為好和壞兩種效應。非金融企業需要資金支持,加上金融可得性造成的融資約束等問題,有必要持有部分流動性金融資產以應對流動性問題,這在凱恩斯的預防性動機學說中已有體現,這可以稱為蓄水池正效應。此外,當代自由化經濟中風險頻發,企業有必要進行風險管理,因此購買金融資產很有必要,而19世紀70年代以來的金融創新的初衷也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進行風險管理,保證財務安全,這可以稱為風險管控正效應。至于負面效應,非金融企業大量涉足金融業,“不務正業”,“擠出”了非金融企業主業經營活動,創新乏力,實體不斷變弱,與此同時,顯然當代金融市場遠遠偏離了最初風險管理的初衷,進行過度金融創新、投機賭博的成分占相當比例,最終泡沫破滅后的危機是災難性的。
三、近年來我國的金融化研究
鄧迦予2014年的文章提出了三個定量度量金融化的指標,同時得出結論中國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程度不高,也沒有表現出很強的增長,但這是根據2012年以前的公司數據得到的結論,而經濟環境現在與當時差別巨大,表現為三點。一是宏觀經濟增長放緩,2002到2011十年中國GDP增長率都在9%以上,最高達14.23%,如此強勁的實體經濟金融企業自然不會向金融業轉移,而2012年以來,經濟增速放緩,實體經濟疲軟,大量僵尸企業、落后產能問題凸顯,非金融企業的生存環境發生巨變,進入金融業等其他行業牟利有了條件。二是樓市的瘋漲,以及中國放開部分金融業準入門檻,樓市投資盈利難度低,數額大,風險小;中國金融業高利潤眾所周知,本文統計,2019年財富中國企業五百強中,僅工農中建四大行和平安保險五家企業占500強利潤總額的28.7%,巨大的利潤份額和準入放松,必然吸引非金融企業進入。三是中國貨幣超發量巨大,2011年以前中國貨幣發行量增長也很高,但是與經濟高速增長同步,是多發而不是超發,近年來,經濟放緩而貨幣發行量增長速度并未減緩,有大量流動性無法為實體經濟吸收,房地產和傳統金融業的增長有了資金基礎。因此,近年來中國金融化問題成為學術熱點,有經濟環境的支持。
對于中國而言,金融業和居民部門的金融化與西方不同。中國金融創新不足,金融產品不很豐富,居民部門進行金融投資的環境不佳,當然房產投資是中國居民部門的熱門選擇。金融業整體上管制嚴格,近年來的開放廣度深度還有限,因此中國金融部門的規模受政策影響很大。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不論在實務上還是學術上,都是重點問題。中國實體經濟還未完全實現現代化,因此金融化擠出實業,阻礙技術升級,對中國經濟傷害更大。此外,中國企業普遍分紅較低,企業處于成長期,還沒到股東價值導向的公司治理結構。如果非金融企業進行金融資產配置的原因不是風險管理或流動性預防,而是離開主業進入金融牟利,顯然對中國經濟長期向好不利。這需要學術界的進一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