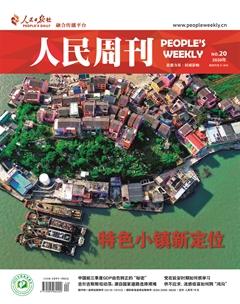96歲的葉嘉瑩:把不懂詩的人接到詩里來
近日,葉嘉瑩的紀錄片《掬水月在手》上映,這部跨越百年私人記憶的“詩意紀錄片”,至今豆瓣評分高居8分以上。
詩人席慕蓉直言“她就是詩魂”;詩人痖弦稱贊葉嘉瑩是“穿裙子的士”;作家白先勇稱“葉先生是引導我進入中國詩詞殿堂的人”。
教書數十載,桃李滿天下,葉嘉瑩在人生的晚年賣掉京津兩處房產,又將自己的稿費、版稅收入悉數捐出,累計捐贈3568萬元,在南開大學設立“迦陵基金”,都讓她為傳統文化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接受記者采訪時,葉嘉瑩說,導演起的“掬水月在手”很有詩意:捧起水來,水里有月亮的倒影;但那不是真實的自己,只是水中的一個影子。
葉嘉瑩,究竟是何許人也?
以熱忱,敬初心
很多人都知道,葉嘉瑩有著中國古典詩詞研究專家的身份,受聘于臺灣大學、哈佛大學等多所大學任教;她是加拿大皇家學會唯一的中國古典文學院士,也是2015至2016年度“影響世界華人大獎”終身成就獎的獲得者。
但浮和沉,名與利,都不是她追求的東西。這些頭銜,也不足以概括她跌宕的人生。
1924年,葉嘉瑩出生在北京的一個書香世家,是葉赫那拉氏的后裔。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后,面對北平的淪陷,葉嘉瑩寫下了悲痛的詩句:“盡夜狂風撼大城,悲笳哀角不堪聽。”
1948年葉嘉瑩南下到南京結婚,不久隨丈夫遷居臺灣,并在臺灣生活了18年。
日本占領時期,母親因手術意外去世;大學畢業后不久,解放戰爭爆發;南下臺灣后,丈夫因白色恐怖遭到政治迫害。20世紀中期,葉嘉瑩輾轉執教于臺灣大學、輔仁大學、淡江大學。
1954年,只有中學語文教學經歷的葉嘉瑩受聘于臺灣大學。若以論文著述為錄用標準的話,她不夠資格。時任臺大中文系主任臺靜農后來回憶,當年邀聘葉嘉瑩到臺大任教,是因為看到了她“所作的舊詩,實在寫得很好”,所以“就請了她”。
1969年她遷居加拿大溫哥華,受聘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
1978年,聽聞中國恢復高考,已在加拿大教書多年的葉嘉瑩向中國政府申請回國。一年后,她收到了中國教育部批準回國教書的信,安排她先去北大教學,不久,又應李霽野先生之邀去了南開大學。
1979年起,她每年利用假期回國講學。2013年,因年老不能再越洋奔波,決定正式回國,定居南開大學。
她一生致力于古典詩詞的教學,獲得了使古典詩詞于當代“再生”的贊譽。
葉嘉瑩最近一次公開露面是在9月10日,96歲的她例行給南開大學新生講開學第一課。坐在輪椅上,她中氣十足,調侃自己的頭發竟變黑了一些。
她習慣站著講課,一站就是兩三個小時。但現在,她從家里的沙發上起身都需要保姆攙扶。她說自己“生命已在旦夕之間”,但仍要努力做到杜甫說的“蓋棺事則已”那一刻。她每天手寫論文、指導學生整理超過2000個小時的講課錄音。
哈佛、耶魯等上百所高校都留下過她講課的身影。剛回到南開講課時,她的課,教室里要加座,凳子椅子一直加到了講臺上,還有人靠墻邊窗口站著,或坐在地上。數學家陳省身、吳大任夫婦也和學生擠在講臺下。
她在臺灣教書時也是這種場面。后來,她帶著詩詞講遍了半個地球。
她沒有大學者高高在上的架子。她給幼兒園的孩子講詩,也給學者、院士、工人和家庭主婦講。92歲那年,她挑選了218首古詩詞,給兒童作古詩讀本,轉年又為這些詩詞錄制了講解和吟誦。
91歲時,她還在70平方米的住宅里給研究生上課。博士生、碩士生,加上來旁聽的人,坐在塑料小矮凳上,每堂課有二三十人。后來,課程和講座的視頻被整理出來放到網上,她一下子成了講詩詞的“網紅”。
她要把“自己親自體會到的古典詩歌里邊美好、高潔的世界”告訴年輕人,她希望能把這扇門打開,讓大家能走進去,把不懂詩的人接到里面來。
以理想,傳詩詞
葉嘉瑩說:“其實我一生經過了很多苦難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來,我卻一直保持著樂觀、平靜的態度,這與我熱愛古典詩詞的確有很大的關系。”
“現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為被一時短淺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認識詩歌對人的心靈和品質的提升功用,這是一件極可遺憾的事情。如何將這遺憾的事加以彌補,這原是我這些年來的一大愿望。”
定居臺灣時,丈夫因思想問題入獄。葉嘉瑩抱著幼小的女兒寄居在友人家的客廳里,寫下“剩撫懷中女,深宵忍淚吞”。為了老父和兩個讀書的女兒,她辛苦教書維持整個家庭,極盡忍耐。
王安石的《擬寒山拾得》把她從悲苦中提振了起來。“眾生造眾業,各有一機抽”一句,如當頭棒喝。她跟自己說,要把精神感情完全殺死,殺死了,就不再為它煩惱。
1969年葉嘉瑩攜全家遷居加拿大溫哥華。1976年3月24日,長女言言與婿永廷以車禍同時罹難,又一次給了她沉重的打擊。料理完女兒女婿的后事,她閉門不出,日日哭泣,寫了10首哭女詩。
“平生幾度有顏開,風雨逼人一世來”“痛哭吾兒躬自悼,一生勞瘁竟何為”,她嘆命運不公,反思勞瘁一生的意義。
經此一難,葉嘉瑩突然覺悟到,“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一個終極的追求和理想。”1978年,她開始向中國政府申請回國教書。
聽過葉嘉瑩講座的學生覺得,葉先生先“降低了詩詞賞析的門檻,又手把手領著人進來”。“她講詩是結合著自己生命的經歷,是與生命相融會的感發。”比如葉先生講杜甫的詩,講到‘國破山河在,她是真正體驗過的——七七事變后,北平淪陷,吃混合面,穿補丁衣,學校更換了教師,英文課程改上日語課,她們在教室按要求把歷史、地理課本逐頁撕毀涂抹。
葉嘉瑩說自己“好為人師”,因為急于把自己所知道的詩詞里的好處告訴別人。
她閱讀涉獵廣泛。中國的、外國的,文學的、心理學的,經典的、暢銷的,她都看。
受聘于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20年間,葉嘉瑩幾乎每天開車經過西南海邊大道。大道右邊是高高的森林,左邊是住宅區,越過住宅區,是廣闊無邊的太平洋。退休之后,只要從中國講學回來,她仍每天風雨無阻地在這條路上往返,去亞洲圖書館看書、研究、撰寫新的論著。除了午飯時分到休息室吃自帶的三明治和水果,她要待到圖書館關門才離開。
她在海外查著英文字典教書,英文提高了,就去聽西方人的課,借西方文學理論的書。她發現西方文學理論中有的說法與中國傳統詩論有暗合之處。
葉嘉瑩指出:中國傳統文論,需要以西方的新理論來補足和擴展。
以此生,許詩學
葉嘉瑩為她一生獲得的學者、教師和詩人等眾多名號排了個序,說大半生的時間都用于教學了,所以首先是教師,其他的都排在這后面。
“我天生就是一個教書的。”葉嘉瑩說。從1945年大學畢業至今,她在講臺后站了整整70年。
初回南開,葉嘉瑩白天講詩,晚上講詞,堂下座無虛席。她寫下了“白晝談詩夜講詞,諸生與我共成癡”的句子。
詩詞幾乎是葉嘉瑩生活的全部,尤其現在當她孑然一身邁入老年,給年輕人講課成了她最愿意做的事。只要有人邀請,她都欣然前往。30多年來,她曾經應邀到國內幾十所大學講學,舉行古典詩詞演講有數百場之多。
當被問及,為何在如此高齡,還要堅持推廣普及古詩的吟誦時,葉嘉瑩這樣說:“因為我覺得我對不起年輕人。以前我上課大多是在講批評啊講欣賞啊,但是我沒有教吟誦。近代之后,吟誦被認為是腐朽落寞的文化,逐漸不被提倡。離開臺灣后,我覺得吟誦要是斷絕了真的可惜。不留下正統的吟誦,我覺得對不起下一代的學生。”
她講心與物相感的關系,是中國傳統詩詞的“比興”,是西方現象學所說的主客體之間的相互關系。
她講秦觀填詞的用字和內心的敏銳時,提出希利斯·米勒的觀點——不管小說的內容有多少不同,他總能在不同故事、情節和風格之中,找到作者的本源。她因此解釋用詞源于“真正心靈情感的本質”。
談到溫庭筠的《菩薩蠻》,一句“懶起畫蛾眉”,她講杜荀鶴和杜甫的詩,也用西方學符號學的觀點解釋:“蛾眉”就是聯想軸上的一個語碼。因為“照鏡畫眉來做托喻,在中國文學已經形成一個傳統。可以喚起我們的聯想。你一看蛾眉,就能想到離騷中‘眾女嫉余之蛾眉兮,想到李商隱《無題》里的‘長眉已能畫。”
以樂語,教國子
2000年起,葉嘉瑩開始在南開大學招收研究生。
她不喜歡麻煩別人。回國教書后,她在南開大學校園內獨自居住,不請保姆。一次起夜,她在衛生間滑倒,摔斷了鎖骨,怕影響秘書休息,她在地上躺了4個多小時,天亮才撥對方電話。
為了節省做飯的時間,她讓秘書可延濤買好速凍水餃,最多一次買了10斤。可延濤說,葉先生對學問的要求很嚴謹,但對生活的要求很低,特別是不愿意在吃飯穿衣這樣的瑣事上浪費時間。她的衣服好多都是二三十年前買的,很舊的衣服,她也從不舍得扔掉。有的破了洞,葉嘉瑩就自己拿針線把破處縫好。
《掬水月在手》副導演沈祎記得,到葉先生家里拍攝時,她捧著飯碗大口吃餃子,但從沒有衣著隨意、不打扮不收拾的片刻。
一生里,她最看重“教師”的身份。直到91歲時,她還在家中給學生上課。她要求學生讀文獻原文,多背誦。對于不認真的學生,她會嚴厲地批評,語氣近乎呵斥。但學生如果刻苦認真,即使談詩談得笨拙可笑,她也寬容。
只要血壓平穩,學生和朋友們傳來的郵件她會在晚飯后逐一回復。哪怕是收到群發的風光圖片,她也會一個手指敲打鍵盤,認真地回復“收到,謝謝”。熱愛古典詩詞的陌生學生寫信或郵件給她,也能收到她的回應。
葉嘉瑩認為,吟誦是傳承中國古典詩詞的重要形式。在國外生活了許多年的葉嘉瑩強調:只有中國有吟誦,其他國家的文學沒有。英文詩有朗誦、朗讀,也有輕重的讀音,但是沒有我們這樣拿著調子的吟誦。當詩詞加上韻律聲調,不僅更好記憶,也離作者的情感世界更近一步了。
如今,96歲的葉嘉瑩為了讓詩詞走入更多孩子和年輕人的生命,仍然在堅持辛勤工作。她最大的心愿,一是把自己對于詩歌中之生命的體會,告訴下一代的年輕人;一是接續中國吟誦的傳統,把真正的吟誦傳給后世。
“我想在我離開世界以前,把即將失傳的吟誦留給世界,留給那些真正的詩歌愛好者。”葉嘉瑩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