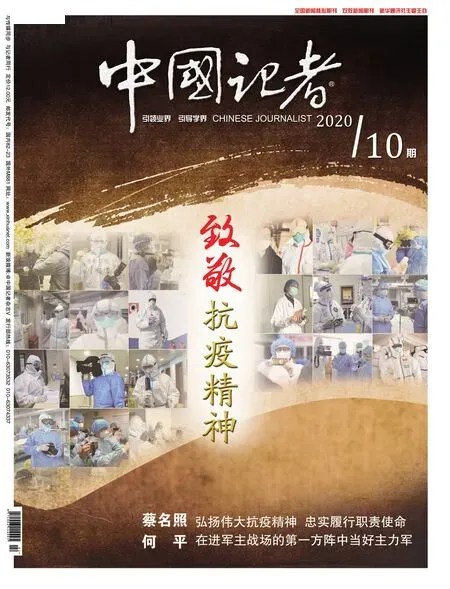現象類監督報道初探
——以《半月談》的實踐為例
最近兩三年,《半月談》做了大量輿論監督報道,這些報道直擊基層干部痛點,切中基層治理難點,反映基層群眾堵點,廣泛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反響。
一是引領話題,建設性效果非常顯著。在《半月談》大量報道基層問題之前,這一領域話題進入媒體較少,而如今,很多媒體和知名公眾號上,基層話題十分常見。可以說,《半月談》報道在帶動輿論界更多地關注基層難題、關心基層干部工作和生活狀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報道也產生了很好的建設性效果,推動了《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等重要文件的出臺。
二是兩頭滿意,打開輿論監督報道新局面。這些報道直面中央高度關注、基層干部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不回避矛盾,講實情、說真話,不僅得到讀者的廣泛好評,而且獲得中央領導高度關注,《求是》雜志連續3期轉載,這在公開報道中較為少見。上級部門專門以“半月談直面基層問題掌控輿論監督主動權”為題提出表揚,認為《半月談》“牢牢把握輿論監督主動權,積極發起、參與批評報道,很恰當、很必要”。
《半月談》輿論監督報道在打出影響力的同時,也展現了明顯的特色和風格。其中之一就是,這些監督報道與一般的監督報道不同,它們往往不是對一事一地的監督,而是對一些不良現象的監督,其數量之多、影響之大成了一種“現象”,同時也引發一個話題的探討:現象類監督報道生命力如何?是否有其獨特的存在價值?
一、認識現象類監督報道
《半月談》最近兩三年在輿論監督報道上是比較發力的,比如最近的《暗開收費棧道,周邊水庫污染嚴重:野蠻旅游正在傷害“野長城”》《長江禁漁數年,“貓鼠游戲”仍上演》《紙面服刑15年,真相待揭穿》等報道,都是一事一“報”,實名實姓,均產生了較大的輿論反響,直接促進了一些問題的解決。
不過《半月談》引發同行關注的,還是現象類監督報道。所謂現象類監督報道,就是對一類不良現象進行監督,形成報道,如問責泛濫、過度留痕、壓力甩鍋、教育焦慮、家校矛盾等,它不針對具體的個人、單位或地方,而是把焦點對準不良現象本身,及其出現的原因。
因此,現象類監督報道表現出兩個鮮明特點。
第一,地名、人名作模糊化處理。我們常常采用西部某縣一名鄉黨委書記、中部地區一個街道辦主任等表述,來代替報道中出現的具體的地名和人名。對比其他個案監督報道,我們可以發現,對爆料人、線人的姓名進行模糊化處理,是比較常見的,但是對地名(或企業名等)進行模糊化處理則十分少見。因為如果個案監督不出現地名,幾乎就不知所云了。這是個案監督與現象類監督十分不同的一點。
第二,操作上,常常是幾個記者分頭獨立采訪,提供素材,然后由牽頭記者或編輯部匯總成稿。這又是與個案監督很不同的一點。個案監督報道常常也需要一個團隊,但團隊的合作方式不同,個案監督報道的記者需要在調研中相互配合打掩護,現象類監督報道的記者基本不用這樣,但需要對各自采訪搜集的素材進行印證、補充和調整,以避免對現象做出以偏概全的判斷,使報道不能精準擊中不良現象的靶心。
對于這樣的特點,許多人是理解的。“不點名”是為了報道可持續、能深入。如果哪一次把受訪對象千叮嚀萬囑咐不要公開的地名、人名發出去了,那很可能就沒有下一次了。
更重要的是,我們真心地認同,現象類監督報道就是針對不良現象本身的。因為此類現象到處都有,誰出頭誰就可能挨處分,既然如此,為什么要把向我們掏心窩子講實話的人暴露出來呢?地方(或單位)最好也別暴露,不僅因為暴露了地方就有暴露人的風險,而且因為許多時候,一旦地方暴露了,該地就會被抓典型“解剖麻雀”,注意力都集中到這里,全局性的問題反而容易被放過,這與我們報道的初衷不合。
二、選題取向及其獨特價值
通過《半月談》兩三年的實踐,我們認為,現象類監督報道有其獨特的存在價值。
最直觀的表現,就是《半月談》大量的現象類監督報道獲得了讀者的廣泛認可,讀者們評價《半月談》報道“太真實了,好像臥底在我們身邊”“流著淚看完,說出了我們不敢說的心聲”“《半月談》,你真是太懂基層了”。這些評價本身就是對報道價值的肯定,更不用說這些報道還受到中央領導高度關注,推動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臺和實際問題的解決。

□《暗開收費棧道,周邊水庫污染嚴重:野蠻旅游正在傷害“野長城”》報道截屏。
更深入地分析還會發現,現象類監督報道的價值源于其選題的獨特性,即有一類選題更適合甚至只適合用現象類監督報道的形式呈現,傳統的個案監督報道對此往往無能為力。
以《半月談》最近刊發的一篇爆款現象類監督報道為例——《3部手機刷分忙,60個小號愁斷腸:“被動形式主義”綁住基層》(在網絡上,以文章中的一句話《怎么辦啊書記,今天的60個APP賬號還沒登錄》為題,傳播甚廣),反映一人照管60個“小號”、3部手機隨時連著充電寶、上廁所開會都不忘“刷分”的社區工作者,應付各種形式化考核的無奈。我們可以發現,此類現象放在個體身上,算不了什么事,更不是什么罪大惡極。
正如這篇報道所說:“被動形式主義”的危害性并不顯而易見,往往隱蔽在井井有條的“照章辦事”體系之下。也正因此,許多基層干部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反感形式主義,但不得不搞形式主義”的撕裂,“只能用形式主義來對付形式主義”的無奈,是許多受訪基層干部的心聲。這種事,個案監督瞄準哪個地方、哪個單位、哪個人都不恰當,感覺沒有發力處;它只有作為一個現象整體,才適合成為監督和批評的對象。
概括而言,這樣的選題更適合以現象類監督報道的形式呈現:第一,被批評的對象從個體來看是小惡,或者僅僅是行為不當,但這些小惡比較普遍,合在一起就成了一種嚴重的問題,一個值得批評的不良現象;第二,在這種不良現象中,沒有特別明確的誰對誰錯的界限,許多人常常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人;第三,不良現象產生的原因,不是個體或少數人故意作惡,而是有更深層次的癥結,這其中有的人因不自知而成為幫兇,更多人則因無力反抗而被裹挾其中。
再從標題上感受一下現象類監督報道選題的特點:《上面一句“看著辦”,基層干部直冒汗》《干完再說話,容錯有點尬》《找背鍋人易,找負責人難!》《責任層層甩,基層兜不住》《以痕跡論政績,“痕跡主義”有點過了》《學校越來越松,家長越來越瘋》《啥都“從娃娃抓起”,娃娃快被“抓”壞了》《脫貧認定被一頭豬難住了》《“填表村醫”:填表倒比看病多》《特殊就業季上演“表格就業”?》……
可以看出,現象類監督報道可以開掘的領域很廣泛,既可以包括基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官員不作為、慢作為問題,也可以包括教育、醫療、就業、扶貧等民生領域問題。這些問題都是真問題,是與基層干部群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大難題,但它們的表現往往較為日常,適合以現象類監督報道的方式去反映。這正是現象類監督報道的價值和生命力所在。
三、先守正,然后可以致勝
有人認為,不管怎么說,現象類監督報道都比較討巧,比較容易,個案監督才能體現媒體人的膽略和水平。這種說法反映了個案監督的困難。許多個案監督報道需要長時間冒著風險調研、暗訪,還要頂住利益相關方的各種或明或暗、或硬或軟的壓力,才能成稿刊發。《半月談》常發個案監督,我們深知此中不易。
但是,現象類監督報道也并不是看上去那樣得來容易。一個簡單的道理,如果現象類監督報道容易做,如此投入少、產出大,誰不愿意參與,市面上此類報道應該很多才對,而現實是,優秀的現象類監督報道仍然是稀缺品,《半月談》受到領導關注和廣泛傳播的報道,多是此類。
為什么這樣?首先,得有能夠摸來情況的記者,不是一兩個,而是一大批。搞個案監督可以是拿到線索后,由經驗豐富的老記者順藤摸瓜,或者由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年輕記者死磕到底,但是搞現象類監督,這些招可能都不好使。因為許多現象類監督的“核心事實”不是明擺著的,阻礙你抵達“現場”的也不是物理障礙,而是心理障礙。你必須跟采訪對象成為真正的朋友,他才可能向你吐槽、對你訴苦,帶你拿到你想要的東西。
《半月談》背靠新華社這棵大樹,各地方分社有眾多長期行走在基層、在某一領域深耕細作的記者,他們在長期與基層干部群眾、與科教文衛等各行各業工作者打交道的過程中,建立了信任關系;他們的采訪也常常不是很正式的形式,而是在同桌吃飯、同車趕路、同屋工作時“閑聊”完成的。這是《半月談》優質現象類監督報道源源不斷生產的基礎保障。
不過僅有基礎保障還不夠,現象類監督報道面臨的更大難題,是如何把握報道的基調、控制報道的風險。個案監督只要把采訪做扎實,相關證據留充分,報道的風險是相對可控的;現象類監督則總是要由個別到普遍、由局部到整體,必須要防止以偏概全、以小概大,把握好報道的調子,既有難度,也需要膽識。
《半月談》做現象類監督報道總的基調是“建設性”3個字,即報道不是為了博眼球、掙流量、宣泄情緒,而是旨在把黨的主張不折不扣地變成老百姓的獲得感幸福感,破除“中梗阻”“腸梗阻”,打通“最后一公里”,及時反映違背黨的主張的各種表現、損害群眾利益的各種現象,為中央決策提供真實準確的一手信息,解決實際問題。
《半月談》雜志社黨委書記、總編輯葉俊東多次鼓勵我們說:“在輿論監督上怕惹事、怕出事,實際上是不擔當、不作為的一種表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你放棄了本該堅守的陣地,讓自媒體掌控了話語權,引領了社會輿情的走向和節奏。連陣地都沒有了,話語權喪失了,還何談引導輿論、堅持正確的輿論方向?《半月談》就是要在掌握基層陣地輿論監督話語權的基礎上,起到舒緩社會情緒、引導輿情走向朝著服務大局方向發展的作用。”
這是一種擔當,也是一種自信。自信來自于堅定地“守正”。何謂“守正”?是指要吃透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吃透中央精神,吃透中央決策部署,并以此為指導,辨明對錯,校準批評的靶心。
比如《來督導督查的人比抓落實的還多》一稿,如果對中央精神把握不準,全盤否定督導督查,那就錯了;又或者認為督導督查為中央所倡導,一點不能批,那也錯了。《半月談》報道批評的不是督導督查本身,而是督導督查過多過濫,沒有推動實際工作,反而干擾實際工作這種不良現象,是為了幫助中央精神不打折扣地落實到基層。這正是報道建設性的體現。
四、管控風險的技術考量
在調研采訪中,現象類監督報道不可能窮盡所有的案例,事實上,相對于不良現象的普遍,采訪的對象、采集的素材永遠只能是一小部分。正如前文所講,現象類監督報道必然有一個從個別到普遍、由局部到整體的跨越,這一步很關鍵,也是最大的風險點所在,搞不好就會出現以偏概全、以小概大。同時,由于現象類監督報道常用匿名,確保報道中事例的真實性和準確性也面臨一定的風險。
管控風險,核心和靈魂是要吃透精神,并以此為定盤星校準報道,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僅此還不夠,新聞報道最底線的要求是真實,如果不能保障真實,出發點再正確,最終結果也是錯的。對現象類監督報道來說,真實有兩個層面的內涵。第一,報道中所舉事例等是真實無誤的;第二,報道所指的這種不良現象是成立的,而不是記者或編輯臆想出來的。為此,《半月談》一般從以下幾個技術環節來進行把握。
首先,分散采寫。《半月談》現象類監督報道一般約請3個左右的分社記者參加,每個記者在各自不同的省份進行相對獨立的采訪調研。如果每個省份都有類似的情況,現象就基本可以成立了。同時記者分散采寫也可以相互印證、相互補充、相互校正,不至于出現大的偏差。有的報道只有一個記者完成,這種情況,記者和編輯就要向別的省份的記者求證,以保證現象的普遍性。當然即使如此,在做出整體性判斷時,也要注意分寸,留有余地。
第二,核對事實。盡管在公開報道中隱去了地名和人名,但真實性必須保障。新華社各分社都有嚴格的把關機制,記者采寫素材須由分社值班領導審核、一讀校對后才能簽發使用,這是一道關口。到了《半月談》成稿時,須對核心事實進一步核對,雖然公開報道不一定出現具體人名地名,但編輯要做到心中有數。其三,常識驗證。現象類監督報道所反映的問題,許多就在我們的身邊,只不過見慣不驚了。所以我們往往可以用常識去判斷,某篇報道所提的現象是否成立,認識是否有偏頗。比如《半月談》關于教育減負異化的一篇報道《學校越來越松,家長越來越瘋》,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在同事朋友間,就能聽到不少關于這一話題的議論,并由此形成對于這一話題的印象和看法。如果報道所舉事例或所作判斷偏離這些常識太遠,就須慎重把握。
第四,梳理邏輯。一種現象的出現不會是無緣無故的,現象類監督報道要尤其重視對現象原因的分析和梳理,做到邏輯嚴整。比如做痕跡主義的報道,你得厘清從痕跡管理到痕跡主義的演變脈絡,出現的背景,發展的趨勢等情況,這些情況不一定全都在稿子里體現出來,或進行長篇的論述,但一般要做必要的交代和分析,這樣稿子才能立得住,才有可信度。邏輯不夠充分的現象類監督報道,也需要慎重把握。
這四個環節,前兩個硬,后兩個軟,但都很重要,不可偏廢。近年來,《半月談》做的大量現象類監督報道都是按此操作的。到目前為止,這些報道沒有出現事故或失實情況,各界也極少對報道的真實性提出質疑,在讀者中也引發了廣泛共鳴。事實證明,只要做到以上幾點,現象類監督報道的風險可以得到較好防范,沒有真名實姓的短板也可以得到較大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