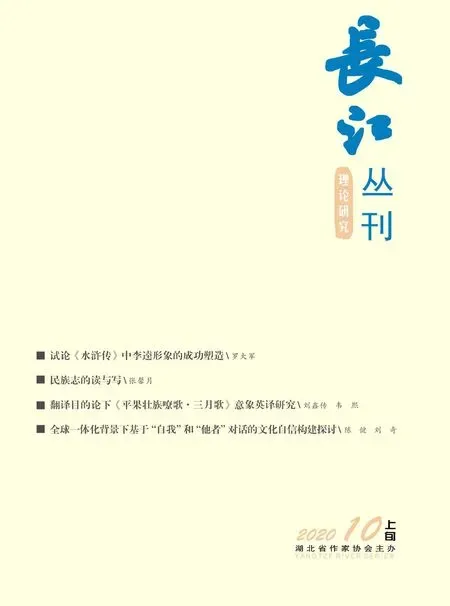譯事不易
——從《第二十二條軍規》譯本分析看譯者素養的重要性
■呂黃艷/上海工程技術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一、前言
“一國的文字和另一國的文字之間必然有距離……從一種文字出發,積寸累尺地渡越那許多距離,安穩到達另一種文字里,這是很艱辛的歷程。一路上顛頓風塵,遭遇危險,不免有所遺失或損傷。”[1]切斯特曼也說:“And so(translation)research,like the path of true love,never runs smoothly.”[2]譯事不易早已不是新鮮事。原滋原味重現原文,是每個譯者的終極追求。譯者素養直接決定了譯文質量。具體來說,譯者文學素養的高低決定譯者是否能在譯文中把握住原作文化意象;譯者對原文風格的把握決定譯者對原文意義傳達的準確性;譯者的審校能力決定了譯者辛勞收獲的成果大小。好的譯者應是博古通今,通曉中外的“全才”。目前國內《第二十二條軍規》的譯本共有八種。本文選取了國內首譯本(南文、趙守垠、王德明譯本)(以下簡稱南譯)和目前國內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譯本(揚恝、程愛民、鄒惠玲譯本)來做譯本分析,嘗試從譯者素養的角度分析其在在翻譯中的重要性。
二、譯者文學素養與文化意象
文學作品來源于生活,不同民族因生活環境、文化背景等因素不同,導致其所產生的文化意象也大有不同,而這些文化意象又往往體現在這個民族的文學作品中。《路線圖:翻譯研究方法入門》一書中指出“There are obviously many levels of or dimensions of causation that are relevant to translation.…The proximate(most immediate)one is that of the translator’s cognition”(Williams & Chesterman,p.54)此處,作者特別強調的是譯者的認知。翻譯時,譯者的認知水平體現在從文學作品中一眼拾掇出其中的文化意象的能力。也就是說,即譯者本身要具備較好的文學素養,具有文學認知,在翻譯時才能感知文化意象的。否則,就如謝天振先生在《翻譯研究新視野中》說“由于忽略了文化意象的意義……嚴重者,會影響對原作意境、人物形象的把握。”Catch-22這部作品中涉及到許多文學意象的內容,戲仿是其中之一。如若譯者本身文學素養不足,那么翻譯制約就十分明顯,只怕就難以洞曉約瑟夫·海勒隱藏在字里行間的奧秘。下面來看一個例子:
例1.He turned the other cheek on every occasion and always did unto others exactly as he would have had others do unto him.When he gave to charity,his left hand never knew what his right hand was doing.He never once took the name of the Loud his God in vain,committed adultery or coveted his neighbor’s ass.In fact,he loved his neighbor and never even bore false witness against him.MajorMajor’s elders disliked him because he was such a flagrant nonconformist.[3]
這段話是對梅杰少校品行的描寫。不熟悉圣經的讀者可能一下子無法理解其中玄機。這段內容幾乎是對摩西十誡內容的戲仿。此處是對十誡第三條(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第七條(不可奸淫)、第九條(不可做假見證陷害人)、和第十條(不可貪戀他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仆婢、牛驢,并其他一切)的戲仿。摩西十誡本身是神圣的,小說對其的戲仿好像是在贊美梅杰少校品行的高尚,但諷刺的是即使梅杰少校有這些“高尚”品行,他的長輩們也都不喜歡他。這使得戲謔反諷的效果在這種矛盾一躍而出。來看這南譯和揚譯兩個譯本的處理:
南譯:在各種場合,他都逆來順受,心里希望人家怎樣待他,他就怎樣對待人家;他行起好來,一貫慷慨大方,而且從不褻瀆上帝的名字,從不和人通奸,從不想去勾引鄰居的老婆。事實上,他喜歡他的鄰居,甚至從來沒有作過不利于他的偽證。梅杰少校的長輩不喜歡他,因為他這樣公開地違反了他們心目中的生活準則。[4]
揚譯:無論什么時候,他一貫逆來順受。他一向以誠待人,就像他覺得別人也會這么待他一樣。他一旦做善事,從來都是慷慨大度。他從不濫用上帝的名義,從不與人通奸,或是垂涎鄰居的老婆。其實,他很愛他的鄰居,從來就沒有作過不利于鄰居的偽證。梅杰少校的長輩們都討厭他,因為他竟如此明目張膽地置約定俗成的傳統規范于不顧。[5]
在該段話的處理上,兩個譯本都把“turned the other cheek”譯為“逆來順受”,雖然語義正確,但原文“把另外一半臉湊過去”的戲仿意向被抹去了。同樣,“When he gave to charity,his left hand never knew what his right hand was doing”只譯出了“慷慨”的語義,省略了原文意象,無法傳神地傳達出原文的戲仿。而對于“coveted his neighbor’s ass”的翻譯,兩個譯文都出現了誤譯。摩西十誡第十條原文是“You shall not covet your neighbor’s house; you shall not covet your neighbor’s wife,or his manservant,or his maidservant,or his ox,or his ass,or anything that is your neighbor’s.(第十條:不可貪戀他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他人的妻子、仆婢、牛驢,并其他一切)[6]”,相對應的“neighbor’s ass”應翻為“鄰居的牛驢”。此處,兩個譯本都沒很好的把握原文的意象,沒有依據圣經權威譯本進行文字處理,因此沒能在譯文中保留戲仿的痕跡,沒有能很好地突出戲謔反諷的矛盾效果,從而使小說黑色幽默的風姿也喪失不少。由此可見,譯者不僅要從原作中抓住戲仿的影子,更要在譯文處理時,將戲仿的元素考慮進去才是上上之策。
例2.…and since his father had it on excellent authority that Russia was going to collapse in a matter of weeks or months and that Hitler,Churchill,Roosevelt,Mussolini,Gandhi,Franco,Petron and the Emperor of Japan would then all sign a peace treaty and live together happily ever after.(Heller,p.249)
該段描寫的是內特利的父親對局勢判斷太過樂觀導致把兒子送上戰場當空軍的片段。在這句話中,“live together happily ever after”最為關鍵。這句話通常出現在童話小說的結尾“(王子和公主)從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此處原文采用這樣的句子是對童話小說的戲仿。通過“(王子和公主)從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這個完美的結局與戰爭的殘酷血腥的強烈對比,使人更加切身的感受到戰爭的冷酷,這種對童話小說戲仿的語言張力使得戲謔諷刺的黑色幽默的效果躍然紙上。來看兩個譯本對這段話的處理:
南譯:……還因為他父親自認為有充分的證據,斷定俄國在幾星期或幾個月內就會垮臺,而希特勒、丘吉爾、羅斯福、墨索里尼、甘地、佛朗哥、庇隆以及日本天皇就會共同簽訂一項和約,從此相安無事。(南,第385頁)
揚譯:……同時還因為他父親根據權威人士的消息說,俄國將會在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內垮臺,而希特勒、邱吉爾、羅斯福、墨索里尼、甘地、佛朗哥、庇隆和日本天皇將簽署一個和平協議,他們從此將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揚,第298頁)
南譯將“live together happily ever after”譯為“從此相安無事”,看似傳達了原文語義,符合時代的背景,但是沒有保留原作對于童話結局的戲仿,沒有與時代背景構成強烈反差,諷刺戲謔的效果大打折扣,原文中想要傳達的黑色幽默的效果也無法重現。而揚譯將這個短語譯作了“……從此將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通過童話小說圓滿結局模式的保留,使得原文中戲仿所想傳達的戲謔反諷效果也準確表達了出來。
上述部分僅是Catch-22中眾多戲仿中的兩個例子,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通過上述分析可見,如果譯者沒有一定的文學素養,定是無法識別原作的文化意象,更別提在譯文中傳達其精妙了。譯者扎實的文學素養對文學作品翻譯十分重要。
三、譯者把握原文風格與意義傳達
除了譯者扎實的文學素養,原作風格是譯者在處理譯文時需要考慮的又一大因素。約瑟夫·海勒將原文黑色幽默的風格著力體現在了邏輯矛盾上,以荒誕表現荒誕。這就要求譯者在翻譯Catch-22時除了要識別原文的文化意象,更要顧及原文的表現形式,努力使譯文貼近于原文,“把原作的藝術意境傳達出來,使讀者在讀譯文的時候能夠像讀原作時一樣受到啟發、感動和美的感受。”[7]Catch-22是黑色幽默的巔峰之作,其譯文也必先體現其黑色幽默的風格,即以荒誕的形式來表現荒誕的現實。通讀Catch-22可以發現,語言邏輯的前后矛盾是約瑟夫·海勒試圖體現黑色幽默的著力點。就像海勒自己說的“皮亞諾扎島是個極小的島嶼,本書敘述的時間顯然不可能全部發生在那里”(南,第1頁),他沒法描繪驚天動地的大場面,但是他一直試圖在文字與邏輯之間,拿捏沉吟,從矛盾的碰撞中扒搔出柳暗花明又一春之感。通過語言的邏輯矛盾,加大語言的沖擊力,展示現實對人的異化。所以在翻譯這部作品時,譯者需努力克服慣性思維的束縛,時刻牢記原文黑色幽默的風格,對譯文文字加以處理。下面來看兩個例子:
例3.It was truly a splendid structure,and Yossarian throbbed with a mighty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each time he gazed at it and reflected that none of the work that had gone into it was his.(Joseph Heller,p.18)
該例取自約塞連看到軍官俱樂部時心理活動的片段,句子展現的是一對明顯的邏輯矛盾,即“throbbed with a mighty sense of accomplishment”和“reflected that none of the work that had gone into it was his”。按照正常的思維邏輯來說,一般人應該是為某件事做過貢獻,才會在看到成果時產生強烈的成就感。但是原文描寫的卻是,約塞連產生成就感的原因正是想起自己沒有為俱樂部建設出過一點力。這使得讀者在思維邏輯的困惑中不經深究為什么。來看兩個譯本的處理:
南譯:它確實是一座堂皇的建筑物。尤索林每次望著它,總有一股強烈的完美感覺涌上心頭,同時也總回想著,自己竟然沒有為它干過一點點事情。(南,第20頁)
揚譯:說實話,這幢建筑的確很壯觀。每當舉目凝望時,約塞連內心總升騰起一股極強的成就感,盡管他意識到自己從未為此流過點滴汗水。(揚,第16頁)
在對這段話的翻譯中,最值得斟酌之處就在于譯者如何處理前文所說的邏輯矛盾。兩個譯本的譯文,都讓讀者有一絲約塞連對于“沒有為它干過一點點事情”是覺得可惜的。但事實上,約塞連產生了成就感的原因正是因為想起自己沒有為俱樂部建設出過一點力。正是因為他沒有為這座戰爭產物出一點力,他覺得有成就感,這一點說明了他的反戰與逃離情緒。也就是說,楊譯與南譯此處出現了誤譯。這可能是因為譯者在閱讀原文時忽視了對原文黑色幽默的風格的把握,所以陷入了邏輯思維慣性的泥淖,出現了上述的誤譯。由此可見,譯者在處理譯文時一定要牢記原文的風格,才能更加精確地傳達出原文。
例4.He(Colonel Cargill)was a self-made man who owed his lack of success to nobody.(Joseph Heller,p.27)
此處是對卡吉爾上校的描寫。這一句話中,“Self-made”“owed”兩個詞與“lack of success”構成了一對邏輯上的矛盾。“self-made”意為“靠個人奮斗成功的”,“owe”意為“欠,感激,應給予,應該把…歸功于”,兩個詞表明卡吉爾上校應該是成功人士;而“lack of success”筆鋒一轉,語義相反,“成功人士”卻“不成功”。這種的反邏輯的戲謔,體現的是對卡吉爾上校的諷刺,加重了荒誕色彩。因此,在翻譯時形式應予以保留。來看兩個譯本的處理:
南譯: 卡吉爾上校是自己奮斗出頭的,他的一事無成歸功不了別人。(南,第36頁)
揚譯: 卡吉爾上校是白手起家的,因而,他的一事無成也就怪不得別人了。(揚,第28頁)
在兩個譯本的翻譯中,南譯將“self-made”翻譯為“自己奮斗出頭”,揚譯翻譯為“白手起家”。兩者比較,南譯更加體現原文的“Self-”,強調了卡吉爾上校是靠個人的奮斗,語義上的矛盾關系可以得到加強。對于“owed”的翻譯,揚譯為“怪”,這雖與“lack of success”語調一致,但沒有充分意識到原文的邏輯矛盾。相比之下,南譯的“歸功”就更恰當地再現了原文語言的反邏輯性,更準確地保留了原文邏輯矛盾形成的語言張力。由此說明,在翻譯時,譯者不應當簡單在譯文中輕易進行改動、補充。而是要像劉宓慶先生所說:“拿到原文以后通過反復閱讀、鉆研,掌握原文的總體風貌……并運用自己學到的翻譯技能處理原文,使自己的譯文盡可能適應原文的總體風貌。”[8]Catch-22是黑色幽默的經典之作,常以一種近似悖論的形式來突出現實世界的混亂不堪以及個人與世界的對抗。因此,譯者在翻譯時,應時刻牢記Catch-22黑色幽默的總體風格,突出語義上的矛盾關系,從而最大程度使譯文貼近原文。
四、譯者審校能力與出版成果
在當今信息化迅速發展的世界,僅具備較好的文學素養與較好的文字處理能力已不足以稱“合格的譯者”。信息化發展迅猛,譯者翻譯成果發表出版化的大背景,要求譯者還需具備出色的翻譯審校能力,熟練掌握與翻譯相關的信息技術,比如翻譯過程中運用相關詞典、術語庫、平行語料庫等。一部翻譯作品的發表和出版是對譯者本身極大的肯定,某些時候由于疏忽等原因,導致翻譯作品無法及時出版、出版有誤(比如南譯本第384頁把“熱衷”寫成了“熱中”,揚譯本第298頁把“丘吉爾”寫成“邱吉爾”的簡單錯誤),甚至是不能出版,都是對譯者前期翻譯工作的否定。朱振武先生也曾提過“譯事八型”,其中“編輯的工作:馬虎型;時間的限制:緊逼型;后期的制作:隱秘型;”講的都是譯作完成后譯本出版時的問題。這三個問題隱患決定了譯作的質量。也就是說譯者不僅要具備較強的專業能力,而且要具備較強的翻譯審校能力,這樣才可杜絕上述所講的排版出錯,后期審校原文譯文錯亂,譯者名也會出錯等出版錯誤。在比對Catch-22的兩個譯本時筆者發現南譯、揚譯兩個譯本中原文的感謝與前言部分兩個譯本均未譯出,不知這是出版社有意為之還是大意失之。筆者認為譯出原作的感謝內容是對作者及在寫作過程中給與作者幫助支持的人或組織的認可,更加符合翻譯標準中的對等原則。而翻譯的前言則是作者交代了自己的寫作背景與意義,這對更好的了解作品內容有很大幫助,因此在譯文時也應保留。比對時還發現Catch-22原文中沒有目錄,南譯增加了目錄,而揚譯沒有。筆者認為在該點上南譯要優于楊譯。因為對讀者來說,南譯創新性的此舉讓讀者在閱讀前就能把作品內容一目了然,也使譯文顯得更加有序。
五、結語
通過筆者對Catch-22所做的譯本分析中不難看出譯事不易。譯者扎實的文學素養、譯者對原文風格的準確把握以及譯者出色的審校能力都是譯者在翻譯時應具備的譯者素養。只有三者齊備,才有可能使譯文原滋原味重現原文。當然,譯者素養還包括其他許多素養,如翻譯策略能力、翻譯心理能力等,這也是筆者繼續探究和亟待提高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