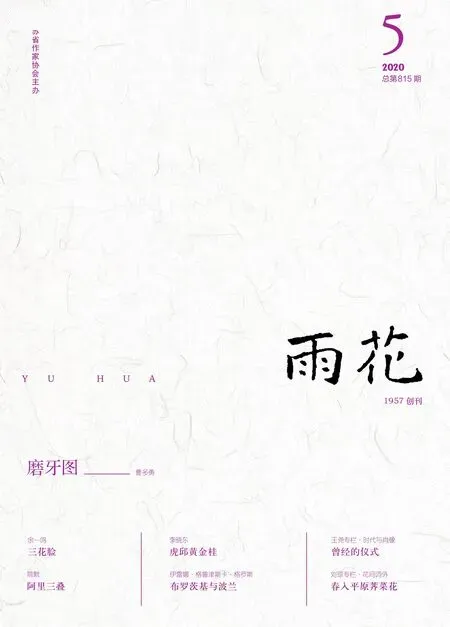一個鐵匠的黃昏(外一篇)
李新勇
抵達川滇接壤的老街,西斜的太陽快坐到山梁上。白天熱鬧的老街客走人散,漸漸安靜下來,有的門店關門落燈,店主人吃晚飯去了。這條老街,從街頭到街尾四五百米長,幾無岔巷。街面寬窄隨便,寬的地方三米樣子,窄的地方一米多。街道兩邊,統一規劃興建不過二十年的仿古建筑,從街頭到街尾連成一片,形制多樣。或水鄉臨河式,或西南吊腳樓式,或川滇民居式,各具特色,雜亂而自然,營造出濃郁的古韻古味。這條老街是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的必經之處,向北五百公里是成都,向西南六百公里是昆明。一街跨兩省,北面半截屬于四川,南面半截屬于云南,像川滇之間緊緊扣在一起的盤扣,從地緣到文化,分不出彼此。從古至今,天天趕集,客貨兩旺。如今雖暫未被開發成旅游景點,除趕集的四鄉八鄰,每天慕名而來的游客,竟有百十號人。
老街上唯一的鐵匠鋪師傅老李也落錘封爐,端起大茶缸來,蹲在鋪面門口仰起脖子,把茶水變成一個個看不見的湯圓,咕咚,咕咚,一個接一個地吞到肚子里去。歇口氣,待一會兒,再把門前鋪子上的菜刀、鋤頭、鐮刀、釘耙等自制的產品收進鋪子。把鋪子里的打鐵工具收拾好,一天的職業活動就算結束。
他聽說我從江蘇跑過來聽他講故事,便高興得又遞煙又讓茶,又聽說我還是個四川人,就更健談了。“這個好,免得操普通話舌頭不曉得往哪里擱!”說得大家都笑起來。他說,他從出生就在這條街上生活,從能舉起大錘就開始打鐵,今年六十五歲了,眼不花,耳不聾,牙齒不松,照著樣子,還能再干十年八年。
我們在老李鋪子前面的石階上坐下來,遞過去一支煙,故事便打開了閘門。老李給我和朋友各遞一把蒲葵扇。初夏的淺熱還用不著扇涼,不過捏上一把土扇,我們的交談就更像老友間拉家常。老李說,聽他父親講,過去四川的生絲、鹽巴、綢緞、布匹、宣紙,云南的火腿、沱茶、核桃、花椒,南來北往,都打這條街上經過。幾十上百人一伙,用馬馱的叫馬幫,靠人力背的叫背幫。那時候這地方偏僻,四野高山林莽,中間一條小道,時有土匪出沒。出滇入川的商旅,走進小鎮便可以緩口氣。為保商旅安全,他父親年輕的時候還有鏢局,習武的鏢師身挎德國造的連發長槍。雇鏢的馬幫都是善主,出發前通過手語通知散客、背幫和其他遠行人尾隨于后。人多時,數百人同行,人吼馬嘶,邊行路還能邊談笑。
鐵匠房里的火爐留了一條縫,使爐火靠一口氣,活到明天早上老李升爐開工。老李的鐵器自產自銷,既有實用型的農具,也有可作旅游紀念品的精致的馬蹄鐵、風車、船錨等等。我注意到,跟傳統鐵匠鋪比起來,老李的鋪子更現代,有空氣錘、砂輪機、游標卡尺、激光水平儀、切割機、電鉆、電焊機等等。這一行在經濟發達的地方,早已絕種。聽說這些新鮮玩意前年才購進,我便分明感到,這一次找的采風點有意思,不虛此行。
老李說他原本不姓李,因這一行把八仙中的鐵拐李尊為開山祖師,后世凡入此行,都改姓李。有一句古話叫“人生有三苦,打鐵撐船磨豆腐”,鐵匠排在第一位。過去家里只要還能喝得上稀飯,誰也舍不得把自己的兒子送去打鐵。他九歲父母雙亡,要是不打鐵,他可能早都餓死了。憑借勤勞肯干、眼巧人乖,他繼承了師傅的鋪子,師傅去世的時候,他以兒子的身份參與葬禮。師兄弟八人,如今只剩他一人在世。教了八個徒弟,個個改行,種天麻,販木材,做房地產。這些徒弟到過年從天南地北趕回來給他拜年,但他覺得這些徒弟早就不是徒弟了,或者只能算親戚——對一個一生熱愛打鐵的鐵匠師傅來講,這些不打鐵的徒弟,最多只能算親戚。
那都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收的徒弟。機械化、電子化和全民經商的熱潮,讓這些徒弟改弦易轍。鐵匠鋪一度歇爐關門,哪怕他的手藝好得連師傅都翹拇指,半個月也賣不出一把菜刀。一度窮愁潦倒,靠老婆炸油條糊口。“那時候老百姓不懂,以為商店里便宜光亮的不銹鋼菜刀好用。其實鋼刀里除了張小泉、永光幾家名牌,沒有哪家趕得上我打的刀。”說著他從毛刷子上扯下四五根毛,隨便在攤子上拿起一把菜刀,把毛放在刀口上一吹,齊刷刷斷了。他說他打的刀具,會根據買主的用刀習慣,打出不同的刀口斜面,用起來省力,越用越好用。
我想知道是什么信念支撐他把爐火重新燃起來,天天堅持在這里打鐵,成為老街的一道風景。老李說:“瀕臨絕種的手藝,大有商機,你看我打的這些東西,有的供人使用,有的可以買回去當紀念品。老街天天人來客往,少不得有我的財神菩薩。”說罷開心地笑起來,看來每天財神菩薩還不少。
“如今有沒有人跟你學打鐵呢?”這是個很關鍵的問題,總不能到你這里就成絕版。向一個被采訪對象提問,絕對不能給他回旋的余地,得一句話把他逼至墻角。
“暫時還沒有,不過很快就有了。”老李說,鐵匠干活,一般由兩個人組合,師傅的小錘點哪里,徒弟的大錘就打哪里,既省力,還出活兒。他的兒子在外地打了幾十年工,在工地上砌房子,前幾年還可以,這幾年到處房子砌得差不多,每年拿回來的鈔票,還趕不上他打半年鐵。老李信心滿滿,遲早要把這小子收編。
“還有一個。”老李笑瞇瞇地指著斜對面那個跟面館小妹說笑的紋身青年說,那是他的孫子,跟他孫子說話的女孩,不消多久就會成為她的孫媳婦。他說,現在的青年整天光曉得玩手機,除了會玩手機,別的什么都不會,不會還不算,還根本不想學。老李說,等結了婚,到處要花錢,為了生活,他也要把這小子給收編。“現在別管也別問,讓他玩,也不跟他提這個事,船到橋頭自然直。”說罷又信心滿滿地笑起來,“頂多讓他在網上替我買幾樣鐵器,讓他先嘗點甜頭,一步一步地來。”老家伙顯得老謀深算,年輕人不讀書,不琢磨,根本不是他的對手。
老李指著屋子里新買的工具和手上的鐵錘說:“這些遲早都是他們的!”
“老匠人的晚年,真是有意思!”這樣想的時候,太陽落下去,老街上空布滿赭紅的晚霞。從老街的屋檐下仰望,被老街的房屋切割過的天空像一條色彩繽紛的河。零星的流云,詩意地擺在天空中,仿佛河中溫潤的卵石。
腰系紅繩的女子
趕到小劉畫畫的地方,已是深夜。小劉在寒風中迎著我,直接把我帶進羊肉館。羊肉、炒飯、饃和二鍋頭,不到三個小時,小劉沒把我灌倒,自己先醉成一堆捏不成形的爛泥。
我知道他心頭有許多苦,此刻正處在人生低谷。他是我們村的異數,全村人包括他的爹娘,都把他當怪物:高中成績優異,放著好大學不考,考前三個月惡補美術,以文化成績同榜最高考進美院學油畫;大學畢業不找工作,一心考研究生,一戰二戰三戰,終于如愿以償,三年后拿上畢業文憑,就來宋莊尋找自己的夢。他的爹娘先是盼他找個體面工作,繼而期盼他結婚生子,如今,只盼他早日停止漂泊,回到故鄉,過正常人的生活。他的爹跟我是遠房表兄弟,知道我在北京學習,便打電話請我無論如何幫他們去看看,看看這個“逆子”是死是活,怎么如今連他們的電話都不接。我用他們給我的號碼撥過去,一撥就通了。我說我去看他,他在電話那頭高興得不得了,說我是全村唯一到北京看他的人。
在滑到桌子底下之前,小劉對我說,表叔,我愛我的爹娘,時刻都感覺自己不孝順,可我得暫時做幾年逆子。他們太嘮叨了,照他們的思維,我就該過平庸的日子,按部就班,找一個單位,整天在領導面前唯唯諾諾,把夢想塞到褲襠。可是表叔,我才二十九歲,誰甘心二十九歲就把這輩子看穿?我得趁年輕出來闖蕩闖蕩。導師評價我才情高,只要找到合適的平臺,油畫這條路能走出來。我得在這兒尋找一切機會,要是三十五歲還混不出個樣子,就認命,回故鄉去,該做啥就做啥。
我問他住什么地方,好把他送回去,他已經完全不懂我說的是哪國語言,通通用“嗯”“啊”作答。夜已深,羊肉店快打烊了,店里只剩我們兩個客人。這時,他的手機響了,我替他接,一個女子好聽的聲音:“在哪兒呢?”沒有稱呼,表明他們很熟。我說他喝醉了。女子在電話里頭說:“這下可好,啥都不記得了。”這話越發讓人覺得他們很熟。按女子發過來的地址,凌晨三點,終于摸到小劉的住處。
出租屋,兩個房間,一個公共廚房,一個公共衛生間。屋子雖小,收拾得干干凈凈,不僅干凈,還有一股淡淡的年輕女子的氣息。前來開門的女子自稱米粒兒,跟我一起把小劉擱到床上放平,便下廚房端來一盆熱水和兩塊冰,熟練地用冰擦小劉的手心和臉龐。米粒兒跟我說話的時候,我打量著她。二十五歲上下,五官清秀,面孔白皙,齊肩披發,身材姣好,偏瘦,配上恨天高,怕有一米七。我心想,這是小劉的誰呢?米粒兒像是看出我的心思,指指對面的房間說,那是她的房間。她說她在這兒租住了五年。傳說中的男女合租,我算見著了。我心想,萬一這般美貌的女子跟小劉發展成男女關系,我那老表和表嫂睡著都可能笑醒,很多男女合租,最后都修成這個結果。
米粒兒問:“喝了多少?”
“一瓶二鍋頭,我喝了三兩,離開的時候還剩二三兩。他喝了半斤不到,該是沒有問題的。”
她接過話說:“你跟他什么關系?他二兩酒就醉你不知道?”態度有些嚴肅。當她知道我是小劉的表叔,態度就有了一些親近,口氣也變得緩和了。細微的轉變,使我感受到她跟小劉關系確實不一般。收拾完畢,把小劉塞進被窩,米粒兒端起盆子出門去,隨手關了門,便再也沒有進來。米粒兒端盆子出去的時候,毛衣上提,露出一截細腰。這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我不經意看見米粒兒雪白的腰上,赫然系了一條細細的紅繩。要不是她腳步快,我有句話就沖口而出了。
此時回學院不可能,地鐵要再過一個小時才開。我在小劉旁邊和衣而臥,怎么也睡不著。我覺得,天亮一定要跟表侄交代清楚,這女子他千萬不能碰。那根紅繩跟這女子的工作有關,這是不得不從事那一行的女子最后的尊嚴,意味著哪怕把衣服脫光,都還有最后一件薄紗遮羞。這我是在故宮一份密卷上讀到的,一般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第二天小劉醒來,屁事沒有,相約去參觀韓美林藝術館。吃早點的時候,我指指另一個房間門,意思是喊不喊米粒兒起來吃。小劉說,她的早晨從下午兩點開始,這會兒是她的深夜。在路上,小劉告訴我,他在宋莊先后換了九個住處,這是第九處。一年多了,住下來就沒想離開過,這房間是他向她租的。他說這女子心腸好,剛來時候窮得沒錢交房租,半年多時間,她竟然不怕他跑了,也不問他要房租;屋子都是她收拾的,人熱情,肯幫忙,平時陪他說說話,每個月總有那么幾天待在家里,全天候給他做飯。他的畫,無論好不好,她通通說好,還說等她掙到大錢,一定以最高價格買了去。最近小劉要在798辦畫展,米粒兒又忙前忙后張羅,比他還積極,比他考慮還周到。我問小劉,你們是不是在談戀愛?他說有時候像,有時候又不像。平時光說說話,像;想親熱一下她不給,又不像。我問他,你知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工作?小劉說,米粒說她是形體教練,專上夜班。聽他這么說,在嘴邊盤旋大半夜的話,沒有說出來。
魯院畢業,我很快忘掉了這件事。三年后,我從報紙上看到小劉在比利時辦畫展的消息,從新聞稿給小劉的頭銜看,他已取得階段性成功:他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油畫探索領域。把他的名字輸入書畫交易網,已達到中等江湖地位,假以時日,他會取得更大的成功。我發現,在小劉的多幅油畫中,都有一個身段熟悉的女子,腰上隱約系了一條細細的紅繩,只是面目模糊,不能確定。他倆是走到了一起呢,還是繼續從前的合租狀態?無法判斷。
終于有一天,我們相會在故鄉的山梁上。他的爹娘以他為驕傲,他出資替父母建起全村最漂亮的樓房。只是人還單著,三親六戚給他介紹對象,他一概婉拒,他說我已經有女人了,只是沒有帶回來。坐在一塊大青石上,各人翹上一支煙,我問他:米粒兒呢?我在你的畫里經常看見一個女子,特別像她。他把煙灰彈到地下,用腳踩了又踩,說,我們在宋莊見過面后不久,我跟她真的戀愛了,我們住到一起,把另一個房間租了出去。一年以后,我得了個大獎,興沖沖回去向她報喜,到了出租屋,發現人去樓空,事前沒有任何征兆,事后沒有留下只言片語,哪怕指甲蓋大的紙片,電話從此打不通。至今我不知道她為什么離開我,不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這些年我始終憋著一口氣,一心想把藝術上的動靜搞大些,希望她能看見,有一天會來找我。
我問他,你有沒有問過她為什么要在腰上系一條紅繩?
他說曾問過一次,她說這是她的愛好。
“你至今不知道那根繩子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你是作家,讀書多,你說說看呢。”
我回答他:“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