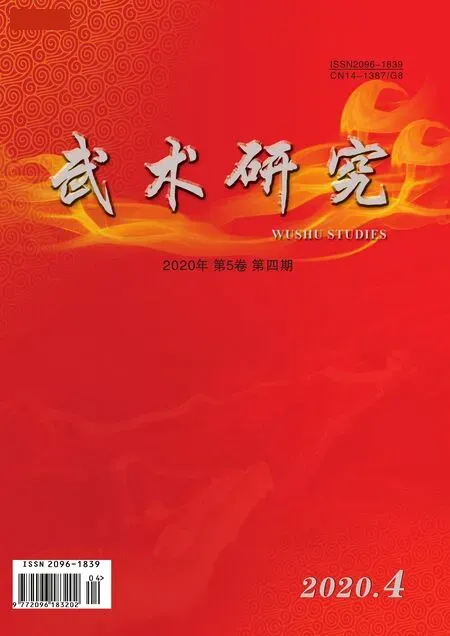當代武術集體記憶的保存與傳承研究
徐 帆
山西師范大學體育學院,山西 臨汾 041000
1 集體記憶概述
1.1 集體記憶的研究發展
“集體記憶”這一概念是由著名的涂爾干學派莫里斯.哈布瓦赫所闡述。在他去世后出版的《集體記憶》中對于時空、個體、歷史等記憶關系有了進一步的闡述。哈布瓦赫在涂爾干的基礎上進一步的延續并發展了他的思想,對于哈布瓦赫來說研究過去是一種社會建構,他并沒有在其著作中給集體記憶一個明確定義,他認為集體記憶控制著個人記憶和個體身份的形成,他還認為人在生活中有著超越自我的集體記憶,人是在社會群體中才能夠記憶的。哈布瓦赫的這一理論為學術界開辟了另一個廣闊的視野。隨著社會的發展集體記憶理論在研究中還出現了一個重要的轉變,這種轉變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原有概念的發展。
在20世紀80年代初,集體記憶這一概念逐步轉向了社會記憶的方向,從而使廣大研究者產生了興趣,許多學者分別在人類學、歷史學中運用社會記憶解釋當下的世界。1989年美國著名學者保羅·康納頓出版了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社會如何記憶》一書,康納頓將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擴展到了“社會”,這也使集體記憶研究更具有了可行性。伴隨著這一邊界的轉變,集體記憶的研究重點也發生著改變,康納頓還認為,哈布瓦赫在研究中過于集中地關注集體記憶的當下建構,反而忽略了集體記憶的保存和傳承,因此在康納頓的研究中社會記憶的保存和傳承也是他的主要研究問題之一。
1.2 集體記憶下的武術反思
“盡管我們確信自己的記憶是精準無誤的,但社會卻不時要求人們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現他們生活中以前的世界,而且還要潤飾他們,削減它們,或者完善它們,乃至我們賦予了它們一種現實都不曾擁有的魅力。”[2]集體記憶也會失憶。任何事物都是辯證統一的,有記憶就會有遺忘,遺忘是記憶不可分割的。中華武術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寶貴財富,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在5000年達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武術歷經風雨的沖刷和洗禮,隨著時代的發展,時代選擇性的消亡使中華武術走上瀕危之路,高科技的時代需求疏遠了武術,武術作為我國優秀傳統文化該如何在當下建構?在新時代的進程中新媒體的傳播力與影響力無疑將是中華武術發展的便車。對于中國武術,除去少部分專業人士對于武術有清晰的了解,眾多人群對于我國傳統武術仍然有許多偏見,隨著近幾年中國武術的發展,質疑的聲音也越來越突出,武術究竟是功夫還是花架子等等一系列問題撲面而來,大眾了解武術最廣泛的途徑就是依靠新媒體的傳播,大眾重新認識武術最重要的途徑之一就是武術影視作品。可以說武術影視作品是武術集體記憶的重要承載媒介。在眾多武術影視作品當中,以黃飛鴻系列電影為例,從人物的選擇、劇情的構思、史料的取舍、表達的主題等角度出發,展現黃飛鴻在當今人們心中的形象,這一人物重塑出發于史實又更貼近當代需求的集體記憶形成機理。在任何電影情結塑造中基本上是都是圍繞著當時重大的歷史事件、突出的人物進行展開的,正如哈布瓦赫所說:“盡管現代人可以重寫歷史,但是不可能是在一張白紙上來寫的”。[3]歷史的記載一定程度上是上層的,對于民間社會階層的群體關注度非常少,而對于武術來說更是圍繞武術的精英展開建構,這也就會導致當代人們對于我國傳統武術在整體認識上出現偏差。
2 武術記憶的建構
事物的產生在不的同時期價值是有區別的,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寶貴一部分,中國武術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分別有著不同的記憶。人們對于中國武術的記憶分為了以下階段:原始時期的武術、奴隸社會時期的武術、封建時期的武術、近代武術和現代武術五個階段,現如今中國武術作為寶貴的文化資源重新站起來迅速的發展,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出現的新問題,就需要系統的對武術進行重新的建構,不斷的重新挖掘那些不為所知的大眾武術,傳統武術所蘊含了我國古代哲學思想,作為中國獨特的文化瑰寶它還具有系統的技擊理論、獨特的人體模型、完整的一套鍛煉體系必然還依賴于一定的政治、經濟背景。各種權力正是通過對集體記憶的加強或者遺忘來達到強化或削弱群體凝聚力的目的。秦統一六國,為了維護皇權收繳天下兵器并在民間禁令習武,阻礙了后期武術的發展,隨著秦的滅亡武術的發展又展露出了頭角,在歷史的發展中,由于社會的需要武術英雄人物也就出現了。古代的武術產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軍事的需要,適應社會的需求。直到現在大眾流傳較廣的武術認識、對武術的真正的競技意義的理解是來自曾經的精英武術影響流傳至今。事實上,現代大眾對于武術的直接認識就是武術影視作品,武術作品都圍繞歷史上的武術精英展開,在歷史的基礎上、在當下的視覺上很好地詮釋了中國武術的雄風,一定程度上精英武術也是一種個人崇拜,中華武術的傳播匯集著每一代人的集體記憶。
2.1 武術電影中集體記憶的建構
集體記憶這一概念就有深厚的歷史性與時代性并且在新媒體時代下這一特性顯得尤為重要。早年就有學者認為:電視作為一種媒介對于構建集體記憶和集體認同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4]當富有古老韻味的傳統武術文化遇見新時代的電影他們就結合出來絢麗的火花,喚起了人們的記憶并且重建人們的記憶。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宣揚正義的時代,任何一個年代的集體記憶都是夾雜了權力的關系,這種關系導致了集體記憶的書寫難度同時帶給了現代人詮釋的困難。對于傳統武術的慢慢歷程,時光所抹去的記憶任何時候都會存在,直至影視作品對傳統武術的再現與傳承。
當前我國對于武術文化發展非常的重視,歷史悠久的中國武術正走向偉大的復興。在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背景下,武術文化呈現出生機勃勃的景象。近些年武術電影的涌入不僅為影視界增添了一份亮點,更重要的是喚起了廣大人民對于中國傳統武術文化的認同。中國自古就以禮儀之邦著稱海內外,任何古老的優秀中國文化都將是在這種優秀的內涵中孕育而生的,傳統武術中所蘊含的優秀文化也將是中國傳統武術的靈魂。[5]作為人類靈魂正義的象征出現了中國式的英雄:“俠”。一定程度上,“俠”寄托了人民對于生命的渴望以及反對階級勢力壓迫的,人們內心中祈求這股神奇力量的出現去解救生活在苦難中的他們。在這種封建勢力的壓迫下另一種形式的宣泄產生了,人們通過武俠小說來寄托英雄情結,與封建的惡勢力作斗爭。這種對于武俠精神的詮釋一直至今影響著人們的認知,但是任何時候對于過去的重建都是需要依照現在的需求。放眼望去,如今隨著時代的進步,科技的發展中國武術的真正內涵意義在這個時代中發生著改變,在人們的記憶中不斷的重新建構。但是這絕不表示傳統武術的消亡。探索中國古老的文明發展史,中國古代百家爭鳴的哲學態勢,實用技術的領先與高超時至今日依舊被沿用,這些都是讓我們驕傲的文化寶藏,它們流淌在我國5000多年文明的血液中,卻也不免受到爭議,這是由于社會的快速發展對于舊事物沖擊的結果,即便這樣我們不能否認國人對于歷史的淡漠與事實的遺忘。
2.2 當代記憶下武術的反思
與傳統意義所講的武術是不同的,在當前大多數人的心中對于武術的認識依舊是金鐘罩鐵布衫這類神功,當然這種認識是源于對武術影視最直觀的見解。假如曾經武術電影給觀眾帶來了最直觀的感受是武打,那其實現在映在觀眾心中的應該是武術所蘊含的江湖正義—武德。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都保存著不同階段在自己生活中不同的記憶,這些記憶不停的重現;通過它們,就像是通過一種連續的關系,我們的認同感得以終身長存。[6]中國武術在歷史上曾經作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這是源自于傳統武術在古代的實用性,在古代不論是軍事還是娛樂生活,武術無疑是最佳的選擇之一,以前人們對于武術的認識就是英雄、武術的俠義精神。影視作品刻畫了武林高人習得絕世武功就是為了救國救民,這些對于武林高手的描寫本身就是對過去武術的一種集體記憶的建構。這是因為從古至今對于不同階段人們的回憶進行了保存,人們對于中國武術的不斷認識本身就是對武術記憶的一種建構。人們生活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但是曾經的記憶依舊存在,它不斷的涌入到不同時期的不同觀念里,這樣,中國武術原有的記憶肯定會失去曾經的形式和外表,這并不影響對于武術在當下的重新建構,因為我們要看到傳統武術發展的將來時。
對于武術我們在建構中依靠史料典籍還有如今人們越來越重視的口述資料的整理與保存,它們都將是活著的生動歷史。武術史的記憶并非是像動物化石中保存完好的脊椎,可以憑借這個就可重建包含它們的整體。對于中國武術的歷史記憶,我們必須是要通過現在所被消磨或者當代人對于武術本體認同去尋找武術的記憶。傳統意義所賦予了武術的記憶就是“打”,這是在歷史中很長一段時間由于特殊的歷史環境所造成的賦予人本性的功能,而如今當代社會中,“不打”是對于中國武術在歷史長河中優秀文化的提煉。這種武術記憶的重建必須要建立在當代的理性上,脫離了這種理性的思考武術的重建依舊是一場設計好的綜合技擊功法。現在武術電影在我們的生活中喜聞樂見,一部對當代武術重構的電影打戲,只能說這是一種最直接的武術表象,對于“武德”的重建才是當代武術所反映的本質。在如今的武術影視作品中展現出那些習得上層武學精粹的大師,無不體現了我國古代文化之精華,也隨時代的發展體現出了對武術完美理想追求與體悟。
3 武術保存與傳承所遇見的問題
哈布瓦赫認為:群體成員是通過接觸周圍的符號和物質來獲得集體記憶的。符號和物質是外在于人保存和傳承集體記憶的兩大媒介形態。武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特殊符號對于記憶的獲取可以有不同的渠道,在不同的時期,對于武術記憶的表征是不同的,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變遷以及人們意識形態的轉變等等這些都會影響到傳統武術未來發展的命運,同時還會威脅到記憶的傳承。
武術作為一種記憶在傳承中是一定會面臨挑戰的,面對社會的變遷事物的改變從根本上造成了對原有記憶的破壞。這種破壞的延續會導致對于武術記憶的缺失,不能真正的去把握傳統武術真正的內涵。物質環境是最容易改變的,就像在我國經濟騰飛的今天,高樓大廈的平地而起,短短的幾十年,人們的生活可以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對于曾經的記憶再也找不到物質符號去回憶過去,他們僅有的就是曾經映在腦海中記憶,另一種影像記載也許是最好的記憶媒介之一。
對于群體來說從過去到現在很多的經歷是會被遺忘的,就像是我們每個人不可能清楚的記得我們從小到大發生過的每一件事情。對于集體記憶該如何保存與傳承,康納頓在其深入研究后的出:對于集體記憶如何保存和傳承是需要通過紀念儀式和身體實踐來實現的。[7]而哈布瓦赫對于集體記憶的保存和傳承也曾經說過:“個人所享有的集體記憶得以保存的方式就是把他們與周圍的社會、物質環境聯系起來。”其中對于康納頓在保存與傳承中重要的兩部分就是“紀念儀式”和“身體實踐”。其中身體實踐又分為兩種:“體化實踐”和“刻寫實踐”。刻寫實踐就是指通過人體之外的手段和媒介傳遞、記錄、保存信息,這一形式也通常被認為是傳遞社會記憶的重要方式。對于紀念儀式是通過操演完成的。到目前為止,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中國武術找到了發展的契機,它為中國武術的傳承提供了良好的平臺,通過這一儀式更有利于在多元的時代準確的分析中國武術現在的位置與它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中國武術集體記憶在時間的推移中保存和發展,為了避免當代社會成員對于中國武術文化的遺忘,同時在一定程度上讓他們對于中國武術保持著強烈的情感,使這種文化不斷的發展并且讓新一代的成員獲得集體記憶的信息和訓練。中國傳統武術的保存與傳承需要紀念儀式去喚醒人們對于過去的回憶,它還會使人們在紀念的同時強化人們對過去的記憶并使得這種記憶得以延續。更為重要的是身體實踐,集體記憶的保存和傳承最終是靠身體實踐來完成的。在每一部武術影視作品中我們發現每位演員所扮演的角色在他們的行為中都頗具有儀式感,這種儀式感成功可以勾起相關的記憶。
4 結語
不同事物的存在是可以通過群體特有的集體記憶來表征的。通過集體記憶的傳承使得這些事物不斷得到延續和發展。傳統武術歷經歷史的洗禮一直在今日換發這獨特的光芒,當今社會是武術傳承與發展的重要時期,中華民族的武術在今后發展的航向與訴求是每一位中華兒女應該承擔的責任,作為民族的驕傲、世界的瑰寶我們的中國武術道路是光明的。面對未來武術的發展道路也許有波折,我們只有兩者選擇:被動的接受或者主動的調試。武術集體記憶的建構一定程度上就是對于武術文化的保存與傳承,面對新時代文化的沖擊,西方文化的碰撞,武術的集體記憶在保留本真的同時更加具有了生機與活力,大眾如何正確的認識傳統武術,在新時代我們該如何去回憶我們的傳統武術,該如何去建構我們的傳統武術去傳承去保護我們的傳統武術是值得我們去探討的。在新媒體時代下,中國武術應該把握機遇建構出屬于新時代的武術里程碑,讓大眾去讀懂中國武術,讓每一位中國人講好中國的武術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