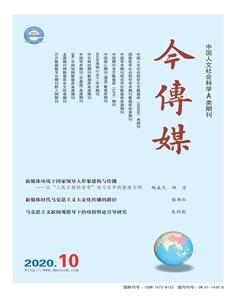角色理論視閾下短視頻主體角色建構透析
王姝媛
摘?要:短視頻角色扮演主體作為網絡空間的產物、現實社會的延伸,為了達到角色期待,在扮演過程中一方面需滿足現實社會已有的扮演規則,另一方面則需跟隨網絡空間的環境特點做出角色扮演技能方面的調整:明晰受眾的心理需求,善于運用網絡優勢,借助各類媒介進行角色加固。同時身處于視覺符號拼接的社會景觀中,角色扮演者更需深入思考角色的意義價值,才能避免成為虛擬空間的傀儡。而日常穿梭于虛擬狂歡與現實壓力的交織環境中,無論是角色扮演者還是受眾都應正確認知感官刺激的愉悅性,回歸現實中的理性思考。
關鍵詞:角色扮演;短視頻;角色沖突;視覺景觀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8122(2020)10-0027-03
隨著各類視覺符號的大量涌現,人們穿梭于視覺符號拼接而成的社會景觀,享受、消費著視覺文化帶來的快感。短視頻平臺作為生產視覺符號的重要工廠,以新奇、便捷、趨于真實的特征迅速吸引著大量的注意力經濟。據QuestMobile 短視頻2019年半年報告,截至2019年6月,短視頻用戶8.2億,同比增速32%[1]。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用戶從觀看者角色逐步轉變為參與者、制作者、創作者、表演者角色。這一轉變使得人們在短視頻平臺中的行為不僅僅是簡單的網絡互動,而逐漸轉變為在以短視頻為核心的網絡虛擬與現實社會交織的特殊結構中所執行的角色職能行為。
一、角色主體:網絡空間的產物,現實社會的延伸
短視頻借助網絡空間的新科技媒介進行社交互動,但短視頻中扮演的角色卻是現實社會的延伸,或現實社會的角色補充。首先,從短視頻的功能來看,簡單地將短視頻使用者分為兩部分,即用戶和制作者。用戶通過短視頻作品消遣娛樂、交往互動,制作者通過短視頻作品贏得關注、獲取流量,從而實現流量變現、獲得社會效益、心理滿足。因此,無論從用戶還是制作者來看,最終受益者仍舊是現實社會中人的本體,而在網絡空間中所扮演的角色,只不過是本體扮演眾多角色中的一枚;其次,從短視頻創作主體扮演角色種類來說,以短視頻創作主體在現實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第一層次的分類,可分為明星類與普通類。明星類是指創作主體以現實生活中明星的身份進行短視頻創作,這類創作主體在短視頻中所扮演的角色依舊是現實社會中的明星角色,需要注意的是這里所指的明星,更廣泛指某一領域的意見領袖、偶像等具有權威和高關注度的人。其創作目的更多是為了維護原有的明星角色形象,提高關注度。而普通類則指相反的一類人群,這類人群進入短視頻平臺后所扮演的角色情況較為復雜。在此我們進行普通類的二次分類,此次分類的依據則轉變為主體在短視頻中所扮演的角色。具體可分為帶貨推薦類、生活記錄類、內容生產類。每一類別的角色扮演者,因其所占據的角色位置而進行著一系列的態度和行為模式。從以上分類我們可以看出,短視頻平臺已經逐漸成為一個完善的虛擬空間,在這一空間中產生著與現實社會結構相同的角色分工、角色職能。短視頻的每一個用戶也通過視覺符號認識自我和他人,從而找到符合自我的位置。
無論從短視頻的功能還是短視頻主體角色分類來分析,短視頻中的角色雖以視覺符號顯現于網絡空間,但其角色本質卻來源于現實生活。面對這一特殊的定位,短視頻角色主體通過何種方式、途徑,如何更好地構建角色、盡快地穩定角色,是接下來本文探討的重點。
二、 角色構建與穩定:線上虛擬與線下真實優勢交織
短視頻既然作為線上的產物,線下的延伸,因此,構建角色需從現實社會與虛擬網絡空間同時入手。短視頻中的角色構建既要遵循社會行為規范,滿足現實社會中觀眾的社會期待;又要在此基礎上學會利用網絡空間的優勢更好地提升角色扮演技巧,以便觀者享受到異于現實社會的感受,從而更好地穩定角色。
(一)明晰現實社會受眾心理需求
短視頻作品以視覺符號極大地刺激著受眾的感官,再加之網絡空間的隱匿性,受眾可卸去以往的角色偽裝,完全回歸“本我”,享受極度的放松與快感。這正如弗洛伊德所說“人格可分為本我、自我和超我”,現實生活中大眾為了能夠滿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將會扮演多種角色,因此“本我”被掩蓋在眾多角色當中,但這并不意味著“本我”的消失。反而使得“本我”在毫無約束的空間中內爆。因此,短視頻受眾使用短視頻的根本需求在于視覺的消遣、“本我”的釋放。
短視頻受眾除了滿足獵奇心理、娛樂消遣外,找尋現實社會中缺失的社交需求和尊重也是其使用動機。日常交際中,具有相同話題的角色主體會簇擁談論,而缺失對話題關注和角色主體逐漸轉變為邊緣人。為了能夠融入群體、增加人際間的交流,角色主體會及時關注短視頻相關內容,以此獲取社交貨幣,并從邊緣人位置逐步走進社交圈,滿足社交需求。此外,部分觀者則因在現實社會中缺少歸屬感和認同感而進入短視頻的虛擬環境中。當短視頻中相關內容與之產生共鳴,這類觀眾會迅速成為短視頻主體的擁護者。例如,短視頻創作者房琪,以短視頻“北漂逆襲記”引起232.3萬人次的點贊關注,她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人生理念以及真實的自身經歷引起了大眾的共鳴。
(二)提升網絡空間角色扮演技能
當個體進行一個全新的角色扮演時,為了盡快能塑造成功角色,會主動進行相關行為準則、技能的角色學習。在短視頻平臺中,網絡空間獨特的前后臺環境也成為角色扮演所借助的條件。戈夫曼曾用“前臺”和“后臺”的概念來描述人在不同情境中呈現出的角色扮演的差別。短視頻平臺正是角色扮演者的前臺,在前臺區域角色扮演者“有意識地控制自己的行為,展現樂于被人接受的行為,隱藏屬于真實自我又不符合他人期望的行為”[2]。長久以往使受眾對角色扮演者形成固定的認知,樹立長久的標簽。例如,短視頻角色扮演者“小李朝ye”,他借用一人飾多角的方式,模仿日常生活情節,以此在受眾心中形成搞笑、生活的角色形象。在鏡頭前臺,角色扮演者通過角色扮演技巧對角色進行理想化的展示。而在短視頻實際的角色扮演過程中,部分角色扮演者除了緊緊抓住前臺的塑造區域,也會巧妙運用前后臺間連接的中區進一步展現角色形象。現實舞臺中中區作為隱藏角色扮演者本我的屏障,具有一定的隱私性。短視頻角色扮演者正是借助大眾傳統觀念對中區的認知,故意在短視頻平臺適當地顯露出自我在中區的行為,進一步滿足受眾的獵奇心理,同時也增加了前區角色扮演的真實性。
不同類別角色應掌控好不同側重點。“所謂角色扮演,是指個體根據自己所處的特定位置,按照角色期待和規范進行的一系列角色行為”[3]。針對不同類別的角色,角色扮演者的展示和技能學習側重點也有所不同。內容生產類角色扮演者李子柒,借用影像敘事手法、專業的拍攝方式成功塑造了田園式生活。而帶貨推薦類角色創作主體李佳琦的首要技能則是語言和副語言。標簽化的語言“OMG”“所有女生”“買它買它”,使得女性在視覺與聽覺的雙重刺激下毫無猶豫地進行購買。不同類別的角色扮演者依賴著針對性的角色扮演技巧,在短視頻平臺成功構建了既能達到自身目的又能滿足大眾期待的角色形象,并且在角色扮演過程中,角色扮演者所構建的角色形象也從角色本身逐步轉變為特定的符號,產生著更多的價值。
(三)媒介互動中的角色加固
米德認為“角色扮演是社會互動得以進行的基本條件”[3]。在短視頻平臺中,僅僅通過短視頻的評論功能并不能使創作主體與受眾持續保持持久的互動。為了能夠增加角色扮演者與用戶的互動,角色扮演者通過開啟話題、發起挑戰彌補互動缺失的時效性。例如,短視頻中的“萌寵”話題,所有用戶均可通過拍攝短視頻的形式參與這一話題。這類互動使受眾可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完成角色扮演者的互動,這不僅增強了話題感、加固了角色扮演者的形象,而且使得親身參與的用戶真正找尋到了尊重感和歸屬感。
病毒式傳播分享助力角色形象符號化。大眾周身充斥著各種媒介,從一個軟件行走至另一個軟件。在這個過程中,大眾會將前一個交流平臺中的信息帶入下一個平臺。加之網絡傳播的即時性,這一被分享的信息以病毒式的傳播速度迅速散開。這一情境下,當同一角色被多次分享傳播,角色在受眾心目中已悄然演變為符號,而后用戶不斷地消費這一角色形象的符號,與此同時,符號化的形成實質上加固了原有角色扮演者的地位。
三、角色扮演的新思考
角色扮演者經過反復的考量決定選擇扮演某一角色時,無論是為了彌補現實社會生活中的缺失,或尋找失去的“本我”獲取極度的狂歡,還是以獲取流量以此轉變為現實社會的貨幣,都帶有一定的目的性。相比現實社會的制約性,虛擬空間的較大隨意性和大量涌現的視覺碎片,使得角色扮演者能夠較快地達到目的,于此同時,也迷失在虛擬空間的迷障中。但短視頻為網絡空間的產物,其所具有的社會延伸屬性使其無論如何都逃脫不了現實社會的道德約束、行為規范。當受眾從短視頻的狂歡中意猶未盡的走出,面對他們的依舊是原有的現實社會。當現實與虛擬的差距到達了極點,對于受眾和角色扮演者來說是在虛擬世界中得到了釋放,還是激化了原有的矛盾,我們無從得知。同時,短視頻進入門檻低,各類角色扮演者都一涌而進,其中不乏低質爛俗以及未成年角色扮演主體。部分爛俗角色扮演會被大眾拋棄,但當刺激、享樂超越了理性選擇,角色扮演者和主體會從低俗中逐步走向娛樂至死的道路。此時僅單一依靠于受眾的辨識能力難以解決根本問題,現實社會中監管主體的介入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短視頻中所出現的低俗糜爛之風。
隨著短視頻用戶體量的快速增加,巨大的商業價值呈現于資本面前。現實社會中資本、權利的控制在短視頻平臺逐漸滲入。原本作為釋放“本我”的清靜之地,在主體與受眾的表演狂歡中悄然而入。各大資本投入者占據話題、聯合網紅,為了利益為受眾編織出觸手可及的即時性快感。迷失在利益和欲望下的角色扮演者不斷制造著各種奇觀迎合受眾的心理。資本控制下的角色扮演者雖獲得了利益,但卻永久失去了角色扮演的初心。
四、結?語
總而言之,短視頻中角色扮演者與主體雙方所產生的一系列交際行為,不僅僅是網絡空間的互動,而且是不同角色扮演者因身份位置而做出的行為反應。短視頻中大量用戶的涌入,豐富了當下的角色集合,滿足著社會需求。并且角色扮演者在短視頻空間的經歷過程豐富著本體的人格,所獲取的角色扮演技巧以及應對角色沖突的方式,同樣對現實生活中的角色扮演現象具有借鑒意義。但不得不警惕的是,面對資本控制的不斷滲透,角色扮演者如何在利益誘惑中,找尋角色扮演真正的意義。在長久的視覺刺激中,無論是角色扮演主體還是受眾都迷失了原有方向,逐漸成為視覺景觀的傀儡。因此,角色扮演的價值和意義并非僅僅是填補社會結構的空白,更多是讓個體在角色扮演中找到自我,完善人格。以此在繁雜的景觀中把握自我的價值和意義。
參考文獻:
[1]QuestMobile研究院.QuestMobile 短視頻2019半年報告[EB/OL].http://www.questmobile.com.cn/research/report-new/58.
[2]田雅楠.戈夫曼“擬劇論”的再思考———從《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談起[J].中國報業,2017(8):84.
[3]奚從清.角色論——個人與社會互動[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23.
[責任編輯:楊楚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