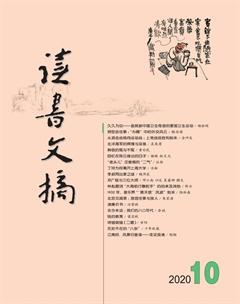1932年,音樂界“‘黑天使’風波”始末
陸林森
20世紀30年代,一場“黑天使”風波,引起了上海電影界、音樂界人士的高度關注,尤其是在明月歌劇社內,議論紛紛。事情的起因是,1932年7月13日,上海《時報》電影特刊發表《黎錦暉的〈芭蕉葉上詩〉》一文,批評明月歌劇社創始人黎錦暉音樂創作中的不良傾向。一個多星期后,上海灘頗有影響的電影期刊《電影藝術》(第三期),也發表了批評黎錦暉的文章《中國歌舞短論》。這兩篇批評文章,署名都是“黑天使”。在肯定了黎錦暉的歌舞作品“并非全是一塌糊涂;有的卻帶有反封建主義的元素,也有的描寫出片面的貧富階級懸殊”之后,“黑天使”將筆鋒一轉,直言批評:“然而,我們需要的不是軟豆腐,而是真刀實槍的硬功夫!你想,資本家住在高樓大廈享其福,工人們汗水淋漓地在機械下暗哭,我們應該取怎樣的手段去尋求一個勞苦大眾的救主?!”面對民族存亡的危難,如果表演的“仍是為歌舞而歌舞,將不會再有人要看”。“你要向那群眾深入,在這里面,你將有新鮮的材料,創造出新鮮的藝術。喂!努力,那才是時代的大路!”
黎錦暉看了文章,心里很不好受,他無法接受“黑天使”的批評,便以干女兒黎莉莉之名寫了反駁文章,投寄《電影藝術》發表。黎錦暉在文章中辯解,說自己是愛國的,寫了不少積極向上的歌曲。
黎錦光是黎錦暉的五弟,看了批評文章,也是忿忿不平,表示要寫信給上海《時報》和《電影藝術》,質詢“黑天使”為什么措辭如此激烈?他更想知道,這位“黑天使”究竟是誰。
面對黎錦光的怨憤之情,明月歌劇社內的一位年輕人站了出來,對黎錦光說:“你不要寫信了。我就是‘黑天使。”
黎錦光大吃一驚:“聶耳!你?”
聶耳坦言:“‘黑天使就是我,文章都是我寫的!”
消息傳到了黎錦暉那里。黎錦暉簡直不敢相信,他越想越氣惱,立刻跑去找聶耳,和他當場發生了激烈爭執。
“聶黎紛爭”發酵
黎錦暉是中國流行音樂的奠基人,他早期的音樂創作,主要是兒童歌曲。他寫的兒童歌曲,以保護兒童創造才能、反對封建教育為主題。早在1918年,黎錦暉就開始投身于“國語運動”。“五四”時期,他參與編寫小學國語教材,有意識地將自己創作的兒童歌曲如《美呀,中國的山河》《國恥的地圖》收入其中,對兒童灌輸愛國思想。在他看來,教兒童學國語,最好是從教兒童唱歌入手:在坊間流傳甚廣、幾乎家喻戶曉的“小孩子乖乖,把門兒開開,快點兒開開,我要進來”,就出自他創作的《老虎開門》。這是黎錦暉最早為兒童譜寫的一首兒歌。
作為一位卓有建樹的中國音樂家,黎錦暉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創造了好幾個第一:首創中國最早的歌舞學校“美美女校”,首創中華歌舞專門學校(這是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最早的一所專門培養歌舞人才的學校),首任上海國語專修學校教務主任(后任校長。該校享有中國兒童歌舞搖籃之譽),首創中國最早的歌舞表演團體“中華歌舞團”(黎錦暉為團長,其女兒黎明暉兼任副團長,歌舞團成員有徐來、章錦文、薛玲仙、王人美、錢蓁蓁、嚴折西、譚光友、黎錦光、王人藝、王人路等),首創中國近現代商業文化演出(中華歌舞團是中國第一個赴南洋演出的歌舞團,中國歌舞商業化即肇始于該團)等等。
黎錦暉,一位譽滿上海灘的音樂家,被公開點名批評,怎能不引起社會反響?尤其是在明月歌劇社,又怎能不引起激烈震蕩?有的人同情黎錦暉,有的人不理解聶耳為什么要批評黎錦暉,甚至有的人指責聶耳“忘恩負義”!原來,聶耳來到上海在云豐申莊打雜,半年后因云豐申莊倒閉而失業,經黎錦暉破格錄取,才進了明月歌劇社當練習生。
影星王人美是如何看待這件事情的呢?“黎錦暉是位值得敬重的長者。他不僅教我歌舞藝術,而且教我如何做人。”“我不想為他辯護,也不可能對他作什么全面的評價,我只是想把我接觸或了解到的有關事實回憶出來,供大家分析、研究。”(王人美:《我的成名與不幸》)。王人美還說,“(黎錦暉)在北平創辦過‘明月音樂會,有志推廣國語、研究民族音樂,也很重視兒童的音樂教育。1931年,他應上海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伯鴻之請,任教科書部編輯,編寫國語教科書。第二年出任新創立的國語文學部主任,他當主任后,大膽吸收青年。我二哥王人路也在那時當了編輯。國語文學部共有十八位編輯,都年輕力壯、不怕辛勞,工作效率很高……1933年,他們十八個人發起‘一日書運動,一年之內果然出了361本書。在他們大量出版的兒童刊物和書籍中,《小朋友》周刊最暢銷,發行量占全國定期刊物之冠。黎錦暉在《小朋友》周刊上連載自己編寫的兒童歌舞。”
事情發生后,很快發酵成一場孰是孰非的“‘黑天使風波”。聶耳記下了由批評文章掀起的軒然大波,“黑天使問題,似乎要擴大起來。錦光在忙著寫信責問黑天使,桌上擺著第三期《電影藝術》,特別在那篇文字上面有許多記號,大概是預備反駁之處吧!”(《聶耳日記》:1932年8月1日)。
是也黎錦暉,非也黎錦暉
黎錦暉一生寫有大量歌曲。1930年代的黎錦暉,才40多歲,就寫下了二千多首歌舞曲作品,“黎著歌曲已有二千七百余闋”(丁悚:《介紹白虹女士》,1934年6月14日《大晚報》,轉引自黎氏研究學者孫繼南《黎錦暉與黎派音樂》一書)。
對于黎錦暉的音樂創作,當時的社會輿論的確褒貶不一,毀譽參半。20世紀20年代,黎氏歌曲十分流行,甚至還在校園里流行開來,這種狀況,就連國民政府也深感不安,不得不明令校園內禁唱《毛毛雨》《妹妹妹妹我愛你》等黎氏歌曲。江西省音樂教育委員會甚至揮舞大棒,禁唱《三蝴蝶》《月明之夜》《葡萄仙子》《春天的快樂》《小羊救母》《小小畫家》《最后的勝利》等。理由是,黎錦暉的歌曲含有“海洛因的毒”,必須禁唱。但是也有輿論認為,黎錦暉的《月明之夜》等兒童歌曲,內容健康,積極向上,是對孩子進行品德教育的好音樂。還有人說,黎錦暉的歌舞作品,許多是健康的、格調明朗的。作為一位在中國樂壇卓有影響的音樂人,黎錦暉早期的音樂創作,既然以兒童歌舞為主,為什么要寫被后人貶之為“靡靡之音”的情歌呢?
王人美是這樣說的:“三十年代,《毛毛雨》《桃花江》等歌曲的流行是起了麻醉人們斗志的消極作用,我并不想為他辯護。其實,這些流行的愛情歌曲大多是黎先生二十年代的作品。”在王人美看來,就藝術而言,《毛毛雨》《桃花江》等歌曲是有特色的,黎錦暉在創作的時候,態度也是嚴肅認真的。按照王人美的解釋,黎錦暉創作這些“靡靡之音”,目的是希望借助這些歌曲作品,探索愛情歌曲的大眾化。這與黎錦暉一貫提倡的“音樂要為平民服務”的“平民音樂意識”不無關系。而且,黎錦暉創作這些迎合小市民需要的“靡靡之音”,也是“事非得已”,是為了籌集辦校組團的需要。他帶領中華歌舞團赴中國香港及南洋地區巡回演出,也是為了籌建歌專(即中華歌舞專門學校)募集經費,“結果,近一年的辛苦,演出所得除了支付日常開支外,都給大家分了場費,團體并無積累……他們寫信敦促黎先生趕寫愛情歌曲,并保證只要歌曲完工,回國川資、歌專經費都有著落。”然而,盡管黎錦暉“為了資金解困”而應邀創作《毛毛雨》《桃花江》等百首愛情歌曲,但在客觀上確實是起到了“海洛因的毒”作用,以致到了20世紀30年代,“起到了麻醉人們斗志的消極作用”。不過,正如一枚硬幣的兩面,黎錦暉的音樂創作,也有另外積極向上的一面。孫中山先生逝世后,黎錦暉寫了《總理紀念歌》,北伐戰爭開始后,寫了《同志革命歌》《歡迎革命軍》《解放歌》《當兵保民》等。這些歌曲,與《毛毛雨》《桃花江》的靡靡之音截然不同,格調是積極的、奮發向上的。
對于音樂的“平民化”,黎錦暉也以極大的熱誠身體力行。1930年5月,他率明月歌劇社赴津演出,此行的目的是要“使天津人知道中國人已經有了歌舞劇,希望大家都愛護這初萌的芽”(《黎錦暉語錄》,載《北洋畫報》,1930年5月20日,轉引自孫繼南:《黎錦暉與黎派音樂》)。三個月后,他又率團,踏上為期兩個多月的公演之旅,在大連演出期間,大獲成功,輿論極佳。日本文藝界向他發出邀請,希望第二年春天赴東京、大阪等地演出。當時,中日關系急劇惡化,黎錦暉婉言拒絕了日本文藝界的邀請。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黎錦暉拿起筆,作詞作曲,在一個月內創作了《追悼被難同胞》《向前進攻》等抗日救亡歌曲,發表在當時全國發行量最大、影響甚廣的《申報》。從這年9月到當年底,他在《申報》一共發表了十多首抗日救亡歌曲。他創作的愛國救亡歌曲,前后有幾十首之多。上海“一·二八”事變發生后,他將四十首救亡歌曲交付出版,在“卷首語”中發抒心聲:“這些歌曲,是供給全國國民齊聲高唱的……操練時、出發時、上課時、集會時,……都可運用……慷慨悲歌,激我士氣。向前奮進,效力疆場,救我國危亡,增我國榮光。殺盡敵兵,凱歌齊唱!”
難怪黎錦暉、黎錦光兄弟,讀了聶耳的批評文章感到委屈,認為聶耳的批評有失公允。但是,在黎錦暉留存的數千首音樂作品中,像這類積極向上的歌曲畢竟比例不大,他的歌曲創作主流依然是“另類”的,甚至,像《毛毛雨》《桃花江》之類的歌曲,也是與時代格格不入的,這不能不說是黎錦暉音樂創作的“缺憾”。
事件發生后,黎錦光在明月社召集會議,聶耳被禁止參加。緊接著,明月歌劇社在《時報》刊登“啟事”:“前本社社員聶紫藝(即聶耳)君,茲因故退出本社。”“黑天使”風波,看似可以了結了。不料,“電影皇帝”金焰后來無意間向友人透露的一句話,使“風波”又起“風波”:聶耳之所以撰文批評《黎錦暉的〈芭蕉葉上詩〉》,是因為沒有如愿出演主角。
黎莉莉身世之謎
由黎錦暉編創的《芭蕉葉上詩》,是中國的第一部歌舞片,故事并不復雜:昭昭因思念營長愛人,題詩芭蕉葉上。村上舉行踏歌節,昭昭前往參加,不慎將芭蕉葉遺落,被垂涎昭昭的無賴拾得,這無賴遂心生一計,將自己的名字寫在芭蕉葉上,寄給營長。營長大怒。村里人秀秀知道內因,寫信相勸,終于真相大白。
聶耳具有出眾的表演才能,早在昆明讀書期間,他就是個文藝活動的積極分子,反串過女角。誰來主演《芭蕉葉上詩》?聶耳確實也考慮過,自己是一個合適人選。不料,黎錦暉在決定人選時,并沒有考慮聶耳,而是“圈定”了黎莉莉、王人美。
黎錦暉為什么“棄”聶“取”黎,這是有隱情的。
黎莉莉,原名錢蓁蓁,系中共隱蔽戰線“龍潭三杰”之一錢壯飛的女兒。1927年“四一二”事變發生后,上海左翼劇團聯盟負責人田漢受黨指示,將錢蓁蓁托付給黎錦暉,希望他照顧好錢蓁蓁。黎錦暉不負田漢重托,對錢蓁蓁呵護有加,悉心培養,錢蓁蓁的表演潛質得到充分展現。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灘,有“四大天王”,錢蓁蓁就是其中之一,另三位是王人美、胡笳、薛玲仙。她們都是黎錦暉旗下的明月歌劇社演員。錢蓁蓁十分感激黎錦暉的撫育之恩,將他認作“義父”。在明月社,黎錦暉和錢蓁蓁以父女相稱,這是明月社公開的秘密。但人們多有不知,黎錦暉認錢蓁蓁為“干女兒”,是有難言之衷的。收養錢蓁蓁此舉,黎錦暉也是意在扶持“黨的后人”。所以,選擇《芭蕉葉上詩》的主演,黎錦暉完全“一邊倒”,但他沒有向外人透露“內情”,事實上也不可能透露。明月社幾乎沒有人知道他是受田漢之托,聶耳也不知其中原委。
聶耳沒有成為主演,頗感失望,但如果斷言因此遷怒黎錦暉,這是牽強的。《芭蕉葉上詩》雖然是中國第一部歌舞片,但它并不能算是一部成功之作,反應也并非如黎錦暉事先所愿,受到不少觀眾批評。頗感失望的聶耳,對黎錦暉“紅男綠女”的創作傾向也漸漸感到不滿。然而,他并沒有全盤否定黎錦暉,恰恰相反,而是稱贊黎錦暉的音樂創作具有“反封建的元素”,是“階級懸殊”的記錄。
1931年10月28日,他在日記中記下了兩天前的一場“愛國歌舞表演今天在‘黃金表演,‘聯華應得都捐入抗日救國團。‘上下客滿,明日請早這套把戲在上海卻是第一次。在有兩千座位的‘黃金,能有如此成績,倒是出人意外。”(“黃金”,即黃金大戲院,后來的黃浦劇場)。對于這次演出,輿論反應是“國難聲中”的一帖“興奮劑”,以雄壯的歌聲“刺動”同胞努力。對此,聶耳顯然是表示贊賞的。
聶耳:音樂要呼喚時代最強音
上海“一·二八”事變后,聶耳的思考和苦惱越來越強烈:“怎樣去作革命的音樂?”這年5月,明月歌劇社赴南京、漢口一帶巡回演出,觀眾起哄,大嚷“退票”,節目不良,嗓子壞,布景襤褸,引起了聶耳的強烈不滿。此時,田漢在“左聯”提出文藝評論主張。聶耳回到上海,應田漢之約,寫下了《黎錦暉的〈芭蕉葉上詩〉》《中國歌舞短論》,肯定了黎錦暉作品的“反封建因素”等積極一面,也尖銳地指出,國難當頭,民族危亡,如果表演的仍然是“為歌舞而歌舞”,那是不會有出路的,為了“票房”收入而媚俗,給民眾以低俗音樂,這是一種“毒害”!
聶耳一方面感慨黎錦暉不辭辛苦,帶領一班“紅男綠女”東奔西跑,國內國外,顯了十幾年來的軟功夫,一方面又不無憤懣地大聲疾呼“什么叫社會教育?兒童教育?被麻醉的青年兒童,無數!無數!”這時候的聶耳,就音樂創作而言,正在走向成熟。他在思考:什么是中國的新興音樂?音樂要呼喚時代最強音!
1933年6月3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什么是中國新音樂?這是目前從事音樂運動者,首先要提出解決的問題。我們知道音樂和其他藝術、詩、小說、戲劇一樣,它是代替大眾在吶喊,大眾必定會要求音樂的新的內容和演奏,并作曲家的新的態度。”
聶耳有兩個上海“伯樂”,一個是田漢,一個就是黎錦暉。“在上海的五年,是聶耳的事業高峰,也是其短暫人生落幕前的最后一個高峰。在此期間,有兩個人對聶耳的命運起到了推動作用,在藝術上與政治上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個是關系亦師亦友的黎錦暉,另一個則是共同創作并肩作戰的田漢。”“如果沒有黎錦暉,就不會有聶耳。”(密斯趙:《黎錦暉與田漢:聶耳在上海的兩個“伯樂”》,2016年第2期《名人傳記》)“聶黎紛爭”發生后,“左聯”內部也有不同的聲音。田漢是聶耳和黎錦暉的共同朋友,他指出,音樂的“民族化”是一個復雜的創作課題,不能簡單否定或肯定。聶耳也意識到自己的“淺薄”和“偏激”,因此,他特意去了黎錦暉處,“聽了錦暉處新收的唱片,音樂卻有很大進步,嘴上雖在罵,心里卻不安:自己實在淺薄,何敢去批評人?!”(《聶耳日記》,1933年1月30日)聶耳對黎錦暉明顯表示出了“修好”和合作的愿望:自己和黎錦暉的紛爭,是創作和學術上不同觀點的紛爭,別無他意。黎錦暉畢竟是一位音樂大家,也沒有因為聶耳的公開批評而耿耿于懷,當聶耳上門主動和解,顯得非常高興,除了公開稱贊聶耳是一位非常優秀的音樂人,同時也以師長和曾經的音樂引路人直言,聶耳的“脾氣”急躁了。
“聶黎紛爭”,最終以和解而落幕,這是頗具戲劇性的。但是,這場紛爭改寫了20世紀30年代“黎氏音樂”幾乎一統天下的格局,出現了三種不同的音樂流派:一種是以黎錦暉為代表的流行唱法(通俗唱法),風格接近歐美流行音樂,比較社會化、個性化和都市化。還有一種是從歐美舶來的美聲唱法,比較經典,是典型的學院派。另外一種,就是聶耳和冼星海倡導的群體化、美聲化和民族化(新民歌唱法)。“聶黎紛爭”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筆,推動了中國音樂發展。
(選自《檔案春秋》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