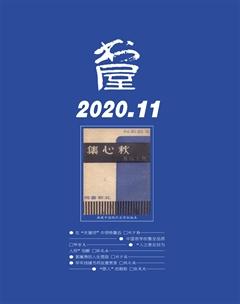莊生曉夢迷蝴蝶
章繼光
《痖弦回憶錄》是一部聯通海峽兩岸風云記憶的文化經典。筆者在閱讀它時,有幸和眾多的臺灣詩人及文化名人相遇,其中之一就是傳奇詩人周夢蝶。
周夢蝶(1921—2014),河南淅川人,淅川今屬南陽。周夢蝶與痖弦是同鄉,長痖弦十一歲。周夢蝶原名周起述,“夢蝶”為筆名,源自晚唐著名詩人李商隱《錦瑟》一詩中“莊生曉夢迷蝴蝶”這句詩。莊周夢蝶的典故源出《莊子·齊物論》,莊周夢醒,“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表達出莊周對消泯物我的無差別境界(物我一體)的探索和追尋;對于苦吟詩人周夢蝶而言,這個典故則似乎多了幾分凄美的宿命。
周夢蝶是遺腹子,年幼時在家鄉入私塾,跟隨塾師熟讀古詩文,打下了較好的舊學根底。1943年考入開封師范學校,由于戰亂中途輟學。十七歲時由母親包辦結婚,生有二子一女。1948年到武漢求學,參加國民黨青年軍,一人隨部隊去臺灣,子女發妻均留在家鄉。1956年退伍后曾在書店當過店員,后來長期在臺北街頭擺舊書攤維持生計,一天的收入有時只能買兩碗陽春面或者幾個饅頭,難以果腹。《蝸牛》這首詩寫出了他生活在底層的窘迫:
……
我沒有一飛沖天的鵬翼/只揚起沉默忐忑的觸角
一分一寸忍耐向前挪走——我是蝸牛。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周夢蝶胃部做手術后,結束書攤生涯,靠友人接濟為生。七十八歲時由弟子、高雄師大中文系曾進豐教授資助,安排住進臺北新店五峰山下某公寓的單人套間,直至去世。
當年周夢蝶的書攤就擺在臺北武昌路明星咖啡店門口,他每天早上從逼仄的居住地坐第一班公交車前來開攤。攤位不過方寸之地,全部書籍也就四百來本,大都是詩歌、哲學、佛教類舊書和詩歌期刊。沉默寡言的周夢蝶面對大街,像一尊泥塑,在一張破舊的椅子上靜坐終日,或揮灑一下雋秀的瘦金體書法,雖然有時不乏圍觀者,但他旁若無人,成為臺北鬧市中一道出名的文化風景。后來連于右任都知道了這個地方,曾派秘書到這里來找他需要的書。
周夢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在報刊發表詩作,1955年加入覃子豪、余光中組織的藍星詩社,進入文化圈子。1959年他出版第一部詩集《孤獨國》,自稱要“以詩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他在《孤獨國》一詩中寫道:
昨夜,我又夢見我/赤裸裸地趺坐在負雪的山峰上
這里的氣候黏在冬天與春天的接口處/
……
這里沒有眼鏡蛇、貓頭鷹與人面獸/
只有曼陀羅花、橄欖樹和玉蝴蝶/
這里沒有文字、經緯、千手千眼佛/
……
這里白晝幽闃窈窕如夜/夜比白晝更綺麗、豐實、光燦/
而這里的寒冷如酒,封藏著詩和美/
甚至虛空也懂手談,邀來滿天忘言的繁星……/
過去佇足不去,未來不來/我是“現在”的臣仆,也是帝皇。
在詩里,詩人是“孤獨國”中唯一的角色,他獨自“赤裸裸地趺坐在負雪的山峰上”君臨一切,俯瞰世界。在這個國度里沒有任何可怕的動物,甚至沒有神靈,“只有曼陀羅花、橄欖樹和玉蝴蝶”,詩人既是“‘現在的臣仆,也是帝皇”;這個時間凝固、“寒冷如酒”、“封藏著詩和美”的國度,是詩人獨享的精神樂園。“孤獨國”是高冷的詩人與世隔絕的心靈圖像。
整首詩意境孤高冷寂,飄逸空靈。它和詩集中的同類詩歌展現出獨拔流俗、高標出塵的美學趣味,贏得了讀者和詩壇的注意,周夢蝶因此獲得“孤獨國主”的稱號。
1965年周夢蝶出版了第二部詩集《還魂草》。詩人寫道:
“凡踏著我腳印來的/我便以我,和我的腳印,與他!”
你說。
這是一首古老的、雪寫的故事/寫在你底腳下
而又亮在你眼里心里的,你說……,
………
穿過我與非我/穿過十二月與十二月
在八千八百八十之上
你向絕處斟酌自己/斟酌和你一般浩瀚的翠色。
南極與北極底距離短了,有笑聲嘩嘩然
從積雪深深的覆蓋下竄起,/面對第一線金陽
面對枯葉般葡匍在你腳下的死亡與死亡
在八千八百八十之上/你以青眼向塵凡宣示:
“凡踏著我腳印來的/我便以我,和我的腳印,與他!”
詩中寫的這株高冷無比的還魂草,它與凡塵遙不可及,有著神奇的生命力和悲憫的情懷。這株超凡脫俗、無比奇絕的還魂草,與《石頭記》中生長于靈河岸邊的絳珠仙草一般神奇,卻遠比它要高冷。還魂草的意象是周夢蝶孤絕精神世界的一個隱喻,是他與世隔絕、孤芳自賞的精神圖騰。詩作以特別的遣詞造句的方式結合神話傳奇色彩,傳達出詩人遺世獨立的自我意識,呈現出古典與現代融合的特有風貌。
《還魂草》之后,周夢蝶又出版過《周夢蝶世紀詩選》、《約會》、《十三朵白菊花》、《有一種鳥或人》幾種詩集。
作者的一些小詩善于雕繪,頗具情趣;有的作品是從王維等古代詩人的禪詩中得到啟發,它們抒發詩人對自然、人生剎那間的興會與感悟,蘊藉空靈,耐人尋味:
讓軟香輕紅嫁與春水,讓蝴蝶死吻夏日最后一瓣玫瑰,
讓秋菊之冷艷與清愁酌滿詩人咄咄之空杯;
讓秋雨歸我,孤寂歸我……
——《剎那》
坐斷了幾個春天?又坐熟了幾個夏天?
當你來時/雪是雪,你是你/
一宿之后/雪即非雪,你亦非你……
……
——《菩提樹下》
行到水窮處,/不見窮,不見水
卻有一片幽香/冷冷在目,在耳,在衣
——《行到水窮處》
……
寶島詩壇和讀者對這位長期混跡于生活底層、才華突出的詩人頗為眷顧。周夢蝶一生獲獎較多,曾先后獲得笠社首屆詩歌獎、臺灣文藝家協會新詩特別獎、首屆臺灣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學獎等;1999年他的《孤獨國》與洛夫的《魔歌》、痖弦的《深淵》、余光中等詩人的詩集一道被評為臺灣文學經典。這些獎項代表了周夢蝶詩歌創作的成就,為他帶來了很大的聲譽。
但周夢蝶終身窮愁。痖弦回憶,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時,他和朋友常去明星店喝咖啡,喝完咖啡后就下樓到周夢蝶的書攤看舊書,與他聊天。當時周夢蝶到臺灣有十多年了,已經是很有名氣的詩人。但他還保持著豫西農民的打扮和生活習慣,身著一件空心棉襖,不穿內衣,腰間系著一條老皮帶;經常買一個燒餅貼身揣在懷里,拿出來吃的時候往往還是熱的。明星咖啡店對周夢蝶還不錯,晚上收攤時,讓他將破椅子和書箱擱在走廊里。后來更是借重這位窮詩人的名氣做生意,對他多少有一點照顧——因為周夢蝶的詩名,這個十分簡陋的書攤已成為明星咖啡店的廣告牌。七十年代時,享譽詩壇的周夢蝶已被臺灣文藝界人士尊稱為“周公”(痖弦稱其為“夢公”)。也許真是“詩能窮人”,盡管詩名不小,但周夢蝶的生活困窘并沒有明顯改善。
正是出于這一原因,富有同情心的痖弦在擔任《聯合報》副刊主編的時候,對這個河南老詩人特別照顧。凡周夢蝶送來的稿子,都盡量幫他發出,就是在其他媒體刊登過的作品也同樣照登;同時在稿費上予以優惠,開給周夢蝶的稿酬是最高的。當時為副刊寫稿的有不少名家、大家,如梁實秋、張愛玲、夏志清等,周夢蝶拿的稿酬比他們都高。在痖弦心中,這個來自河南農村的老鄉生活太不容易了,就像個“詩僧、詩丐一樣”。一些名家知道這個情況后也表示理解,從不與周夢蝶計較。
痖弦心里還經常惦念著這位老鄉,有時請文化界的朋友們吃飯,特意通知周夢蝶前來參加。有一次聚會時,聽到門鈴響,痖弦岳母前去開門,老人打開門隨即便關上了;回來說,外面來了一個要飯的。痖弦一聽,估計是周夢蝶來了,連忙出去將這位“大詩人”請進來。
周夢蝶性格十分拘謹、內向,不善于同人打交道。著名學者葉嘉瑩曾為他的詩集寫過序,這是她第一次為臺灣的現代詩人寫序。痖弦談到,周夢蝶在痖弦的介紹下與葉嘉瑩見面時,他竟然緊張到手足無措,似乎不知道怎么辦才好。
有一年痖弦回南陽家鄉探親,文藝界辦了一個座談會,請他談談自己的詩。痖弦推辭了,說:“我們河南有一個老鄉叫周夢蝶,那個人很值得尊敬。今天我就講講夢公的詩。”座談會結束后,有一位愛好詩歌的企業家找到痖弦,要他回去轉告周夢蝶,他要給痖公、夢公兩位南陽詩人各辦一個研討會,兩人來回的機票、住宿費以及參會人員的交通費和會議的所有開支全部由他負責。后來,痖弦將這個意思轉告周夢蝶,周說:“我現在已經是一個死去的人了。你老兄有一句詩我很欣賞:‘死人從不東張西望。”他明確地謝絕了這件事。
2013年下半年痖弦從加拿大回臺北,聽說周夢蝶生病了,專程去新店看望他。病中的這位老鄉憔悴不堪,痖弦憑直覺估計老人很難撐下去了,以后可能再也難見到他了。他知道老人平日喜歡喝白酒,特意陪他喝了金門高粱酒。就在第二年5月1日下午,九十三歲的周夢蝶因多種器官衰竭在新店去世,這位一生清苦的詩人帶著詩歌的夢想,永遠進入了他的“孤獨國”。
周夢蝶到臺灣后沒有再婚,孤身一人的他喜和女性接觸,也不乏追求者,據說三毛曾向他表白,遭到婉拒;常有一些女生慕名來到書攤向他傾吐心事或索求書法作品;在他的住地會見到一些女性寄來的書信和照片;有的女性長期和他保持著友好的關系,用朋友的話說,周公雖然“浪漫出了名,多情而不及于亂”。這是因為他“深知感情的十字架太重,既背不動也不愿成為別人的十字架”。痖弦在談到周夢蝶的感情生活時說,他對女性的渴望比我們普通人還波濤洶涌。大家都知道他喜歡誰,而且喜歡的不止一個人。他一直寫情詩,不過都是抽象的、柏拉圖式的,影影綽綽地通過藝術形象寫下來。總之,他是詩人,不是和尚;如果要說他是僧人,那他也是個情僧。他喜歡的女性很多,有些對方自己都不知道,有些對方也知道,但覺得他是無害的,跟他在一起聊天也很高雅。痖弦認為周夢蝶對感情生活主要是追求一種精神之戀,這是契合周氏個性的知人之見。周夢蝶生前在日記中寫道,自己要求的女人必須是完美的,世界上只有觀世音才完美,而觀世音是不嫁的。自己雖然一點條件也沒有,卻對女方要求這么高,其實很可笑,可見他對女性的這種感情渴慕不過是空谷足音或鏡花水月。
作為著名詩人和評論家的痖弦對周夢蝶的詩歌成就評價很高。痖弦說,周夢蝶的詩非常好,受佛學、禪宗影響,在意象經營、遣詞造句上都是非常富有創意的,也是大膽的。他有他的現代性,他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他的精神世界不同于古人。表面上看,他的精神世界穩定、莊嚴,但詩人心緒的底流是波濤洶涌的,思想的放膽、句法的反傳統并不輸于強調現代的諸子;“時間越久,周夢蝶的聲譽會越高”,“因為只有一個周夢蝶,不可能出現第二個”,“可以這么說,周夢蝶會變成一個美麗的文化傳說,是臺灣一道消失的風景”。痖弦充滿感慨地指出:“詩是一種修行,一種自牧,也是一種信仰,一種永遠的獻身……詩人是一輩子的身份,詩人的努力是一輩子的努力,詩人的最高完成也就是詩的完成。正如楊牧的詩句說的,‘在維也納郊外的墓園中躺著一個完成了的海頓,周公是完成了的詩人。”痖弦的評價贊譽、敬重之情溢于言表,令人感動。